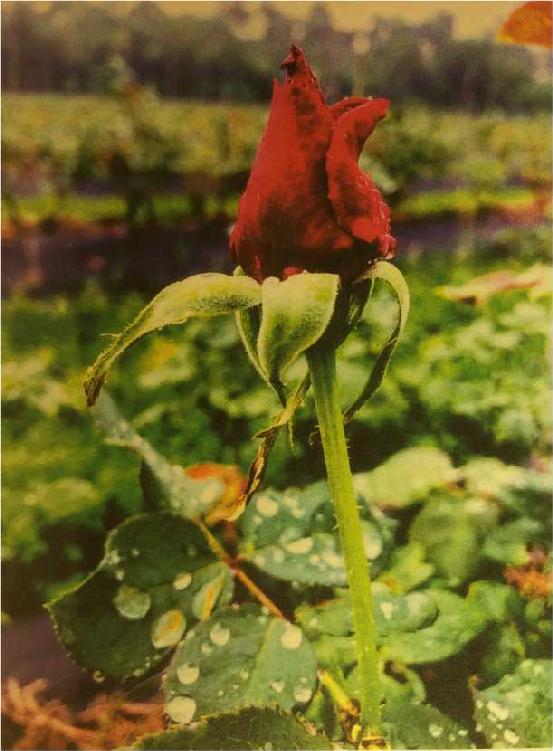| 天长地久 | 收藏 |
永远的女生
天长地久 作者:龙应台
脸上的皱纹都是她的,身上的关节都不是她的。
可是她眼睛里的光芒、声音里的力量,
永远是她自己的,独一无二。
你记得安琪拉吗?
八十五岁的安琪拉来信说她病了,我专程飞到德国去看她。人生历练告诉我:超过八十岁的“闺蜜”生病了,必须排除万难在第一时间探看。
从台北直飞法兰克福十二个小时,从法兰克福转火车沿着莱茵河北走二小时,波昂站下车,再加十五分钟计程车程,到了她家门口。远远就看见她的花园,她银白发亮的头发在一排紫丁香花丛的后面。听见我的车门声,她直起身,看向安静的街道,然后笑吟吟地向我走过来,怀中是刚采下的大朵绣球花如孩子的粉脸,一派阳光灿烂。
我说,“原来你好好的,那我可以走了。”我作势要掉头,她抱着花大笑着走过来,我才发现,她一拐一拐地走,走得很慢,很慢。
我们就坐在那花园里,在北国的蓝银色天空下,看着美满得不真实的绣球花,有一搭没一搭说了两天两夜的话。
风霜
人和人真的很神奇。有些人,才见一面就不想再见;有些人,不论你怎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朋友;有些人,即使在同一个屋檐下日日相见,也不见得在晚餐后还有话可说——晚餐嘛,还有食物的咀嚼和杯盘的叮当声响可以掩饰空白,晚餐后,那空白的安静大声到耳鼓发麻,你无可逃遁。
有些人,却是从第一个照面,就知道,他是。
安琪拉大我二十岁。我们在纽约机场等候接驳车的空档中聊了一下。那时的她才五十多岁,短短的卷发,两颊还有一点婴儿肥的可爱感。二十年后第一次在银幕上看见总理梅克尔,我失声说,“这不就是安琪拉吗?”
安琪拉坚持要为我泡茶、切蛋糕、洗葡萄。每一个动作,其实都很艰难。她拉开橱柜取出果酱,说,“此身一半不是我的了。膝关节、髋骨……”
“膝关节……那就不能骑单车了?”
她对我眨眨眼,笑了,“那也成过去了。”
安琪拉的儿子站在一旁,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我记得上一次站在这厨房里,是安琪拉先生过世后五年,安琪拉六十五岁的时候。我说,“安琪拉,找个人去爱吧?”
她说,“男人多半笨。老年丧偶的尤其无聊,只会坐在家里看电视,而且是看球赛,喝啤酒。”
安琪拉是一个爱看戏剧、爱读小说、爱打抱不平、爱大自然、爱运动、爱社会正义、爱流浪狗、到老都天真热情的女人,要怎样去找到兴趣广泛、生趣盎然、不瘫在沙发里看球赛喝啤酒的进步老男生呢?
那次厨房会议的决议就是:到《时代周报》去刊登一个广告。德国《时代周报》是一个知识菁英的报纸,以思想品味自诩。有整页的交友广告,广告里的女人多半宣称热爱莎士比亚,男人多半强调会背诵歌德。
安琪拉真的依照我们的厨房决议去登了一则广告:
六十五岁女生,兴趣:看戏、读书、运动、大自然。
政治倾向:厌恶右,但绝非左。
外貌:腿力很好。
征求兴趣相近的男生从德国波昂骑单车到波兰华沙。共九百七十六公里。
很多人来应征,安琪拉最后挑了一个大概是“腿力最好”的男人,阿芒。两个人清风明月、两鬓风霜,骑单车共度了一个月。
花园外就是麦田,麦子熟了,整片田像一个方块形的大盘,托着沉甸甸、满盈盈的柔软黄金,阳光刷亮了麦穗如花的芒刺。
我们在天竺葵旁边坐下来。儿子已经识相地走开,让我们女生单独说话。
“阿芒呢?”我问。
安琪拉把拐杖小心地靠在门边,拿了一条毛毯盖在自己膝头,说,“两个月前走了。”
“走了?”
“突然的,三更半夜。他固定每周三来我这里,那个周三他没出现,半个月后我才知道。”
我想像事情的可能发生顺序。阿芒是有家室的,他和安琪拉之间长达二十年的情份,是一个人世间的秘密。他的突然离世,没有人会去通知安琪拉。所以,安琪拉经过的是什么?等待,失望,不安,焦灼,直到发现阿芒爽约的原因时,非但无法执子之手温柔告别,连告别式远处的驻停凝眸都不可能……
全家福
我要安琪拉跟我细谈她在波兰度过的童年。
“你知道我是在波兰洛兹长大的?”
“洛兹?”我从躺椅一下子坐了起来,“洛兹就是你的故乡?”
十八世纪末强大的普鲁士收编了部分波兰国土,包含洛兹,紧接着鼓励大批德国人到那里定居。安琪拉家族几代人就在洛兹生根。一九三九年希特勒的军队入侵波兰,洛兹变成一个关系特别紧张的地方——占领者德国人声色凌厉,波兰人忐忑不可终日,犹太人沉默地等着大难临头,而像安琪拉这样在波兰已经好多代的德国人——“外省人”,尴尬地夹在中间。
“有一天大概清晨四五点钟,突然很吵,”安琪拉说,“我爸硬把我从床上拖起来,让我趴到窗口,不开灯。”
隔壁邻居是犹太人。十岁的安琪拉目睹的是,荷枪的德国士兵闯入犹太人的屋子,驱赶还在熟睡中的一家老小,喝令他们立刻出去。安琪拉一家人眼睁睁看着隔壁邻居家住在三楼的老奶奶,可能因为下楼的动作太慢,士兵把老奶奶直接从三楼窗口抛出来。
安琪拉在爸爸的怀里,趴在窗口,全身发抖,爸爸在黑暗中说,“孩子,你听好:我要你亲眼看见我们德国人做的事,你一生一世不能忘记。”
被抄家出门、失魂落魄站在马路上的犹太人到哪里去了呢?
安琪拉说,洛兹有一个用高墙围起来的区,看不见里面,但是每次她经过,心里都充满恐惧。她模煳地知道,凡是进了这里的人,都不会活着出来。全城的犹太人,都进去了。
安琪拉的家是个照相馆,爸爸是摄影师。德军进驻洛兹之后,照相馆的生意突然爆红。村子里的人每天在门口排着长龙,等候拍全家福。
“因为,”安琪拉说,“本地人觉得时局不好,很不安;犹太人当然更觉得是世界末日,恐怕马上要生离死别,而村子里的德语人则担忧自己的儿子恐怕很快会被德军征召当兵,所以大家都赶着来拍全家福……”
有一天,外面排队的长龙里似乎起了争执,突然人声嘈杂,安琪拉的父亲停止拍照,出门去看。原来是队伍里的几个本地德语人认为波兰人现在没有资格排到前面,要他们排到队伍后面去。安琪拉看见照相师爸爸对着这些讲德语的同胞非常愤怒、非常大声地挥手说:
如果要在我这里拍照,就请排队。如果不愿意排队,可以,就请你们到别家去,我这里恕不奉陪。
大家就安静了下来。
好样的
傍晚,安琪拉拄着拐杖和我走到村子尽头一片草原上采集野生的洋甘菊,她是个大自然的信徒。早餐,配的就是采回来的洋甘菊。喝茶的时候,我八十五岁的闺蜜说:“应台,战后很多德国人说他们当时不知道有集中营这回事。我想说的是,如果十岁的我就知道洛兹有个杀人的地方,你大人敢说不知道?也不要跟我说,国家机器太大、个人太小,个人无能为力。我父亲就用他最个人、最微小的方式告诉十岁的我说,个人,可以不同。个人,就是有责任的!”
我看着她。八十五岁的安琪拉,脸上的皱纹都是她的,身上的关节都不是她的。可是她眼睛里的光芒、声音里的力量,永远是她自己的,独一无二。
在安琪拉的身上,我也看见你,美君。日前在整理旧物时,翻到你回忆录的这一页,说的应该是一九四三年,你十八岁:
兵荒马乱,大家都怕兵。一个宪兵队驻在淳安城里。有一天,我家隔壁不知道闹什么事,几乎要打架,很多邻居看热闹。这时宪兵来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当事人和一二十个一旁看的人全都抓走了,关起来,一关就是三天,而且不许家属探访。小老百姓不懂法律,害怕家人是不是会被宪兵枪毙,吓得半死,来找我,我才十八岁。他们说,大小姐,这街坊只有你会讲国语,求求你去宪兵队沟通吧。
我也很怕,但是怎么办呢?
最后还是下了决心,我一个人走到了宪兵队,抱了一大包热烧饼。
见我的是位中尉排长。我说,我是来看我的邻居们的。他说,上面不准见。我说,他们犯了什么罪,这么严重。我受邻居之托,要求不大,只想看到他们是死是活。
他考虑了很久,最后说,好,可是你带来的东西不能带进去。我说,好,不给他们吃,只是给他们看,表示我的人情到。
排长勉强点头。
我走到犯人间,他们一看见我就同声哭叫:大小姐救救我们,我们已经三天没吃饭了,快饿死了。
我毫不考虑,当下就把烧饼用力丢进铁窗里,乡亲抢着吃光了。
守门的宪兵报告排长说我不守信用。我很生气,对排长说,“这世界上哪里有饿罪?就是犯了死罪,也要给犯人吃饱才枪毙。我是可以告你们达法的。”
排长看看我,不回话。
第二天上午,所有的犯人都放回家了。
十八岁的女生美君,好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