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人称单数 | 收藏 |
查理·帕克演奏波萨诺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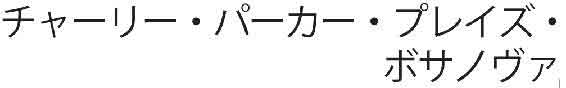
第一人称单数 作者:村上春树
大鸟回来了。
多么精彩的旋律啊!没错,大鸟回来了,伴随着那魁伟的翅膀扇动的声音。在这颗行星的每一片土地上——从新西伯利亚到通布图——人们仰望天空,目睹飞鸟伟岸的身影,无不欢声雀跃。世界从而再次注满崭新的阳光。
时间是一九六三年,距离人们最后一次听到大鸟——查理·帕克的名字,已经过去了一段漫长的岁月。大鸟现在在哪里,在做什么呢?世上每个地方的爵士乐爱好者都曾这样窃窃私语。他一定还活着,因为没人得知他死的消息。但是啊,也没人听说他还活着——有人说。
关于大鸟,人们听到的最后一个消息,是他被赞助人妮卡男爵夫人[潘诺妮卡·科尼格斯沃特男爵夫人(Baroness Pannonica de Koenigswarter),著名犹太巨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后代。]收容,在她的豪宅中与病魔斗争。大鸟是大名鼎鼎的瘾君子,这件事大概没有哪个爵士乐迷不知道。海洛因——众所周知的纯白色粉末,足以置人于死地。还有传闻说,大鸟患上了严重的肺炎,五脏六腑都有各类疾患,还饱受糖尿病折磨,最后竟连精神也出了问题。就算他幸运地活下来,现在恐怕也等同于一个废人,不可能再拿起乐器。大鸟就这样从世人面前消失,成了爵士乐坛的美丽传说。那是一九五五年前后的事。
可是八年以后,一九六三年的夏天,查理·帕克再次拿起中音萨克斯,在纽约近郊的录音棚里录制了一整张专辑。专辑的名字叫《查理·帕克演奏波萨诺瓦》!
你相信吗?
最好相信。不管怎么说,这件事真的发生了。
以上是我读大学时写的一篇文章的开头。有生以来,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章变成铅字,并领到了一笔微薄的稿费。
当然,《查理·帕克演奏波萨诺瓦》这张唱片并不存在。查理·帕克早已于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二日去世,波萨诺瓦经过斯坦·盖茨等人的演绎,在美国爆红时已是一九六二年。但如果大鸟活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对波萨诺瓦的曲风萌生了兴趣,如果他演奏了波萨诺瓦……我用这样的设定,写了这篇架空的乐评。
不过,大学文艺杂志的主编误以为那张唱片真实存在。他选中我这篇文章,直接当作一篇普通的乐评刊载在杂志上,没有提出任何质疑。主编的弟弟是我的好朋友,承蒙他向主编推荐了我:“有个写文章还算有趣的家伙,你们不妨用用看。”(这份杂志出版了四期便停刊了,登载我稿子的是第三期。)
我文章的设定是:这卷查理·帕克留在世上的贵重录音带,偶然在唱片公司的保管室被人发现,此番首次见了天日。虽然这样评价自己写的东西有点不好意思,不过我在这篇文章中可以说投入了相当的热情,将每个细节都捏造得像模像样。到最后,连我自己都快相信真有这么一张唱片了。
杂志发售后,读者对我写的这篇文章反响不小。那原本是一份普通的大学文艺杂志,平时对文章的阅读反馈几乎没有。但世上将查理·帕克奉若神明的粉丝似乎不少,编辑部收到了好几封抗议信,说我的恶作剧“过分且无聊”,“无情地亵渎”了他们的偶像。很难判断到底是这世上的人缺乏幽默感,还是我的幽默感生来就偏离正轨。还听说有些写信的人把我写的文章当真,特意到唱片店去,就为了买那张唱片。
主编因我捉弄他这件事诉过一次苦(实际上我并没捉弄他,只是省去了详细的作品说明),但面对读者对那篇文章的哗然,即便是以批评为主,他的内心似乎仍然是喜悦的。证据便是他曾告诉我,今后要是又写了什么,无论是评论还是创作,都不妨给他看看(不过,我还没来得及给他看,那份杂志就不存在了)。
我前面那篇文章后续是这样写的:
……查理·帕克和安东尼奥·卡洛斯·裘宾,有谁能预言到这场不寻常的邂逅呢?吉他是吉米·拉尼,钢琴是卡洛斯·裘宾,低音提琴是吉米·加里森,鼓是罗伊·海恩斯。光是看到这些人的名字就足以令人心潮澎湃,感受到这支组合的魅力了。至于中音萨克斯当然是查理·“大鸟”·帕克。
让我们看看曲目。
A面
(1)《科尔科瓦多山》
(2)《平静的爱》
(3)《只是朋友》
(4)《思念满盈》
B面
(1)《突然出现》
(2)《何等愚昧》
(3)《再一次》
(4)《爱人》
除了《只是朋友》《突然出现》这两首曲子,其他都是出自卡洛斯·裘宾之手的名作。而这两首是以前因大鸟自己的精湛演奏闻名于世的标准曲目,这次按照波萨诺瓦的曲风,以全新形式演绎(也只有这两首曲子的钢琴手从卡洛斯·裘宾换成了多才多艺、经验丰富的钢琴家汉克·琼斯)。
那么,爱好爵士乐的你听到《查理·帕克演奏波萨诺瓦》这个专辑名,心里是怎样的感受呢?想必先是惊讶地“欸!”一声,然后感到好奇和期待填满了胸口吧?但说不定要不了多久,警惕情绪就会一点点抬头——仿佛刚才远山外还有一片美丽的晴空,下一秒却涌起不祥的乌云。
等一下,大鸟,你说那个查理·帕克演奏了波萨诺瓦?大鸟是发自内心地想要演奏那些乐曲吗?难不成他是屈服于商业主义,被唱片公司的花言巧语蒙蔽,才把手伸向了当下的“热门货”?更何况他这名中音萨克斯演奏者的骨子里,已经深深刻下了波普爵士乐的基因。就算真想演奏那样的音乐,他的演奏风格能和源自南美、个性十足的波萨诺瓦完美地调和吗?
不,先不说音乐风格,经历了长达八年的空白期,他还能像从前那样随心所欲地操控他的乐器吗?现如今,他还保持着曾经的高水准演奏能力和创造力吗?
老实说,我之前也有过这样的担忧。我一方面迫不及待地想听到那音乐,一方面又惴惴不安,害怕听了会失望。不过现在我已经屏气凝神,将这张碟反复听过好几次了。我敢打包票,不,让我站上高楼的屋顶,朝每一条街道声嘶力竭地呼喊也无妨——如果你是爵士乐爱好者,不,但凡喜欢音乐的人,面对这火热的心灵和冷静的思维锻造出的迷人音乐,都应该放下手里的一切,侧耳倾听。
(中略)
这张碟首先惊艳到我的,是卡洛斯·裘宾简洁而毫无赘余的钢琴演奏和大鸟那娓娓道来、流畅奔放的乐句,二者的完美结合简直妙不可言。也许你会说,卡洛斯·裘宾的音色(他没在唱片中献声,我指的不过是乐器的音色)和大鸟的音色不是存在着性质和方向性的不同吗?这两个人的音色当然有很大区别,以至于寻找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可能都成了难事。况且他们似乎根本没想着让自己的音乐去贴合对方。可这种违和感本身,他们二人在音色上显而易见的不一致本身,正是创造出这无与伦比的美妙音乐的原动力。
首先请各位附耳倾听A面的第一首曲子,《科尔科瓦多山》。在这支曲子里,大鸟没吹奏开头的部分,只吹了后面一段。开头只有卡洛斯·裘宾的钢琴,安静地弹奏那段熟悉的旋律。节奏组[乐队中为乐曲搭建节奏的演奏者们。一般包括鼓手、贝斯手和节奏吉他手。]只管在背后沉默。那曲调让我们想起坐在窗边的少女眺望窗外美丽夜景时的目光。大部分是单音节,偶尔小心地加入一个简单的和弦,仿佛在少女身后温柔地添一只柔软的靠垫。
这段钢琴弹奏的旋律结束后,大鸟的萨克斯声悄悄响起,就像从窗帘的缝隙溜进房间的黄昏浅影。待你缓过神来,它已经出现了。那不间断的袅娜旋律,恍若隐姓埋名潜入你梦中的甜美思念。风从你心灵的沙丘上拂过,留下的精妙砂纹化作优雅的伤痕;你不禁许下愿望,希望它就这样永不消失……
后面的部分就不放了,全是这些煞有介事的修辞和描写。不过,那张唱片里的音乐给人的大致印象诸位已经心中有数了吧?当然,那些音乐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本应是不存在的。
故事到这里暂且告一段落。接下来要讲的,是后来发生的事。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将学生时代写过这样一篇文章的事忘得一干二净。毕业以后,我的人生出乎意料地兵荒马乱,最终,那篇架空的乐评成了年少时一场不负责任的轻松玩笑。可大约十五年后,它又以一种意外的方式回到我身边。就像一支回旋镖,你已经忘了曾把它掷出去,它却在意想不到的时刻飞回你手中。
一次,我因公务在纽约市内停留,那天时间充裕,我在下榻酒店的附近散步,走进了东十四街一家小小的二手唱片行。在那家店的查理·帕克专区,我竟然发现了一张名为Charlie Parker Plays Bossa Nova[《查理·帕克演奏波萨诺瓦》。]的唱片。它看上去像是私制的盗版盘,白色封套的外侧没有图画也没有照片,只有黑色铅字敷衍地印着唱片的名字,内侧记有曲目和人名。令我震惊的是,曲目和演奏者的名字都与我学生时代随意编造的内容分毫不差。仅有两支曲子与汉克·琼斯有关,他的名字代替卡洛斯·裘宾出现在钢琴手的位置。
我拿着那张唱片,无言地伫立在原地。身体深处似乎有某个小小的部分麻了一下。我再次小心地环顾四周,这里当真是纽约吗?此地毫无疑问是纽约的商业区。我就在这间小小的二手唱片行里,并没有沉醉于幻想的世界,也不在逼真的梦境中。
我从封套里抽出唱片。唱片上贴着白色标签,上面印着专辑名和曲目,没有唱片公司的商标之类的东西。再看看唱片的声槽,每一面都整齐地录有四首曲子。我询问收银台前那位长发的年轻店员能否试听,他摇摇头。“店里的唱片机坏了,现在不能试听。”他说,“抱歉哦。”
这张唱片标价三十五美元。该怎么办呢?我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走出店门,没有购买。我想那肯定是某个人无聊的恶搞。某个好事的家伙按照我以前写的文章,原样捏造出一张架空的专辑。这人找来一张A面和B面各录了四首曲子的唱片,泡在水里剥下标签,用胶水把一张亲手做的标签粘上去。花三十五美元买这么个假货,怎么想都蠢透了。
我独自走进酒店附近的西班牙餐厅,喝了啤酒,吃了简单的晚饭,之后在附近漫无目的地散步。这时,心里忽然涌起一阵悔意。还是应该把那张唱片买下来。就算是毫无意义的假货,就算它溢价过高,刚才还是应该买下来,作为我崎岖人生的一份古怪的纪念。我立刻再次往十四街走去。急匆匆地走到那里,可唱片行已经关门了。安在卷帘门上的牌子显示,这家店工作日上午十一点半开门,晚上七点半关张。
第二天中午,我又一次来到这里。一个头发稀疏的中年男子坐在收银台前,穿一件松散的圆领毛衣,边看报纸的体育版边喝咖啡。咖啡像是刚用咖啡机做好的,店里隐约飘荡着新鲜而令人舒心的香气。由于刚刚开门不久,除了我,店里没有其他客人,天花板上的小扬声器里流淌着费拉·桑德斯的老曲子。看上去那位中年男子应该是这家店的老板。
我到查理·帕克的专区找了找,并没有那张想要的唱片,但我确定自己昨天把它放回这里了。无奈之下,我又将爵士分类的所有唱片箱翻了个遍,心想说不定错放到别的地方去了,可无论怎么找,都没找到那张唱片。这么短的时间它就被卖掉了吗?我走到收银台前,对穿圆领毛衣的中年男子说:“我要找一张昨天在这里看到的爵士乐唱片。”
“哪一张?”他说话时眼睛不离《纽约时报》。
“Charlie Parker Plays Bossa Nova。”我回答。
男人放下报纸,摘掉金属质地的细边老花镜,目光缓慢地移向我:“不好意思,能再说一遍吗?”
我重复了一遍。男人一言不发,啜了一口咖啡,然后轻轻摇头:“这张唱片根本就不存在。”
“那是当然。”我说。
“如果你想要Perry Como Sings Jimi Hendrix[《佩里·科莫演唱吉米·亨德里克斯》。]的话,我们倒是有。”
“Perry Como Sings——”说到一半,我意识到对方在跟我开玩笑。这男人是说玩笑话时故作严肃的类型。“但我真的看见了。”我说,“虽然我认为那不过是捉弄人的把戏。”
“你是说,在我家看见那张唱片了?”
“对。昨天下午,就在这家店。”我向他描述那张唱片装在什么样的封套里,收录了哪些曲目,还说了标价三十五美元的事。
“你肯定是哪儿弄错了吧,我家没有这样的唱片。爵士乐唱片的采购和标价就我一个人做,要是见过那样的东西,我怎么也能记住。”
他说着摇摇头,戴上老花镜,刚要接着读刚才的体育新闻,忽然像想到什么似的,又摘下眼镜,眯起眼,仔仔细细地看我的脸,然后说:“不过,如果你有一天搞到了那张唱片,一定要让我也听听。”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
之前那件事过去很久以后的一个夜晚(其实就是最近),查理·帕克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梦中,查理·帕克为我,就为我一个演奏了《科尔科瓦多山》,是一段没有节奏组的中音萨克斯独奏。
阳光不知从哪里的缝隙中洒下,大鸟独自站在那道竖长的明亮里。那大概是清早的阳光,新鲜、直爽,还没混入杂质。大鸟面朝我,整张脸笼着暗影,不过我还是勉强能看出他穿的是双排扣的深色西装,白衬衫上打着亮色的领带。而他手中的中音萨克斯脏污不堪,灰尘满布,锈迹斑斑。还有一根按键断掉了,用勺子把和胶带勉强固定着。见此景象,我不得不陷入沉思。乐器这样惨不忍睹,就算大鸟再怎么厉害,也吹不出像样的音符吧?
这时,我猛然间嗅到一股醇香的咖啡味。多么迷人的味道啊!热烈而醇厚,是刚做好的黑咖啡的香气。我的鼻腔喜悦地轻颤。虽然那味道让我心动,我的目光却一刻也没从眼前的大鸟身上离开。我担心稍微一错神,大鸟的身影就会消失不见。
不知道为什么,那时我已经明白这是梦了——此刻,我正在做一个有大鸟登场的梦。偶尔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一面做梦,一面确知“这就是梦”。不过我以前从未在梦里如此清晰地闻到过咖啡的味道,让我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动。
大鸟终于将吹嘴含在口里,谨慎地吹了一声,好像在测试簧片的状态。过了一会儿,待那声音消失,他又以同样谨慎的态度,安静地排布出几个音符。这些音符在空气中飘浮了一阵子,然后柔软地降到地面。等它们一个不落地降到地上,被沉默吞噬,大鸟又向空中吹送出一连串比刚才更深沉、更有质感的声音,就这样开始了《科尔科瓦多山》的演奏。
到底该怎样描述这段音乐呢?之后回忆起来,与其说大鸟在梦中为我一个人演奏的音乐是一段流淌的音符,不如说那接近于一次瞬间的全面曝光。我能清清楚楚地忆起那音乐,它确实曾经存在。但我无法再现那音乐的内容,也无法沿着时间回溯,就像无法用语言描述曼陀罗的图形一样。我可以肯定,那音乐触及了灵魂深处的核心。它能让人体会到,自己身体的构造在听到它的前后有些许不同——世上确实存在这样的音乐。
“我死的时候,只有三十四岁。三十四岁啊。”大鸟对我说。我想他应该是对我说的,因为那个房间里只有我和他两个人。
我没能对他的话做出恰当的反应。在梦中采取合适的行动是很难的事,所以我只是默不作声地等待他的下一句话。
“你想一想,在三十四岁的时候死掉是怎么样一回事。”大鸟继续道。
我试着想象自己如果死在三十四岁上,会有怎样的感受。三十四岁时,我人生中的许多事才刚刚开始。
“没错,对我来说,一切也才刚刚开始。”大鸟说,“我才刚开始生活。可当我猛地回过神,看看四周,才发现一切已经结束了。”他静静地摇摇头,整张脸还在阴影之中,我无法看到他的表情。满身伤痕的脏兮兮的乐器用细带挂在他的脖子上。
“死当然永远都是突如其来的。”大鸟说,“但同时又是十分缓慢的。和你脑海中浮现的那些美妙的旋律一样。它是转瞬之间的事,又可以无穷尽地延长。就像从东海岸到西海岸一样长——或者像永远一样长。在那里,时间的概念消失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我活着的每一天都在逐渐死亡。可尽管如此,真正的死还是无限沉重的。直到死亡来临前的那一刻,一直存在的东西突兀地尽数消失,回归彻底的虚无。而对我来说,那存在指的就是我本身。”
有那么一阵子,他低着头,定睛望着自己的乐器。接着,他再度开口:
“你知道我死的时候在想些什么吗?”大鸟说,“脑海中只有一段旋律,我将它重复了再重复,一直在意识里哼唱。那段旋律怎么也不肯离开我的思绪。常有这样的事吧?某段旋律一直在人心头盘桓。而我心中的这段旋律居然是贝多芬《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的一节。是这样的—”
大鸟轻声哼唱,我对这段旋律也有印象,是一段钢琴独奏。
“在贝多芬写下的曲调中,这一段最摇摆。”他说,“我以前就特别喜欢这第一协奏曲,听过好多好多遍施纳贝尔演奏的SP唱片[唱片的初期形态。每分钟七十八转,每面可录制三至五分钟的音乐,因此又被称为“78转唱片”或“标准时长唱片”。SP即“Standard Play”的缩写。一九四八年,每面可录制三十分钟音乐的LP(Long Play)唱片问世,SP唱片随之淡出市场。但SP唱片单面录制时长的限制导致如今流行音乐的长度仍多为三至五分钟。]。可这还真是件新鲜事啊,我查理·帕克要死的时候,脑子里一遍遍哼唱的竟然偏偏是贝多芬的旋律啊。然后黑暗就来了,像垂下帷幕一样。”大鸟发出沙哑的轻笑声。
我什么都说不出来。面对查理·帕克的死,我到底该说什么好呢?
“不管怎样,都要对你说句谢谢。”大鸟说,“你给了我又一次生命,还让我演奏了波萨诺瓦。这对我来说,是再开心不过的经历。当然如果我能活到这事真正发生的那天,一定更让人欢欣鼓舞。可就算是死后能这样一回,也够棒了。要知道,我本来就喜欢新出现的音乐类型。”
那么你今天在这里现身,是为了向我道谢吗?
“是啊。”大鸟说。他好像能听到我内心的想法,“我是为了向你道谢才站在这儿的,为了说句谢谢。要是你觉得我的音乐好听,那就最好。”
我点头。我本该说些什么,但到底没能找到适合当时情景的话。
“Perry Como Sings Jimi Hendrix啊……”大鸟若有所思地嘟囔着,又沙哑地哧哧笑了起来。
然后大鸟消失了。先是乐器消失,接着是不知道从哪里洒进来的光消失,最后是大鸟消失。
从梦中醒来时,枕边的时钟指向凌晨三点半。四下当然还是一片黑暗,本该填满房间的咖啡香也不见了,屋里没有任何味道。我到厨房喝了好几杯凉水,然后坐在餐桌前,再一次试着重现大鸟为我、只为我一人演奏的那段美妙旋律的吉光片羽,可还是连一个小节都想不起来。尽管如此,他说的话却在我脑海中苏醒。趁着这份记忆还没褪淡,我用圆珠笔将那些话一字一句地、尽可能正确地记在笔记本上。这是我为那个梦能做的唯一的事了。是的,为了向我道谢,大鸟造访了我的梦。为了感谢我很久以前给了他演奏波萨诺瓦的机会,他还随手拿起手头的乐器,为我吹了一曲《科尔科瓦多山》。
你相信吗?
最好相信。不管怎么说,这件事真的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