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人的朝圣2 | 收藏 |
诗人
一个人的朝圣2 作者:蕾秋·乔伊斯
戴维在剑桥开始了他的第二学年。之后,毫无征兆地,突然来了一封信。信在一个周六送到我的公寓。按信件的标准来判断,这封信很短。他仍喜欢课程,戴维说,尽管阅读书目有时很枯燥。他说在欧洲玩得很疯!(我从来信不过感叹号,尤其是一大堆的感叹号。)他还说,他想念皇家舞厅,并给了我回信地址。有一条附言。我能不能给他一点现金?又有一条附言。他很抱歉。
我当天下午就回信了。我认为他敢再张口要钱实在很有种,但我原谅了他,一部分因为他还记得我,让我很感动,另一部分是因为他对皇家舞厅的评价。我寄给他一张卡片和一张五英镑的纸币,放在同一个信封里。
陆续有信寄来。不定期,每隔几个星期一封的样子,每次他都求我给钱。有时我直接无视这些信件。那些更紧急的我才回复。我得承认,哈罗德,我觉得被利用了。我知道如果我告诉你,你会很无地自容。十二月初,戴维写信询问,他能否来我家过个周末。他需要见我,他说;情况变得太压抑了!他把我称作他的朋友。
为了不引起惊慌,我问你和莫琳有没有听说什么,你可能记得,可能不记得,但你的回答一如往日,说戴维太忙,没时间联系。在戴维的信里,他给了我长途大巴的班次,问我能不能帮他付车钱,于是我回信时寄了去。(这次是二十英镑。)我打扫了公寓,给他在沙发上置了一张床铺。等他一到金斯布里奇,我就打算建议他回去看你和莫琳。周五下午我早早下班,很小心地不让你看到我离开。
戴维没有出现。我拿着书在巴士站等了三个小时,而他压根没来,也没再写信。蠢女人,我心想。他当然从没想过要来。他只想要钱。他很可能已经把车费喝光了。但至少我不用骗你。
十二月中旬,你又拿着空罐子出现了。我不知道戴维敢不敢再次出现在我的公寓门口,但他没有。我第一次在金斯布里奇看见他时,都不敢相信那是他。
一年一度的圣尼古拉斯集市在码头那里办得热火朝天。我问你去不去,你说圣诞市场不是莫琳的菜。那是个没有雨的冷夜,摊档的灯光在河口黑水里投下晃动的图形。我记得,有热葡萄酒的辛辣气味,还有热狗和汉堡包的炸洋葱味。有一些露天游乐设施供幼童玩耍,人们的叫喊和起哄声压过了发动机的噪音。市场尽头,一大群人已经聚集起来,观看临时舞台上的一支本地乐队。我握着塑料杯装的热红酒暖和手指,看了他们一会儿——乐队的成员都很年轻,或许跟戴维同样年纪——观众里有人开始跳舞。我看到了纳比尔的秘书席拉,和她的丈夫一起,还有几个销售代表。温热的红酒撞击我的喉咙,让我情绪高昂。某种意义上,这又像是在皇家舞厅——你属于某样东西,又不属于。真是遗憾,我记得自己想着,真遗憾你留在家里。我继续走,因为另一群人已经聚集起来,我能听到笑声。我也想大笑。
我站在人群的最外面,很难看到里面,而且乐队的音乐也太吵,听也听不清。我侧身往里挤进去一点,就在那时,我不得不停下,确认我看到的真是我以为的那个人。
戴维站在一圈强光的正中央,拿着一个手持式麦克风。他的体重轻了不少。轮廓更加锐利,或者说更加疏离。我突然想到,他很可能用了化妆品。他留长了头发,绑成一个马尾。穿一件松垮的深色大翻领西服,搭配他的旧靴子,还有我的连指手套。我现在回想起那幅场景,是那副手套提供了唯一真实的色彩。就像看着一张黑白照片里一团扎眼的红,近乎触目惊心。
我仍在生戴维的气,因为他浪费我的时间,还找我拿钱,但我最主要的还是气我自己,气我被他利用。我继续躲在人群里,不想让他看见我。戴维在背一首诗。尽管天气很冷,他身上还是有着一种闲适,一种魅力,一种光辉,吸引人们靠近,让人愿意聆听。我能看得出来。他一边抽烟一边表演,脚边还有一个瓶子,他不时俯身举起瓶子灌一口。有人大声叫道:“把酒瓶传给大家啊,戴维!”他就大笑着说:“自己买酒去,先生。”似乎有不少人认得他。
戴维攥着几张纸,但他基本不看。他以深沉有力的嗓音表演,颇具感染力。就我听到的部分来说,这些诗都是讽刺作品。他每读完一首诗,观众就狂热地鼓掌。他们明显喜欢他,而他也知道。他的脚边放着他的费多拉帽,一个女人走上前去,往里面丢了几枚硬币。
我听到他说,他很快就要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作品了,几个人点头,表示他们会有兴趣一读。
“那么下一首,”戴维说,“叫《一个待字女仆的情歌》。”人群大笑,同时他停下来又猛灌一口。“它有一段类似迭句的地方,你们都可以,你们知道的,可以加入。”他从夹克口袋里抽出一条丝巾,在脖子上打了一个结。我推断那是莫琳的。有人高呼一声:“同性恋!”戴维咧嘴一笑,说:“是啊,对。”我又凑近一些。
戴维开始用尖锐的高音背诵,像在模仿一位年长的妇女,那是我熟知的语句。我一直放在手提包里的语句,直到我丢失它们。是我的诗。
(“我看着世界,却只看见你”那种东西。我几乎难以复述。)
然后迭句开始了——这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整个人群都在吼——“我的爱是纯洁的。我是你的女仆。哦,我啊,哦,天啊,我会和你上床吗?”
人群刺耳地重复喊着这首诗,我的脸因为羞耻而烧得通红。
戴维又继续背了四首诗。我之所以留下,只是因为我听到的东西太伤人,脑子太乱,动弹不得。他所有的诗都在拙劣地模仿我。所有的诗都让人群起哄。等到第五首诗结束,我再也受不了。我转身,推开人群出来。
之后我开始跑。跑过了摊档,跑过了儿童的旋转木马。我用手捂着脸,这样就没人能看到我。等到了码头的另一边,我不得不停下,坐在一条长凳上。隔着油腻的黑水,我想象人群在哄笑,觉得自己就像被扒光了衣服。我无法自抑,痛苦地放声大哭。要是你已经看过那些诗呢?更糟糕。要是你妻子已经读过它们呢?我想待在自己的公寓里,但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人群开始吹起挑逗的口哨,开始鼓掌。我猜戴维的朗诵会结束了。我坐了很久,看着人们沿着码头走回家。家长扛着他们的孩子。几个男人——我认出他们是销售代表——把一个年轻女子举到水面上,假装要把她丢进去,那女子在尖叫。一匹被装扮成麋鹿的马被牵进马厩隔间。酒吧开始满了。集市将近尾声。
“嘿,是你。”一只纤细而坚定的长手扣住了我的肩膀,把我拉转过身。我闻到他的气味,不得不故作镇定。“你刚才在吗?”
我站起来要走,但戴维跟上来,挡住了去路。我看到他眼圈周围黑色的眼线,嘴唇上深红的色渍。他把脸盖上了一层白色的粉底。
“你父母都知道这些吗?”我冷冷地问。
他大笑着说,很可能不知道。他没提信,没提我寄的钱,也没提他未能兑现的拜访。他越过自己的肩膀扫了一眼集市。
“还不错。人们喜欢我。有现金吗?”
我的下巴都要掉了,他又开始大笑。“我开玩笑的。”他给我看那顶帽子。里面装满了硬币,还有几张纸币。“你想喝点东西吗?我请你喝一杯。”
“不用。”
“随你的便。”戴维耸耸肩,走开了。我看着他逛到街上,往外卖酒铺走去。
那个周一,我坐进你的车里时,几乎无法看你。你问我是不是感觉很憔悴?憔悴?我打断你的话。那算个什么词?你尴尬地笑了一下,继续专注于前方的路。
“圣诞节准备做什么好玩的事吗?”你说。我没回答。
我们一定沉默地行驶了一段时间,因为我记得你在停车带靠边。“在这儿等着。”你说,然后下车从行李箱里拿来一个袋子。
等你在驾驶座里坐稳后,你让我看。
你从袋子里举起一个红色的装饰球,小心地把它绑在后视镜上。你的手移动的时候,球转了一下。你拉下了我这边的遮光板,又挂上了一个装饰球,这次是一个金色的。然后你在方向指示灯上挂了一个蓝色的球,最后,是一个银色的,你绑在了我座椅后面的衣帽钩上。
“圣诞快乐,奎妮。”你说。
“我不懂,戴维。”
那天是节礼日[每年的12月26日,为圣诞节次日或圣诞节后的第一个星期日,是在英联邦部分地区庆祝的节日。这一日传统上雇主会向雇员赠送礼物。],他决定突然拜访我。他站在公寓共用大门的门口,送来一瓶半满的金馥力娇酒,还有一小枝冬青。他因为湿冷而打着哆嗦——他只穿着夹克和牛仔裤,外面下着瓢泼大雨——但这个年轻人绝不可能进我的家门。
“和解吧?”他说着递出那瓶酒。
他的衬衫湿透了,领子像纸一样贴在皮肤上。我正准备关门,或许他察觉到了,我不知道,因为他抬起脸来,我就看到了。他哭过了。
他的身后,大雨击打着街道、人行道、河口。一切都是浸透的灰色,都是水。我看着戴维,他两眼通红,嘴巴因为悲伤而嘟起,瘦高的身体穿着湿衣服那么不适,我动了怜悯之心。
“那就进来吧。”
他穿过走道,进了公寓,划过地毯,径直停在了椅子处,所到之处留下了一条水迹,他脚踝缠绕着坐进椅子里,手臂紧抱着自己的身体。他的膝盖抖动着,上上下下。
“戴维,我在生你的气。”我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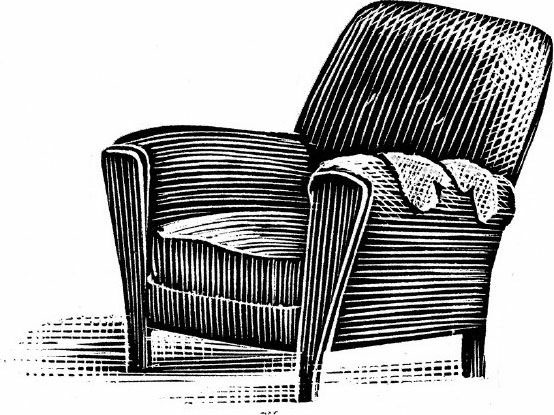
“是啊,我知道。”他甩甩湿发,雨滴飞溅在衣服上。“而且我很抱歉,小奎。我真的抱歉。”
我给戴维沏了茶,拿来毛巾和一床毯子。我一直忙个不停,这样就不用坐下来和他对话。不过,现在他在我的公寓里,情况变得不同了。他看起来小了一点。他喝光了绿色茶杯里的茶,往里面倒满金馥酒。
我坐在地板的靠垫上。好了,我告诉他:解释一下。
他讲了一个下午。他跟我聊课程、大学,聊他在剑桥的生活。他承认功课很难。他有过一个女朋友,但她离开了他。现在他发现自己喝醉后更容易和人们打成一片;喝醉的他更有趣,更不受拘束。但功课很痛苦,当然。助教们已经盯上了他,父母不知道这件事。
朗诵自己的诗是向人们展现他是谁的一种方式,他说,可以不用惹恼他们或让他们反感。他在学生会和大街上做诗朗诵。这就像知识分子的街头卖艺。他喜欢这件事带来的关注,还有现金。
“我想让人们注意我,”他说,“父母对此一无所知。”
“但你偷了我的诗,戴维。你把它们当成笑料。”
他温柔地看着我,用你的那双眼睛,然后坦白地说:“我只是想有人看到我,小奎。看到我本来的样子。”
说到底,我们都想这样:被人看到。
“你朗诵的那些诗都不是你的。其他人怎么能从里面看到你呢?如果他们能从里面看到什么人,那也是我。”
他短暂一笑,然后再次开口,仍旧一副放下戒备的诚实模样:“可是,正是那样啊。你在看着我,小奎。你看到我是个骗子。”
我的愤慨、被背叛的感觉,都消融了。我想帮助这个男孩。我真的想。“你得表露你的真心,戴维。”我把手放在心口,感觉到它贴着我的手掌在搏动。
过了片刻,他问:“你在你的诗里就是这么做的吗?表露你的真心?”
这一次我不回答了。
戴维去拿他的瓶子,拧开瓶盖,又往绿色茶杯里倒满了金馥酒。他很小心地用袖子擦净瓶颈。最后我竟然加热了一块圣诞布丁(一人份),和他一起在火炉边分吃了。我们把盘子放在腿上吃。他跟我说起一点他夏天在欧洲的事,直到光暗下去,他才问道:“它们是写给谁的?你的诗?”
“不是你认识的人。我是好几年前写的。”
我抬起头时,他正非常仔细地看着我,微笑着。他相信我。他没有意识到我爱他的父亲。戴维给我倒了一杯金馥酒,我喝得太快,结果酒精直冲我的喉咙。“我只是想确切知道是谁。”他说。
接下来的几周,戴维打过几次电话。当然,他用的是应答付费方式,他告诉我他在剑桥的状况,让我放心,说自从我们谈过话后,他感觉好些了。更加踏实。他开始写自己的诗,他说,他真的很满意自己的作品。他的诗不再有趣,我觉得那样也可以吗?我向他保证,只要他真的在表达自我,那就是好的。真的很好。“我可以把它们寄给你吗,小奎?”他问。
显然他在剑桥遇到一个人,这个人又认识另外一个人,另外那个人读了诗,觉得戴维大有前途。说他有能力拎起一个主题,把它推至极致。第一批诗次日就到了:揉成厚厚一团,装在一个棕色信封里。
我得跟你说老实话,哈罗德。戴维的诗不怎么样。它们满是陈词滥调。大多数都没有写完。而且它们都有一种阴郁感,显得很是自我陶醉。我在页边的空白处写了注释。意象松散的地方,我提出新的构思。我在尽己所能地帮他。更多的诗寄来。它们更加阴冷。它们谈论死亡,那个黑洞。他经常在页尾写上一句:“只给你一个人看!”他强烈要求我不要告诉他的父母,否则他永远不再信任我。“你的秘密很安全。”我向他保证。然而我有所担心,而且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
复活节来了又去。我记得在你的车里藏起用锡箔纸包的巧克力蛋,作为复活节寻找彩蛋的惊喜,但你一屁股坐在一个巧克力蛋上,于是我们在咖啡馆里花了好久清理污迹。
戴维在家里短暂待了一阵。夏季开学,他回校后,又开始寄来诗歌。我继续帮着构想新的措辞,有时,我承认,我也借此机会来提其他的建议。或许他应该参加诗歌社团?他吃饭正常吗?如果有人问我,和戴维搅在一起做什么,我就会这么解释:我在通过帮助你的儿子来帮你。我,曾经也是一个牛剑[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合称。]名校的学生。我,也有过敬畏我才智的父母。我希望戴维能站稳脚跟,然后我就会随意地在我们的谈话中顺便提及整个真相,关于我们去跳舞,我给他寄钱,诗歌,还有所有我未能向你承认的其他事情。事后再提的话,那些事件就会看似无足轻重,因为它们会安全地留在过去,戴维也会开心。
于是我们继续一同驾驶,你和我。我注视着你,给你带巧克力棒,用小东西表示我在那里。有时你绕远路回家,指点我看鸟。我们停过一次车,你还记得吗,因为你说觉得我看起来面色苍白。(我的确是。当天早上戴维寄给我一首诗,关于他脑海里的“蓝色野兽”。)我们坐在一棵无花果树下,但我苦不堪言。过了一会儿,你开始收集无花果,仔细地把它们沿着空荡荡的避让带排成一条直线。你玩过无花果球没有?你问。我说,没,我没玩过,你表示惊讶,告诉我很简单,就像保龄球一样,其实,只不过是换成无花果来玩。
“你在哪里都能玩。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它不是奥运会项目。要是你找不到无花果,用板栗玩也可以。”
意外地,我很擅长玩无花果球。“你看,”你说,“现在你又笑了。”
“有一天我要和我儿子来这里。”
我们坐在斯莱普顿沙滩上的酒吧外面。我要了雪利酒。你要了一品脱的酸橙柠檬水。一包薯片躺在我俩之间的桌上。那一定是夏天——戴维在剑桥的第二年年末。海很平静,像磨光的玻璃,天空也闪着银色,间歇地被斯塔岬的眩光打破。“我们会来杯啤酒,”你说,“我和戴维。”
一杯啤酒?我心想。你确定吗?你就好像读出了我的想法,微微一笑:“要不还是柠檬水吧。我们会聊一聊。你知道的。”你蓝色的眼眸蒙上了雾,“男人与男人间的聊天。”
“那不错啊。”我说。
“人年轻的时候,不那么容易和父亲聊天。但有一天。有一天他会像我一样老。等我们都老了,聊天就会容易些。”
我想象戴维戴着我的连指手套。我放声大笑:“我无法想象戴维戴着驾驶手套的样子,哈罗德。”你看起来那么悲伤,那么不确定,而我在试图让你感觉好受些,但还没等我把这句意见说完,我就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我真希望能把这些话塞回嘴里,但我只能吞掉剩下的雪利酒。
“我不理解,”你对着宁静说话,“你见过戴维吗?”海水默默地冲刷着海滨。
答一句“是”会很快。是,哈罗德;是,我见过。你把契机现成地摆在我的面前。我们跳过几次舞,我会说。他打电话给我。要过钱。坦白交代还不算太迟。永远都不会太迟——然后我想起我的诗,被他讽刺的诗,我不知该如何解释我爱你。
“没有。”我说。我又说了一次,生怕第一次不够大声。“没有。没见过。我从来没见过他。”
你夹着怪声地笑了一下。没有大笑那么猛烈,但比单单一个微笑要温暖。
“我觉得你会喜欢他的。他肯定会喜欢你。”
一切都变得不堪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