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夜 | 收藏 |
娜斯津卡的故事
白夜 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的故事有一半您已经知道了,那就是,您知道我有一个老奶奶……”
“要是另一半也像这么简短的话……”我笑着插了话。
“别开口,听我说。有言在先:不许插嘴,不然的话,我说不定会被您弄糊涂的。好,您乖乖地听着就是了。
“我有个老奶奶。我来到她这里时还是个很小的女孩儿,因为我的父母全都去世了。可以肯定,奶奶过去很有钱,因为她现在还常提到当年的好时光。她教我学法语,后来又给我请教师。我十五岁时(现在已经十七岁),我们谁也不再提学习的事了。原因是当时我搞了一次恶作剧;我干了什么事无须告诉您;只要说一句就够了,过错并不大。只是一天早上,奶奶把我叫到跟前,说是她眼睛瞎了,看不住我了,说着便拿起一根别针把我的衣服和她的别在了一起,当时她说,如果我当真不学好的话,我们就要这样坐上一辈子。总之,起初我怎么也无法脱身:干活、念书、学习——全得拴在奶奶身边。有一次,我想蒙骗她,好歹说动了菲克拉坐到我的位子上。菲克拉是我们家的女用人,是个聋子。菲克拉代我坐在那里;奶奶这时候在安乐椅里睡着了,我跑出去找附近的一个要好的女孩儿。唉,结果可糟啦。我出去后,奶奶就醒了,问了几句话,以为我还乖乖地坐在那儿呢。菲克拉看得出奶奶在问话,可就是听不见奶奶说什么,想来想去没办法,干脆抽掉别针,跑掉了……”
娜斯津卡说到这里停了下来,随即笑了。我也跟她一块儿笑。她马上收敛了笑容。
“听着,不许您讥笑我奶奶。我发笑是因为觉得这事挺好玩儿的……有什么办法呢?说实话,奶奶就是这样子,不过,我对她还是有好感的。嗬,这一回可够我受的:我立刻又被拴在老地方,再也不准动一动了。
“哎,我忘了告诉您,我们家的房子是自己的,是奶奶的,那是一座小房子,一共只有三扇窗,房子全是木头的,并且很老了,跟奶奶的年纪差不多;上面有间小阁楼;后来小阁楼里搬来了一位新房客……”
“这么说,原来还有位老房客啰?”我随便一问。
“那还用说,当然有过,”娜斯津卡回答道,“那人从不多嘴多舌,比您强多了。真的,他难得开口讲话,是个又瘦又哑、又瞎又瘸的小老头儿;最后也没有活下来,他死了;此后只好再找一个新房客,因为我们没有房客就没法过下去:阁楼的房租再加上奶奶的养老金几乎就是我们的全部收入了。说来也凑巧,新房客竟是个年轻人,他不是本地人,是从外地搬来的。因为他不讨价还价,奶奶便答应了他,后来奶奶问:‘怎么样,娜斯津卡,我们的房客是年轻人还是老头儿?’我不想撒谎,于是回答说:‘这么说吧,奶奶,不算很年轻,也不是老头儿。’‘怎么,长得挺好看吗?’奶奶又问。
“我还是不想撒谎。‘对,我看嘛,长相挺不错,奶奶!’奶奶说:‘哎哟!罪过,罪过!小孙女儿,我得告诉你,你可不能偷着瞧人家。如今是什么世道啊!你看,来了这么个小房客,长相居然也不错:跟很久以前可大不一样啦!’
“奶奶总是怀念当年的青春时光!很久以前,她比现在年轻,太阳比现在温暖,很久以前连奶油也不像现在这样很快就变酸——张口闭口不离当年!我静静地坐着,暗自心想:为什么奶奶要来开导我,还要问房客是不是年轻漂亮呢?我只不过这样想一想,立刻又去计算绒线的针数,编织起袜子来,不久便把这一切全都抛在脑后了。
“一天早上,房客跑来找我们,问到我们答应过用花纸给他糊墙的事。东拉西扯,唠叨个没完,然后说道:‘娜斯津卡,你到我卧室里去把算盘拿过来。’我立刻一跃而起,不知道为什么变得满脸通红,竟忘记了我坐在那里是和奶奶别在一起的;本来是不该这样的,我应当悄悄地把别针取下,不让房客看见,谁知道我竟猛地一跳,带动了奶奶的安乐椅。我发现房客这时已看清我的底细,我便红着脸站在原地,纹丝不动,接着突然大哭起来——当时我是多么羞愧和伤心啊,真恨不得死了才好!奶奶吼了一声:‘你还站在那里干什么?’——而我却哭得更加厉害……房客看出我是由于他在场才害羞的,便低头一鞠躬,马上走开了!
“从那时起,只要过道里有点动静,我就吓得要死。我猜想一定是房客来了,为了以防万一,总是偷偷地把别针取下。但每一次都不是他,他再也不来了。过了两个星期,这房客转托菲克拉传过话来,说他有很多法文书,全是值得一读的好书;问奶奶是否想让我念这些书给她解闷。奶奶答应了,并对他表示感谢,只是一再查问这些书是否教人为善,因为如果是一些有伤风化的书,她说,娜斯津卡你就绝不能读,读了你会学坏的。
“‘我会学到什么呢,奶奶?书里都写的是什么呀?’
“‘哼!’她说,‘那些书里写的尽是年轻人怎样勾引品行端正的姑娘,借口要和她们结婚,带她们离家私奔,然后又抛弃了那些不幸的姑娘,让她们任凭命运摆布,她们的结局惨极了。’奶奶说,‘这种书我读得可多了,全都写得那样棒,害得你整夜坐着,偷偷地读。你呀,娜斯津卡,’她说,‘要注意别去读它们。’她又问,‘他送来的,都是些什么书呀?’

“‘都是沃尔特·司各特的小说,奶奶。’
“‘沃尔特·司各特的小说!得啦,这里面有没有什么鬼花招?你看看,这房客是不是把情书什么的塞进书里了?’
“‘没有,’我说,‘奶奶,没有情书。’
“‘你再看看书皮底下;他们有时候就塞在书皮下面,那些坏蛋!……’
“‘没有,奶奶,书皮底下什么也没有。’
“‘嗯,这就好!’
“于是我们开始读沃尔特·司各特的书。一个月左右便差不多读完了一半。此后他又接连不断地送书,还送来了普希金的作品,最后弄得我离开书简直就没法过,至于怎样嫁给中国皇太子的事,就再也不想了。
“事情凑巧,有一次我在楼梯上偶然碰见了我们家的那位房客。奶奶打发我去取一件什么东西。他站住了,我红了脸,他也红了脸;可是他却笑了,向我问好,问奶奶身体好,又说:‘怎么样,您把书读完了吗?’我回答:‘读完了。’他说:‘您最喜欢什么书?’我说:‘最喜欢《艾凡赫》和普希金。’这一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过了一星期,我又在楼梯上碰见他。这一次奶奶没有打发我找什么,是我自己要去取东西。时间是两点多钟,房客往往在这个时候回来。‘您好!’他说。我回答他:‘您好!’
“他说:‘怎么,您整天和奶奶坐在一块儿不觉得无聊吗?’
“听他这样问我,我不知怎的马上红了脸,觉得很难为情,又感到挺委屈,看来是由于别人问起了这件事的缘故。我本想不搭理他就走开,可是浑身没有力气。
“‘请听我说,’他说道,‘您是个好姑娘!请原谅我跟您这样说话,不过,您尽可相信我,跟您的奶奶相比,我更希望您好。您连个可以去看望的女伴都没有吗?’
“我说,现在一个也没有,过去倒是有一个,她叫玛申卡,可是她到普斯科夫去了。
“‘请听着,’他说,‘您肯跟我一起去看戏吗?’
“‘去看戏?奶奶那边怎么办?’
“‘您呀,’他说,‘别让奶奶知道就得了……’
“‘不,’我说,‘我不想骗奶奶。再见,先生!’
“‘好吧,再见。’他说。再也没有讲什么话。
“可是刚吃过饭,他就到我们房间里来了。他坐了下来,跟奶奶说了好长时间的话,问她出门到过什么地方,有没有熟人——接着忽然说:‘今天我在歌剧院订下了包厢,演出的是《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塞维利亚的理发师》是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1792—1868)所作的歌剧。],有几个熟人本来都想去,后来又不去了,我手里还剩下一张票。’
“‘《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奶奶叫了起来,‘是当年常演的那个理发师吗?’
“‘是的,’他说,‘这正是那个理发师。’说完瞅了我一眼。我一下全都明白了,不由得红了脸,我的心由于期待而猛跳起来!
“‘不错,怎么能不知道呢!’奶奶说,‘想当年在家庭演出晚会上,我本人就扮演过罗茜娜!’
“‘那么今天您不想去吗?’房客说,‘要不,我的票也就作废了。’
“‘好吧,让我们一块去吧,’奶奶说,‘为什么不去呢?我的娜斯津卡还从来没去过剧院呢。’
“我的天,叫人多高兴呀!我们马上收拾停当,穿戴整齐就动身了。奶奶虽说眼睛看不见,可还是想听音乐,再说,她老人家心肠好:最想让我开开心,而我们自己却永远也去不起剧院。《塞维利亚的理发师》给我留下了什么印象,我不告诉您,只想说当天的整个晚上我们的房客是那样亲切地望着我,说话是那样动听,我立刻就看出来,早晨他提出让我一个人跟他去,是想试探我。在躺下睡觉的时候,我是那样得意,那样快乐,心跳得像患了轻度的寒热病,我说了一夜梦话,说的都是《塞维利亚的理发师》。
“我本想此后他会来得更勤些——谁知不是这么回事。他几乎根本就不来了。这么说吧,往往是一个月才来一次,来了也只是请我们看看戏。后来我们又去看过两次戏。不过,我对这事非常不满意。我看得出,他只是由于我被奶奶管得这么严而可怜我,此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了。时间慢慢过去,我像得了什么心病:坐也坐不稳,书也没心思念,活也干不下去,有时候笑,还故意跟奶奶怄气,有时候干脆就哭一阵子。后来我瘦了,差一点儿没病倒。演歌剧的季节过去了,房客也根本不来看我们了;我们相遇的时候——自然还是在那个楼梯上——他总是默默地、一本正经地点头,好像连句话都不肯说,等他已经走到门廊上,我还在楼梯中间呆站着,脸红得像樱桃,因为我只要遇见他,全身的血液就会向脑袋涌上来。
“现在快要讲完了。整整一年前的五月里,房客跑来找我们,对我奶奶说,他在这里的事情全都办完了,要回莫斯科住一年。我一听,脸就唰地变白了,像死人一般跌坐在椅子上。奶奶没觉察出什么来,他呢,交代一下要离开我们家,接着行个礼就走了。
“我该怎么办?我想来想去,发了半天的愁,最后横下一条心。他明天就要走,我决定等晚上奶奶睡下后,让一切都了结。情况也正是这样。我把几件连衣裙和必不可少的换洗衣服捆成一个小包袱,放在手里提着,半死不活地走上阁楼去找我们的那位房客。我觉得我在楼梯上足足走了一个小时。我推开他的门,他看见我便失声惊叫,还以为我是个幽灵呢。他赶忙跑过来给我倒水喝,因为我几乎都站不稳,心脏狂跳不止,头疼,神智也恍恍惚惚的。等我清醒了,忙把包袱放到他床上,在包袱旁坐下,双手捂住脸,呜呜痛哭,泪如泉涌。看来,他很快就明白了一切,脸色惨白地站在我面前望着我,那副悲伤的模样弄得我的心都碎了。

“‘您听着,’他开口说道,‘您听着,娜斯津卡,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我是个穷光蛋;目前一无所有,连个像样的职业都没有;如果我跟您结了婚,我们怎么过活呢?’
“我们谈了很久,最后我急得简直要疯了,我说,我再也不能跟奶奶一起过日子,我要离开她,我要逃走,我不肯让人家老用别针把我别住。我说,只要他乐意,我就跟他去莫斯科,因为没有他我就活不了。羞耻、爱情、自尊心全都猛地在心中翻腾起来,我在近乎惊厥的状态下倒在了他的床上。我是多么害怕遭到拒绝啊!
“他默默坐了几分钟,然后站起来,走到我跟前,握住我的手。
“‘您听着,我的好姑娘,我亲爱的娜斯津卡!’他开始说道,眼里也噙着泪水,‘您听着,我向您起誓,只要有朝一日我能结婚,我的幸福就必定非您莫属,请您相信,如今只有您一个人能够使我幸福。您听着:我要到莫斯科去,在那里待上一年整。我打算闯出一番事业来。等我回来了,要是您不嫌弃我,我向您发誓,我们一定会幸福。现在可不行,我不能也无权答应您什么。但我要再说一遍,即使一年之内办不到,那么总有一天肯定会成功;条件自然是除我之外您没有爱上别的人,因为我现在不能也不敢用什么诺言限制您。’
“这就是他跟我说的话,第二天他走了。我们相约对奶奶一字不提这件事。他主张这么办。好,现在我的故事很快就要讲完了。过去了整整一年。他来了,他到这里已经整三天,可是,可是……”
“可是什么呢?”我喊道,急于听到故事的结尾。
“可是他到现在还不露面!”娜斯津卡好像鼓足了勇气才回答出来,“没有消息,没有踪影……”她说到这儿,停了下来,沉默片刻,低下头,忽然用双手捂住脸,痛哭不止,这哭声使我心里难受极了。
我怎么也没有料到结局会是这样。
“娜斯津卡!”我用委婉的口吻欲言又止地说道,“娜斯津卡!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哭啦!你是怎么知道的?他也许不在这里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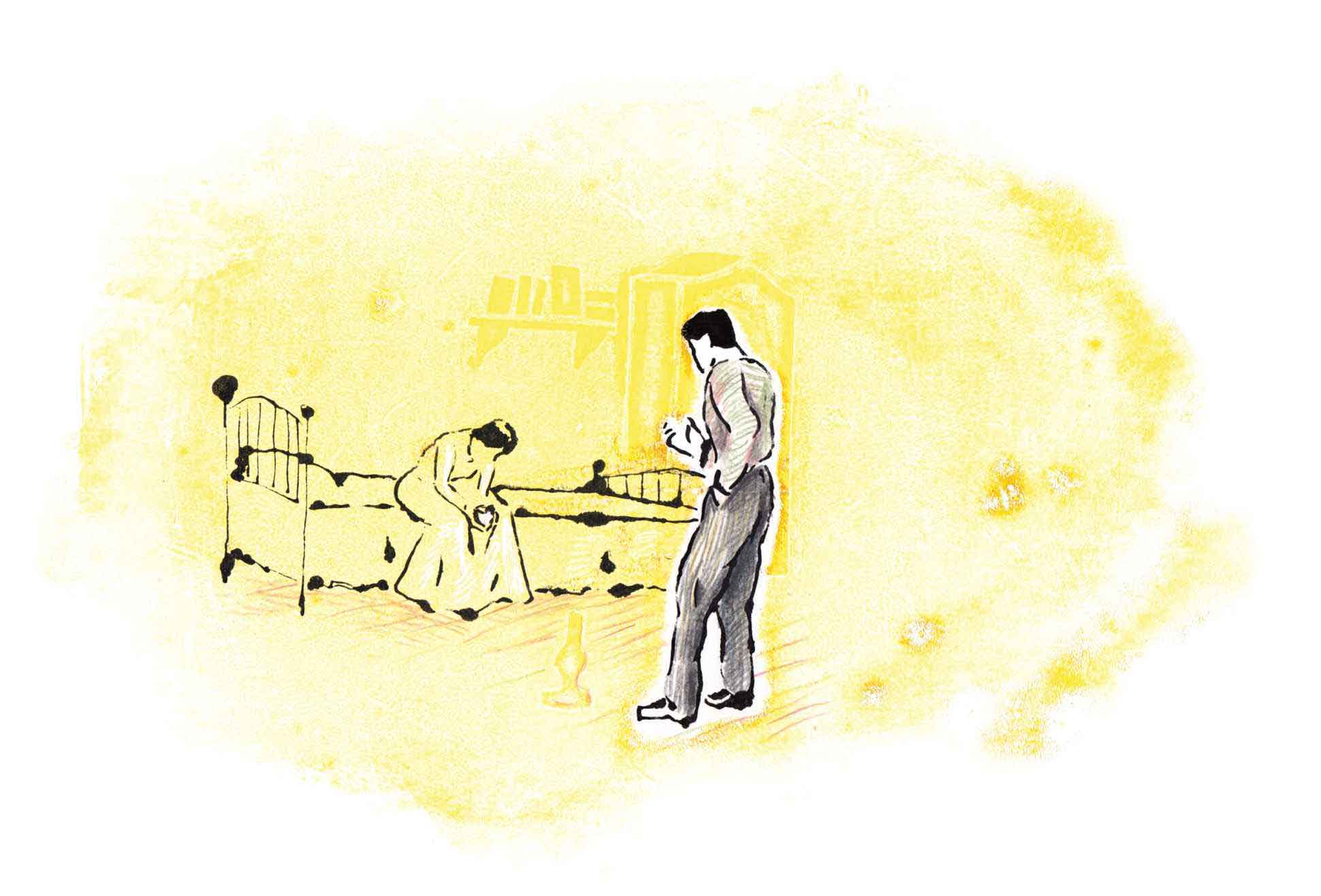
“在这里,在这里!”娜斯津卡应声答道,“他在这里,我知道。我们当时约定好的,就在那天晚上,他临走的前夕,当时我们说的话,我全跟您讲过了,我们商量妥当,便出门到这儿来散步,就在这条沿河街上。那是七点钟光景;我们坐在这张长椅上;我已经不哭了,心里甜丝丝地听着他说话……他说,他一回来立刻就来看我们,如果我不拒绝他,我们就向奶奶讲出这一切。如今他来了,我知道这一点,可就是见不着他,见不着!”
她忍不住又流下泪来。
“我的天!难道没办法帮您减轻痛苦吗?”我大声说道,万般无奈地从长椅上霍地站起来,“请问,娜斯津卡,我能不能去找他一趟呢……”
“难道可以这样吗?”她猛地抬起头来说。
“不,当然不可以!”我说,忽然改变了主意,“这样好了:请您写一封信吧。”
“不,这不行,不能这样做!”她断然回答道,但是已经低下头,不再看我了。
“怎么不行呢?为什么不行呢?”我接着说,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过,您知道,娜斯津卡,这要看写的是什么信!信和信可大不一样,再说……噢,娜斯津卡,就这么办!请您相信我,相信我!我不会给您乱出坏主意。这一切都会办好的。您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为什么现在又……”
“不行,不行!这样做好像我要强求人家似的……”
“唉,我好心肠的娜斯津卡!”我打断了她的话,忍不住要笑出来,“不,不;说到底,您有权这样做,因为他曾经答应过您。再说,我根据种种迹象看得出,他是个能体贴入微的人,品行端正。”我接着说道,由于自己的论点和论据的逻辑性而越加兴奋,“他的为人怎样?他曾许下诺言来约束自己。他说过,只要他结婚,就非您不娶;他让您有充分的自由,哪怕是现在也可以对他表示拒绝……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首先表明态度,比方说,即使您想解除他许下的诺言也未尝不可……”
“请问,要是您的话,您会怎么写呢?”
“写什么?”
“写这封信呀。”
“要是我的话,我会这样写:‘敬爱的先生……’”
“非得写上‘敬爱的先生’不可吗?”
“非写不行!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写呢,我想是……”
“好吧,好吧,请说下文吧!”
“‘敬爱的先生!’
“‘对不起,我……’不,不必,用不着道歉!事实本身足以证明一切。您可以干脆这样写:
“‘我在给您写信。请原谅我缺乏耐心;不过整整一年来我还是很幸福的,因为我满怀希望;如今,这令人疑虑的日子,我连一天也难以支撑,难道这是我的过错吗?现在,您已经来了,也许您已经改变初衷。果真如此的话,这封信就要向您表明,我决不会怨恨和责备您。我不责备您,是因为我无权占有您的心;我是命该如此啊!’
“‘您是个高尚的人。您在看到我忍不住写下的这几行文字时,不会付之一笑或大伤脑筋。请想一想,这可是个不幸的姑娘写的啊,她孤孤单单,没有人给她指点,没有人可以商量,因而她从来也管束不住自己的心。不过,请原谅,我的内心已暗暗——虽说只是一瞬间——出现了疑团。您决不会欺侮,甚至在情理上也决不会蔑视那个姑娘,她过去和现在都对您一往情深。’”
“对,对!这跟我想的一个样!”娜斯津卡喊道,眼睛里闪现出欢快的光彩,“啊!您打消了我的疑虑,您一定是上帝为我派来的!谢谢,谢谢您!”
“谢什么?是感谢上帝派我来吗?”我反问道,高兴地望着她那喜气洋洋的面庞。
“对,那也值得感谢。”
“啊,娜斯津卡!有时候我们感谢某些人,仅仅因为他们和我们一起活着。我感谢您,因为您让我遇见了您,因为我将一辈子记着您!”
“嗯,够啦,够啦!现在这么办吧,请听我说:当时曾经约定,只要他一到,就会立刻转告我,办法是在我那几个忠厚老实的熟人家的某个地方给我留下一封信,他们对这事一无所知;如果担心在信里无法把情况全说清楚,不能给我写信的话,那他就在抵达的当天十点钟,准时到我们约定会面的这个地方来。我已经知道他到了;可是已是第三天,居然既没有收到信,也没有见到人。早上,我实在没办法从奶奶那里跑出来。请您明天把我的信亲手交给我跟您谈到过的那几个好心人,他们会转交给他的。如果有回信,请您晚上十点钟一定把信带来。”
“可是信呢,信呢!要知道先得写好信啊!这一切也许以后才能办妥呢。”
“信……”娜斯津卡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道,“信……可是……”
然而,她没有把话讲下去。她先是扭过脸去不看我,脸红得好似玫瑰花,我突然感到手里塞来一封信,原来是一封早就写好、准备停当、已经封口的信。我的头脑忽地闪过那种亲切而又动人的往事[《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中也有少女罗茜娜冲破重重阻碍向意中人送信的情节。]。
“罗——罗,茜——茜,娜——娜。”我先哼了起来。
“罗茜娜!”我们俩一齐哼着,我兴奋得差点把她抱住,她的脸红得厉害极了,她含着眼泪笑了,那乌黑的睫毛上闪动着珍珠般的泪珠。
“行啦,行啦!现在您该走啦!”她急急切切地说,“信已经给了您,这是送信的地址。可以分手了!再见!明天见!”
她紧紧地握了握我的两只手,又点点头,便箭也似的向她住的那条小巷飞跑而去。我目送着她的背影,在原地站了很久。
“明天见!明天见!”她在我的眼前消失了,这声音却仍然在我的脑海里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