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造自然 | 收藏 |
18 洪堡的《宇宙》
创造自然 作者:安德烈娅·武尔夫
1834 年 10 月,洪堡宣布:“疯狂攫住了我,我将在一部书中重现整个物质世界。”他想包罗万象,将一切事物聚拢在一起:从遥远的星云到苔藓的分布,从风景画、人类不同种族的迁徙到诗歌。他写道,这样一部“关于自然的书,应该让人在阅读过程中想到自然本身”。
于是,65 岁的洪堡开始着手写作自己留下最深远影响的一本书:《宇宙:对世界的简要物理描述》(Cosmos: A Sketch of the Physical Description of the Universe)。书的内容大致基于他在柏林的讲座,但俄国之旅提供了最后一部分必要数据。这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洪堡说:《宇宙》就像“插在我胸口的一把剑,必须将它拔出来”,这将是“我一生的终极之作”。书的标题来源于希腊语χóσμοζ,意为“美”与“秩序”,同时也体现了宇宙是一个有规律的系统。洪堡现在用它来涵盖和表达“天空与大地”这个整体。
同年,“科学家”(scientist)一词首次出现,(1834 年,博学的英国学者威廉·休厄尔(William Whewell)在《书评季刊》上为玛丽·萨默维尔的著作《论物理科学的关联性》(On The Connexion of the Physical Sciences, 1834)撰写书评,造出了 scientist 一词。)象征了科学专业化的开端。与此同时,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分明。也正是在同一年,洪堡开始写作一部著作,倡导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神:当科学逐渐远离自然而进入大学和实验室,并分离出无数各异的子领域时,洪堡想在一部著作中将所有被刻意分离的知识熔于一炉。
因为《宇宙》涵盖的门类如此庞杂,所以洪堡能够在一切可以想见的方向上展开自己的研究。他明白自己未曾,也不可能掌握一切知识,于是招募了一群助手:其中有科学家、古典学家和历史学家,都是各领域的专家。见多识广的英国植物学家们周游诸国,很乐意将大量植物列表寄给洪堡。天文学家与他分享观测数据,地质学家提供地图,古典学家则为他解答古文献中的疑问。他在法国的老朋友也非常支持这一研究计划。一位法国探险家给洪堡寄来关于波利尼西亚植被的手稿,弗朗索瓦·阿拉戈等昔日密友更是有求必应。洪堡有时会请教某些具体问题,有时也会就应该查询某本书中的哪页而请教他人,甚至会给人寄去长长的问卷。每完成一个章节,他就将留有空白的清样寄给他的通信圈子,请他们填入相关的数字或事实证据,或修正他的草稿。
洪堡负责总体把握书稿,助手们则提供他所需的具体数据和信息。他从宇宙的视角看待问题,每个人的知识都是这一宏大计划中的必要工具。他极其仔细,极力追求精确性,总是就同一个问题请教若干位专家。他对事实的渴求是无止境的,甚至曾向在中国的传教士询问中国人是否不爱吃奶制品,或写信讨教尼泊尔棕榈树的种类数目。他承认,“在同一个话题上刨根问底,直到解释清楚”是自己的执念。他经常会发出数千封信件,并饶有兴趣地询问来访者。例如,一位刚从阿尔及尔回到欧洲的年轻小说家发现,洪堡连珠炮般地问起那里的岩石、植物和地层情况;小说家不禁感到恐慌,因为自己对这些一无所知。洪堡可不会轻易放过谁。他对另一位访客说:“这回您可跑不掉了,因为我必须尽量从您这里搜刮信息。”
各地的回信纷至沓来,一波接一波的新知识和数据涌向柏林。每个月,洪堡都需要阅读、理解、区分和整合收到的新材料,工作量迅速增加。
洪堡对出版商解释道,新知识像洪水一样奔涌而来,自己眼看着手上的资料越来越多。他承认,《宇宙》确实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工程”。
唯一的办法就是以更清晰的架构开展研究。洪堡将材料收在箱子里,每个箱子再按照话题收入不同的文件夹。每收到一封信,他就将重要的信息剪下来,连同任何可能用到的只言片语——报纸、书页、写有几个数字的纸条、一则引文或一幅速写,一起放入对应的文件夹。比如,其中一个箱子专门收集与地质学相关的资料,洪堡在里面收集了记录有山峰高度的数据表格、地图、讲稿、老朋友查尔斯·莱尔的来信、另一位英国地质学家绘制的俄国地图、化石骨架的铜版画以及古典学家提供的古希腊的地质记录。这套系统的优势在于,他可以连续地收集材料,写作时只需拿起对应的箱子或信封。虽然洪堡的书房一片凌乱,财务收支也混乱不清,但他在研究上一丝不苟,务求精准。
有时,他会在一则笔记旁标注“非常重要”或“重要,在《宇宙》中待续”。另一些时候,他将写有自己想法的纸条黏在来信上,或从书里撕下一页。一个箱子中可能收有报刊文章、一块干燥的苔藓,以及喜马拉雅山的植物列表。其他箱子里收有一个写有“空气海”(Luftmeer)的信封——这一迷人的词是洪堡用来称呼大气层的——还有关于上古的文献资料、浩大的温度数据表格、引用了希伯来诗歌中提到鳄鱼和大象的文字。此外,还有专门收集关于奴隶制、气象学、天文学和植物学资料的箱子。一位同事惊叹道,只有洪堡能够如此熟练地将科学研究的很多“散碎线头”抓在一起,打成一个巨大的结。
洪堡通常都非常感激别人给予的帮助,但有时他也管不住自己那张出了名的刻薄嘴。例如,柏林天文台的台长约翰·弗朗兹·恩克(Johann Franz Encke)就遭遇过不公平的对待。恩克极为刻苦地工作,曾连续几周为《宇宙》收集天文数据,而洪堡却在私下里对别人说,恩克“变得冷冰冰的,好像他母亲子宫里的冰川”。就连威廉也没能逃过洪堡时而爆发的讥讽。当威廉试图建议弟弟出任柏林一所新博物馆的馆长,以缓解他窘迫的财务状况时,亚历山大倍感愤怒。他告诉哥哥,这个职位与他的地位和名誉不相称,自己可不是为了出任一个区区的“图画展览厅”的领导才离开巴黎的。
洪堡已经习惯了仰慕与恭维。一位柏林大学的教授注意到,围在他身边的年轻人俨然组成了一个洪堡的“王廷”。当洪堡走进一个房间,气氛骤变,好像一切都以他为中心进行了重置,“所有人都朝他转过身去”。年轻人怀着崇敬之情,静静地聆听他吐出的每一个音节。几乎可以肯定地推测,这位柏林最负盛名的人士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是其他人注意的焦点。一位德国作家抱怨道,洪堡讲话时,没有人可以插进一个字。他的滔滔不绝闻名天下,就连法国作家巴尔扎克都把他写进了一个讽刺故事:故事中有一个盛在罐子里的大脑,人们会从中汲取想法;还有一位“普鲁士学者,以其滔滔不绝的流利演讲而著称”。
一位年轻的钢琴家收到为洪堡演奏的邀请。他本来觉得十分荣幸,但迅速发现这位老者有时候十分粗鲁(并且对音乐毫无兴趣)。当他坐下开始弹琴时,房间里一时安静了下来,但洪堡又马上开始大声讲话,导致别人都不能专心聆听音乐。洪堡像以往一样口若悬河,并且会随着音乐的渐强和渐弱改变自己的声调——使嗓音总是比琴声响亮。这位钢琴家后来说:“这是一场二重奏,而我没能坚持多久。”
对很多人而言,洪堡是个谜。虽然他可以十分傲慢,但与此同时,他又极其谦虚地承认,自己仍然需要学习。柏林大学的学生们惊愕地看见他走进讲堂,揣着一个文件夹——不是来讲课,而是来聆听某位年轻教授的课程。洪堡旁听了希腊文学的讲座,称这是为了弥补自己年轻时落下的教育。在写作《宇宙》的过程中,他旁听了化学系一位教授和地质学家卡尔·里特尔(Carl Ritter)的课,以便跟进最新的科学进展。他总是静静地坐在讲堂的第四或第五排靠窗的座位,和旁边的年轻学生一样认真地记笔记。不管天气多坏,这位老人总是按时而至,唯有国王要求他陪侍左右时才会缺席。同上一节课的学生经常打趣道:“亚历山大今天翘课了,因为他要和国王共进下午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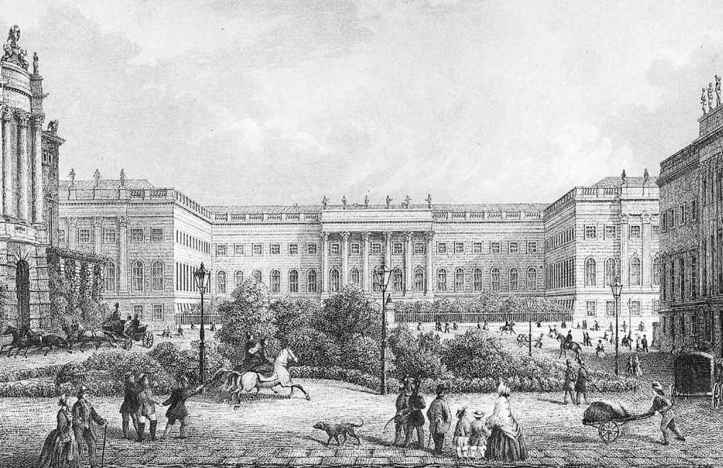
洪堡从未改变过对柏林的看法,坚持认为这是一座“狭隘、没有文化、恶意满满的城市”。威廉是他生活中的主要安慰之一。在过去的几年中,兄弟二人变得更加亲近,并尽可能多地共度时光。1829 年春,卡洛琳娜去世以后,威廉退隐到泰格尔宫,而亚历山大则尽量抽空去看望他。虽然只比亚历山大年长两岁,但威廉日益衰老,看起来完全不止 67 岁,精力也一日不如一日。他的一只眼睛已完全失明,双手剧烈颤抖,再也无法书写,瘦弱的身躯日益佝偻。1835 年 3 月底,威廉在泰格尔为卡洛琳娜扫墓后,回到家就开始发烧。次日,亚历山大一直陪在哥哥床边。他们谈到死亡,威廉表达了想葬在卡洛琳娜墓边的愿望。4 月 3 日,亚历山大给威廉朗读了一首弗雷德里希·席勒的诗。5 天后,威廉在弟弟的陪伴下溘然长逝。
遭逢丧事,洪堡觉得被整个世界抛弃了,感到无比孤独。在此之前,他给一位老友写信说:“我从来没想过这双老眼还能流下那么多泪水。”威廉的去世让他失去了唯一的亲人,以及“一半的自己”。在给法国出版商的信中,洪堡表达了自己的心情:“怜悯我吧,我是最不幸的人了。”
在柏林,洪堡倍感凄凉。威廉去世一年后,他写道:“周围的一切都如此凄惨,如此凄惨!”幸好,在与国王协商的雇用条件中,他每年都被允许去巴黎几个月——为《宇宙》收集最新的研究资料。他承认,想想巴黎是唯一能让自己开心的事了。
一到巴黎,洪堡就投身到紧张的工作中,连人际往来和晚间的消遣都安排得十分紧凑。每天早晨,他会喝一杯黑咖啡——洪堡称其为“浓缩的阳光”——然后工作一整天;晚上则穿梭在各个沙龙之间,直到凌晨两点。他到处拜访科学家,探询他们最新的研究进展。巴黎纵然令人振奋,但他一想到要回柏林就十分沮丧——那个“墓地中的跳舞嘉年华”。每次来到巴黎,洪堡就会更进一步地拓展自己与国际上的联络。他总是带着装满最新材料的行囊回到柏林,然后将它们逐步整合到《宇宙》中。239 然而,每一项新发现、每一个新测量结果或每一笔新数据,都不免再次推迟《宇宙》的完成和出版。
在柏林,洪堡必须在不耽误宫廷义务的同时开展科学研究,为此他十分痛苦。他入不敷出,因此需要这份内务大臣的薪水来维持生存。他必须跟随国王从一座城堡去往另一处行宫。国王最喜欢的莫过于波茨坦的无忧宫(Sanssouci),距离洪堡在柏林的公寓约 20 英里。这意味着洪堡必须带着自己的二三十箱资料——写作《宇宙》时要用到的“移动资源库”——来回奔波。有时,他在路上花费的时间比在其他地方花费的都多得多,“昨天在孔雀岛,然后到夏洛滕堡用茶,再到无忧宫观看喜剧和用晚餐;今天在柏林,明天再到波茨坦”,这都不是什么超乎寻常的日程安排。洪堡觉得自己像一颗不停沿轨道运转的行星,不能停下来歇息片刻。
宫廷事务占据了太多时间。他必须陪同国王用餐,然后为国王朗读,而晚间又会被国王的私人信件占据。1840 年 6 月,腓特烈·威廉三世去世,他的儿子腓特烈·威廉四世登基。新国王向他的内务大臣索取更多的时间,亲切地称他为“我最好的亚历山德罗(Alexandros)”。
据一位访客观察,洪堡在宫廷相当于一部“活字典”,因为他可以随时回答从山峰高度、埃及历史到非洲地理的任何问题。他为国王提供的信息包括世界上最大的钻石尺寸、重要朝代的起止年份以及土耳其士兵的薪水。他还为皇家图书馆和收藏提供采购建议,并推荐王室赞助一些探险考察——通常都是利用国王的好胜心,提醒他普鲁士不能落在别国后面。
洪堡也试图间接地对国王施加一些影响——“尽力而为,但更类似于营造一种潜移默化影响国王的氛围”,尽管国王对社会改革和欧洲政治都没有兴趣。普鲁士正在走回头路,洪堡感叹道,就像英国探险家威廉·帕里(William Parry)所说的:以为自己正在朝北极行进,而事实上,自己所在的浮冰正朝着远离极点的方向漂去。
大多数情况下,洪堡回到自己在奥拉宁堡大街的住处时已经是午夜了,这里距离国王在城里的宫殿不到一英里。但即使在这里,他仍然不得安宁,因为不断有访客拉响门铃。洪堡抱怨道,自己的公寓好像被当成了“酒馆”。为了至少能够完成一些写作,他通常都工作到深夜。出版商已经开始怀疑《宇宙》是否有完成的一天,而洪堡保证:不工作到凌晨两点半决不睡觉。然而他一再推迟发表的计划,因为自己总是在发现新材料,并想整合到书稿中。
1841 年 3 月,也就是他宣布开始写作《宇宙》的 6 年多后,洪堡允诺交付第一卷书稿,然而再一次没能如期完成。他与出版商开玩笑道:和“一个行将就木的人”打交道很危险。然而,无论对方怎么催稿,洪堡依旧按照自己的步调继续写作。他坚持认为,《宇宙》太重要了,这是他倾注毕生心血的作品。
每过一段时间,当洪堡感到太过沮丧时,他便将手稿和书籍留在桌上,不去翻开它们;然后驱车两英里,前往自己协助建立的柏林天文台。在那里,他通过高大的望远镜凝望夜空,看到壮阔的宇宙展现在眼前。他注意到月球上暗淡的陨星坑,美丽的双星则似乎在向他眨眼,遥远的星云散布在天穹上。新型望远镜让他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观察土星,那圈神秘的环带好像是人工所绘。洪堡告诉出版商,正是因为捕捉到这些凝聚着深切之美的瞬间,他才有了继续工作的动力。
在写作《宇宙》第一卷的几年间,洪堡数次搬到巴黎小住。1842 年,他陪同腓特烈·威廉四世访问英国,参加威尔士亲王(未来的爱德华七世)在温莎城堡的洗礼仪式。行程总共不到两周,颇为匆忙。洪堡抱怨自己没有时间留给科学上的事务,甚至没能抽空去一次格林尼治的天文台或皇家植物园。不过,他还是想办法安排了与查尔斯·达尔文的见面。
洪堡请他的老朋友、地质学家罗德里克·麦奇生(Roderick Murchison)组织一次聚会,麦奇生欣然从命(虽然正逢行猎季节,他将因此“错过本年度的最好一击”)。最终,聚会定在了 1 月 29 日。马上要被引见给洪堡的达尔文十分紧张。他一大早就从家里出发,赶往麦奇生在贝尔格雷夫广场的住所,那里距白金汉宫仅数百码之遥。达尔文心里装满了想要和洪堡讨论的问题。他正在发展一套自己的演化理论,并且还在仔细地考虑植物分布和物种的迁徙问题。
过去,洪堡曾用植物的分布来探讨非洲与南美洲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但他也注意到沙漠和山脉等阻碍了植物的迁移。他曾描述过,“在北方冰封的土地下”发现过热带的竹子,继而指出:地球本身也在运动,并带动了植物分布的变化。
32 岁的达尔文到达麦奇生家时,见到的是一位老者:顶着一头蓬松的银灰色头发,穿着深色燕尾服配白领巾,就像在俄国考察时的装束一样。洪堡称其为“万能着装”,无论面见国王还是与大学生交谈,都很适用。
72 岁的洪堡走路更加小心、缓慢,但仍然十分忙碌地在房间里转来转去。当他出席一处聚会时,通常会先在房间里走一圈,微微颔首,频频朝左右点头打招呼,同时大步向前。在这一出场式中,他一直不停地讲话。他一进房间,其他所有人都安静下来。如果此时有人发表一句评论,那只会激发起洪堡另一番冗长的哲学演讲。
达尔文震惊了。他几次试图发言,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努力。洪堡心情不错,给予达尔文“极其慷慨的赞扬”,但这位老人太能滔滔不绝了。
在连续三个小时的时间里,洪堡一直说个不停。达尔文认为这种喋喋不休已经“超出常理”,与他设想的第一次见面大相径庭。作为洪堡多年来的崇拜者及其著作的忠实拥趸,达尔文有些泄气。后来他承认,自己“可能预期过高了”。
洪堡漫长的独白使得达尔文无法和他进行任何有意义的对话。他一边听着洪堡的演讲,一边任由自己的思绪游移。忽然,他听洪堡讲到西伯利亚的一条河流,虽然土壤和气候条件完全相同,但河岸两边的植被“迥然不同”。达尔文只听到了其中的只言片语,大感好奇:如洪堡所说,河岸这边的植被多为亚洲的物种,而另一边的则是类似欧洲的物种。他没有听清楚大部分细节,但又不敢打断洪堡如暴风骤雨般的语速。回到家后,达尔文马上将听到的所有内容记在本子上,虽然并不确定自己是否正确理解了洪堡的意思。他写道:“难道两个不同的植物世界各自独立演变,然后在此处相遇了?多么奇特的情况。”
达尔文在思考自己的“物种理论”,不断为其积攒材料。在外人看来,他的生活规律得如同上了发条的钟表,每天的工作、用餐与家庭时间都十分固定。1839 年,也就是从“小猎犬”号返回英国两年多后,他与自己的表姐爱玛·威治伍德(Emma Wedgwood)结婚,现在带着两个孩子一起住在伦敦。(同年晚些时候,1842 年 9 月,查尔斯和爱玛·达尔文搬到了肯特郡的唐宅(Down House)。)与此同时,他心中却在酝酿一些最具革命性的想法。他体弱多病,经常头痛、胃痛、容易疲劳,脸上常过敏,但仍然坚持发表文章和出版著作,并一直认真地思索演化问题。
此时,之后将在《物种起源》中呈现的大部分论断已经基本成形,但谨慎的达尔文不想急于发表任何没有足够证据支撑或未经确实的理论。在向爱玛求婚前,他曾在一张纸上列出结婚的诸多好处和坏处,对待演化论也一样:在将研究结果公之于世之前,他需要仔细评估一切证据。
如果洪堡和达尔文能在见面的那天好好聊一聊,也许洪堡会分享自己关于世界的新想法——主宰世界的不是平衡和稳定,而是动态的变化。这些想法将被写进《宇宙》的第一卷。洪堡会写道,任何一个物种都是整体的一部分,同时连接过去与未来,充满变化的可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他还会在《宇宙》中讨论化石记录缺失的演化环节,以及“中间步骤”。他将讨论“循环的变化”、过渡阶段和不断的更新——总而言之,洪堡的自然一直处在变化之中。所有这些思想都是达尔文演化论的前身,正如后世的科学家对洪堡的称呼:一位“前达尔文时代的达尔文主义者”。(洪堡没能读到《物种起源》,在该书于 1859 年 11 月首次出版前就去世了。但他却曾经对另一本书发表过评论——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匿名出版的《生命起源的自然志遗迹》(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 1844)。此书不像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那样有那么多的科学证据,但却就演化和物种演变问题给出了类似的极具革命性的言论。1845 年底,英国科学界流传着这样一则谣言,洪堡“几乎支持这套理论的每一处具体细节”。)
然而事实上,虽然那条西伯利亚河流的故事继续深深地吸引着达尔文,但他从未和洪堡谈起过这些想法。1845 年 1 月,洪堡访问伦敦的 3 年后,达尔文的密友、植物学家约瑟夫·道尔顿·胡克(Joseph Dalton Hooker)
因公务前往巴黎。达尔文知道洪堡当时也在巴黎从事研究工作,所以就请胡克当面向洪堡请教关于那条河流的难题。他坚持请胡克转告洪堡,自己一生的事业都受到《旅行故事》的影响。恭维话说完之后,胡克便问起了“那条位于欧洲东北部的河流,其两岸的植被相差悬殊”的事情。
胡克也预订了洪堡下榻的酒店——圣日耳曼区的伦敦酒店。洪堡一如既往地慷慨相助,而胡克也向他提供了关于南极的信息。一年多前,胡克刚刚完成了一次长达 4 年的航行。他加入詹姆斯·克拉克·罗斯(James Clark Ross)船长领衔的船队,踏上这次被称为“地磁远征”的探险,志在找到地磁场的南极点。这次航行也可以看作是英国对于洪堡呼吁建立全球观测站网络的回应。
和达尔文一样,27 岁的胡克视洪堡为传奇英雄。当他在巴黎首次见到这位 75 岁的老人时,一开始有些小小的失望。胡克后来说,“我吓了一跳”,见到的是一个“硬朗的德国小个子”,而不是想象中的那个意气风发、身高六英尺的探险家。胡克的反应颇为典型。很多人都觉得,这位传奇的德国人应该更加威风凛凛才是,“像朱庇特(Jupiter,古罗马神话中的众神之王。)一样”。洪堡从来都不具备高大敦厚的体格,随着年纪增长,他逐渐有些佝偻,并且比以前更瘦了。胡克感到不可思议:这位瘦小的老人竟然曾经登上过钦博拉索峰!但他迅速回过神来,并且很快就被老人的魅力所俘获。
他们谈论共同的英国朋友,也谈到了达尔文。胡克觉得洪堡频繁引用自己著作的习惯颇为好笑,但又对他的思维之敏锐印象深刻。洪堡的记忆力和“概括能力”仍然惊人。胡克多么希望达尔文也在,这样就可以一起回答洪堡所有的问题了。当然,洪堡仍然滔滔不绝,精神依旧健旺,这从他对达尔文的答复就可以看出来。胡克转述洪堡的话,告诉达尔文那条河流名为鄂毕河(Obi)。当时,洪堡他们快速穿过炭疽病肆虐的草原,渡河去往巴尔瑙尔。他兴致勃勃地讲述着自己所知道的西伯利亚植物,尽管距离俄国的考察已经过去了 15 年的时间。胡克在给达尔文的信中写道:“我不认为他在二十分钟内停下来喘过气。”
然后,让胡克震惊的是,洪堡给他看了《宇宙》第一卷的清样。像很多人一样,胡克已经放弃了对《宇宙》的期待,因为洪堡已经写了十多年的时间。胡克马上告知达尔文,因为他知道,达尔文会和自己一样兴奋不已。
两个月后,即 1845 年 4 月底,《宇宙》的第一卷终于在德国出版。漫长的等待是值得的。德文版的《宇宙》迅速成为畅销书,在一开始的几个月内就卖出了两万多本。几星期内,洪堡的出版商就开始加印,几年内就被译成了英语、荷兰语、意大利语、法语、丹麦语、波兰语、瑞典语、西班牙语、俄语和匈牙利语等多个版本——洪堡称这些为“我在德国以外的《宇宙》之子”。
《宇宙》不同于此前任何一本关于自然的书籍。洪堡带着读者们从外太空旅行到地球,然后从星球的表面深入地下核心。他讨论彗星、银河系和太阳系,以及地磁现象、火山和山顶的雪线。他描写人种的迁徙、植物、动物,以及生活在一潭静滞的水中和受到侵蚀的岩石表面的微生物。其他人都在强调人类已经揭开自然最深层的秘密,因而为自然祛魅,洪堡的信念却刚好相反。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极光的五彩光芒“与海面闪耀的波光融而为一”,洪堡试问道,这样的魔力怎么可能消失呢?知识永远不能“杀死想象本身所富有的创造力”;相反,它只会带来更多激动、惊奇和妙不可言的感受。
长达百页的引言是《宇宙》中最重要的部分。洪堡在其中讲述了他的愿景:一个充满生命脉动的世界。洪堡写道:一切事物都是“生命力永无止境之跃动”的一部分;自然是一个“活着的整体”,有机生命体在其中以“精妙的网络纹路”交织在一起。
书的主体由三部分组成:首先是天文;然后是地球,其中包括地磁现象、海洋、地震、气象学和地理学;第三部分则是对植物、动物和人类等有机生命的探索。《宇宙》一书探索的是“造物之博大尺度”,所涵盖、集合的学科远超之前的任何一部著作。与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法国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派代表。)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不同,这本书远远不止是事实与知识的简单集合,因为让洪堡更感兴趣的是其中的关联。他对气候的讨论最能代表其方法取径的不同:当其他学者专注于温度和天气等气象数据时,洪堡率先以大气、245 海洋和陆地之间因复杂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系统来理解气候。在《宇宙》中,他谈到了空气、风、洋流、海拔和陆地植被密度之间“永恒的相互关联”。
《宇宙》的广博程度令其他书籍望尘莫及。更惊人的是,在这部关于宇宙的巨著中,“上帝”这个词竟然一次都没有出现。他的确曾将自然的律动归功于“同一种呼吸——从北极到南极,灌注于岩石、植物、动物甚至人类鼓胀的乳房中”,但这种呼吸来自地球本身,而非由某位神祇策动。对于了解洪堡的人来说,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从来不是一个虔诚的教徒,相反地,他一生都在强调宗教狂热的可怕后果。他曾猛烈地批评南美洲传教士以及普鲁士教会。洪堡从不谈论鬼神,他只反复述说“有机生命的奇妙之网”。(《宇宙》出版后,一所德国教堂认为这是一本亵渎神灵的书。他们在表达震惊之余,还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评论,谴责洪堡“与恶魔作了交易”。)
整个世界都为《宇宙》疯狂。一位评论家写道:“如果知识共和国要改变其宪法、选择一位君主,那么智性的王杖理应交到亚历山大·冯·洪堡的手中。”这部书的受欢迎程度在整个出版史上都具有“划时代”意义。
洪堡的德国出版商从未见过数目如此巨大的订单——甚至连歌德的巨著《浮士德》在出版时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
学生们争相阅读《宇宙》,学者、艺术家和政治家也不例外。奥地利首相梅特涅曾在改革和革命的立场上与洪堡意见相左,现在也放下政治上的偏见,感叹唯有洪堡才能完成如此伟大的作品。诗人和音乐家也仰慕他。法国浪漫主义作曲家埃克托·柏辽兹(Hector Berlioz)称赞洪堡是一位“才华耀眼”的作者。这本书在音乐家当中也拥有众多拥趸。柏辽兹曾听说,一位乐师在演出歌剧期间利用空闲的间隙把《宇宙》“读了又读,努力思索与理解”,浑然不顾乐队其他人还在继续演奏。
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订购了一部《宇宙》,达尔文则公开表示自己正在焦急地等待英文版的面世。在德文版和法文版问世后的几周内,一部未经授权的英文版开始在市面上流传——翻译的文句十分蹩脚,洪堡甚至担心它会“严重损坏”自己在英国的名誉。
在这个版本里,“可怜的《宇宙》”被拆分得七零八落,不堪卒读。
不知情的胡克购买了盗版翻译的《宇宙》,并借给了达尔文。1845 年 9 月,达尔文写信给胡克:“您真的确定可以暂别《宇宙》吗?我太想读到它了!”不到两周时间,他便读完了全书。达尔文对书中“糟糕的英文”感到绝望,但仍为其中“作者对自己想法的精准表达”印象深刻。他急于和胡克见面讨论,还告诉查尔斯·莱尔:这部书的“活力和所涵盖的内容之广泛”令人震惊。他觉得其中一些部分像是对《旅行故事》的简单重复,因此稍稍有些令人失望,但其他部分“绝妙无比”。他还惊喜地发现洪堡引用了自己的《乘小猎犬号环球旅行》。一年后,《宇宙》正式的英文版由约翰·默里公司出版,达尔文争先购入了一本。
虽然《宇宙》大获成功,洪堡仍然十分不安。每一则负面评论都令他介怀。和《旅行故事》面世时一样,英国保守的《书评季刊》对《宇宙》进行了批评。胡克告诉达尔文:“《书评季刊》对《宇宙》的评论让洪堡十分生气。”两年后,即 1847 年,《宇宙》第二卷面世,洪堡恳求出版商如实地告诉他一切反馈。不过,洪堡完全不必担忧。出版商记述道,为了抢到一本《宇宙》,人们“动真格地打了起来”,他们的办公室像被洗劫过一般。有人甚至贿赂出版商,而其他供应商则不惜拦截寄往伦敦和圣彼得堡书商的包裹,然后再把书卖给汉堡和维也纳的如饥似渴的读者。
在第二卷中,洪堡引领读者踏上了一趟从古代文明到当代社会的心灵之旅。没有任何科学著作曾作过类似的尝试,也没有科学家能够如此自如地谈论诗歌、艺术与园林、农业和政治,以及人类的感受与情绪。《宇宙》第二卷“诗意地描述了自然的历史”,绘就了一幅从古希腊和波斯时代直迄近代文学与艺术的壮阔画卷。它也是一部关于科学、发现与探索的历史。书中无所不谈,从亚历山大大帝延伸到阿拉伯世界,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漫谈到伊萨克·牛顿。
如果第一卷考察的是外在世界,那么第二卷则聚焦于内在世界:即外在世界“在内在情感上投射下的印象”。他强调感官的重要性,这既是向 1832 年去世的歌德致敬,也是对他们早年在耶拿友谊的纪念——当时年长的诗人给予了他看待自然的“全新感官”。洪堡这样写道:眼睛是观照世界(Weltanschauung)的器官,我们同时也通过眼睛来阐释、理解和定义世界。在一个想象力被严格排除出科学的时代,洪堡坚持认为,理解自然别无他途。只要抬头仰望天空,便可以理解这一点:璀璨群星“愉悦感官,启迪心灵”,然而与此同时,它们也按照精准的数学定律运行。
《宇宙》的前两卷太受欢迎,四年之内竟然出现了三个不同且相互竞争的英文版本。洪堡告诉自己的德国出版商,英国因《宇宙》而掀起了“纯粹的疯狂”,不同译者之间剑拔弩张。截至 1849 年,一共售出了大约四万部英文版《宇宙》,还不包括销往美国的另外数千部。(洪堡没有从这些译本中获利,因为当时还没有为版权立法。直到 1849 年新的法规生效后,洪堡才得以从于该年之后出版的著作中获得一些收益。)
当时,很少有美国人读过洪堡的著作,而《宇宙》改变了这一切。“洪堡”迅速成为北美洲家喻户晓的名字。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就在最先购得《宇宙》的读者之列。他在日记中写道:“神奇的洪堡,用他广博的胸怀和展开的翅膀,像一支军队一样前行,沿路将所有事物收入囊中。”没有人比洪堡更了解自然。另一位热爱洪堡作品的作家是埃德加·爱伦·坡,他把最后一部重要的作品——发表于 1848 年、长达 130 页的散文诗《尤里卡》(Eureka)——题献给了洪堡。这部长诗本身也是对《宇宙》的直接回应。爱伦·坡试图在《尤里卡》中遍历宇宙中的一切“灵魂和物质”,这与洪堡探讨外在和内在世界的方式相呼应。宇宙,爱伦·坡写道,是“最壮美的诗歌”。同样受到启发的还有沃尔特·惠特曼:在创作著名的《草叶集》(Leaves of Grass)时,他的案头就放着一部《宇宙》。惠特曼甚至专门创作了一首题为《宇宙》的诗,并在著名的《自我之歌》(Song of Myself)中称自己为“一个宇宙”。
洪堡的《宇宙》影响了美国两代科学家、艺术家、作家和诗人。而其中最重要,而且深受《宇宙》启示的,或许是美国最负盛名的自然文学家:亨利·大卫·梭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