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错失之爱 | 收藏 |
四月故事
错失之爱 作者:兹旦内克·斯维拉克

在布拉格,普利谢克先生下了公交车,从敞开的防雨外套胸兜里掏出一张小地图,想看一眼接下来的路怎么走。他穿一条过节时才上身的西裤,裤线熨得笔挺,显然大多时候它是被挂在衣柜里很少穿出门的。普利谢克把裤子皮带稳稳地系在腰部,而不是按照如今大家的习惯松松地搭在胯上。他系一条蓝底金色条纹领带,底端塞进裤子里。显然老先生来自某个边远小镇,他的风格和现代审美格格不入。
这个乡下人左手提一个沉甸甸的塑料袋,他谨慎地环视四周,等到所有的车子驶过,再次环顾左右,眼见两侧的车道绝对安全了,才异常敏捷地跑向马路对面。他循着地图,穿过医院大门,走过栽满栗子树的林荫道,朝14A大楼走去。他暗暗称赞社区医生纳布拉夫尼科博士如此精确地给他标出了目的地,然而当他站到白色房门前时,不觉怔住了,标牌上写着:
医学博士赫什曼•布雷斯克
精神科二科室
纳布拉夫尼科医生说是把他转给一位专家,他们俩是昔日校友,可是目前看来,医生把他送到了精神病院。这下普利谢克被吓住了,他惊恐地四下打量,走廊里来来往往的都是正常人啊,并没有人摇晃着脑袋,也没有人口吐白沫,更没有人穿约束紧身服。于是他抬手敲了敲门。
布雷斯克副主任医师眼睛不离电脑,招呼说:“进来吧,普利谢克先生,我知道是您。等我把手头这点屁文件保存好,就接待您。”医师把那个“屁文件”存入了电脑,这才抬起头,年轻的蓝眼睛注视着来访者。医生的眼睛下方有黑眼圈,那是熬夜阅读或者饮酒作乐造成的。
“您说说看,您怎么了?”
“纳布拉夫尼科医生向您问候,他请求您不要询问在我身上发生的特殊事情。”普利谢克先生说罢,坐到了椅子上,同时小心翼翼地将沉甸甸的塑料袋放到地板上,紧挨椅子。他的动作那么谨慎,仿佛在安放一袋鸡蛋,或者更像是一包一旦剧烈碰撞就会爆炸的炸药。
“我洗耳恭听。”副主任医师在处方笺上工整地写下“普利谢克”几个字。
病人摸了摸外套的胸兜,里边除了指路地图,还有一张纸。
“我罗列了几点。”他开始念起来,“在1936年春天,我们镇子修建下水道。当时我六岁,和其他小伙伴一起钻进了直径为80厘米的排水管,它们被码在事先挖好的水沟旁。每根水管重达200公斤。我不小心脚底一滑,摔进沟里,随后一根管子朝我滚来,它压断了一根木桩,然后在距离我头顶20厘米处的第二根木桩那儿停了下来。当我被拉上地面的时候,客栈店主拉伯塞克说我捡回了一条命。”
“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布雷斯克副主任医师感叹,在处方笺“普利谢克”的名字下方画了一道。
“是的,副主任医师。现在我讲另一个事件:在我十二岁那年,市政厅的墙壁涂抹了新灰泥。在拆除脚手架的过程中,一块重达1.5公斤的尖石块从楼顶坠落下来,扎穿了我右脚上的帆布鞋,砸伤了我的脚背。伤疤至今还在呢,您想看一眼吗?”病人卷起裤腿,打算脱掉右脚上的皮鞋。
“不用了,普利谢克先生。”医生回绝了,然后将处方笺上病人的名字画进了方框里。
“差几厘米就砸到脑袋了,那必死无疑。”普利谢克先生补充,显而易见,他需要医生更多的关切。
精神科医生却淡淡地接嘴道:“那是肯定的。”
这时,响起了一阵短暂的敲门声,身穿蓝白色大褂的年轻护士走进了诊室。
“副主任医师先生,那个割草的乌克兰人非说他放在医院过道里的长筒靴被人偷走了,他说那双靴子是新买的。”
“长筒靴的事不归我管,阿伦卡。”副主任医师推脱。
“还有,5号病房的工程师今天过生日,他提出想喝啤酒。我能同意他就着啤酒服药吗?”
“可以,既然是他生日。不过,给他提供10度酒。”副主任医师笑了起来。
“那好吧。”护士转身欲离开。
“您今天晚上值夜班吗,阿伦卡?”
“是的。”
“那就好。”副主任医师说罢,揉了揉疲倦的双眼,“普利谢克先生,类似的事件您还遭遇过多少起?”
“还有六起呢,医生。”
“那么您挑主要的讲。”
“好的,那我略去1944年,那次我得了严重的白喉,弗鲁豪夫医生在晚上八点给我注射了大管针剂。他说,为了保证疗效,他必须给我使用超大剂量的注射液,不过他也担心我的心脏会经受不住。”
“经受住了。”副主任医师猜。
“医生说,午夜时分是关键。夜半时刻我开始呕吐,如此便脱离了危险,我活了过来。弗鲁豪夫医生合上自己的小药箱时,对我父母说:你们的儿子捡回了一条命。这是我第三次绝处逢生,此后我开始记录这些重大事件。”
楼外面有人在一次次试图发动拖拉机的引擎。
副主任医师站起身,掩上了窗户。
“您要喝点水吗?”他问,拉开了冰箱门。
“您问得正是时候。”普利谢克感激地点了点头。
医生往两个杯子里倒入微气泡矿泉水,水珠澄澈晶莹,然后把矿泉水瓶搁在冰箱上。两人喝完水,病人看了一眼纸条,继续往下说:“然而最大的悲剧……”
诊室里突然响起“噼啪”一声。
副主任医师看到普利谢克被声音吓傻的模样,不觉怔住了。浑身抽搐的普利谢克,向医生投去惊恐的目光。
“是矿泉水瓶,”精神科医生指了指冰箱,“它恢复原样了。”
“对不起,今天我很紧张。”乡下人道歉说,然后把露出来的领带末端掖回裤子里,“最大的悲剧,教授先生,我无法略过不谈,它发生在1947年。那年我十七岁,完成了战前的三角测量,实际上那是一个精巧周密的三角测量点网络,就是把地区划分成三角形,有利于测量员展开工作。在我们的赫鲁特卡小镇之上是普拉尼什山丘,海拔为525米。在工程师沙尔夫的指导下,我们在山丘上用圆木修建起三角测量木塔,而我像一只鹰隼,主要负责攀登。”
“您从多高的地方摔下来了呢?”副主任医师想加快谈话的速度。
“发生了更加不幸的事情呢,医生。那位工程师沙尔夫有一个女儿叫奥特莉卡,我很喜欢她,我认为自己对她比较关照。这位测地学专业的女学生是来见习的。当木塔竣工的时候,工程师沙尔夫在‘林中之屋’酒店举办了一场庆祝会,会上我和奥特莉卡一起跳了舞。庆祝会结束后我们一伙人兴高采烈地沿公路返回赫鲁特卡小镇。那时大约是凌晨一点半。我走在最后,因为我把钱包落在了酒店,里面装了这次兼职挣的所有收入。从山顶出发往下走,当我赶上队伍的时候,所有人横跨在公路上,手挽手站成一排,齐声唱着歌。我从边缘加入他们,边上站着的是奥特莉卡,但是她另一旁的女孩却对我说:‘来,阿道夫,加入到我们中间来吧!’于是我拉起两位姑娘的手,这样一来,奥特莉卡还是处于队伍的最边缘。此时从山上驶来一辆没有马达声的摩托车,我们谁都没有留神,因为它没有打车灯,也听不到任何声音。摩托车手前面载了一个醉酒的男孩,后座上还坐了一个女孩。奥特莉卡被摩托车一下子撞进了壕沟里,当场身亡。医生,您要知道,她是替我死的。因为那一排边上的人应该是我。”
普利谢克先生猛地饮下一大口水。
“那么,你是第四次捡回了性命。”副主任医师说道。
“对啊。然而那个姑娘却丧了命。至今公路边还立着她的墓碑呢。”
话音刚落,外面响起了爆炸声。普利谢克立刻蜷缩起身子,抱住膝盖,将脑袋藏到桌子底下。医生穿白拖鞋的两脚赫然出现在他的眼前。
“普利谢克先生,是拖拉机排气管发出的声响。”副主任医师安抚桌底下那个惊恐地盯着他的人。然后打开窗户,朝外面喊道,“嘿,快点弄好吧,您是来除草的,别吓着人!”
“医生!”外面传来乌克兰口音的捷克语,“我把新靴子放在了你们医院的走廊上,现在不见了。靴子被人偷走啦。”
“您跟大楼管理处说去!”副主任医师给完他建议,随后关上了窗户。
病人在他们对话时镇静下来,回到了自己的座椅上。医生往他的杯子里续了水,询问道:“普利谢克先生,您总在害怕什么,对吧?您总是胆战心惊。这种状态持续多久了?”
“就这一阵子,医生。这段时间对我来说是关键时期。我能继续往下说吗?后边还有几个事件呢。”普利谢克先生在膝盖上抚平他那张写了要点的小纸条。
“您稍等。”医生打断他,“普利谢克先生,不是您一个人遭遇这种事情。人们经常和不幸擦肩而过。如果我处在您的位置,我会很平静。”
乡下人默默地点了点头,然后说:“它们总是发生在4月20日那天。”
说完这句话,他的身体靠向椅背等待着,看专家对此会发表什么高见。显然这是他的方程式中最可怕的未知数,让人束手无策。
“您是想说,您所有的倒霉事都发生在同一天?”赫什曼•布雷斯克疑惑地发问。
“确实如此。”普利谢克先生点头。
“您确定吗?”
“没错。因为我都一一记录了。前两个事件我核查过《市政编年纪事》,那里记载说下水道在1936年4月铺设,编年史官还直接在纪事里提到4月20日一个小男孩差点儿丧命,所以建议老师们以后务必提醒孩子们不要进入危险的建筑工地。”
“您不会说,《市政编年纪事》里还记录了您的布鞋和右脚背被刺穿的事儿吧?”医生笑着接过话头。
“没有直接提布鞋,但是编年史官写到了脚手架于1942年4月20日拆除,感谢奈哈西尔建筑公司的优质石膏材料,让我们的市政厅焕然一新。”病人反驳。
“您都背下来了……”布雷斯克副主任医师忍不住夸他。
“自1970年起,由我接手撰写《市政编年纪事》。我家里就有一本。”
“倒不是说之前您的事没让我感兴趣,但是普利谢克先生,现在您吊起了我的胃口。来杯咖啡怎么样?”医生瞄了一眼腕上的表。
“正合我意。”普利谢克回答。医生拎起电话指示:“阿伦卡,给我送两杯咖啡来。什么?要过一会儿!现在我就要!”
放下话筒时,副主任医师无奈地摇了摇头,蓝色的眼睛望向自己的病人,真诚地请求男性之间的理解。但病人对调侃性的幽默并没有表现出兴趣。
“我能继续吗?”病人问。
“您只须读那些要点,不必展开。”副主任医师叮嘱。
“嗯……”病人吸了一口气,照着那张小纸条读起来。
1954年4月20日,盲肠破裂。
1961年4月20日,拔智齿,针剂过敏。
1980年4月20日,我的汽车在利什纳村被倒下的树砸中。
2008年4月20日,脑出血。
…………
精神科医生揉了揉疲惫的双眼,伸了个懒腰,弄得肩胛骨嘎嘎作响,然后他问:“对此,普利谢克先生,您自己怎么解释呢?为什么这一切恰好都发生在4月20日这一天?”
“因为希特勒在那一天出生,医生。”普利谢克吐出一口气,双脚触碰到了白色塑料袋,里面有什么东西重重地倒下了。他吓了一跳,伸手到下面摸了摸,把袋子里的东西扶正。
早已对各种心理障碍病症了如指掌的布雷斯克副主任医师,之前就想到过,眼前这个人如此谨慎地把袋子轻放到地上,那里面该不会有炸弹吧?然而一打量这个胆怯的乡下人,他立刻否决了自己的想法。而现在,出乎意料地,当“希特勒”登台亮相时,他觉得刚才的怀疑似乎并非毫无根据。
“您不需要去方便一下吗?我们坐了很久了……”他问病人,希望自己有机会对塑料袋的内容一探究竟。
“不需要,谢谢您。”普利谢克婉拒。
护士阿伦卡用托盘端着两杯咖啡进屋,她被太阳光晒黑的两腿上套着一双白线袜。
“医生,5号病房的工程师还要求喝一杯啤酒。”她说。
“绝对不行。”副主任医师回答。
“他今天没有过生日。我查阅了登记簿,他出生在10月。”
“他还说德语吗?”副主任医师问。
“时不时会说。”
护士踩着软木底皮鞋离开诊室之后,布雷斯克副主任医师带着友好的微笑问病人:“普利谢克先生,那您为什么认为,您必须以如此倒霉的方式庆祝希特勒的生日呢?”
“也许存在缘由。我叫阿道夫。”
“哦。”副主任医师为了鼓励病人继续吐露心声,把这个认作令人信服的原因,他顺手把“阿道夫”几个字写进了处方笺里。起作用了。普利谢克先生补充了另一条线索:“我老婆叫艾娃。跟希特勒的情妇艾娃•布劳恩一样,您明白吗?”
“我明白。我知道希特勒还和她结了婚。”
“在他们躲到地堡之后。”普利谢克补充完整,“还有一件事,我会画画。我在《市政编年纪事》中插入了我们赫鲁特卡各种活动的插图。希特勒也会画画。”
“遗憾的是他没有从事这个职业。”布雷斯克干巴巴地说。
“是的。如果他被维也纳艺术学院录取的话,历史也许就改写了。还有一件事也很可惜,那次暗杀没能成功实施,炸弹与他擦肩而过。”病人补充道,他用脚悄悄地将塑料袋往自己座椅下挪了挪。这一举动促使副主任医师转移话题:“在您这个年纪有前列腺问题吗,普利谢克先生?”
“谢天谢地,我没有。”
“您很少上洗手间。咖啡可是利尿的……”
“有时候我半天都不去解手。”普利谢克有点得意,他继续说道,“有一件事就发生在不久前,我在电视上看到了新纳粹——我们家住在18号。”
医生不解地低下了头。
“‘18’就像一个暗码,医生。1相当于A,就是字母表里第一个字母,8相当于H!”病人为他详细介绍元首名字缩写字母的秘密代码。
“嗯,这样来排列?”副主任医师评价。
“是吧!”阿道夫•普利谢克兴奋地把座椅拉近了一些。
“普利谢克先生,您之前从事什么职业呢?您是工科专业的?”医生询问,为了搞清楚他是否具备制作炸弹的能力。
“怎么说呢,医生。我毕业于商学院,毕业后在学校里教过算术,我还在林业局当过公务员,后来在农业合作社任会计,现在我是个职业养蜂人。”
“在战争年代您没有加入过抵抗组织什么的?比如游击队。”
“‘二战’期间我还在上学呢,医生,我是1930年出生的。”
“嗯,也是啊。”医生有些惭愧,事先没有仔细查看患者的病历。他把出生年月写入了处方笺。
“不过,您猜得没错,”普利谢克伸出食指,“我的秘密确实与德国纳粹入侵有关。在我五年级的时候,我们老师创作了一首诗,并在班上征集志愿者,希望有人勇敢地在学校庆祝会上朗诵这首诗。我因为记忆力不错,也喜欢当众表演,所以就自告奋勇举起了手。只是我并不知道,这个活动是为了庆祝希特勒五十一周岁生辰而举办的,医生,我发誓我事先真的不知情。在读完整首诗之后,我已经无法反悔了。我非常害怕。我背下了那首诗,在学校庆祝会上进行了朗诵,就在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播放结束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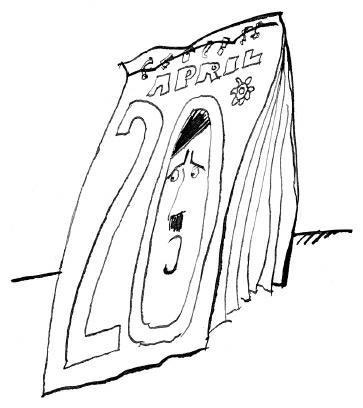
“那又怎么样呢?当时您才十岁,还不谙世事。”医生安慰道。
“不,我已经懂事了。我知道那么做不对。为了不被家人发现,我在家里偷偷地练习。学校的庆祝活动一结束,在回家的路上我的右脚就被尖利的石头扎伤了。”
“所以您认为,您的一切遭遇都是命运对儿时所犯错误的惩罚?”布雷斯克医生看了一眼手表,这位患者占用的时间已经远远超出了预期。
“医生,您愿意听一听那首诗吗?”此刻,老人的两眼紧紧盯着他,貌似一个必须坦露一切的忏悔者,否则将得不到宽恕。
“那您念吧。”医生双臂交叉放在胸前。老人开始背诵当年那首诗:
在赫鲁特卡小镇,
我们敬爱自己的元首。
他一手打击敌人,
一手爱抚儿童。
这就是为什么,
他深得我们爱戴。
“这简直就是个玩笑,普利谢克先生!”布雷斯克医生哈哈大笑起来,“真是个讽刺呀,伙计!”
“没错。我们的老师在1950年担任区文化馆馆长之后,说这首诗是反法西斯讽刺诗。但在当时并不是,医生。这是世人皆知的卖国行为,连十岁的小孩都知道,而我被卷入其中。”
“喏,普利谢克先生,您的生活很顺利,只有一件事例外。如果说所有那些发生在4月20日的危机,都是您在希特勒诞辰庆祝会上表演后的报应,那么您怎么解释第一次呢?那根向您滚去的水管,那可是在很早之前就发生了的。”布雷斯克医生在患者的逻辑当中找出了漏洞。
“我也说不清楚。”患者说。
布雷斯克医生发现,病人已经有些疲惫,于是想转换话题,尽快结束这段问诊。
“普利谢克先生,这么说吧,对希特勒和拿破仑这两个人物的评价始终存在争议。其实,从精神病学上来讲,这是常态。每个人都有神经质的一面,我们同样如此。也许,那两个人因为是没有得到治疗的疯子,所以在死后选择了不安定的灵魂。但您跟他们不一样,普利谢克先生,您应该庆幸您没有把自己视为领袖,只是恰好在希特勒生日那天遭遇各种不测。这很烦人,然而您遇见的麻烦也不会更多了,想想看,在这十年时间里您不也相安无事吗。”
“可我八十岁了,医生,恐怕我在今年会被彻底击垮。”
“您经历了美好的岁月,普利谢克先生。”医生随口敷衍,说话时打了个哈欠。他推开窗户,欲让新鲜的空气进入诊室,却发现太阳已经落到15B大楼的后面。他必须把普利谢克打发走了。于是他递给病人一瓶镇定剂,叮嘱他说,如果病情没有好转的话,再来找他。
然而,对于“美好岁月”的传统表述,患者却另有一番解释:“我知道,医生,正如您所说,为什么人在这把年纪惧怕死亡?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残生寥寥,他还能期待什么呢?可是人总会有他眷恋的东西,比如我的妻子身材娇小,厨房里有些物件够不到,烤蛋糕的模具、漏斗或者装罂粟籽的袋子等放在高处架子上的那些东西,从来都是我取下来递给她的。每天清晨我起得比蜜蜂还早,清理蜂巢外的杂草,那是万万不能用镰刀割的,会对蜜蜂不利,每次在我收拾好之后,蜜蜂才飞出来。我站着休息时会观察充当侦察兵的蜜蜂,它们爬上蜂巢的隔板,感知外界的温度,再给巢内的伙伴们汇报说:还不行呀,外面太冷。我站在那儿,清晨的空气洗涤着我的肺,我暗想:要是我不在了,一切会变成什么样子?大概蜜蜂也会有一阵子不习惯呢。四周会长出高高的荨麻,夏天没有人夸赞它们的蜜,冬天也没有人喂它们糖,那该怎么办?我们这些职业养蜂人都会死光的,医生。我的孙子胜任不了这份工作,他平日里都自顾不暇。也不知他在哪里弄到一本大规模农场经营手册。我告诉他应该先学会编铁丝架子,然后找寻蜂王,他不听——医生!”普利谢克突然想起来什么,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说,“我有一样东西要给你!”说罢弯下腰拿起他的袋子,放到膝盖上,小心翼翼地掏出两瓶蜂蜜来,一瓶色泽透亮,一瓶颜色暗沉。
“这瓶是草地上采的蜜,另一瓶是森林里采的。”说着,把两瓶蜂蜜放到医生办公桌上。
“您让我过意不去!”布雷斯克医生真诚道谢。
几下敲门声之后,护士走进来。
“布雷斯克医生,我想告诉您,已经七点了。还有,5号病房的那位工程师不知从哪儿弄到了三瓶啤酒,可能是从窗外递进来的,在他床底下我发现了两个空酒瓶,第三瓶还剩余一点儿。”
没等布雷斯克医生开口,普利谢克站起来,惊讶地发问:“已经七点了?”
“七点多了。”护士回答。
“那我已经赶不上回程火车了。”普利谢克一脸遗憾。
“没有大巴吗?”护士小姐一边问,一边把用过的咖啡杯收到托盘里。
“倒是可以坐大巴,只是大巴走D1高速公路,您应该知道那里经常出事故吧,我不想冒这个险。”
护士疑惑地瞟了一眼医生,耸耸肩,离开了。
“平时您乘坐公交车吗?”医生问病人。
“平时坐的,但4月20日这天我不坐,医生,那会危及其他乘客的性命。”普利谢克又坐回到椅子上。
布雷斯克医生觉得自己像个白痴,可能是劳累过度和睡眠不足导致的,他对此竟然毫无意识。
“嗯,今天是20号。”他瞟了一眼桌上的台历,又看了看沮丧无助的普利谢克,这位在特殊的日子前来向他寻求帮助、试图消除内心焦虑的病人。
“我哥哥住在布拉格,要是以前的话我可以上他家借宿一晚,但他在前年去世了。”家远在赫鲁特卡小镇的普利谢克愁容满面。
“住我们这儿吧,普利谢克先生。3号病房应该还有空床位。”医生决定后,拿起了电话。普利谢克正在以没带睡衣为由推辞,只听医生在电话里吩咐,“阿伦卡,为普利谢克先生准备床位。”
“不要5号病房!要3号。我强调,绝对不要5号病房!”
放下电话后,医生心满意足地笑了:“您什么都会有的,睡衣、晚餐、茶,还有优质安眠药,不用担心,您会睡得香甜安稳。”
布雷斯克副主任医师因为妥善安排了这件事,满心欢喜。他往冰箱里瞧一眼,看冰箱里是否还冷藏有灰罗兰葡萄酒,因为他突然很想喝一杯葡萄酒,简直无法抑制。
护士阿伦卡将普利谢克先生带到3号病房,递给他药丸和一杯水,等着看他把药服下去。然而病人并不傻,他不想在昏睡中过完白天,他需要清醒和警觉。他将药丸夹在手指缝之间,然后假装用手掌把药丸扔入口中。妻子强迫他服用那些安眠药时,他常常这么干。出乎意料,护士虽已看穿他的把戏,却没有理会。
3号病房里住了两位男士。普利谢克先生先向年长的那一位做了自我介绍,那位先生看起来跟他是同龄人。
“您不必自我介绍,我们在办公楼里见过面,”那位先生带着温和的笑容说,“我是二处的斯鲁内奇克呀,人们称我‘小太阳’!”
“我想不起来了。”普利谢克说。那位先生又问他:“您觉得我们这个乡下怎么样?”
“这里很美。”这位新病友尴尬地回应,转身朝第二位病人走去。那人的床头写着科鲁迪•约瑟夫,他的整条右腿打了石膏,他正埋头在石膏上用圆珠笔画各种蛇。他连头都没抬,只问道:“谜语:哪条蛇是米列娜?”
“我不知道。”普利谢克先生老实承认。
“明明是这条呀!看不出来吗?米列娜就是这条虎纹大蟒!”
“伙计,”老先生冲他喊,“请您把这几只鹅赶走,省得它们没完没了地啄我。”普利谢克先生明白了他的请求,便冲着窗户吆喝:“去去去,坏蛋们!”
“就得这么对付它们!”“小太阳”对他满脸赞赏。
阿道夫•普利谢克换上了医院的睡衣,躺到了床上。门上方的时钟显示差两分钟十点。
护士阿伦卡走进来,问道:“谁还需要什么吗?一切都好吧?那我们就祷告吧,先生们,祝各位晚安。”
说罢,她熄了灯,只有时钟下昏暗的备用灯冲淡了3号病房里的黑暗。
“这些都是她养的鹅,”“小太阳”悄声嘟囔,“但她什么也不管。我和她说:阿伦卡,你的那些鹅早晚得被汽车轧死。不过说了也白说。”
然后,一片静默。普利谢克先生注视着电子钟巨大的指针,指针切割着他艰难一天的最后时刻。他想起刚才用老年手机给妻子打电话时,妻子说的话:“至少你在安全的地方,孩子他爸。你在医生的照看下,什么意外都不会发生了。”
夜里十一点四十分,门被悄悄地推开了,走廊天花板上的灯盏像是照明弹那般映亮了3号病房,“阿道夫•希特勒”走了进来。他更苍老了,八字胡和刘海儿都已花白,跟他那张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将希特勒少年营的孩子送上战场的照片一样。他棕色睡衣的裤腿塞在锃亮崭新的靴子里。然而那不是皮靴,而是橡胶雨靴。

普利谢克先生从床上坐起来,摇了摇头,想确定自己不是在梦里。
“先生们!”“元首”啪地并拢脚跟,举起右手。
“滚开,傻瓜,要不我就叫护士了!”科鲁迪•约瑟夫在床上喊,把自己那条缠着画满了毒蛇的石膏绷带的腿指向“阿道夫•希特勒”,像是炮筒似的。
“你尽管去叫啊,凯特尔[威廉•凯特尔(1882—1946),曾任德军最高统帅部总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军资历比较老的指挥官之一,战后在纽伦堡审讯中被判绞刑处死。],然而护士不会听到的,因为她不在,每当布雷斯克医生值夜班的时候都是这样。”“希特勒”呵呵笑起来。
“工程师先生,即便在这个村子里也要守规矩,”病人“小太阳”悄声回应,“在夜里病房之间是不准串门的。您应该待在5号病房里,请您回去吧。”
“隆美尔[埃尔温•约翰内斯•尤根•隆美尔,纳粹德国的陆军元帅,著名的军事家、战术家、理论家,绰号“沙漠之狐”“帝国之鹰”。1944年10月14日在希特勒的逼迫之下服毒自尽,时年52岁。]!你给我站起来!”“元首”迈着大步凶狠地冲了过去。当“小太阳”先生站直之后,“元首”的双手掐住他的脖子,“隆美尔,你在非洲一败涂地,完全不像沙漠之狐,而是像老鼠,你还参与了对我的暗杀行动,你居然跟我谈什么规矩!”
普利谢克先生觉得,那位二处的老先生眼珠子都要凸出来了。他穿着后背开口的医院病服站到了病床边,大声喊道:“4月20日。诗歌。”
“元首”惊奇地循声望过来,发现是个名不见经传之人,便松开了紧箍的双手。
“你来自哪里?”“元首”问道,冲他的床走过来。
普利谢克先生吸了一口气,朗诵道:
在赫鲁特卡小镇,
我们敬爱自己的元首。
他一手打击敌人,
一手爱抚儿童。
这就是为什么,
他深得我们爱戴。
很明显,“元首”被感动了。他微微颔首,双手搭在普利谢克的肩膀上说:“你知道今天我过生日,是吗?”
“是的。”普利谢克先生回答。
“你们都看到了吧?”他不满地转向自己的两位将军,“凯特尔和隆美尔,你们俩看到没有?一个捷克的无名小辈都知道我今天过生日,而你们在我的大本营却漠然无视。”
“你要是不马上回到床上,我明天就去报告医生,他们会把你绑起来,他妈的纳粹。”科鲁迪•约瑟夫说。
“元首”被激怒了。
“凯特尔,你这条狡猾的毒蛇,你既不想去法国也不想去俄罗斯,你居然想威胁我?”“元首”说着拿起普利谢克的枕头,而科鲁迪•约瑟夫立刻按下了床头的按钮。穿着棕色睡衣的“希特勒”走到他床头,威胁地重复道:“悄悄去死吧!悄悄地死……”
这时候阿道夫•普利谢克瞄了一眼电子钟,发现他度过了自己生命中又一个4月20日。午夜已经过了一分钟。当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了危险,他离开3号病房朝护士站走去。但是屋子里空无一人,只有蜂鸣器徒劳地发出嗡嗡的声响,于是他咣咣地砸起医生值班房间的门。过了一会儿,蓝眼睛的副主任医师布雷斯克半打开门,普利谢克先生的第一个念头是,那双蓝眼睛下面的黑眼圈并不是因为读了太多的书,而是因为护士阿伦卡小姐,他在布雷斯克背后瞥见了她。然后,他快速汇报了3号病房里的情况。
副主任医师布雷斯克系好了白大褂的最后一粒扣子,请求普利谢克先生协助他处理那个危险的病人。简单商量之后,普利谢克先生拉开了门,站在大本营的门槛边宣布说:“元首,保卢斯将军给您打电话来了!”
“保卢斯!那个冻死的投降分子吗?我不接!”“希特勒”不再用枕头捂住科鲁迪•约瑟夫的脑袋,而是穿着偷来的橡胶雨靴径直冲出房门奔向走廊,一头扑进布雷斯克副教授手里的紧身衣中。
“普利谢克先生,您再次转危为安了。”早晨,两人告别的时候,副主任医师说道,“请代我问候纳布拉夫尼科医生,如果明年您依然有忧虑的话,请过来吧!”
“谢谢。”来自赫鲁特卡的病人回答说。只是不清楚他说的是“谢谢,我会来”,还是“谢谢了,我不想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