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错失之爱 | 收藏 |
在火车上
错失之爱 作者:兹旦内克·斯维拉克

下午的列车在冬日白茫茫的原野上飞驰,山坡顶上依稀挂着一轮小而清冷的太阳。车厢里乘客寥寥无几,所以我能享受到双腿恣意伸展的那种舒适。等火车到了贝隆站,新上来一拨乘客,他们在过道上使劲跺脚,抖落掉沾在皮靴上的积雪。
我收回伸在座位底下的双脚,旁边走来一位面带微笑的越南姑娘,几朵雪花贴在她黑色的头发上,她身后是一位少妇,领着一个小男孩。越南姑娘坐到窗边的座位上,以便能看清楚报纸上的纵横字谜。那个少妇解开大衣,精疲力竭似的坐到我对面的座位上,她脑袋上的貂皮帽一摘下,一位美丽的金发女郎便呈现在眼前,只是神情倦怠。也许她的金发是染的,如今所有女人,不管什么年龄,不知何故都热衷于把自己的头发染成别的颜色。小男孩跑到窗口,发现玻璃窗外的景色了无趣味,一片荒凉单调的雪原而已,便回到母亲身边。年轻的母亲一只手从提包里摸出手机,另一只手摘下小男孩脑袋上的帽子,手指飞快地抚了一下他的头发。小男孩跪到人造革座椅上,背对我,脑袋探过椅背打量起后面的车厢。
“妈妈,我认识这里写的字哪。”他说。
“嗯,好的。”那位母亲心不在焉地回答,亮闪闪的指甲在手机键上灵活地跳跃,她在写短信,很急迫的样子。眼睛下方的黑眼圈加深了她的焦虑。专注让她的双唇紧闭,仿佛没长嘴唇一般。
“夫人,我在学习捷克语。”越南姑娘跟她搭话,脸上的笑容永不凋谢。
“好啊。很有必要。”捷克少妇应答,并没有抬头看一眼,她发出了那条短信。
“吸——烟,”小男孩在念,“妈妈,吸烟!”
“没错。”母亲表扬了他,把手机放回提包的拉链下面,准备随时接收消息。
“我通过填字谜学习捷克语,因为这个方法很适合我。夫人,我能请教您一个问题吗?”越南姑娘手握圆珠笔请求。
“但愿我知道。”金发少妇耸了耸肩膀。
“妈妈,禁止吸烟!”小读者得意扬扬地宣布。
“是的,史捷潘,你认得不错,但现在不要打扰别人。”
“Paznehtník,这个词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亚洲女孩读了一遍填字谜面。
“这个我也不知道。”欧洲妈妈摇了摇金发脑袋,眼睛转向我,向我求救。
我这个填字谜老手,自然义不容辞。
“您写上‘爵床草’。”我说。
“爵床草?”外国女孩逐字填入方块中,“这个词我得记住。”
“用不着记,”我说,“这您用不上。”
“还有风衣,我也不会填。”那双美丽的眼睛盯着我。
“风衣就是滑雪衫。”捷克少妇连忙插话。
“滑雪?是滑雪袋吗?”美丽的黑眼睛一片茫然。
“滑雪穿的,是夹克,曾经很时兴。”
“您填上滑雪衣,”我提示说,“只是这个词您也不必记,这种滑雪衫只在填字游戏里才派得上用场,平时用不上。”
“在其他场合不穿吗?”
“只在填字游戏里。”我重申一遍。
女孩惊愕地摇了摇黑发脑袋,头发上的几片雪花已经融化,她用工整的书写体把“滑雪衣”填入字谜方格。
“请——乘——坐——火——车——旅——行……火——车!妈妈,这里写了,让我们乘坐火车,我们在乘火车旅行,对吧?”史捷潘认出了字母表里的新朋友,满心欢喜。
“对啊,你都认识了,进步很大,小读者。”母亲打了个哈欠,揉了揉疲惫的双眼。
“先生,您是否知道,‘药房实习生’怎么说?”越南姑娘又转向我,露出她健康的牙齿。
“‘药房实习生’叫‘提罗’,可是姑娘,您这样是学不会捷克语的,”我说,“因为提罗仅在填字游戏里出现,在生活中您不会遇见的。”
“它在其他场合不存在吗?提罗是死的吗?”
“完全不存在。”我决绝地回答,省得她没完没了。此时困意袭来,我想打个瞌睡。但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我睡意顿消。
“我——有……我有,大……大鸟。”小男孩又在逐字拼读,“妈妈!我有一只大鸟!”
“好吧,史捷潘,别闹了。”母亲把手伸进提包里取出手机,手机发出了收到短信的提示音。
惊恐之余,我睁开眼睛搜寻史捷潘看到的文字,我的老年性远视让我一眼击中对面车厢胶木板壁上的那行字,千真万确,黑炭笔大写字体:我有一个大鸡巴,只给你,请拨打电话603……恕我在此不列出完整的手机号码,省得您忍不住也去尝试。但它确实写在墙上。
想象可怜的母亲读罢收到的短信后,该如何回应那个小男孩,使我不觉燥热起来,于是我引导他去读另一条标语。
“看这里,史捷潘,看你认得不?”我用食指指向车窗下端,那里写着:火车行驶时请勿探身窗外。
然而小男孩并不好糊弄,他的两只眼睛直直盯着那条“鸟”标语。
“妈妈,妈妈,这里写了,您看,让我们打电话。”小男孩冲母亲的耳朵迫切地请求。
“往哪里打电话?”疲惫的少妇放回手机,显然接收到的消息让她伤神。她浑然不觉有更棘手的事亟待她解决。
“打这个电话吧。咱们家阁楼上有一只爷爷留下的大鸟笼子。”史捷潘恳求。
“行了,史捷潘,安静点儿,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母亲让儿子坐到自己身边。然而小男孩从座位上出溜下去,站到车厢地板上,牵住母亲的手,把她领到那条标语跟前。
两人回来后,坐定,母亲深深叹了口气。
“那你觉得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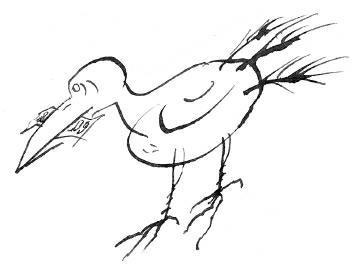
“爷爷说了,那是一只大鸟笼。所以你给他打电话啊,说我们要那只大鸟。”
少妇飞快地扫了我一眼,眼神里饱含谴责,显然在说:瞧您都干了什么?就好像我跟那些在墙壁和火车上涂鸦的下流鬼是一伙的。她伸出手捋了捋小男孩前额的头发,思索片刻,然后说:“史捷潘,那个广告……嗯,贴在这里很长时间了,那只鸟早就被卖掉了,你明白吗?早有人打过电话,买走了那只鸟。”
“没准没有人打呢。没准那是一只大鹦鹉呢,就是爷爷养过的那种。没准就是一只鹦鹉,妈妈!”小男孩不依不饶。
“鹦鹉叫‘阿拉’,这我记得。”越南姑娘自作聪明地搭话。
少妇没有搭理她。
列车的车轮沿着冰封的轨道咔嚓行驶,在咔嚓的节奏声中混合了机车高昂的轰鸣,仿佛有一只狗在怒吼。小男孩呜呜哭了起来。
越南姑娘收起了笑容,温柔地摸摸男孩的头发。
“不要哭。他为什么哭了?”她问。
少妇把眼睛望向天花板,仿佛在说:别添乱了。然后回答说:“他想要买一只鸟。”
“小鸟吗?那给他买啊。”
“是大鸟。我们家阁楼上有一只大鸟笼子。”男孩抽泣着说。
“你为什么不给他买呢?”外国女孩替小男孩求情,“价格太贵吗?”
“已经卖掉了,那个人。”母亲回答。
“没有卖掉!没准还在呢!妈妈,你给他打电话问一下嘛。”说着,小男孩从母亲的手提包里掏出手机,塞到她的掌心里。
“好吧。”少妇叹口气,又瞥了我一眼,俨然我是整个事件的罪魁祸首。然后用手指头摁下写在墙上的那组数字。微弱的蜂鸣声之后,少妇悄悄摁断了通话,这没有逃过我的眼睛。她在等待,好似在等鸟主人接听电话。小男孩、越南姑娘和我都盯着她的嘴唇。
“您好,我打电话想买那只鸟,您打了广告。”
她煞有介事地停顿,一个劲儿点头,然后才说:“哦,晚了。我也这么想的。当然,很有兴趣。好吧,那也没办法了。非常感谢您。”母亲摁下按钮,结束了通话。
“已经卖掉了。”她疲乏地嘘了口气。
“那位先生已经没有鸟了。”越南姑娘用纤细的手指抹去小男孩脸颊上的泪珠。
母亲将手机放回提包里,闭上眼睛,脑袋靠在座椅背上。
“白痴。尽给我添乱。”她悄声自语。
窗外,天已黑下来。
“我想有一只鸟。爷爷养过的,可惜后来死了。”小男孩吸了下鼻子。
“把鼻涕擤了。”母亲递给他一块手绢。史捷潘擤完鼻涕,躺到座椅上蜷缩起来,脑袋远离那个没有为他实现愿望的女人。
“既然你没有买到那只鸟,我给你讲一个大黑鸟的故事吧。”我听到从窗口传来柔和的声音,“这样的话,你就不会伤心了。在巴赫丹[位于越南胡志明市。]河畔有一个地方,那里一年四季烈日当空。人们在水稻田里干活,汗流浃背。农人们出汗,水牛也出汗,大家都期盼傍晚早点来临,盼着那只大黑鸟飞来。天热得像蒸笼,没有一丝风吹拂。但是,每当黑鸟飞近时,树上的树叶就会轻轻地舞动,地上的小草也开心地摇摆,于是每个人都知道,鸟正往这里飞呢,很快就要到了。当黑鸟在巴赫丹河畔停下来,张开它巨大的翅膀,罩住整个田野和村庄,暑热就止住了,大家也停下了手里的活儿。在大鸟黑色的羽毛间有许多小孔隙,那是一颗颗星星。你知道吗?有时候出现一个大孔,那便是月亮。刚才,黑鸟也飞到我们这里来了,捷克语把它称作‘夜’。在填字游戏中是这样写的:白天的悖反。你喜欢我们越南的童话故事吗?”外国女孩轻抚小男孩的头发。
小史捷潘没有回应,因为他睡着了。
在小男孩听童话故事的时候,母亲为他脱下了脚上的小鞋,此刻她用自己的手掌心温暖着儿子的双脚。两个女人的眼睛短暂相遇了。我本想说点什么,转念一想,我还是闭嘴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