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生日的女孩 | 收藏 |
过生日的女孩
过生日的女孩 作者:村上春树

二十岁生日那天,她同平时一样上班做服务生。礼拜五一直是她当班。本来那个礼拜五是可以不去上班的,她已经同另外一个打工的女孩谈妥了对调班次。照说也是,一边要忍受着厨师劈头怒吼,一边要端着意式南瓜团子意式炸海鲜往餐桌上送,这不能说是二十岁生日的正当过法。可是讲好了跟自己换班的女孩子却感冒恶化,卧床不起了。说是发烧到将近四十度,还腹泻不止,根本无法干活。于是她仓促上阵,赶着上班去了。
“你不必介意啦。”她对着电话说道,倒像是她在宽慰表达歉意的对方,“又不是说因为是二十岁生日就会有什么特殊之处嘛。”
事实上,她也并没怎么感到扫兴。几天前,和本该一道共度生日之夜的男朋友大吵了一场,也是理由之一。那是从高中时代就交往至今的对象,吵架的起因也渺不足道。可不承想竟越吵越凶,你有恶言我有泼语,激烈的争吵持续了一阵子之后,便觉得此前维系着二人的那条纽带受到了致命损伤。她心里有一样东西变得像石头一般坚硬,死掉了。吵架过后,他再没打过电话来,而她也无意打过去。
她打工的地方是六本木一家名气不大不小的意大利餐馆,从六十年代中期开业至今。提供的菜式虽无领先潮流的锐气,可口味本身却极其纯正,百吃不厌。店内的氛围也毫无咄咄逼人之处,倒有着一种安详的从容。比起年轻客人来,上了年纪的常客居多,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其中也包含著名的演员与作家。
两位男服务生是正式职工,每周工作六天。她和另外一位勤工俭学的女孩子轮流各做三天。此外还有大堂经理一人。收银处坐着一个精瘦的中年女子,据说打开业以来便一直坐在那里。就像狄更斯的《小杜丽》里出场的那个阴郁的阿婆一样,她极少从那个位子上站起身来。从顾客手上收取费用,电话铃一响便拿起听筒,除此之外不做任何工作。如无必要,则口也不开。永远穿着黑色连衣裙。整个氛围又冷又硬,倘若掉进大海里浮在海面上,只怕轮船撞上去就会沉入海底。


大堂经理大概已过四十五岁。人高肩宽,年轻时恐怕是体育健将的体形,可如今腹部与下颚长起了赘肉,又短又硬的头发也在顶部变得稀薄。渐渐老去的独身男子身上难免的某种气味,悄然飘游在他周围。是那种类似将止咳糖与报纸一起在抽屉里放上一段时间之后的气味。她那位独身的叔父身上也散发出相似的气味。
大堂经理永远身穿一套黑西服,白衬衣上系着蝶形领结。不是那种按扣式的,而是当真自己动手系的。就算不看镜子也能灵巧自如地系好,是他引以为豪的几件事之一。他的工作是核对顾客的出入,把订座状况铭刻脑中,牢记常客们的姓名,当他们来用餐时好语相迎、笑脸寒暄,客人抱怨时则诚恳地侧耳倾听,对于有关葡萄酒的专门性提问尽可能详细地予以解答,监督男女服务生们的工作情况。他日复一日游刃有余地完成这些工作。再加上另外一项:往老板的房间里送晚餐。
“老板在餐馆所在的大楼六层有一套自己的房间。不知道算住宅还是算事务所。”她说。
我同她由于偶然的机缘,谈起了各自的二十岁生日。关于那是怎样的一天。人大抵都清晰地记得自己二十岁生日的情形。她迎来自己的二十岁生日已经是十多年前的往事了。
“不过吧,老板不知道什么缘故,从来都没有在店里露过面。能见到老板的,就只有大堂经理一个人。往那儿送餐,也是他的工作。所以我们这些打下手的员工,还没有一个人见过老板长什么模样呢。”
“就是说,这位老板每天都从自家店里叫外卖喽?”
“对啦。”她答道,“每天晚上八点钟,经理都会把饭菜送到老板的房间里去。对店里来说,这是最最忙碌的时刻,而这种时候经理却不在店里,的确教人犯难。不过这是很久以来的惯例啦,没办法。菜肴放在宾馆客房送餐用的那种小推车上,经理毕恭毕敬地推着它乘上电梯,大约十五分钟之后再空着两手回到店里来。过了一个小时经理再次上楼去,把放着空盘子空杯子的小推车撤下来。雷打不动,每天重复。第一次看到这番情形时,我感到奇怪极了。简直就像宗教仪式一样,是不是?不过渐渐地也就习以为常,不觉得有什么了。”

老板吃的永远是鸡。烹饪的方法与搭配的蔬菜因日而异,多少有些变化,但主菜必定是鸡。年轻的厨师偷偷告诉她:他曾经试过连续一个礼拜都上烤鸡,老板却没有一句怨言。然而作为厨师,自然不免会想着要翻新花样,历任大厨各显神通,千方百计挑战一切鸡肉菜式,还制作了匠心独具的调味汁。鸡肉供货商也尝试了一家又一家。然而这种种努力也仿佛是向虚无的空穴中投进一块块小石头,没有任何反应回馈。于是每位大厨最后都打了退堂鼓,改为每天烹制普普通通的鸡肉菜式送上去。必须是鸡不可,这就是对大厨们所要所求的全部。
她的二十岁生日是十一月十七号那天,工作一如平日,照常开始了。过了正午,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到黄昏时分变成了大雨。五点钟,员工们被召集起来,经理对当日特供菜品做说明。男女服务生必须一字一句牢记在心,不得有误,无小抄夹带。米兰风味小牛肉,沙丁鱼卷心菜意面,栗子慕斯。有时经理还会扮演客人提问,对此员工一定要有问必答。然后就是员工餐上桌了,所谓的“管饭”。必须避免出现在餐桌旁向客人说明菜品时肚子咕咕作响的事态。

餐馆开门时间是六点,因为大雨倾盆的缘故,与平素相比,客人上门要晚一些。有几个预约取消了。女性讨厌连衣裙被雨水淋湿。大堂经理怏怏不悦地将嘴唇抿成一条直线,男服务生们百无聊赖,不是擦擦小盐瓶,就是跟厨师闲聊烹调,借以打发时间。她一面留心观察着只有一桌客人的大堂,一面倾耳细听天花板上的扬声器里流淌出来的羽管键琴曲。店堂里飘荡着深秋雨水浓浓的气味。
经理的情况变得不对是在七点半钟过后。他虚弱无力、摇摇晃晃地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捂着肚子半晌不动,简直就像挨了枪子儿一般,额头上冒出了油汗。看来还是上医院为好啊,他粗声说道。经理健康失衡,是一件极为罕见的事儿。来到这家餐馆工作已逾十载,他连一次假都不曾请过。没生过一次病,没受过一次伤。这也是他引以为豪的事情之一。然而因痛苦扭曲了的面孔,表明他状况相当糟糕。
她撑了一把伞走到店外,拦下一辆出租车。一个男服务生架着经理坐进车厢,送他去了附近的医院。上车之前,经理用嘶哑的嗓音对她说:“等到了八点钟,你帮我把晚餐送到604号房间里去。只要按下门铃,说一声‘晚餐送来了’就行啦。”
“604号房间,对吧?”她问。

“八点整,准时。”经理叮嘱道,说完又皱起了脸。出租车门关闭,他离开了。
经理走了之后,大雨仍旧势头不减,客人也稀稀拉拉,没几个上门。餐桌一直只坐满了一两桌。哪怕少了经理和一个男服务生,也不成问题。要说幸运倒也算是幸运。毕竟上上下下撸起袖子齐上阵都忙不过来的情形也不算稀罕。
到了八点钟,老板的晚膳准备停当后,她推着小推车进入电梯,上了六楼。拔去了软木塞的小瓶红葡萄酒、咖啡壶、鸡肉主菜、配衬的热蔬菜、添配了黄油的面包卷,一成不变的那一套。狭窄的电梯内弥漫着肉类菜肴那种分量实足的香味,还混杂有雨水的气息。好像有人手拿淋湿的雨伞乘过电梯,脚下地板上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水洼。
她沿着走廊向前,在写有604的门前停下,在脑海里再次确认听来的号码:604。然后清了清嗓子,按下了安在门边的铃。
没有回应。约莫二十秒钟,她站在门前不动。正在想是否要再按一次门铃时,门突然从内侧打开,出现了一个瘦小的老人。身高大概要比她矮至少十公分。身穿深色西服,系着领带。白衬衣配颜色好似枯叶的领带。一切都干干净净,没有一丝褶皱,白发梳理得整整齐齐,看上去仿佛马上就要去出席晚会一般。额头上刻着好几道深深的皱纹,让人联想起航空照片里拍到的深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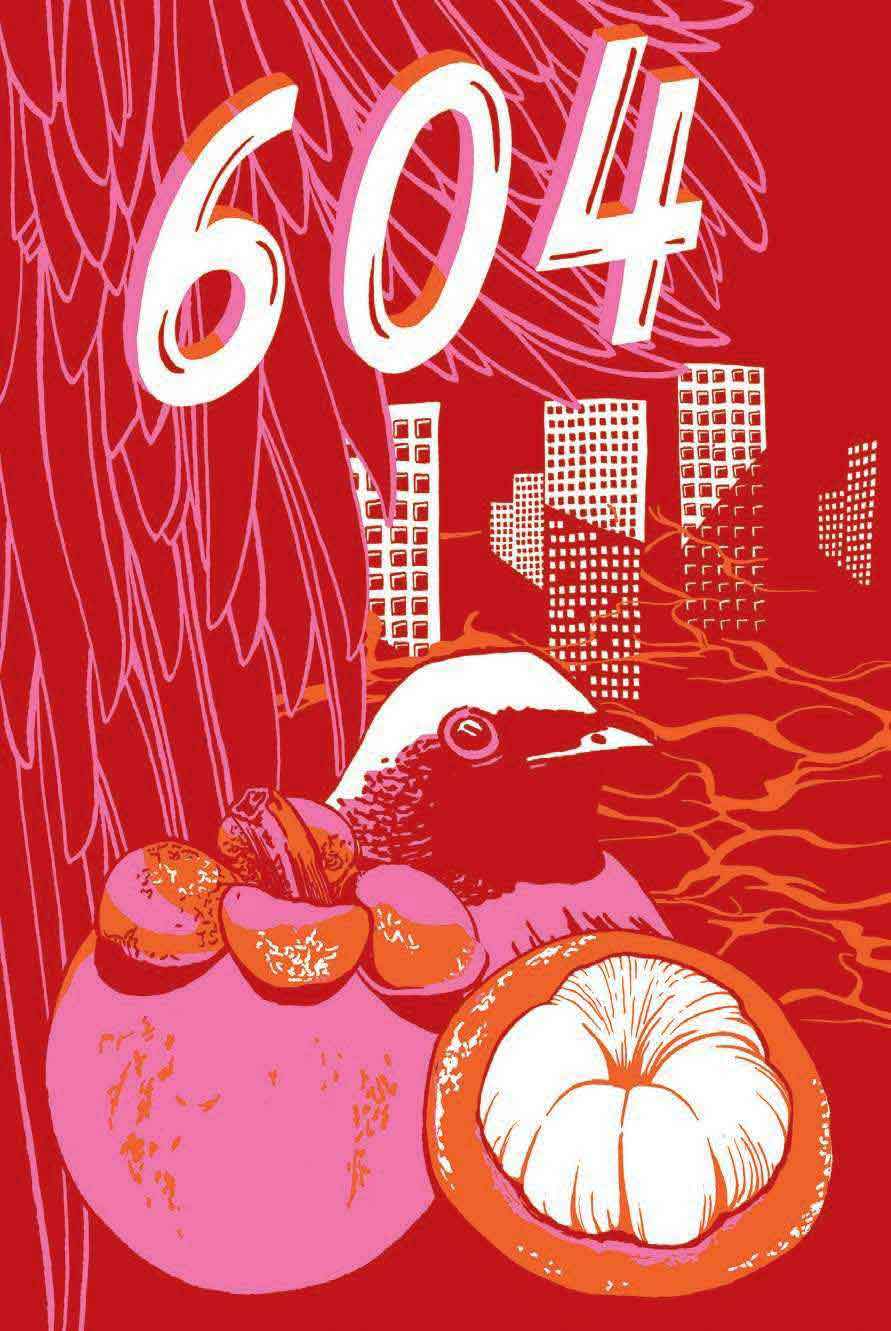
“给您送晚餐来啦。”她声音嘶哑地说道,然后又轻轻地清了清嗓子。一紧张,她就会声音嘶哑。
“晚餐?”
“对。经理突然身体不适,改由我来给您送餐。”
“原来如此。”老人说道,一只手犹自抓着门把手,仿佛说给自己听似的,“哦,身体不适?”
“对。突然肚子痛,于是就去医院了。弄不好是阑尾炎——他自己说。”
“还真不妙啊。”老人说道,随后用手指轻轻地抹了一下额头的皱纹。“那可不行。”
她清了清嗓子。“请问,我可以把饭菜送进去吗?”
“嗯,当然。”老人说道,“当然。我无所谓啦。如果你希望这样的话。”
如果我希望这样的话?她心想。这话说得好奇怪。你说,我到底希望什么呀?
老人将门大大打开,她推着小推车走进房间。地板上铺着灰色短绒地毯,可以不用脱鞋直接走进深处去。与其说是住房,未若说是当工作室在使用,房门背后就是宽敞的书斋。从窗口可以看见灯火通明的东京塔就近在眼前。窗前有一张很大的写字台,写字台旁有一套小巧的沙发。老人指了指沙发前的茶几。是一个细长状、合成树脂贴面的矮茶几。她把晚餐摆列在了茶几上,配上布质白餐巾和刀叉餐具。咖啡壶与咖啡杯,葡萄酒与葡萄酒杯,面包与黄油,然后是一盘佐以热蔬菜的烤鸡。
“一小时之后我再上来。请您和往常一样,把餐具放在走廊里,好吗?”她说。
老人饶有兴味地扫视了一圈摆好的肴馔,这才仿佛陡然想起来似的答道:“哦,那当然。我会放到走廊里的。摆在小推车上。一小时之后。如果你希望那样的话。”
对,这就是我希望的,眼下。她在心里想道。“您还有什么别的事吗?”
“没啦。再没有别的事啦。”老人稍作考虑后答道。他穿着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鞋。小尺码的,非常潇洒的皮鞋。这是个讲究衣着的人,她心想。对于这把年纪来说,身姿也很挺拔。
“那我就告辞啦。”


“不,你等一下。”老人说道。
“好的。请问什么事?”
“年轻的女士,能不能占用你五分钟时间?”老人说道,“想跟你说几句话。”
年轻的女士?听到如此称呼,她不觉红了脸。
“好的。嗯,我想大概不要紧。那个,我是说,五分钟的话。”
我不就是被这个人计时付薪雇来打工的吗?既然如此何来什么占用不占用呢。而且这老人也不像是会干坏事的人。
“顺便问一问,你多大年龄?”
老人站在写字台旁,抱着双臂,笔直地盯着她的眼睛,问道。
“二十岁了。”她说。
“二十岁了。”老人重复道,然后仿佛窥视某个缝隙似的眯起了眼睛。
“你用了个‘了’字,那就是说,为时并不久的意思喽?”
“嗯。不如说,是刚刚才满。”接着,稍许迟疑之后又加上一句,“其实,今天就是我的生日。”
“原来如此。”老人恍然大悟似的摸了摸下巴,“哎呀,是吗?原来如此。今天这个日子,就是你的二十岁生日啊。”
她默默地点了点头。
“从现在算起正好二十年前的今天,你降生到了这个世上。”
“对。是这么回事儿。”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老人说,“这可太好了。那,恭喜你。”
“谢谢您。”她说。仔细一想,今天一整天,这还是头一回有人祝福自己生日快乐呢。下班回到家,倒或许会从电话留言里听到来自大分县老家父母亲的祝福。
“可喜可贺。”老人重复道,“这太美妙啦。怎么样,年轻的女士,用红葡萄酒举杯庆祝一下?”
“谢谢您。不过,我现在正在上班呢。”
“就喝一口的话,不要紧吧?是我说可以的,谁也不会责怪你。仅仅表示一下祝福之意就行。”
老人取下红葡萄酒的软木塞,为她往葡萄酒杯里斟了少许,再从一个玻璃门小柜子里拿出一个毫无特别之处的小玻璃杯,为自己斟了一杯酒。

“生日快乐。”老人说,“年轻的女士,愿你的人生硕果累累,没有任何东西将阴影投射其上。”
两人碰了杯。
没有任何东西将阴影投射其上。她在脑海里重复着老人的祝词。为什么这个人说话方式如此与众不同呢?
“二十岁生日,人生之中只有一次。而且它至为珍贵、无可替代哦,年轻的女士。”
“嗯。”她回应道。然后小心翼翼地只喝了一口葡萄酒。
“而且你还在这么一个特别的日子里,专门来到这里为我送餐。宛如好心的精灵一般。”
“可是,我只不过是奉命行事而已。”
“即便如此哦。”老人说,然后轻轻地摇了几下头,“即便如此哦,美丽的年轻女士。”
老人在写字台前的皮椅上坐了下来,并叫她坐在沙发上。她端着葡萄酒杯在沙发上浅浅地坐下,并拢双膝,扯了扯裙子下摆,然后又清了清嗓子。她看见雨点在玻璃窗外描画出线条。房间内不可思议地寂静。
“今天刚巧正是你二十岁生日,加之你还为我送来了温暖精致的晚餐。”老人仿佛再度确认般地说道,随后叮地一下把酒杯放在了写字台上,“这也是某种命运吧。你不这么看吗?”


她沉吟不决地点了点头。
“于是乎,嘿。”老人说着,手放在了枯叶色领带的打结处,“我呢,年轻的女士,想送你一样生日礼物。在二十岁生日这样特殊的日子里,必须要有特殊的纪念品,无论如何。”
她慌忙摇头:“求您啦,请您不必介意这种事情。我只是奉了上司的指令来送了一次晚餐而已。”
老人掌心向前举起了双手:“不对不对,是你不必介意。说是礼物,但并不是有形的东西。不是那种有价的东西。也就是说呢,”他说着,将两手搁在了写字台上,然后缓缓地长吁了一口气,“就是说,我个人呢,是想为你实现一个你的心愿啦,可爱的精灵小姐。我想为你实现你的一个心愿。什么都行。什么样的心愿都没问题。当然啦,如果你有心愿的话。”
“心愿?”她声音干涩地说。
“就是‘如果能这样就好了’那种心愿呀。年轻的女士,就是你心中希望的。如果你有心愿的话,我就帮你实现一个。这就是我能够送给你的生日礼物。不过,仅仅只有一个,你还是好好想一想为佳啦。”老人竖起一根手指,伸向空中,“只有一个。事过之后再反悔,也不能够收回的哦。”
她无言以对。心愿?雨被风吹着,敲打在玻璃窗上,发出错落不齐的响声。沉默持续期间,老人一言不发,注视着她的眼睛。她的耳朵里,时间在刻画着不规则的颤动。
“我许个心愿,就能够成真吗?”
老人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仍旧将两手搁在写字台上,只是愉悦地微笑。那是一张非常自然、友好的笑脸。
“年轻的女士,你有心愿吗?还是没有呢?”老人声音沉稳地这么问道。
她望着我的脸,说:“这可是真人真事哦,绝不是我瞎编乱造。”
“当然。”我说。当然,她不是那种会胡编乱造的性格。
“那么,你当时有没有许下什么心愿呢?”
她仍旧盯着我的脸望了一会儿,然后小小地叹了一口气:“就算是我,也并没有完完全全地把那位老爷子的话当真啦。都二十岁了,又不是在童话世界里。不过,如果要说那是临时起意的幽默,又未免机灵得过分了吧?老爷子有几分洒脱,而我也很乐意配合话题。毕竟是二十岁生日嘛,稍稍有点不同寻常之处也不为过吧。我这么想道。这不是相信不相信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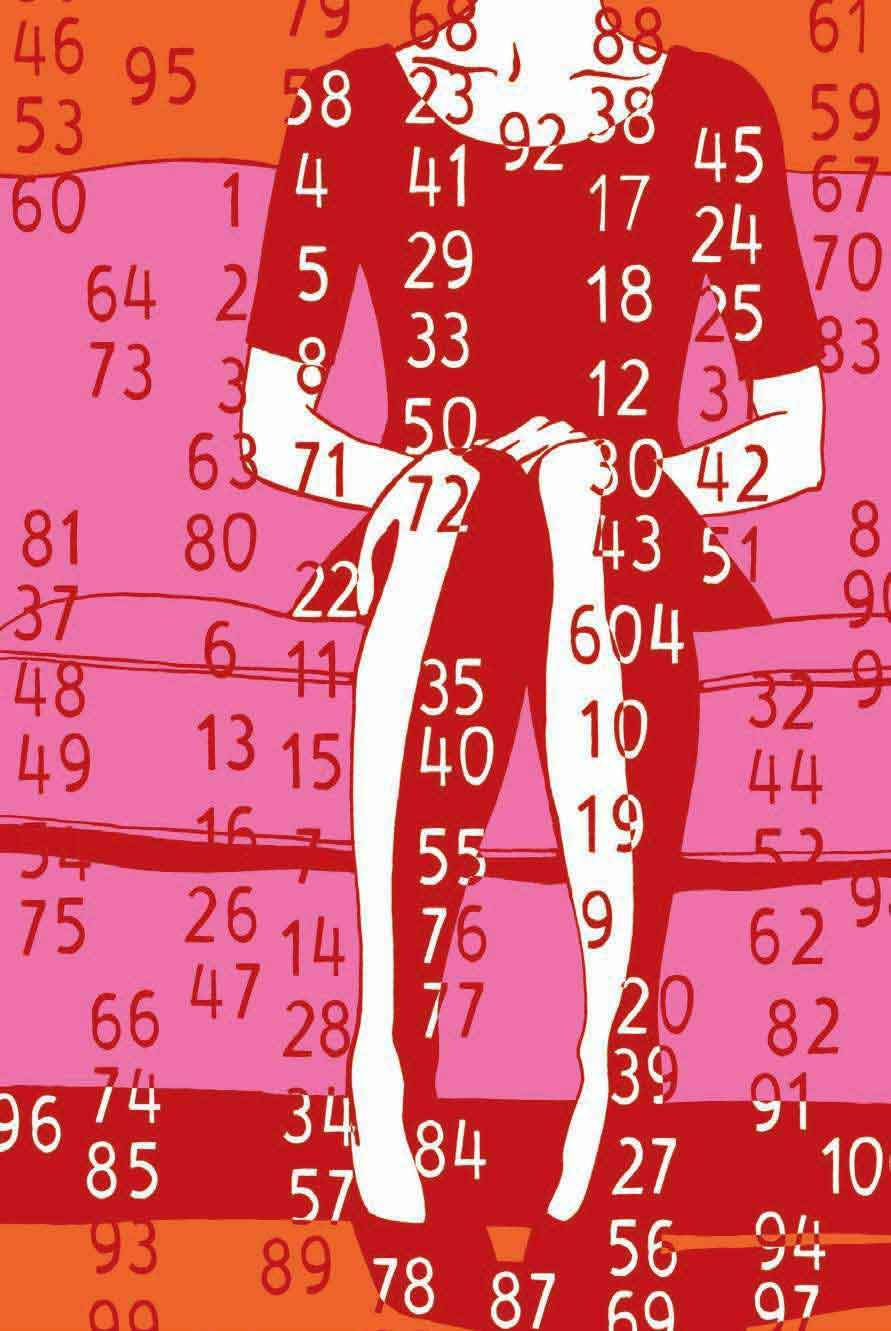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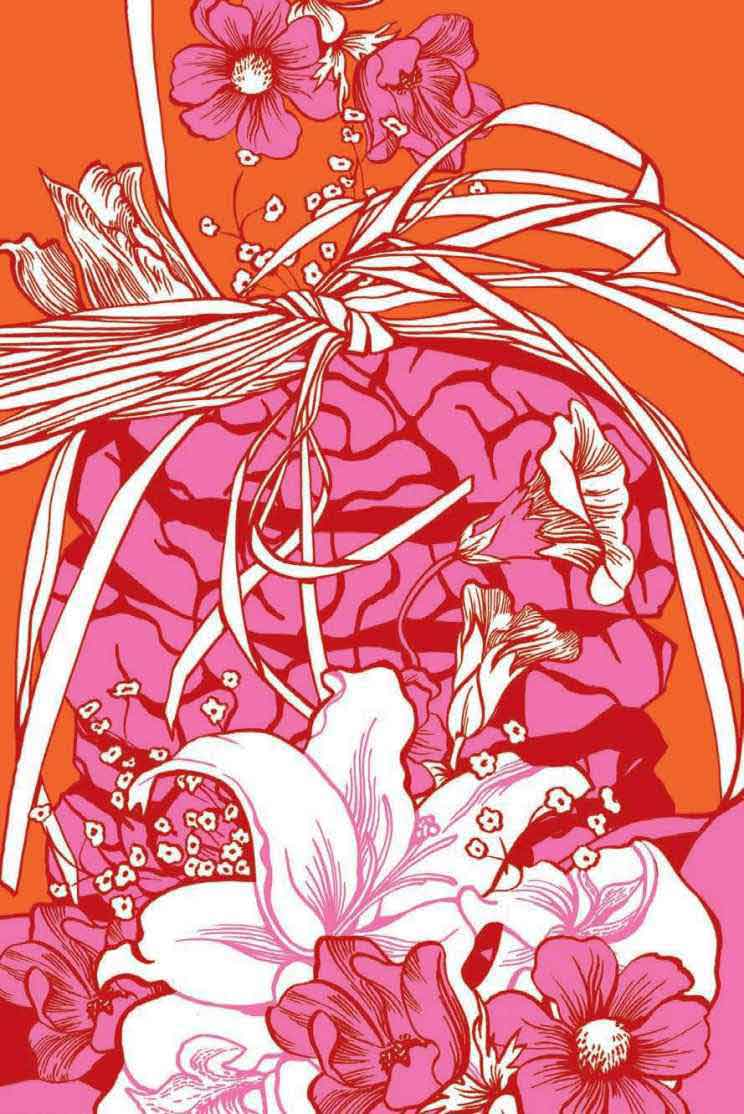
我沉默着点点头。
“你能理解我的心情吧?什么好事都没有,道一声生日快乐的人也没有,就这么端着浇了鳀鱼酱汁的意式馄饨送到餐桌上去,一天即将一去不返。这可是我的二十岁生日啊。”
我再一次点点头。“我懂的。”我说。
“所以我照他说的,许了一个心愿。”她说。
老人半晌一言不发,看着她的脸庞,两手依然搁在写字台上。写字台上放着好几个厚厚的文件夹,像是账簿。也有文具和台历,还有一盏绿色灯罩的台灯。他那小小的一双手简直就像那些物件的一部分,搁在那里。雨点仍旧敲打着玻璃窗,远处东京塔的照明望去模糊一片。
老人的皱纹稍许变深了一些。“这就是你的心愿喽?”
“对,是的。”
“对于像你这个年龄的女孩子来说,可让人觉得有点别具一格啊。”老人说道,“说老实话,我心里设想的倒是更为不同的心愿呢。”
“要是不妥的话,我再换个别的。”她说道,然后又清了下嗓子,“别的也没关系。我来想一想。”
“别别。”
老人举起双手,像旗子一般在空中摇了摇。“不是说不妥,一点也不。只不过吧,我很震惊呢,年轻的女士。就是说,你就没有其他的心愿了吗?比如说吧,对啦,想变得更加美丽呀,更加聪敏呀,想成为富豪呀,你是没有这一类心愿的喽,就像别的普通女孩子所希望的那种?”
她搜肠刮肚地寻觅词句。其间老人一言不语,只是静静地等着。他的双手安静地摆在写字台上。
“我当然想变得美丽,也想变得聪敏,还想变成富豪。不过这种心愿假如真的实现了,自己将会因此变成什么样子,我根本想象不出来。搞不好反而会手足无措。我还没有完全悟透人生。真的。我还不理解它的结构机制。”
“原来如此。”老人双手指头交叉,又分开,“原来如此。”
“像这样的心愿也可以吗?”


“当然。”老人说道,“当然。我这边没有任何不方便。”
老人突然一动不动地凝视着空中的一点。额头的皱纹更加深了,宛如聚精会神进行思考的大脑沟回一般。他似乎是在凝视浮在空中的某种东西——比如说肉眼看不见的微小的羽毛。然后摊开两手,微微抬身,猛地合上掌心,砰地发出一声短促而干燥的响动。随后在椅子上坐下,手指抚慰般地缓缓划过额头的皱纹,静静地微微一笑。“好啦。这下你的心愿就实现啦。”
“已经实现了吗?”
“是啊,你的心愿已经实现啦。小事一桩。”老人说道。
“美丽的年轻女士,祝你生日快乐。小推车我会放在走廊里的,无须担心。你回去工作吧。”
她乘上电梯返回店里。许是空着两手的缘故吧,她觉得身轻如燕,仿佛走在某种飘飘软软不可名状的东西上。
“出了什么事儿?一副魂不守舍的模样。”年纪偏轻的那个男服务生搭话道。
她暧昧地微笑,摇摇头。“是吗?什么事也没有呀。”
“说说,老板是个什么样的人?”
“没什么呀。我没仔细看。”她淡淡地答道。
一个半钟头之后,她去撤餐具。餐具摆在小推车上,放在走廊里。掀开盖子一看,菜肴已然消失得一干二净,葡萄酒瓶和咖啡壶也空空如也。604号的房门毫无表情地紧闭着。她盯着那扇门默默地望了一会儿。它似乎马上就会豁然洞开,然而却并没有开。她把小推车推进电梯,推到楼下,送到了洗碗池边。大厨看了看盘子,干净得一如平素,没有表情地点点头。
“从此以后,我和老板再也没有见过面。”她说。
“经理最后只是一般的腹痛,从第二天起就又自己去送餐了,而我一开年就辞工不做了。打那以后再也没去过店里。不知怎么,我总觉得别靠近那儿为好。隐隐约约地,仅仅是预感。”
她若有所思,用手指抚弄着纸质的杯垫。
“时不时地,我会觉得二十岁生日那晚发生的事情好像全都是梦幻。就是说,存在着某种作用,让我误以为其实并未发生的事情发生了而已。不过呢,那确凿无误,就是现实里发生的事情哦。那个604号房间里的一样样家具一个个摆件,连细节现在也仍旧历历在目。那是实际发生过的事情,恐怕还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呢。”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喝着各自的饮料,大概想着彼此不同的心事。
“我可以问个问题吗?”我说,“确切地说,是两个问题。”
“请问吧。”她说,“不过据我想象,你首先是想知道我当时许了个什么样的心愿,不是吗?”
“可是你看起来不太想谈论这件事。”
“看起来是那样吗?”
我点头。
她将杯垫垫在杯下,仿佛凝视远处某物似的眯起眼。“许下的心愿,是不能对别人说出来的,肯定。”
“我也并没有刺探的意思哦。”我说,“我想知道的,首先是你那个心愿实际上有没有实现。还有就是,不管那是怎样一个心愿,你后来有没有后悔过当时选择它作为你的心愿。就是说,你有没有这样想过:‘要是许了个别的心愿就好了’?”
“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既是yes,也是no。人生的未来之路还很长,我并不是已经看到事情演变的结果。”
“是个需要假以时日的心愿喽?”
“是啊。”她说,“时间在这里将起到重要作用。”
“就像某种烹饪手法?”
她点头。
我就此试着稍作思考。不过在我的脑海里,仅仅浮现出了低温烤箱里慢慢烤制巨大馅饼的情形。
“关于第二个问题呢?”我问了一句。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来着?”
“你不后悔选择它作为你许的心愿吗?”
一段时间的沉默。她将一双没有纵深的眼睛朝向了我。干涸的微笑残影浮上了她的嘴角。这让我察觉到某种寂寥的认命之感。
“我现在跟大我三岁的注册会计师结了婚,有两个孩子。”她说,“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一条爱尔兰长毛猎犬。开着奥迪,每周跟女友去打两次网球。这就是我现在的人生。”
“似乎不太坏嘛。”我说。
“即使奥迪的保险杠上有两处凹陷?”
“可就是为了凹陷才装保险杠的嘛。”
“要是有这种随意贴该多好。”她说,“‘保险杠就是为了凹陷而存在。’”
我注视着她的嘴角。

“我想说的是,”她静静地说,又搔了搔耳垂。形状美丽的耳垂。“人这东西,不管他祈盼着什么,不管他走了多远,都只能成为他自己,不可能变成任何别的东西。仅此而已。”
“这种随意贴也不坏呀。”我说,“‘人这东西,不管走了多远,都只能成为他自己。’”
她愉快地放声大笑。于是,刚才还在那里的干涸的微笑残影消散了。
她手肘撑在吧台上,看看我。“我说啊,假如你处在我的位置,你会许个什么心愿呢?”
“你是说,在我二十岁生日的晚上吗?”
“对。”她说。
我想了很长时间,然而连一个心愿也想不出来。“我什么也想不出来啊。”我如实说道,“而且,距离我二十岁生日也太遥远啦。”
“真的什么都想不出?”
我点头。
“一个都……?”
“一个都想不出。”我说。
她再次看看我的眼睛。那是笔直的、率真的视线。

“你肯定已经许过愿了。”她说。
“不过,仅仅只有一个,你还是好好想一想为佳啦。可爱的精灵小姐。”某处黑暗中,系着枯叶色领带的小个子老人将一根手指伸向空中。“只有一个。事过之后再反悔,也不能够收回的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