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帝掷骰子吗?:量子物理史话 | 收藏 |
Part 5
上帝掷骰子吗?:量子物理史话 作者:曹天元
p×q ≠ q×p。如果说狄拉克比别人天才在什么地方,那就是他可以一眼就看出这才是海森堡体系的精髓。那个时候,波恩和约尔当还在苦苦地钻研讨厌的矩阵,为了建立起新的物理大厦而努力地搬运着这种庞大而又沉重的表格式方砖,而他们的文章尚未发表。但狄拉克是不想做这种苦力的,他轻易地透过海森堡的表格,把握住了这种代数的实质。不遵守交换率,这让我想起了什么?狄拉克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名词,他以前在上某一门动力学课的时候,似乎听说过一种运算,同样不符合乘法交换率。但他还不是十分确定,他甚至连那种运算的定义都给忘了。那天是星期天,所有的图书馆都关门了,这让狄拉克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第二天一早,图书馆刚刚开门,他就冲了进去,果然,那正是他所要的东西:它的名字叫做“泊松括号”。
我们还在第一章讨论光和菲涅尔的时候,就谈到过泊松,还有著名的泊松光斑。泊松括号也是这位法国科学家的杰出贡献,不过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深入它的数学意义。总之,狄拉克发现,我们不必花九牛二虎之力去搬弄一个晦涩的矩阵,以此来显示和经典体系的决裂。我们完全可以从经典的泊松括号出发,建立一种新的代数。这种代数同样不符合乘法交换率,狄拉克把它称作“q数”(q表示“奇异”或者“量子”)。我们的动量、位置、能量、时间等概念,现在都要改造成这种q数。而原来那些旧体系里的符合交换率的变量,狄拉克把它们称作“c数”(c代表“普通”或者“可交换的”)。
“看。”狄拉克说,“海森堡的最后方程当然是对的,但我们不用他那种大惊小怪,牵强附会的方式,也能够得出同样的结果。用我的方式,同样能得出xy-yx的差值,只不过把那个让人看了生厌的矩阵换成我们的经典泊松括号[x, y]罢了。然后把它用于经典力学的哈密顿函数,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导出能量守恒条件和玻尔的频率条件。重要的是,这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新力学和经典力学是一脉相承的,是旧体系的一个扩展。c数和q数,可以以清楚的方式建立起联系来。”
狄拉克把论文寄给海森堡,海森堡热情地赞扬了他的成就,不过带给狄拉克一个糟糕的消息:他的结果已经在德国由波恩和约尔当作出了,是通过矩阵的方式得到的。想来狄拉克一定为此感到很郁闷,因为显然他的法子更简洁明晰。随后狄拉克又出色地证明了新力学和氢分子实验数据的吻合,他又一次郁闷了——泡利比他快了一点点,五天而已。哥廷根的这帮家伙,海森堡、波恩、约尔当、泡利,他们是大军团联合作战,而狄拉克在剑桥则是孤军奋斗,因为在英国懂得量子力学的人简直屈指可数。但是,虽然狄拉克慢了那么一点,但每一次他的理论都显得更为简洁、优美、深刻。而且,上天很快就会给他新的机会,让他的名字在历史上取得不逊于海森堡、波恩等人的地位。
现在,在旧的经典体系的废墟上,矗立起了一种新的力学,由海森堡为它奠基,波恩、约尔当用矩阵那实心的砖块为它建造了坚固的主体,而狄拉克的优美的q数为它做了最好的装饰。唯一缺少的就是一个成功的广告和落成典礼,把那些还在旧废墟上唉声叹气的人们都吸引到新大厦里来定居。这个庆典在海森堡取得突破后3个月便召开了,它的主题叫做“电子自旋”。
我们还记得那让人头痛的“反常塞曼效应”,这种复杂现象要求引进1/2的量子数。为此,泡利在1925年初提出了他那著名的“不相容原理”的假设,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这个规定是说,在原子大厦里,每一间房间都有一个4位数的门牌号码,而每间房只能入住一个电子。所以任何两个电子也不能共享同一组号码。
这个“4位数的号码”,其每一位都代表了电子的一个量子数。当时人们已经知道电子有3个量子数,这第四个是什么,便成了众说纷纭的谜题。不相容原理提出后不久,当时在哥本哈根访问的克罗尼格(Ralph Kronig)想到了一种可能:就是把这第四个自由度看成电子绕着自己的轴旋转。他找到海森堡和泡利,提出了这一思路,结果遭到两个德国年轻人的一致反对。因为这样就又回到了一种图像化的电子概念那里,把电子想象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小球,而违背了我们从观察和数学出发的本意了。如果电子真是这样一个带电小球的话,在麦克斯韦体系里是不稳定的,再说也违反相对论——它的表面旋转速度要高于光速。
到了1925年秋天,自旋的假设又在荷兰莱登大学的两个学生,乌仑贝克(George Eugene Uhlenbeck)和古兹密特(Somul Abraham Goudsmit)那里死灰复燃了。当然,两人不知道克罗尼格曾经有过这样的意见,他们是在研究光谱的时候独立产生这一想法的。两人找到导师埃仑费斯特(Paul Ehrenfest)征求意见。埃仑费斯特也不是很确定,他建议两人先写一个小文章发表。于是两人当真写了一个短文交给埃仑费斯特,然后又去求教于老资格的洛仑兹。洛仑兹帮他们算了算,结果在这个模型里电子表面的速度达到了光速的10倍。两人大吃一惊,风急火燎地赶回大学要求撤销那篇短文,结果还是晚了,埃仑费斯特早就给Nature杂志寄了出去。据说,两人当时懊恼得都快哭了,埃仑费斯特只好安慰他们说:“你们还年轻,做点蠢事也没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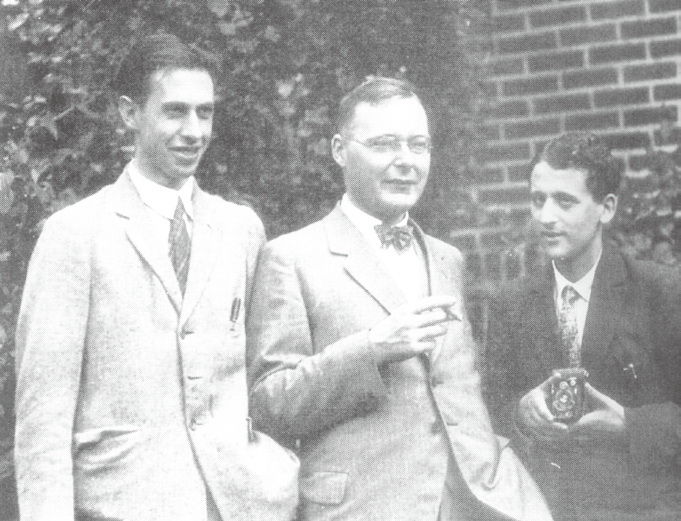
还好,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玻尔首先对此表示赞同,海森堡用新的理论去算了算结果后,也转变了反对的态度。到了1926年,海森堡已经在说:“如果没有古兹密特,我们真不知该如何处理塞曼效应。”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也很快被解决了,比如有一个系数2,一直和理论所抵触,结果在玻尔研究所访问的美国物理学家托马斯发现原来人们都犯了一个计算错误,而自旋模型是正确的。很快海森堡和约尔当用矩阵力学处理了自旋,结果大获全胜,不久就没有人怀疑自旋的正确性了。
哦,不过有一个例外,就是泡利,他一直对自旋深恶痛绝。在他看来,原本电子已经在数学当中被表达得很充分了——现在可好,什么形状、轨道、大小、旋转……种种经验性的概念又幽灵般地回来了。原子系统比任何时候都像个太阳系,本来只有公转,现在连自转都有了。他始终按照自己的路子走,决不向任何力学模型低头。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泡利是对的,电子的自旋并不能想象成传统行星的那种自转,它具有1/2的量子数,也就是说,它要转两圈才露出同一个面孔,这里面的意义只能由数学来把握。后来泡利真的从特定的矩阵出发,推出了这一性质,而一切又被伟大的狄拉克于1928年统统包含于他那相对论化了的量子体系中,成为电子内禀的自然属性。
不过,无论如何,1926年海森堡和约尔当的成功不仅是电子自旋模型的胜利,更是新生的矩阵力学的胜利。不久海森堡又天才般地指出了解决有着两个电子的原子——氦原子的道路,使得新体系的威力再次超越了玻尔的旧系统,把它的疆域扩大到以前未知的领域中。已经在迷雾和荆棘中彷徨了好几年的物理学家们这次终于可以扬眉吐气,把长久郁积的坏心情一扫而光,好好地呼吸一下那新鲜的空气。
但是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歇一歇脚,欣赏一下周围的风景,为目前的成就自豪一下,我们的快艇便又要前进了。物理学正处在激流之中,它飞流直下,一泻千里,带给人晕眩的速度和刺激。自牛顿起250年来,科学从没有在哪个时期可以像如今这般翻天覆地,健步如飞。量子的力量现在已经完全苏醒了,在接下来的3年间,它将改变物理学的一切,在人类的智慧中刻下最深的烙印,并影响整个20世纪的面貌。
当乌仑贝克和古兹密特提出自旋的时候,玻尔正在去往荷兰莱登(Leiden)的路上。当他的火车到达汉堡的时候,他发现泡利和斯特恩站在站台上,只是想问问他关于自旋的看法,玻尔不大相信,称这“很有趣”(这就是玻尔表达不信的方法)。到达莱登以后,他又碰到了爱因斯坦和埃仑费斯特,爱因斯坦详细地分析了这个理论,于是玻尔改变了看法。在回去的路上,玻尔先经过哥廷根,海森堡和约尔当站在站台上。同样的问题:怎么看待自旋?最后,当玻尔的火车抵达柏林,泡利又站在了站台上——他从汉堡一路赶到柏林,想听听玻尔一路上有了什么看法的变化。
人们后来回忆起那个年代,简直像是在讲述一个童话。物理学家们一个个都被洪流冲击得站不住脚:节奏快得几乎不给人喘息的机会,爆炸性的概念一再地被提出,每一个都足以改变整个科学的面貌。但是,每一个人都感到深深的骄傲和自豪,在理论物理的黄金年代,能够扮演历史舞台上的那一个角色。人们常说,时势造英雄,在量子物理的大发展时代,英雄们的确留下了最最伟大的业绩,永远让后人心神向往。
回到我们的史话中来。现在,花开两朵,各表一支。我们去看看量子论是如何沿着另一条完全不同的思路,取得同样伟大的突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