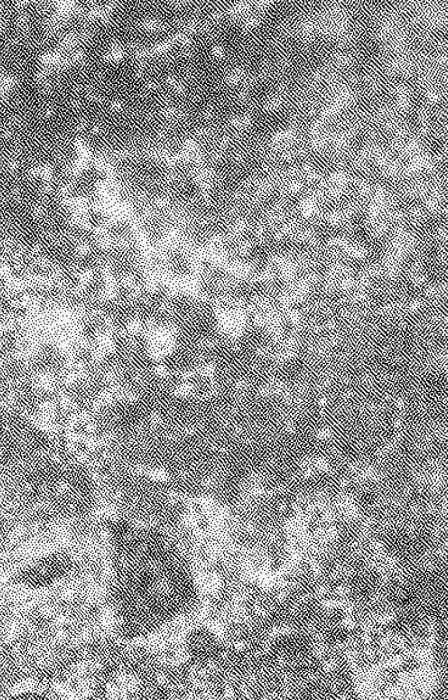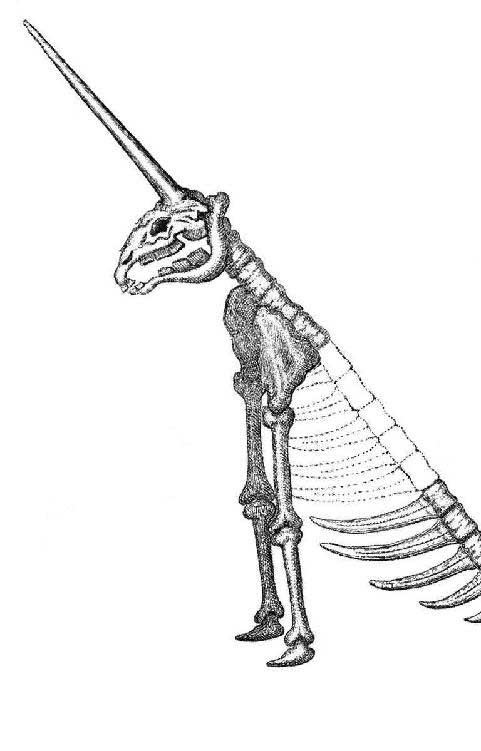| 逝物录 | 收藏 |
古罗马
里海虎
Panthera tigris virgata又称波斯、马赞德兰、赫尔卡尼亚、里海或图兰虎
逝物录 作者:尤迪特·沙朗斯基
* 不到一万年前,西伯利亚虎和里海虎因生存空间隔离而分裂为两个亚种。后者生活在阿拉斯河上游流域,从塔雷什山区覆林的缓坡和平原到连科兰低地;里海东岸及南岸,厄尔布尔士山北坡至阿特阿克河河道;科佩特·达格山脉以南至穆尔加布河流域、阿姆河及其支流上游;阿姆河河谷至咸海,更远至泽拉夫尚河下游水域,逆伊犁河而上,沿特克斯河直至塔克拉玛干沙漠。
† 直接猎捕、栖地消失、最重要的猎物减少,是里海虎灭绝的原因。1954年,最后一头样本被射杀于土库曼斯坦与伊朗交界处科佩特山区的苏姆巴河附近。另有报道称,最后一头虎1959年死于伊朗北部的古利斯坦国家公园。1964年有人曾在塔雷什山脉出口、里海附近连科兰低地的河谷盆地中见到最后的里海虎。20世纪70年代初,伊朗环境保护部的生物学家开始在偏远无人的里海森林中寻找其踪迹,数年之久,徒劳无果。圈养无一例存活。少量制成标本的尸体沦为伦敦、巴库、阿拉木图、诺沃西比尔斯克、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自然历史藏品。70年代中期还能在塔什干的自然博物馆中看到里海虎标本,直至一场大火将其摧毁。
傍晚,她饥饿而焦躁。数日无肉。自被俘起,再未猎食。囚禁吓退本能,直至她兀突突地躺在那,如同被啃光的骨头。火在猫眼里燃烧。那是火把的反光。它告知着每次巡行都穿栏窥视、听入黑暗的卫兵,货是否还活着。
栅子打开。没有餐食,却备好位席。火把引路。刺枪把它们赶入无窗的黑洞,两个木板箱,高不过背隆。有人将其推上等待的车。感官被饥饿磨快。骚乱,动荡,嘈杂:卫兵嘶哑的命令,车夫刺耳的哨声,当啷当啷的辔头,运粮驳船在远处码头的撞击,车轮吱嘎轧过,绳索噼噼啪啪。
队伍冷不防动起来,走上预定路线。进入城市之极内。进入此在之极外。车轴每转一次都吱吱尖叫。
两兽仅隔一墙。它们蜷在暗里。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看不到。不见腐坏的船坞和雾气蒸腾的堆尸场,不见行经的普雷内斯提诺大门,甚至不见夜色中闪烁的大理石和提布尔大石建筑。它们是兽。与我们一样的兽。与我们一样必死无疑。
仍还是夜,它们被送入地下墓穴。在最后几个黑暗的时辰里,绕着窄窄的、无意义的圈子,彼此陌生——是否势均力敌,终会水落石出。隔间,囚室,发了霉,对太阳深藏不露。即使终于日出,也没有一束光穿透至此,到达这由通道、坡面和升降机,由陷阱和门构成的地下世界。
此时,它们头顶张起帆,如第二片天,笼罩着渐渐被人类填满的石质漏斗:执政官、元老、女祭司和武士、公民、自由民、退役军官——最上方,边缘,女人。他们都来了,要看。他们来了,要被看。是节日,大场面。称之为竞技赛的人,不识固存其中的神圣秩序,和随之而来的血腥庄严。
天尚早,皇帝走进包厢,扯掉斗篷上的风帽,露出他健硕高大的身材和粗壮的脖子,人人都认识硬币上那张肥胖的侧脸。当他终于坐下,地牢开了,深渊绽裂,一头从未见过的巨兽从活板门下升起,它沿篱栅冲入场内,跳着高撞击隔开舞台和观众的护栏,用它强劲的前掌轰隆隆地拍击铁门,停下来,环顾四周,僵在那没有尽头的一刻。
吼声跨越山海,抢在怪兽之先:它从赫尔卡尼亚密林深处而来,里海沿岸那蛮荒、险恶、常青的土地。它的名字是咒语,也是誓言。它叫:迅疾如箭,狂暴如河流中最湍急的底格里斯(Tigris),它(Tiger)亦得名于此。它皮毛野火般泛红,面容描画精致,耳朵直立,臀部有力,口鼻具白髭,重眉之下双眼绿光凌厉,额上有对称的深色胎记,其含义无人可解。
巨兽摇了摇沉重的脑袋,张开可怕的血盆大口,露出两颗尖獠牙和多肉的口腔。舌头舔过发亮的鼻子。咆哮从喉中传出,一种从未听过的嘶吼在人群中层层回荡——那是让任何话语都沦为呢喃的可怕声音。一个论断流传开来,半是知识,半是诗:此兽俱雌,因为它们太过残暴,唯有被夺子的母亲才会如此。认为此话正确的只是偶然:再不能生育的肚腹藏在画有一环环深棕纹理的尾下。
巨兽又动了起来,用无声的脚步丈量着广场,随墙影,寻找能提供安全、宁静和庇护的场所——寻而无果。只有木栅油腻腻的灰,装有护栏的窟窿,宽袍闪亮汹涌的白,一块块浅斑,一张张僵成面具的裸脸。
此兽何时第一次对他们显现?不是在噩梦里,作为吃人的蝎狮,长着恶毒的孩子的脸,满是獠牙的露齿大口,抵挡箭镞的尾巴。而是活生生地,随一个印度使团,出现在萨摩斯岛岸。当时也是雌虎,独行者队伍里最后一个样本,熬过无比漫长、痛苦的旅行活了下来。人们用精铸的铁链把她牵到奥古斯都面前,作为恭敬臣服之证——亦是自然的可怕奇迹,与那个并列的神首柱般的少年同样罕见、同样骇人:他半裸着,全身涂满香料,无臂,它们已在婴儿时被人从肩膀上砍下。他们站在那里,龇牙咧嘴的兽和断肢残废的人——两种稀奇的生物,一对诡怪的搭档,每位诗人都会由此写出恐怖之崇高的箴言。
六年后,此兽首次现身罗马。五月望日前的第九天,在这座竞技场期待已久的落成典礼上,她与一头犀牛和一条十肘长的花蟒被一同展览出来。这头猛兽已今非昔比,众目睽睽下,她竟用粗糙的舌头舔起卫兵的手,就像一条狗。
罗马泱泱大国,散线般辐射向天下四方。他们不仅征服了拉丁人、沃尔西人、埃魁人、萨宾人和伊特鲁里亚人,也战胜了马其顿人、迦太基人和弗里吉亚人,连叙利亚人和坎塔布里人也被打败——如今,甚至怪兽也如蛮族一般驯服,鞭笞和撬棒赶走了野性,羊肉和兔肉骗取了信任,它们因此得到所有臣服者应得的保护。这头眨眨眼就能回击阳光、却躲不开人类咄咄目光的雌虎,仿佛一个即将被释放的女奴,马上就会被宣布成帝国的公民。然而,不知何处传来复仇的呼唤,与其说它出于忌疑,莫若是一种喜怒无常,滋长的困惑和突然爆发的狐疑有着永远不变的刺耳合唱,而复仇的回音总是在其中响起。人们硬要说,她的臣服只是表演,她的温柔无异于阴谋。哪怕食肉兽藏起利爪,转身仰卧,露出肚皮让卫兵爱抚,她的可怕依然丝毫不减。这个敌手让人感到虽胜犹败,再没什么能像她曾拥有过的权力那样,持久地激发恐惧。因为真相素来无法否认:自然不可战胜,野性永不驯服。巨兽的每一次呼吸都让人想起古老的恐惧和危机四伏的祸患——她的速死也因此刻不容缓,就像战争获捷后要立刻献祭谢神。审判同心一意:驯兽应战死,一如罗马的所有敌人。然而,当人们开始挑选对手,却没有一个敢上前一步。那就在笼子里宰了吧。
链啷当,剑铮铮,木窗落到沙上。土层裂开。坐席中传开窃窃私语。一个黄褐色的脑袋从暗中浮出,一头狮子走入赛场,平静,镇定,高昂的头颅环以锈黑的鬃毛。深色毛发从肩头高处垂至下腹,皮毛蓬乱。他看着陌生的大猫,领悟到她完美的捕食者形态。两兽相立对视,第一次——从安全的远处。一匹马在门前嘶鸣,一声鞭响。此外则是静寂。所有人都倾身向前,要解读猛兽的目光、它们喑哑的姿态、它们不动的存在。可没有什么走漏风声。绝无丝毫乖顺,没有阔野上强盗与猎物各安其位的融融之兆。
狮子庄严端坐,不露半分躁气,紧腹傲胸,定格成立像,称霸已久的帝王。无人说得出是谁在先,统治之职还是英雄状貌。不敬仰他的世界,不可想象。不以他为王的故事,不值得讲。它的鬃毛在阳光中闪着微微的红光。他目光冻结。眼睛亮如琥珀。他流苏般的浓密尾缨鞭打着粒状的干沙。他张开大口,越来越大,露出黄色巨齿,伸长脑袋,放平耳朵,眼睛缩成细线——开始吼叫,从胸腔深处挤压出的呜咽,一声又一声,随后是可怕的咆哮,每次都似乎来自更深的深渊,更响、更猛,更急、更戾。印度人说,那是狂风呼号,埃及人说,那是冲锋大军的疾驰,希伯来人说,那是耶和华的雷霆震怒。但那也可能是宣告世界终结的创世初音。
雌虎低下头,弓弦般隆起瘦长的身躯,把流苏似的白须压入沙中,猫一样抻开后腿。她肩下郁积着肌肉的纯力。她伸出一只前爪,小心翼翼地,迈出另一只,匍匐着徐徐向前,滑动得越来越近,停下——瞄准了狮子。
他看着她来,镇定自若。对于他的勇气,人言无误。恐惧沾不上他。他纹丝不动地守在原地,静观其变。只有尾巴左右扫动,在尘土上写下一成不变的弧线。他的血沸腾着,宝石也会融化其中。
起风了,一只鸽子忽地卷入帆,扑棱棱寻找着远方。雌虎奔跑起来,急速穿越空中,冲向狮子。他站了起来,两个脑袋撞出一声闷响,两大团皮肉在沙中翻滚——急速旋转,直至厚板的裸木迸出火光。怒吼、喘息和咆哮充斥着斗兽场,混以喧嚣和呼喊的合声,高涨为湮没一切的震耳欲聋:疲惫的狮子在无光的坑穴里呜咽,捕入拖网中的幼虎嘶哑吠泣,一头受伤大象虚弱地低吼,被追至精疲力竭的母鹿凄凄哀吟,被射中肚腹的孕猪可悲尖叫。
它们来自帝国遥远的边缘;毛里塔尼亚、努比亚和盖图里丛林的黑豹、狮子、猎豹,埃及的鳄鱼,印度的大象,莱茵河畔的野猪和北方沼泽的麋鹿。它们乘着有桨有帆的船只而来,顶着倾盆大雨、酷暑和冰雹,苦于海浪颠簸,带着血淋淋的爪掌和磨钝的牙齿,装在粗榆木和榉木造的板箱里,像战俘、像判刑的罪犯,载上重型车。拉车的牛,一旦转过轭下压弯的后颈、无意中瞥见它们的货物,就会挣脱车辕,喘起粗气,吓得直翻白眼。
长天之下,车子穿过微光斑斓的平野和幽黑森林,穿过荒芜或肥沃的土地,在最贫瘠的乡村和城镇中休息,律法要求它们供养这些动物及其卫兵。一切为了罗马,这从其边缘汲养的短暂、脆弱的帝国中心。大多野兽中途丧命。被抛下车的死尸,在水里泡胀,被太阳烤干,成了狗和鹰的食物。命运对它们无情,却似乎比对幸存者更慈悲。
它们开入罗马,在高轮大车上,与军械一起,受万众瞩目,如一切奇珍异宝,巨大的字母宣告着它们的名字和缴获地。
人们将其存放在城墙外的船坞附近,关入窄笼,为所有猎手都将变成猎物的斗兽场做准备,在心平气和处煽动起仇恨。动物太温和,就饿上几天,扔去尖刺和燃烧的小树枝,挂在当啷啷的金属上,或是用红色的稻草人。谁在斗兽场上拒不出战,谁敢违逆其他人安排给它的角色,就会失去性命。比赛庄严。庄严得就像它们纪念的男男女女之死:常胜统帅,早夭的凯撒传人,皇帝的父亲和母亲。
战斗神圣。为强造壮观,屠夫们把野兽绑成串:原牛接大象,犀牛接公牛,鸵鸟接野猪,狮接虎,于是,阔野上永无瓜葛者,在斗兽场的半圆里狭路相逢——被逼成敌,剥夺生境,大惊而狂,暴露于众目之下,被不可见的绞索限定于此在,它们被允许活,正是因为要注定丧命于痛苦的、供人消遣的死。判决明确,它们的罪却始终隐晦。
仪式或许古老,可此时无人从头上脱去宽袍,生怕一眼错过死亡。热气腾腾的内脏不会让神明心软。没有悼歌唱诵死者,没墓碑掩埋尸体,只有活过无数比赛、一次又一次挡回死亡、甚至杀掉斗兽士、最终独留场上,才会被赐予后世声名:母熊依诺圣提亚和狮子西罗二世,可它们,终究也会在欢呼沸腾的观众眼前被一头无名虎撕碎。
雌虎摇开身子,滚到一侧。狮子向她的右前爪冲去,击中她的脑袋,撕下一块头皮。他闻到了血,闻到曾在阿特拉斯荒原把他引入陷阱的、受伤的、咩咩叫妈妈的羊羔,他闻到了失败和胜利。他铆足全力跳上她的脊背,后腿撑地,利爪刺入后颈,猛地向后掰起她的脑袋。雌虎大吼起来,咆哮着张开血盆大口。狮子再次发起进攻,逼退雌虎,直至她的尾巴擦过竞技场的围墙,他紧跟上去,一次次向她猛扑,瞄准她的喉咙,牙齿死死咬住她的脖子。似乎胜负已决。雌虎轻轻呻吟,如同一声叹息。左耳下裂开血三角。她弓身、挣扎,终于摆脱了撕扯,一跃跳上对手的脊背,前爪拍向后颈,把他拖倒在地,抠入他的皮毛,又一个抽身,尾尖颤抖着落在两竿外飞扬的尘土里。欢呼如潮,掌声雷动,铜号吹响了。
狮子好似恍惚了,他大口喘着粗气,转着沉重的脑袋查看自己的伤口,脊背上划出两道红色印痕。他甩了甩鬃毛,再次摆出战斗姿势,扑向雌虎,嘶吼着,喘息着——夹着痛苦的咆哮。她后退着摆动身体,看准他的前腿。两兽站立着扭打起来。红、黄、黑的毛发纷飞。人群乱叫,开始大吵大嚷,疯狂地煽动着他们所欲求的打斗。他们称之为捕猎,可没有丛林,护栏封住所有出口,高墙如同被占领的城垛。
他们让死刑和戏剧杂交。一群神经纤细的暴民——习惯了宏大、无穷、残忍。习惯了,一切可想之事。界限之所以存在,只为被跨越。只有好奇、只有想到就要做到的冲动,才能生出他们混着憎恶的欲望和混着欲望的憎恶。因为,自诩有所选择的他们,也无非就像用石头砸死青蛙、只为取乐的孩子,只是听从着本能。
好奇也生出疑问,若把动物园的所有猛兽一起关入这多沙的深穴里较量气力,谁会赢?一场大戏,激发又压制着每一丝恐惧。一幕奇观,比奥古斯都为夭折的继承人举办的所有竞技赛都更宏大。什么是野性的巅峰?一头驯化的虎,撕碎温和的狮子?斗兽场上猎兔的狮子,咬住它、叼在口中四处游走,就像它自己的骨肉,与之嬉戏、再放跑,只为重新捕获?猫科动物的百牲祭,一天内,在斗兽场表演、被杀,直至女人晕倒,遍地尸横,身体不再是身体,七零八碎,浸泡在血中,头颅抽搐,躯干被吃,四肢冷硬?
马戏(Zirkus)继承着竞技(Circus)。一种想法,一旦存世,就会在另一种形式里活下去。蹲在表演台上的大猫,叠成金字塔,排成四对舞。它们会骑马,踩单车,在跷跷板上摇晃,在绳索上平衡,纵身穿过熊熊火圈——穿着戏服的狗被当作跨栏跑的障碍,直到鞭子抽响,信号出现,舔起穿角斗士服的驯兽师的凉鞋,用战车拉着他穿过马戏场:狮子和虎——草原上的群居动物,潮湿森林的独行者——这不等的一对,肩并肩,套在轭下,恍若在古迹马赛克上酒神的车前:非洲对亚洲,统治对狂野。英雄的过往、贵如帝号的头衔又有何用?作为皇帝和圣人的宠物度过狮生。它满足了殉难者最内心的愿望,人们却把它的帝国洗劫一空。赢得一种特权,丢了另一种。城市、国家、帝王把它强铸于名牌上。它在所任的公职中忘记了自己的源地,旷野,太阳的力量,集体捕猎。欧洲人忘了虎几千年,于它又有何用?当然,它的稀少使它免于僵化为符号。这拉丁动物志中的古怪造物,被归入蛇和鸟,度以陌生的美德标准。他们辱骂它的怯懦,实应叫作聪明。只要躲得开,它就避着人。
远远看向未来,看到悲伤的命运;它们将与尤利安一样,家破人亡,末世子孙将被兽皮般塞作标本。永远囚禁在缩微立体布景中,在蒙尘的草原和断裂的草杆前咆哮,玻璃眼珠,血盆大口,露出大犬齿,威胁——或恳求着,就像死前一刻。在保护区、由人照管的一生,玻璃和地堑之后,假山之前,铺砖的房间和无栅栏的野生动物园,终日牺牲给无所事事,头上围着嗡嗡的苍蝇,进食和消化间的此在,在充满骟羊肉、马肉、牛肉和温血味的空气里。
观众暴怒起来。比赛戛然而止。两兽彼此放下、停住,粗重地呼吸着。血从胁腹部淌下。母虎拖着脚步走开,把受尽折磨的身体靠在围墙上,喘着粗气。狮子留在原地,肌肉颤抖,上唇浸透着血,满口泡沫。他的目光钝而空,眼睛无底。他的胸腔起起落落,呼吸着尘土。影子落在舞台上,云藏起太阳,一刹那。
场中突然亮了,陌生的光落在这一幕上。一种可能性开显出来,仿佛奇迹,一道无人想到的看入未来的目光,一个出口,预定轨道的岔路,崭新且不同,对近在咫尺的死一无所知。尽管,在那景象中,也是绝境、是求生欲,命中注定般,把两兽推向彼此。一种并非结束、而是开始的暴力。仪式遵从着一条古老而强大的规则。它说的是:在血统熄灭前,维系你的族,保存你的种。发情期临近,没有选择。本能失效,就让另一个取而代之。活着的,要吃。吃的,要繁殖。繁殖的,不会灭。信号引发异议,信息却明确无误,尿里的麝香是邀请,去加入后果严重的游戏:威胁姿态后是迟疑不绝的羞涩,靠近后是逃避,抗拒后是短暂的服从。
它们彼此摩擦,紧紧贴着脑袋。它们打斗,停住,爪子抬起,目光交错,抗拒着不可避免之事,逃离着心爱的敌人,欲火挑招,醉意漾荡,直至再也绕不过,被勾了魂,中了邪。
橘黑相间的大猫终于低下头,平趴在地上,狮子跨上去,沉下灰棕的身体,坐在她身上,不论如何亲近,总残存一丝陌异,可即便如此,过程还是人尽皆知:他咆哮着咬住她的后颈,直到她怒吼着随他摆动,二者生产出唯有非自然的亲密才能强行创造之物——不论是否盲目。世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如今发生之事。谁来定夺,什么是反自然,什么是自然规律?除了生殖力的传递者,大猫们还是什么?其种属的叛徒,亦是其卫士。后代不会在意,它们曾被迫行房。
初为梦者,百日后以幻象归返,嫁接般的妄诞造物,把双亲的秉性翻了倍、也减了半:黑尾无缨,白腹,短鬃,皮毛浅如沙,泛红的锗黄中圆斑如条纹般闪烁,父亲的体格,母亲的侧影,与之不同的轮廓,狮的平背,虎的鲤鱼脊。庞然大物,天性分裂,如虎般易怒,如狮般淡泊、强韧——被诅咒而注定孤独的群居兽,畏水的泳者,驱逐目光的惹眼物——杂种,狮虎,虎狮。
它们难道不是处处可见?在英国马戏团长的巡回流动展品中,有三只幼崽在涂色的铜板上,人们带走了虎妈妈,留下一只喂奶的猎犬,它们不到3岁就全都死去。稚拙彩画上,房内混杂的大猫之家,里面的驯兽师就像它们自己的孩子。电影胶片上,沙色的狮虎在一位银色泳装的女士身旁,巍峨巨兽,世界上最大的猫科动物,欲望冷淡、生殖力枯竭的雄性。
一声尖叫响彻上方座列,人们一哆嗦,快速转头看了看,又把脸朝向赛场。梦倏然结束,后代并未出世。似乎要赶走思绪,事件进程加速。旷远的地球和它形形色色的世界收缩到这半圆之上,这贫瘠之地,这由沙土、人群和石头构成的光秃秃的狩猎场,苍蝇嗡嗡乱撞,不安的手扇出微凉的空气。
母虎挣扎站起,又围着对手打转。狮子被逼自卫,可他的出击错过了目标。橘色的大猫退回、起跳,箭镞般疾速穿过空气、落于狮背。庞大的身躯滚过斗兽场,涂满血,染了尘土的棕。狮子嘶哑地咆哮,甩掉母虎,喘着粗气,摇摇晃晃,跪倒在地。他背上裂开两道伤口,血从深深的咬痕中流出。母虎已经重新跳上他肩头,獠牙刺入咽喉。他本必死无疑,只是鬃毛才让他躲过窒息。母虎松了口,喘着气,满嘴狮毛。这时狮子后摆、出击,母狮趔趄、平衡,再次向前猛冲。它们又倒在一起。母虎扑到狮身上,死死咬住他的肉。后者挣扎着站起,甩下她,张开大口,吼声渐弱,倒入沙中。躺着,一动不动。
母虎观察着她的作品,瘫倒在地,颤抖地舔着伤口。皮毛上的条纹模糊在血中。
皇帝克劳狄乌斯大笑着他放荡的笑。嘴角粘着唾沫。他起身,向前走了一步,坐下来讲话,要赞美今日祭奉的亡母。
可他口中的话语碎得结结巴巴,他沉默地倒在座椅里,耳中是母亲曾赐给他的可憎之名:怪物。这个恶毒的词阴魂不散,但凡他能想起,就是追杀他的咒语。谁能责怪她?什么助他掌权?只是因为,他还活着,王室的唯一,家族的最后一个。没人把他当回事,他,怪物。
他登基继位,是纯粹的偶然,帝职从不是给他的:民众的恩主,生死的统治者。他看着元老们的大理石座椅,武士宽袍的窄紫边,一道道质疑的目光。只要不怕,就很容易控制自己。汗从他的太阳穴上淌下来。
钟响了。门开了。人群狂吼。一个人走到斗兽场上。斗兽者只穿着束腰的短袖内袍,没有盔甲或盾牌,腿上缠着绷带,左手一具笼头,右手一杆数次高举、指引民众的投枪。母虎看到了这个半裸的人影,悄悄潜近,蹲伏下来,准备跳起——可此时枪头已刺穿她的胸膛。母虎挣扎、盲目地蹒跚乱撞,想甩掉长枪,她垂下头,眼睛搜寻着,难以置信,她的目光看向战士,看向鼎沸如狂的观众——然后瘫倒在地。眼睛爆裂,目光僵硬。鲜亮的血从鼻孔喷出,张开的嘴巴里汩汩涌出红沫。战士已走完一圈,接受掌声、呼号、跳舞的旗子、肆无忌惮的动作。提供了服务,重建了秩序,混乱被暂时攻克。
渐渐地,看台亮了。万物寂然。有人来,把尸体拖出斗兽场,扔进地牢,和上百头其他死兽堆在一起。空气里黏着腐败的味道。主场节目下午开始——角斗士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