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苔丝 | 收藏 |
第六章 改邪归正的人
45
苔丝 作者:托马斯·哈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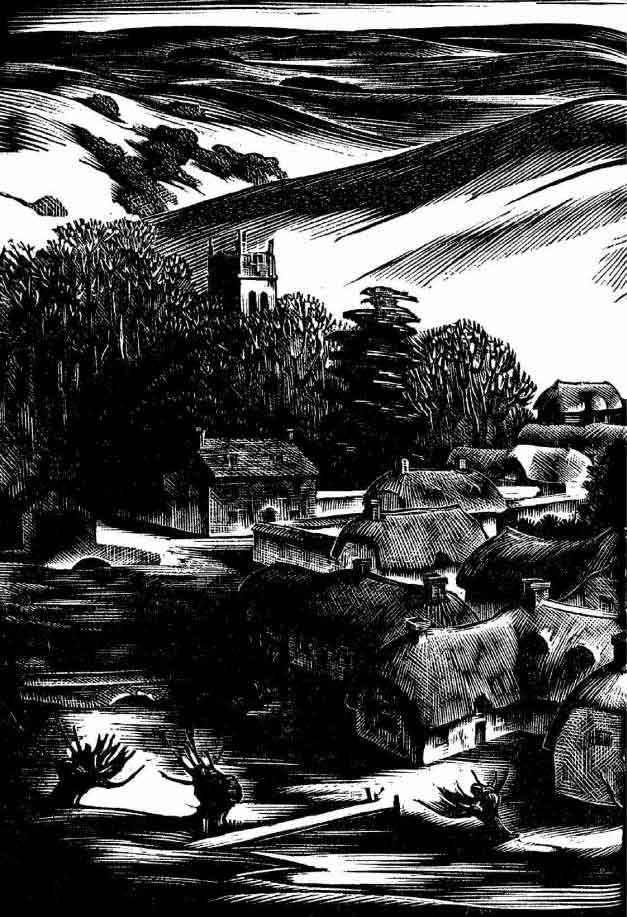

自从离开特兰特里奇以后,苔丝一次都没有见过德伯,也没有听说过任何关于他的消息,此刻却遇上了他。
这次偶遇发生在苔丝心情沉重的时候,按理来说在这种时候这只会给苔丝的情绪带来最轻微的影响。然而,人的记忆有时硬是无法用常理来解释;这会儿她虽然看见站在那儿的明白无误地是一个正在悔恨自己过去不正当行为的改邪归正的人,但是仍然觉得一阵恐惧袭上心头,使她僵立在那儿,既不往后退也不朝前走。
想一想上次看见他的时候他那张脸上是怎样一种表情,再看看他现在的表情!……在那张脸上,在那个时候和现在,有着同样一种机敏但是让人觉得不舒服的神气,不过现在他留着修剪整齐的旧式满腮胡子,原先的黑色八字胡子不见了;他的穿着是半牧师半俗人的,这就完全改变了他的外貌,使人不再看得出他原先那种纨绔子弟的模样,而且使苔丝在那么一瞬间怀疑自己是否认错了人。
《圣经》上那些庄严的词句一本正经地从德伯那张嘴里说出来,苔丝听了,起初觉得惊人地不协调,而且怪诞得可怕。德伯说话的语调她太熟悉了,正是这种语调,在不到四年之前把大异其趣的内容送入她的耳朵,此刻她想到如此具有讽刺意味的对比,不禁感到恶心。
德伯的这种变化,与其说是洗心革面,不如说是改头换面。以前他脸上那些显示追求感官快乐的曲线如今变成了虔诚教徒面部的线条;两片嘴唇的形状从前意味着欺骗和诱惑,如今却做出了求人行善的表示;昔日两颊的红光可以理解为行为不检的标志,今天却成了尽职宣讲福音时能言巧辩所焕发出来的光彩;兽性变成了狂热;信奉异教成了相信保罗神学;他那双眼睛,从前滴溜溜地转着,大胆放肆地上下打量苔丝,如今粗鲁地闪耀着拜神的光芒,令人看了觉得凶猛可怕;从前当他愿望受挫时脸上往往会表现出来的那种阴沉生硬的样子,如今起到的作用是,表示一个堕落者的自暴自弃、不可救药。
德伯这副相貌本身似乎在抱怨。它被改变了——它一向所体现的是另外一种含义,现在却要表示天意本来不打算要它表示的那么一种意思。说来奇怪,要它执行崇高的任务是对它的一种误用,要提高它的品质似乎是要它作假。
不过,事情果真如此吗?苔丝不能让自己继续怀着这种小肚鸡肠的感情。德伯并不是第一个改邪归正以拯救自己灵魂的恶人,为什么她就该认为他这种改变是不自然的呢?这只不过是她已经有了一种成见,听见德伯说话的腔调没有改变,但原先说的是一些不三不四的话,如今说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劝人行善的话,心里就觉得很别扭。作恶越多的罪人,改好了以后就越有善心;这一点是不需要深入研究基督教历史就可以发现的。
以上这一些,只是苔丝头脑中产生的模糊想法,并不十分清晰,并没有使她受到很大感动。等到她由于吃惊而麻木的那短暂一刻过去之后,她觉得自己能够行动了,便立刻产生了要躲开德伯、不让他看见的念头。苔丝这时候背对着太阳,德伯显然还没有发现她。
但是,苔丝刚一重新走动,德伯立刻就认出了她。苔丝的这位旧情人一看见她就好像触了电似的,这种效果比起他出现于苔丝眼前在苔丝心里产生的效果要强烈得多。他讲道的满腔热情、他那雄辩的词语和激动的语气似乎统统离他而去了。话在他嘴边,但是他的嘴唇哆嗦着、挣扎着,只要苔丝在他眼前他就不能言语。他那一双眼睛在看了苔丝第一眼之后便慌乱地四处张望,为的是要避免看到她,但是又忍不住地每隔几秒钟就突然对苔丝脸上投去一瞥。不过他这种不知所措的情形只持续了一小会儿,因为在他如此失态的时候苔丝却稳定了情绪恢复了体力,尽量快地经过谷仓直朝外面走去。
苔丝刚能定下神来想到他们两人的相对位置发生了如此变化,心里便吓了一大跳。德伯过去伤害了她,如今已经站到了上帝这一边,而她的灵魂却还没有得到再生。这样一来,结果就像传说的那样,她那淫荡的形象突然出现在他的圣坛上,于是牧师的激情差不多就消失了。
苔丝头也不回地一直朝前走。她的背似乎——甚至连她的衣服也似乎——对人的目光有一种特别的敏感;此刻她甚至觉得德伯大概已经走到了谷仓外面正在注视着她。在此之前,原先她在路上走着的时候心情沉重、十分伤心,这会儿她心里产生了一种性质不同的烦恼。原先她一直在渴望得到她的丈夫长期以来拒不给她的爱情,这会儿她暂时忘却了这种渴望,而深深地感觉到无法摆脱的往昔仍然缠着她——这一感觉几乎就跟肉体所遭受的种种感觉一样真切。这种感觉使她更强烈地意识到自己过去做错了事,使她简直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了任何希望;她本来所期望的一件事情——过去和现在会被割断开来——终于没有实现。在她本人成为陈迹之前,她过去的历史决不会完全成为陈迹。
苔丝一边这样思忖着一边再次在北段垂直地越过长梣路,不一会儿便看见那条白茫茫的大道在她面前从低处向上往高地伸展;她剩下的路将都是沿着这高地的边缘向前而去。这条大道干燥、灰白,毫无生气,路上一个人影、一辆车或任何一个标记都看不见,只是这儿那儿偶然有一点点褐色的马粪。就在慢慢地使劲往上走的时候,苔丝渐渐地感觉到身后有脚步声,回头一看,她看见越来越走近她的正是那个她非常熟悉的人影——奇里古怪地打扮得像一个循道宗信徒——正是那个世上所有的人当中她这一辈子最不想单独遇见的人。
然而,她没什么时间可以思考或者躲避,于是她尽可能平静地听凭后面那个人赶上自己。苔丝发现他情绪激动,这与其说是因为他走得太急而造成的,不如说是他内心的情感所致。
“苔丝!”德伯打招呼说。
苔丝放慢脚步但没有回过头去。
“苔丝!”德伯又叫了一声。“是我——亚历克·德伯。”
这时候苔丝才回过头去看着他;他走上前来。
“我看出来是你,”苔丝冷冷地回答说。
“噢——你只有这么一句话吗?是呀,我不配你跟我说更多的话!当然,”德伯脸上露出一点笑容添上一句,“看见我这个模样你会觉得有点儿滑稽。不过——那是我不能不忍受的……我听说你离去了,没有人知道你去了哪儿。苔丝,你纳闷我为什么要跟着你吧?”
“是的,我很不明白你为什么跟着我。我但愿你没有这么做,真的!”
“是的——你完全有理由这么说,”德伯板着面孔说;这时候他们两人一起向前走,苔丝迈着不情愿的步子。“但是你不要误会;我之所以请你不要误会我,是因为,刚才你注意到——如果你的确注意到——在谷仓那儿你的突然出现使我多么不能自制,你就很可能会对我产生误会。不过我刚才只是一时间不知所措;如果考虑到你曾经对我意味着什么,那么我现出那种表情完全是很自然的。我的意志随即帮助我稳定了情绪——也许你会认为我这是在说谎——接着我又立刻想到,要是说我有义务也有愿望从世界上这么许多人里面拯救什么人使其免遭将来会受到的谴责[原文是“将来的忿怒”,语出《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3章第7节:“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礼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忿怒呢。”]——也许你要对我嗤之以鼻了——那么,她就是我曾那样严重地伤害过的那个女人。我就是带着这唯一的目的跟在你后面的——再没有任何别的目的。”
苔丝的回答里含有一丝轻蔑:“你拯救你自己了吗?施舍先及亲友,人们说。”
“我没能做任何事情!”德伯不计较地说。“一切,正如我对我的听众们说的,都是上天的力量。对于过去那个堕落的我,苔丝,你的鄙视无论多么强烈,都不会超过我自己的鄙视!哎,说起来也真奇怪,不管你信不信,我可以把导致我悔悟和改变的一件具体事情对你说说,我希望你至少会有兴趣听一听。你有没有听说过埃姆大教堂那位牧师的名字——一定听说过吧?——克莱尔老先生,是他那一个教派中最热诚者之一,也是国教中所剩下的不多几位热诚的牧师之一。比起我现在所投身于其中的这个基督教的极端派别,他还不算那么热诚,不过在英国国教牧师当中他真可算是一个例外了,国教牧师中那些比较年轻者如今正以他们的诡辩和谬见渐渐地把真正的教义的力量削弱,使它们虚有其表了。我与他之间的分歧只是在教会与国家这个问题上——在如何解释‘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主说[参见《圣经·新约·哥林多后书》第6章第17节。]’这句话上——此外没有别的分歧。我坚决相信,作为上帝的卑微仆人,他拯救了许多人的灵魂,比你所知道的任何人拯救的都要多。你听说过他吗?”
“听说过,”苔丝说。
“两三年之前,他代表某个传教团体到特兰特里奇讲道。他对任何人都不带偏见,当时试图引导我,引我走正道,但是我混蛋透顶,竟然侮辱他。然而他并不记恨我的恶劣行为,只说,总有一天我会收到圣灵初结的果子[语出《圣经·新约·罗马书》第8章第23节。]——还说,那些来嘲笑的人有时候会留下来祈祷的[参见英国诗人、剧作家、小说家奥立佛·哥尔德斯密斯(1730—1774)的长诗《荒村》第180行。]。这些话有一种奇怪的魔力,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子里。但是我母亲的去世给了我极大的打击,慢慢地,我被引导着见到了光明。从那时候起我就只有一个愿望,要把真理传达给别人,这也就是今天我试图在做的事情;虽然我只是近来才到这一带来讲道。我开始传教的头几个月是在英格兰北部,在陌生人中间,我选择在那儿做最初的尝试,希望从不熟练到熟练,同时希望自己的勇气会越来越大,以便敢于去面对那些了解我,那些当我尚处于愚昧、黑暗之中的时候是我的同伴的人,去向他们讲道,使自己的真诚受到最严峻的考验。苔丝,要是你能尝一尝自己掴自己一记耳光的那种乐趣的话,我敢肯定——”
“别说了!”苔丝忿忿地说,一边离开德伯走到路边的一个篱旁台阶,把身子靠在上面。“我不相信这种突然发生的事情!我恨你!因为你知道——你知道你多么严重地伤害了我,现在却来对我说这些话!你,还有跟你同一类的人,把我这样的人的生活变得痛苦、悲伤、没有前途,你们自己开心够了,然后你们悔悟、改变、信了教,觉得自己有把握会在天堂里得到幸福了,这种事情多好啊!呸!我不相信你!我恨这样的事!”
“苔丝,”德伯继续循着自己的思路讲话,“不要这么说!这件事情当初在我身上发生的时候我感到自己是接受了全新的观点!你不相信我吗?你不相信的是什么呢?”
“你的转变。你的宗教花样。”
“为什么?”
苔丝的声音轻了下来。“因为一个比你好的人不相信这种事情。”
“真是女人的见识!这个比我好的人是谁?”
“我不能告诉你。”
“好吧,”德伯说话时的怨愤之情听来真是一触即发,“上帝不允许我说我自己是个好人——你也知道我不会说任何这一类的话。我是新近才弃恶从善的,确实;不过有时候新来的人是看得很远的。”
“不错,”苔丝情绪低落地说。“可是我无法相信你已经悔改成了一个新人。你所感觉到的这种醒悟,亚历克,我怕是不能持久的!”
苔丝说着这句话的时候,把靠着台阶的身子转过来,面对着亚历克·德伯,于是德伯的目光便在无意之中落在他所熟悉的苔丝的脸上和身上,注视着她。如今在德伯的内心,那些低级的念头不再活跃了,但是当然并没有被清除掉,甚至并没有完全被克服。
“不要这样看着我!”德伯突然说。
苔丝本来是不知不觉地做出这样的动作和表现出这样的神态的,这时候立刻把盯着德伯的那双又大又黑的眼睛的视线收回,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请你原谅!”说过这句话之后,她心里又泛起了以前经常产生的一种悲哀的感觉——自己由于天生这样一副容貌和身材,便不知怎么搞的总是做错事情。
“不,不!不要请求我原谅。不过,你既然戴着面纱来遮盖你美丽的容貌,为什么你不把它放下来呢?”
苔丝放下面纱,一边急急忙忙地说,“我戴面纱主要是为了挡风。”
“我这样对你发号施令也许显得粗鲁,”德伯接着又说,“不过,最好我不要太多地望着你。那样也许是危险的。”
“嘘!”苔丝说。
“哎,女人的容貌对于我曾经有过太大的控制力,所以我见了就不能不害怕!一个福音传道者本来跟女人的容貌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它使我记起我想要忘记的过去!”
亚历克·德伯说完这句话以后,他们两人在信步朝前走的时候便不再有很多交谈,而只是隔一段时间偶然说一两句话。苔丝思忖,不知德伯会这样跟着她走多远,但同时又不想直截了当地赶他回去。当他们走到一道篱笆门或者一个台阶的时候,常常看见那上面用红漆或蓝漆涂着一些《圣经》语句,苔丝问德伯知不知道是谁这样不怕麻烦把它们涂在那儿的。德伯告诉她说,涂写这些《圣经》语句的是由他本人以及在他那个教区里与他一起工作的同事所雇用的;涂写这些给人以提醒的语句是要不遗余力地感化如今数量众多的坏人。
他们终于到了名叫“十字架手”的那个地方。在这个荒凉和一片灰白的高地上,这地方是最凄凉的了。它与风景画家和风景观赏者所追求的美丽迷人的景致有着天壤之别,以致给人以另外一种美感,一种带悲剧色彩的反面意义上的美。这地方之所以有这样一个名字,是因为这儿竖着一根石头柱子,上面雕刻着一只人手的大致形状。这根孤零零的石头柱子粗糙、古怪,不是从附近任何一个采石场开采出来的。关于它怎么会竖在这儿,以及为什么要把它竖在这儿,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有些权威人士说,本来这里竖着一个用于祈祷的完整的十字架,现在这根柱子只是原先那个十字架的残存的下部一段;另有一些人说,目前这根石柱是完整的,竖在那儿是充当界标或者指示出一个聚会的地点。不管怎么说,无论它的来源如何,在此地凄凉的环境中竖着这么一根石柱,根据看见它的人的不同心情,它或者会显得邪恶,或者会显得一本正经,即使是感觉最迟钝的人路过这儿,也总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印象;这种情况过去存在,现在依然存在。
“我想现在我得跟你分手了,”当他们走近这块地方的时候德伯说。“今天晚上六点钟我得在艾博特-塞耐尔讲道,我必须向右边拐弯。你使我有点儿心烦意乱了,苔丝——我说不出是什么原因,也不想说。我必须跟你分手,使自己能镇定下来……你怎么现在说话这么流利了?是谁教你说得这么好的?”
“我遇到不幸,学到了一些东西,”苔丝闪烁其词地说。
“你遇到了什么不幸?”
苔丝对亚历克·德伯说了她的第一次不幸——跟德伯有关的唯一那一次。
德伯听了一时哑口无言。“这会儿我才听你说了,在这之前我压根儿不知道!”过了一会儿他喃喃说。“当你觉得不幸就要降落到你头上的时候,为什么不写信给我呢?”
苔丝没有回答;德伯打破沉默,又说:“那么——你我还会再见面的。”
“不,”苔丝说。“不要再来找我了!”
“我会再想想的。不过,在我们分手前先到这儿来一下。”德伯向上走几步到了石柱旁边。“这根柱子以前是一个神圣的十字架。我并不非常相信遗迹,可是我有的时候害怕你——远远超过你此刻害怕我的程度,其实你没有必要害怕我。为了使我胆子可以大一些,把你的手放在这只石雕的手上吧,发誓你将决不诱惑我——不用你的风度、你的魅力来诱惑我。”
“天哪——你怎么会提出这样一个毫无必要的要求!你说的那些我压根儿没有想过!”
“是的——可是发个誓吧。”
心里有点儿害怕的苔丝同意了德伯如此坚持的这么一个要求,把一只手放在石雕的手上发了誓。
“我觉得难过,你是不信教的,”德伯接着又说,“我还觉得难过,有一个不信教的人对你有这么大的影响,使你心神不定。不过现在我们不再多说了。当你心情松弛的时候,至少,我可以为你祈祷,我会的。谁知道什么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呢?我走了。再见!”
亚历克·德伯转身走向树篱中间的供猎人通过的篱笆门,不让自己再看一眼苔丝便纵身越过树篱,在开阔的高地上朝着艾博特-塞耐尔走去。从他的脚步可以看得出他心里很不平静。过了一会儿,他似乎想起了先前曾经有过的一个念头,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小书;这本书里夹着一封信,又破又脏的,好像是已经被看过许多遍了。德伯把这封信打开。信上的日期是好几个月以前,署名是克莱尔牧师。
在信的开头,写信的人对于德伯的悔悟和改变表示真诚的喜悦,并且对于德伯诚意跟他通信与他讨论这个问题表示感谢。在这封信里,克莱尔先生热情地再一次表示原谅德伯从前的行为,也对这年轻人有关自己将来的计划表示关心。他——克莱尔先生——本来非常愿意让德伯也进入他自己这么许多年来尽心为之服务的教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本来也很愿意帮助他进一个神学院去学习,但是,既然德伯也许觉得到神学院去学习会耽误许多时间因而不想这么做,那么他也就并不坚持非这么做不可。每个人都必须尽他最大的努力工作,所使用的方法呢,则应该是他觉得自己受到圣灵的激励后希望采用的方法。
德伯把这封信看了一遍又一遍,那神态似乎是在取笑自己。他还一边往前走一边看一张备忘便条上的几个段落,到了后来,他脸上的表情平静了下来,显然,苔丝的形象不再打扰他的思绪了。
在这个时候,苔丝正沿着山边的路走着,这是一条她回家的最近的路。走了一英里不到,她遇见一个孤单的牧人。
“我刚才经过一根很有些年头的石柱,那根柱子有些什么意义呢?”她问牧人。“以前它曾是一个神圣的十字架吗?”
“十字架?不。它不是十字架!它是不吉利的东西,小姐。从前有一个罪犯,就是在那里被吊死的,被吊死之前他先遭受折磨,一只手被钉在柱子上;他的亲属在他死后竖起了那根石头柱子。石柱下面埋着那罪犯的尸骨。人们说他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有时候他还出来游荡呢。”
这么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解释大大出乎苔丝的意料之外,她觉得浑身发抖,撇下那孤单的牧人自顾自往前走去。当她快要走到弗林科姆梣的时候,天已经开始黑下来了。在村口的小路上,苔丝朝一个姑娘和她的情人走近,不过他们并没有注意到她。他们两人不是在说那些不能让别人听见的悄悄话;小伙子的话比较热烈,姑娘与之应答的声音清楚而随意,飘荡在清冷的空气中,在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侵入的一片沉沉暮色中让人听了得到安慰。有那么一会儿,这一对情人的声音使苔丝感到高兴,不过后来她想到,他们现在的约会起因于一方对于另一方的吸引力,而同样的吸引力正是她自己的苦难的序幕,这样一想她也就不再觉得高兴了。当她走近他们两人的身旁时,小伙子害羞地往一边走开去,那姑娘平静地回过头来,认出了她。原来这姑娘是伊丝·休特;她对苔丝这次出门结果如何十分关心,因此立即把自己的事情丢到了一边。苔丝没有把自己这次出门的结果向伊丝解释清楚,伊丝是个机敏的姑娘,在这种情况下便开始谈起她自己的恋爱情况来,苔丝刚才目睹的正是她的恋爱小事的一个方面。
“他是安姆比·西特林,过去有时候常常到陶勃赛来帮忙的,”伊丝大大方方地解释说。“他打听到我来了这里,就跑来找我。他说他爱上我已经有两年了,不过我还没有明确答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