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 | 收藏 |
第二章 鸭子小白,只是回到了它的大海
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 作者:蔡崇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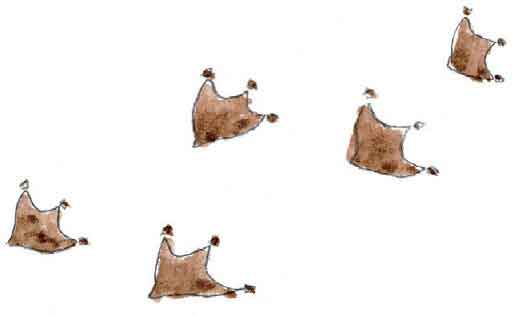
我很笃定,那个自称是我阿太的老奶奶,一定是骗我的。毕竟,要赔偿我一个外婆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实现。虽然我才五岁,经历的事情确实不多,虽然从书里、从外婆那里,听说过这世界还有许多稀奇古怪、匪夷所思的事情,但我的生活中,还从来没有发生过。
除非它真真实实地发生一次,否则,我不相信。
但外婆葬礼后的第二天,我还是一大早就醒了。
我告诉自己,我肯定不是因为等那个阿太才醒的。我还想着,一定不能让母亲或者姐姐知道,我和阿太有这么一个约定,而且我竟然还因为期待着这个约定,早早地起床。她们如果知道了,肯定会觉得我幼稚。我可不愿意被人说幼稚。
毕竟早起得有些不寻常,正在煮地瓜汤的母亲有些担心,问我:“怎么了?”
我假装若无其事:“就是醒了啊。”
母亲小心翼翼地问:“在想外婆?”
我说:“没有啊。”
她疑惑地看着我,我只好继续解释:“我在等一个骗子。”
“骗子?”母亲的目光充满了不解。
“是啊,一个骗子。”
“是谁呢?你为什么要等一个骗子?”
我想了一下,说:“我就是要看她能怎么骗我。”
“那她来了吗?”母亲也好奇起来。
“还没。”我说,“也许,连要来找我这个事情,都是骗我的。”我气呼呼的。
该去上学了,母亲拿出箩筐和扁担。姐姐坐到后面,我却不愿意坐进去了。
“为什么不坐了?”母亲问。
我心里想,坐箩筐是要去找我外婆,我现在没有外婆了,就不坐箩筐了。
但我知道不能和母亲这么说,她听后会难过的。我便说:“我不喜欢了。”
那天虽然起得早,但我穿衣服很慢、洗漱很慢、吃地瓜汤很慢……母亲着急送完我们,还得去上班,看我这样磨蹭,有点不耐烦:“你今天怎么了?为了等什么骗子?”
“没有啊。我本来就知道,那个骗子压根儿就不会来。”
说完这句话,我莫名有点气愤,我也分不清,到底是生气那个骗子,还是生气自己竟然相信她,于是转身要走。母亲突然拉住我:“这个……有个事情得和你们商量下。”
我和姐姐看着母亲:“什么事?”
“以前你们放学了都到外婆家等我,今天放学了,想在哪儿等我呢?”这句话,显然母亲觉得很烫嘴。
母亲这样一问,我顿时蒙了。是啊,外婆真的没有了。我再次悲伤起来。
最终,我和姐姐是在学校等着母亲的。
以前一放学我们就跑到外婆家,感觉时间过得很快。但那天才知道,母亲要我们放学很久之后才到。
姐姐拉着我,坐在路边等,像以前那样。路上人来人往,同学们都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父亲母亲牵着走。我们没有。
母亲充满歉意地来了,我说不清楚心里是什么滋味,闷着头往家的方向走。
我走得越来越快,后来干脆跑起来。姐姐和母亲在后面边追边喊,我就是不肯回头。
我找对路了,我看到家门了——家门口空空荡荡的,没有人在等。
“骗子。”我察觉到,其实我还是期待那个“骗子”会来。我心里反复咒骂着。
母亲追上来,抱着我说:“我知道黑狗达难过了,黑狗达没有外婆了。”
我哭着纠正母亲:“我不是难过,我是生气,那骗子没有来,那骗子真的骗了我。”
究竟过了多少天,我也忘记了。外婆去世后,日子又变得孤独、漫长,长到我恍惚觉得,风的流动在变慢,每一秒的速度都在放慢。我甚至感觉有些恐惧:我年纪还这么小,还有那么多时间,我该怎么熬呢?
我已经不再早起,相反,自从等了一周多那个“骗子”都没来后,我突然泄了气一般,任凭母亲怎么叫、姐姐怎么拉,都像个瘪掉的气球,赖着起不来。
直到那一天。
一大早,估计还不到五点吧——邻居家养了三只鸡,有只公鸡总想抢其他鸡的风头,五点不到就乱叫起来,我叫这只公鸡“坏喇叭”。那天,“坏喇叭”还没响,母亲还没起床准备煮地瓜汤,就听到有人在敲我家的木门。
一上来就是三下,咚咚咚;停了三秒,然后又三下;停了两秒不到,又三下——敲得理直气壮,还有点不耐烦。
母亲喊:“谁啊?”这么不礼貌的敲门声,让她有点不高兴。
“我啊。”回答的声音依然理直气壮,甚至带着责备,语气里似乎蕴藏着“难道不知道我是谁”的不开心。
“你谁啊?”母亲也恼了,哪有人不礼貌得这般扬威耀武。
“我啊,赶紧开门。”门外的人似乎生气了。
母亲嘟嘟囔囔地起床,打开门,是阿太。
她左手拄着一根木头拐杖,右肩上用扁担挑着前后两个箩筐,箩筐上盖着藤编的罩子。
“外婆?”母亲有些吃惊,“你怎么来了?还挑着什么啊?”
阿太对母亲笑一笑,挑着担子径直走进来。她把两个箩筐往地上一放:“这不,我赔黑狗达外婆来了。”
“什么?”
阿太也不愿意多解释,冲着屋里喊:“黑狗达,赶紧起来,我赔你外婆来了!”
“骗子来了!”我本来是赖在床上的,听到“赔你外婆”,一下子跳起来。
“谁是骗子啊?”阿太看来听见了,显得更不高兴了,干脆挑着担子走进房间,把两个箩筐往我床前一放,“喏,赔偿来了。”
母亲也追进房间里,难以置信地问:“外婆,你要赔黑狗达一个外婆?”
“是啊。”阿太依然回答得理直气壮。
“这怎么赔啊?”母亲问。
是啊,这怎么赔啊?我边怀疑边激动起来,跳下床,俯下身,低头看那两个被藤罩盖住的箩筐。
藤编的罩子有些缝隙,但天还不亮,天光很薄,我只能看到里面隐隐有什么在动。
这筐里的东西,还是活着的东西。这些活着的东西,能赔我一个外婆?我不相信地看着阿太,不知是因为激动还是紧张,一直不敢伸手去打开。
阿太一脸笃定地看着我:“当然啊,你快打开。”
母亲和姐姐也跟着激动起来,她们都凑到跟前。
我的心怦怦地跳,伸出手,小心翼翼地掀开藤罩。
我看到了,是一团一团一团,很多团巨大的黄色蒲公英。我知道了,是鸭子,出生不久的鸭子。

“是鸭子?”我失望地看着阿太。
阿太应该是早知道我要这么问,她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就是,就是鸭子。你外婆暂时会在这里面。”
“骗子!”我还是难过地叫嚷起来,“就知道你是骗子。”
阿太没有生气,反倒乐呵呵地说:“你看看你,傻孩子没懂吧。来,我说给你听。”
说完,便上来要抱我。
我急忙往后退,阿太笑嘻嘻地说:“真生气了?不生气啊。你听我说就知道了。我那天和你承诺后,就每天晚上到梦里去等,等着你外婆来找我。我也不知道你外婆去世之后到底忙什么,等了好多天,终于有天晚上她来梦里找我了。我一看到她,就赶紧说,百花啊,你走了黑狗达可难过了,黑狗达追着我要赔他一个外婆,我拿什么赔啊?
“你外婆说,阿母,你把自己当作赔偿,帮我赔给黑狗达就是了,你代替我去照顾他。你外婆说,黑狗达和他姐姐很可怜,自小就没有人疼。
“我说,百花啊,我内外孙这么多,顾不过来啊。我是想代替你去赔偿,但我需要时间,毕竟,我现在还住在郭岑村,带着另外几个曾孙。
“我发愁了好一会儿,想到一个主意。我说百花啊,不如你找个方法先安安身,陪黑狗达一段时间,然后,我也尽快过来。
“梦里你外婆看上去很为难,她这么好地过完一生,本来可以升天享福的。但她还是点点头,说,她去和神仙商量下,看能怎么留个几年来陪你。你看,她多爱你。”
阿太说得非常认真且笃定。
我听着阿太荒唐的解释,不停地摇头,嘴里嚷着:“不可能,这都是假的!”
阿太不管我的吵闹,继续往下说:“又等了好多天,你外婆才再来梦里找我。她说,她将在这一周星期三一大早,安身在东石镇东郊综合市场胡子七家刚孵出的一只鸭子身上。她说,可惜这只鸭子没法说话,她估计也没法带着人的记忆来。她不能来找我,让我去寻她。”
阿太说得斩钉截铁:“咱们东石镇,早市四点多就开始了,我住在离镇上七八里地远的郭岑村里,年纪大了,还拄着拐杖,三点就赶到综合市场胡子七家门口。他店门一开,我就冲进去找你外婆。为了不出错,我把所有刚孵出的鸭子都买了,你数数,十二只鸭子。”
这时阿太用手捅了捅母亲,挤眉弄眼的。
母亲正听得愣神,忽然明白过来,慌乱地接了话:“但是外婆啊,我阿母会寄身在哪只鸭子身上呢?”
阿太笑逐颜开地回答:“这我也不知道,黑狗达他外婆说了,黑狗达那么爱她,肯定能找出来是哪一只的,肯定能感觉到的。”
阿太凑到我跟前:“难道你感觉不到你外婆?”
这个故事一听就很荒唐,我不相信,但阿太这么一追问,我的心却一下子慌了:难道是因为不够爱外婆,所以我感觉不到她?
我还在犹豫,一旁的姐姐倒激动地叫起来:“我好像感觉到外婆了!我就知道,外婆舍不得我们,外婆还会来陪我们。”
我一听姐姐这话,鼻子一酸,眼泪差点刹不住。
就这样,鸭子们被留下来了。
阿太和母亲从家里各个犄角旮旯找来木板、竹子,在天井中间隔出一个活动区域,又用纸箱和布做好了窝。
安顿好鸭子,阿太满意地看着,对它们认真地交代起来:“黑狗达和姐姐就暂时请你们陪了啊,我很快忙完,你们坚持一下啊。”
她又对我说:“记得你外婆偶尔会借其中一只鸭子的身体来陪你,你可得好好珍惜啊。”
说罢,她挑起箩筐,拄着拐杖,风风火火地走了。
我看了看往远处走去的阿太,看了看鸭子们,又看了看母亲、姐姐。
我问母亲:“阿母,你信吗?”
母亲张了张嘴,犹豫着。
姐姐回答:“我信的,外婆那么爱我们,为了我们,即使变成鸭子,她肯定也愿意的。”
我看着母亲,追问道:“阿母,你认识阿太比较久,阿太以前对你撒谎过吗?”
母亲想了好一会儿,终于知道怎么说了:“你阿太一直一直很爱她的所有子孙,她愿意为我们做任何事情。我相信,你外婆也一样。”
“那如果是真的,我们要怎么照顾外婆鸭子呢?”姐姐问。
“这个我倒是知道。”母亲说。
幸好,那是一大早,虽然折腾了半天,但离母亲去上班、我和姐姐去上学,还有点时间。
母亲赶紧教我们怎么照顾鸭子。首先,鸭子得吃。鸭子吃杂食,谷物、蔬菜、草、鱼都可以。那时家里穷,用稻谷和菜喂鸭子太奢侈,只能先拿点玉米,然后母亲带着我们出门寻鸭子能吃的草。
当时东石镇还没怎么开发,虽然我家住在镇里核心的石板路旁,但屋前屋后都还没有人家盖房子,长满了各种杂草。我们在家附近寻了一箩筐鸭子能吃的草。
母亲说:“晚上想想办法,可以去港口边的市场,讨些人家不要的小鱼小虾,给鸭子们加餐。”
然后,母亲继续说:“鸭子需要好多水,它们爱喝水也爱玩水。”
那时候塑料制品不多,能盛水或者菜的盆子对我家来说还算珍贵。母亲在厨房里翻找了许久,觉得合适的只有水盆。但家里就这么一个大盆,她端着盆看着鸭子,犹犹豫豫的。
姐姐看出母亲的犹豫,附在我耳边说:“弟弟,你去把盆拿给鸭子们,要不外婆鸭子怎么办?”
母亲说,鸭子养在天井是非常正确的事情。天井是有排水口的,鸭子不管屎尿,可以想拉就拉。她交代我们:“每天谁路过,就打一桶水冲冲,要不,咱家可要臭死了。”
听到这,姐姐困惑了:“外婆不可能愿意来鸭子身上的,外婆那么爱干净……”
把该准备的准备好,母亲抬头看了看天光,知道时间很赶了,迅速地吃了地瓜汤,催我们也赶紧吃。那地瓜汤还有些热,我端着地瓜汤蹲在天井,边看鸭子边吃。姐姐觉得有意思,也端着地瓜汤蹲在旁边。
姐姐问:“弟弟,你知道外婆是哪只鸭子吗?”
我摇了摇头,说:“外婆不一定在了。”
姐姐好像没听见我的话,欢快地指着其中一只:“你看,这只走路一跛一跛的,像外婆。”
我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姐姐,哪只鸭子走路不是这样的?”
要出门了,母亲把家里的木门关上,我还是忍不住回头,透过即将关闭的门缝,最后看了一眼鸭子们。
母亲看到我的目光,偷偷笑了一下。我赶紧装作一副冷酷的样子。
那天路上,姐姐开心地边走边跳,嘴里还哼着歌。母亲则看着我和姐姐,脸上一直挂着笑容。我不知道她在笑什么。
我提醒自己一定要板着脸,这样才不会让母亲误解我真信了阿太的话,但其实心里莫名暖暖的:难道外婆真的会来陪我?要不我怎么这么开心呢?
那一整天,我不断地想起那群鸭子。
太阳出来了,阳光照在天井里,那一只只鸭子应该暖洋洋地睡着懒觉吧。晒久了,鸭子们应该渴了,也可能在快乐地喝着水吧。到中午了,那些玉米应该被它们吃完了,不知道那些草,它们愿意吃吗?又想着,现在估计屎尿拉得到处都是,如果吃了草,可能拉出的是绿色的……
终于熬到下午放学。我和姐姐在校门口又等了很久,母亲才终于出现。我刚想表达不快,母亲赶在我说话前,拿出一袋小鱼给我。
拿上那袋小鱼,我假装波澜不惊地往家的方向走。但越走越快,最终,我和姐姐都不知不觉地跑起来。
到家了,推开门,鸭子们听到开门声,先是害怕地头一缩,又缩成一团团蒲公英。我对姐姐示意动作小点,我们蹑手蹑脚地走到天井,轻轻地坐在天井的石头上看着它们。
先有胆大的鸭子抬起头,快速地瞄了我们一眼,然后又快速地缩了回去。又一只抬头,偷瞄,缩头……慢慢地,它们一只只伸长脖子,盯着我们看。
有只鸭子嘎的一声。
它在说什么呢?
另外一只也嘎的一声,然后一只只,开始嘎嘎嘎地互相攀谈起来。
姐姐问:“它们在干吗?”
“它们估计在讨论我们是谁。”我说。
姐姐对鸭子说:“是我啊,外婆不记得了吗?”
有只鸭子嘎的一声。
姐姐开心地叫:“弟弟,那是外婆在和我们说话吗?”
“我怎么知道?”我说。
另外一只鸭子像插话一样,冲我们嘎嘎嘎。
姐姐说:“还是这只呢?它在笑我们认错了吗?”
母亲提醒我们该做作业了。我原来是在厅堂的餐桌上做作业的,但做了一会儿作业,我就想转过头看看鸭子们,写了几个字,又想看看鸭子们。后来,我想了想,搬来小板凳,放在鸭子旁边,书放在板凳上,人坐在地上。姐姐觉得好玩,也把作业搬过来。
要吃晚饭了,我还是舍不得离开鸭子们,干脆把晚饭端到刚刚做作业的小板凳上。
但终究要天黑的,晚上终究要睡觉的。
母亲问:“所以你们打算在天井边上打通铺,陪鸭子们吗?”
我问:“可以吗?”
母亲说:“但是你们不觉得臭吗?”
姐姐说:“不臭不臭,我一点都闻不到。”
此刻,我好像也恍然大悟:我似乎开心得都忘记臭味了。
到了周五,鸭子们已经很熟悉我们和家里了。只要一听到开门的声音,它们就开心地嘎嘎嘎。我知道,这个应该是:“你们回来了啊,回来了啊。”
我们一走近,它们就看着空空的盆,对着我们叫:嘎嘎嘎嘎嘎嘎。
这个应该是:“好饿啊好饿啊。”
我还发现,姐姐开始试图和它们说话。
姐姐会坐在天井边,对着鸭子说:“鸭子啊,我的鞋子破了个洞,但还能穿,不过我真想有双新鞋。”
有鸭子听到了,追到她跟前,说了声嘎。
姐姐高兴地说:“我会有的是吗?鸭子啊,其实我还想买个发夹……”
母亲在家里也总有忙不完的事情,她抱着衣服要去洗,看到正在和鸭子说话的姐姐,对我笑着说:“你姐听得懂鸭子们说什么吗?”
我说:“可能懂吧,要不她怎么聊得这么开心。”
周日一大早,可能也就四五点钟,家里的门被重重地敲响。先是三下,然后再三下,又三下。
母亲被吵醒了,嘴里嘟囔着:“肯定是你们阿太。”
姐姐也被吵醒了,边翻身边抱怨:“阿太怎么老这样。”
母亲打开门,阿太一走进来就兴高采烈地嚷起来:“你们认出外婆了吗?”
被吵醒的我,有点起床气:“怎么可能认得出?阿太你自己也肯定认不出来。”
阿太说:“我早认出来了,但我不能说。”
姐姐对着我偷偷翻了个白眼,轻声地说:“弟弟,这个阿太老吹牛。”
母亲问:“外婆,今天来干吗?”
阿太宣布:“我今天可以陪黑狗达和姐姐到中午。”
然后她对我们说:“你们开心吗?”
我和姐姐愣了一下,我知道出于礼貌我应该说开心的,但是这个阿太怪怪的,而且我还不知道外婆的事情她是不是骗我,所以我实在说不出开心。
还是母亲打了圆场:“当然开心啊。”
不过,阿太随后说的事情就让我真的开心起来了。
阿太用很隆重的语气宣布:“今天我教你们带鸭子们去散步。”
“啊?”母亲愣了一下。
阿太嫌弃地说:“你连这都不知道吗?”好像母亲不知道的是很重要但很早就应该知道的事情。
母亲红着脸问:“狗能遛,鸭子也能遛?”
阿太严肃地纠正:“那不叫遛,叫一起散步。鸭子可是全世界最喜欢一起去散步的动物。”
阿太似乎意识到了更严重的问题,她突然转过头对我们说:“怪我,我在你们阿母小的时候,没有陪她,没告诉她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其实所有动物、植物我们都可以交朋友的。知道这一点后,你们就会发现,这世界有太多朋友可以交了。如果不知道这一点,你们会以为,这世界可太孤单了。”
阿太直接说出她的规划:母亲、我、姐姐,必须在半个小时内吃完早饭并且洗漱完,然后她带着我和姐姐学会和鸭子散步。
我们各自忙碌,阿太则走进鸭圈里,冲洗着地板和鸭子,嘴里发出啄啄啄的声音。有鸭子回应她,她对那只鸭子示意了一下,又发出另外一种声音,另外的鸭子也似乎加入了聊天。
我问母亲:“阿太是懂得和鸭子说话吗?”我知道这个问题很奇怪,但对这样的阿太来说,一点都不奇怪。
母亲点了点头:“好像是,我从小就记得,她对着树,对着花,对着草,对着头顶飞过的鸽子、路过的狗都要打招呼。”
“反正你家阿太,从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就挺神奇的。”母亲最后这么总结。
一切准备好了,鸭子们也早已经被阿太洗得干干净净。
阿太去厨房里掰了片菜叶,然后问:“大家准备好了吗?”
我本来想回答,但突然有点恍惚——阿太说的“大家”,好像不仅是我们。
姐姐兴高采烈地回答:“好了!”
果然,阿太点点头,转过身对着鸭子们再次确认:“大家准备好了吗?”
直到有鸭子先嘎了一声,然后鸭子们嘎嘎嘎起来,阿太才觉得,“大家”可以出发了。
阿太再次走进鸭圈里,左手拄着拐杖,右手拿着那片菜叶。她躬下身,让菜叶慢慢地在鸭子嘴边移动,一只鸭子跟着她的右手,另一只也跟上来。
阿太拿着菜叶在鸭圈里划着圈,鸭子们一只跟着一只,追着阿太的手在鸭圈里走出了一条线。
阿太说:“黑狗达,你把鸭圈的门打开,我要带它们出来了。”
走出鸭圈时,阿太把身体摆正,拿着菜叶的右手对着鸭子们,鸭子真的一只只跟着她走了出来。
我兴奋极了,着急地跑过。队伍后面的鸭子看到冒冒失失的我,吓得一个踉跄,跌倒了,赶紧站起来,追着前一只鸭子继续走。
阿太走在前面,因为拄着拐杖,身子一拐一拐的。鸭子们跟在她身后,屁股一甩一甩的。
阿太走到大门口,招呼我和姐姐:“咱们出发吧。”
姐姐担心地问:“出去了,鸭子会不会一下子乱跑?”
阿太说:“不会的,只要第一只鸭子跟着我,后面的鸭子就会都跟着。”
阿太说:“鸭子可比人更早知道信任同伴。”
我和姐姐还是有些担心,于是跟在鸭子的后面,想着如果跑乱了,和阿太一前一后包抄,还有机会把它们都围住。
阿太拄着拐杖走在前头,鸭子们摇头摆尾地走在中间,我和姐姐小心翼翼地跟在后头。
阿太带着我们和鸭子走出家门,走到石板路。有人路过,鸭子们平时很少见到除我们之外的人,有点惊慌,它们追着阿太,追得紧紧的。可能太紧张了,有只鸭子脚一软,摔倒了,另外一只也跟着摔倒。
路过的人走近了,对我们说:“你们出来散步啊?”
我想,他说的“你们”,包括阿太、我、姐姐和鸭子们。我很喜欢这样的称呼。
阿太说:“是啊,你也散步啊?”
那人说:“是啊。”
等人走远了,我好奇地问阿太他是谁。
阿太说:“我不知道啊。”
我问:“不知道你怎么招呼打得这么亲切?”
阿太说:“咱们都是这块土里长的人,当然要亲切啊。”
阿太带着我们走到妈祖庙边上,停了下来:“黑狗达,该你带鸭子们散步了。”
我愣了一下:“但鸭子会听我的吗?”
阿太边说“会的”,边把菜叶交给我:“你要让它们知道,你和它们是一起的,它们就会跟你一起了。”
我拿着菜叶,莫名紧张,僵直着身体,感觉都要忘记怎样走路了。
阿太在旁边喊:“慢点!先让鸭子知道跟着你。”
我转过身,看到排头的几只鸭子,一会儿困惑地看着阿太,一会儿困惑地看着我手里的菜叶。
我赶紧拿菜叶晃了晃,嘴里说:“来来来,咱们一起走啊。”
鸭子们还在困惑。我想了想,脸红着,压低声音模仿鸭子嘎嘎叫了几声。
姐姐听到了,边笑边挠头。阿太也眯着眼睛笑起来。但鸭子们听到了,抬头看着我,然后,跟着我走起来。
我带着鸭子只走了一小段路,姐姐就迫不及待地说:“该轮到我了。”
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接近中午。母亲煮好了午饭,招呼我们吃饭。
阿太抬头看了看天,说:“哎呀,太阳你都走到这儿了啊,那我得赶紧回去了。”
我想,果然,阿太是连太阳也要说话的。
阿太风风火火的,连吃饭也是。她连吃根青菜,都咬得非常用力。
我还是忍不住问她:“阿太,你好像和什么都能说话。你刚才是在和太阳说话吗?”
阿太边用力吃着饭,边说:“没有没有,我认识它们,但我不知道我说的话它们能不能听懂。”
“听不懂为什么还要说话呢?”
“我都活了七八十年了,也认识它们七八十年了,这不,都是老朋友了。即使听不懂,也不妨碍朋友间要常说说话吧。”
说完,阿太转过头对那群鸭子说:“对吧?”
吃完饭,阿太拄着拐杖,风风火火地和我们(包括鸭子)打完招呼,就要回去了。
她说:“下一周,咱们一起去河边玩。”
就这样,周一到周六,鸭子陪着我和姐姐做作业、吃饭;周日,阿太一大早就赶来我家。
阿太带着我们(包括鸭子),先后去了池塘、树林、田里。那时候的每周末,东石镇里经常看到一个老人拄着拐杖,带着一群鸭子和两个孩子,浩浩荡荡地嬉闹过去。

我的这群鸭子朋友,也慢慢褪去黄色的绒毛,长出白色的羽毛来。它们一只只肥嘟嘟的,开开心心的样子,出门的时候,还经常得意地一路叫嚷。
只是,我和姐姐一直没找出哪只鸭子才是外婆。不过我想,反正外婆肯定是来陪我们了。
我记得那个台风的名字,叫海燕。
我记得那天是周四,风开始刮得有些紧。那种紧,人是很容易感受到的。平时东石镇的风都是轻轻柔柔的,还经常被太阳晒得很蓬松,像刚打好的棉被那种松。那天的风,却湿漉漉、硬邦邦的,吹过人的感觉像爪子划过一般,一不小心,抓痕都要出来了。
雨已经先下了许多天,像在为台风预告。因为台风天,学校决定提前放学。
放学的时候,老师特意交代,台风最快傍晚到,最晚明天凌晨,大家回家后尽量不要出门。老师还说,明天就不上学了。
我们走出校门的时候,母亲就在等着了。她说,工厂也让大家赶紧回家检查,免得台风来了要出事。
那个时候,每次台风来,东石镇几乎所有人都要紧张的——东石镇的房子大都是石头砌成,几乎都是要漏雨的。更让人担心的是,房子都有某些部分是土垒的,水一泡风一刮,有些便要倒塌。
我们住的平房,屋顶是石条砌成的,难免有许多缝隙,稍微下点雨,整个房子就如水帘洞一般。让人担心的还有下厅堂。当时父母没钱建好整栋房子,下厅堂就凑合着垒了点土墙当隔断。每次台风,总感觉土墙就要倒了。
因为台风天,天井鸭子住不得了,台风那种雨巴掌一样打下来,肯定要把它们打蒙的。上厅堂供奉着神明和祖先,还摆着餐桌椅,鸭子们因此只能暂时搬到下厅堂。
一个晚上的胆战心惊,台风最终是在晚上十点左右袭来的。那时候我们都睡下了。我听到,屋顶先是像有人撒了一堆豆子,然后安静了片刻,又撒了一圈豆子,突然一股不知哪儿来的粗壮的风,带着子弹一般的雨到处扫荡,紧接着是哗啦啦哗啦啦,一盆盆水朝我们倒下来。该漏雨的地方,果然都漏了,还好我们经验丰富地准备好了各种锅碗瓢盆,还算精准地接住了。
我的床上,就有五个漏雨点。五个碗盆放在床上不同的位置,刚好规定出我能睡觉的姿势,大概类似于一只狗蜷缩的样子。
我认真地听着,有风声和雨声,但没有鸭子们的叫声。我想,它们应该睡得很甜。
大概早上五点多,我又听到急促的敲门声。咚咚咚,三下,再咚咚咚……我知道是阿太。全世界只有她这样敲我家的门。
但阿太不都周日才来吗?而且,台风才刚过去……我赖在床上想。
母亲去开门。
我听到母亲说:“外婆,你怎么台风刚过就来?多危险啊。”
阿太激动地说着:“是哦,这次台风可真厉害,我从郭岑村一路数过来,几十棵树倒了,有好几户人家墙壁泡垮了,老街有一段水都淹到我肚脐眼了……”
母亲这才发现,阿太的下半身都湿漉漉的。
阿太走到姐姐的房间,看了看还在赖床的姐姐。又走到我的房间,看着我也躺在床上,喜滋滋地说:“今天就多睡会儿。反正你们哪儿都去不了。”
说罢,她往下厅堂走去,现在轮到看鸭子了。
我本来想继续睡一会儿,却听到阿太说:“不对啊。”
我的耳朵马上竖起来了,听到母亲问:“怎么了?”
“鸭子蔫了。”阿太说。
我急忙跳下床,到下厅堂一看,一只只鸭子都蔫蔫的,甚至有几只已经抬不起头了。
阿太对着鸭子们啄啄啄地叫,它们也不嘎嘎嘎地回了。
“鸭子怎么了?”我心急如焚地问阿太。
“可能是鸭瘟……”阿太最终说。
“但鸭子们没去哪儿啊。”我有些接受不了。
阿太一边把一只只鸭子分开,一边对我说:“黑狗达不要想太多,就是下了很多天的雨,可能是哪里的污水通过沟渠涌到咱们家天井,鸭子不小心喝了。”
“那鸭子没事吧?”我希望阿太说没事。
但阿太说:“这是鸭子会相互传染的病,咱们得赶紧把它们分开。看能活几只吧。”
我们听从阿太的指挥,抱起一只只鸭子,先用清水冲洗,然后仔细地用布擦干,再一只只分别安放在不同地方——这样鸭子们才不会相互感染。
当时家里实在没有多的地方放鸭子,有的放在厅堂里用木板隔开的几个空间,有的放在厨房堆放杂物的柜子里,有的放在厨房灶台边……可能是身体太虚弱,缩在一起的时候,鸭子们都不愿意叫唤,但一把它们分开,有几只鸭子就挣扎着嘎嘎叫起来。
姐姐问阿太:“有没有办法让鸭子们不叫?它们得省点力气让自己好起来。”
阿太说:“没有办法的,这就是鸭子。鸭子是最认同伴的动物了。就让它们叫吧,它们听到彼此的叫声,心里会安定些。”
终于清洗、安置好所有鸭子,我沮丧地蹲在天井边。阿太走过来,对我说:“黑狗达啊,这世界确实经常会有这种乱七八糟让人难受的事情。”
我看着阿太,以为她要说安慰我的话,但阿太继续说:“而且以后还会有,甚至更让你难受、让你不能理解。但这就是这个世界啊,有这些东西,就像有台风、有雨、有风一样自然。”
“所以呢?”我问阿太。
阿太笑眯眯地说:“所以咱们要拼命珍惜好的部分。这大概是唯一能做的事情吧。”
我忘记自己为什么会睡着了,再醒来的时候,天已经放晴,大片大片的阳光似乎着急拥抱这个刚经历风雨的世界。
我先是怀疑,难道昨天的台风是场梦?然后,我感觉到不对了——我没听到鸭子的叫声。
我去厅堂找,厅堂里没有。我到厨房找,厨房里没有。我急忙喊母亲:“阿母,鸭子呢?”
母亲是和阿太一起来的。
阿太拄着拐杖,还是对着我笑眯眯的,像是外婆葬礼上那般。我有不好的预感。果然,阿太说:“黑狗达不难过,鸭子们离开了。”
我鼻子一酸,眼泪已经涌进眼眶里。
阿太赶紧继续说:“但咱们救活了一只,我想,那一只就是你外婆特意来陪你的。”
我还是哭了:“阿太又骗人。”
阿太说:“我没有骗人,不信你问鸭子,看它是不是你外婆。”
说罢,阿太便从箩筐里捧出最后的一只鸭子,往我怀里递。
鸭子一靠近我,就看着我嘎嘎地叫。我知道,那不是外婆在和我说话,而是它找不到自己的同伴,伤心地呼唤。它或许已经叫了一个早上,但没有听到任何回答。我记得的,阿太说,鸭子是最认同伴的动物了。
我抱着它,说不出话。它看了看我,对着我又嘎嘎叫了几声。
剩下的这只鸭子,名字叫小白。
在失去那群鸭子后,我察觉到一个事情:如果没有名字,再宝贵的东西,都只是东西。比如这群鸭子,它们就只是“鸭子”,是一种归类而已。但我已经认识它们了,我想念的不是鸭子,是它们。
然后我知道了,命名是如此重要的事情。我还知道了,这名字不能是随意地安放什么东西在那个灵魂身上。最好的名字,应该是对于它们灵魂的样子的形容。
剩下的这只鸭子之所以叫小白,是因为它浑身上下都是雪白的羽毛,它看着我的眼神如此洁净如此纯粹。还有,它和我一样,是个这世界的新手,是一张孤独的白纸。
自从同伴们不见后,小白难过了许多天。一开始它一直悲伤地躺在暂时安身的箩筐里,身体很虚弱,但不忘每隔几分钟,就抬起头对着天空叫几声,叫完仍旧抬着头,似乎在等待什么。我知道的,它在等同伴们的回应。
过了几天,它身体好些了,便跳出箩筐,开始了对整个房子的搜索。每到一个房间,便焦急地叫唤,等不到回应,便开始每个犄角旮旯地搜索。当然是搜索不到的,但它还是认真地一个角落一个角落地搜索过去,每到一个角落都要叫唤几声,等待一会儿。最终离开那个房间的时候,还总要转过身再次叫唤几声。
它仿佛在问:“你们在哪儿啊?在哪儿啊?”
这样的搜索,持续了好几个星期,突然有一天,小白不找了。它除了吃喝拉撒,就窝在门口。
我知道它在干什么:它和当时刚失去外婆的我一样,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不知道如何面对突然空荡荡的时间。
姐姐问我:“怎么办呢?”
我想了想,说:“咱们就陪着它。”
姐姐问:“这样有用吗?”
我点点头,没和姐姐说——失去外婆后,我需要的也是一样的东西。
吃饭的时候,我端着饭碗蹲在小白的窝旁边吃;做作业的时候,我坐在天井的地上,用凳子当桌子,陪着它……我想,只要一直这样挨得近一点,小白就知道我是要陪它吧。
一开始小白并不搭理我,我努力着我的陪伴,它孤单着自己的孤单。过了三四天,小白困惑我为什么还在,试探性地对我嘎了一声。我当时正在做作业,开心地模仿着对它嘎了一声。我当然不知道鸭子的语言里,嘎一声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确定自己的一声嘎,又回复了什么。
小白似乎没想到,眼睛直直地看着我,看了好一会儿,它突然站起来,走出它的窝,慢慢地走向我。最终,它在我旁边蹲坐下来。
我激动而忐忑,担心多余的动作会吓到它,于是假装自己还在认真做作业。过了一会儿,我偷偷地缓慢地把头转向它,用眼睛的余光打量它。我看见它睡着了。睡得似乎很安心。
我知道,小白又有伙伴了。我也有伙伴了。

鸭子的优点是认朋友,缺点是太认朋友了。
自打小白那天认我做朋友后,就每分每秒都想跟着我。我走到东,它跟着走到东;我走到西,它跟着走到西。
晚上我得睡觉的时候,小白也跟着我,想进我的房间。母亲不让,把我的门关上,小白就蹲在门口一直叫嚷。我都是等到夜深了,母亲睡着了,才悄悄起床把门打开,招呼小白尽可能安静地进房间来。小白似乎懂得这是需要保密的事情,它看到我,愣是不让自己兴奋地叫出声,张着长长的嘴巴,似乎在笑。门才开一个小缝它就钻了进来,第二天甚至母亲还没醒来就赶紧溜出去。
只是鸭子是直肠子,半点粪便都留不在自己的肚子里。每天母亲看着我房间里那青青绿绿的一摊摊鸭屎,自然便知道是谁来过了。
更窘迫的,是我要上学或者去上厕所的时候。
当时东石镇上有洗手间的人家并不多,人们都得去就近的公共厕所。每次我感觉要上厕所,就发愁地看着一直黏着我的小白。
我试过一次次认真地和小白解释:“我要去上厕所,很快就回来。你真的不能跟着,不是担心你跑丢或者跟丢,而是咱们公共厕所是一个个坑,我很担心你一不小心掉进哪个坑里,我怎么去捞你?”
小白看上去好像很认真地听了。但我一往门的方向走,它立刻就追。我刚打开一条门缝,自己还没出去,小白就子弹一般穿出去了,末了还困惑地看着院子里无可奈何的我,困惑地嘎几声,意思是:“你怎么还不出来?”
最终,都得让姐姐或者母亲抓着小白,我才能够脱身。只是每次我急匆匆想马上冲去厕所的时候,回头看看小白那不解的表情,总还是忍不住想安慰它几句。有几次,我差点拉到裤子里了。
上学就更麻烦些,因为母亲、姐姐和我同时出门,没有人能抓着小白等我脱身。我们最终想到的办法,是主打个出其不意。临近出门的时候,三个人假装各自忙着手头的事情。然后母亲瞥瞥门口,她先拿起东西往那儿走,姐姐帮我拿着东西也往门口走,我则假装要往房间走。小白正跟在我身后,我突然一个急转弯,对母亲喊:“趁现在!”
我人刚滑过大门,母亲就马上关门。留着小白,在院里自顾自嘎嘎地叫。当然,这样的配合并不总是成功的,有几次小白还是领先我一步出来了,我们又得假装没事一样,回到家里,等着下一次准备——事实上我好几次迟到就是因为小白。
小白长得越来越大、越来越胖,我感觉它都快像只鹅了。我开始担心,家里的院门可能要关不住它了。
果然,有一天早上我刚到教室,打开书包正要把准备学的课本拿出来,就听到同学中有兴奋的躁动。我顺着他们关注的方向望去,是小白。它正探头探脑地走进教室,一看到我,嘎的一声,就往我跟前跑来。
幸好老师还没来,家离学校不远,我赶紧抱着小白往家里跑。只跑了一会儿,我就累到没力气:小白真的太重了。我把它放下,对小白说:“跑。”然后自个儿试着先往前跑。小白愣了一下,终于屁颠屁颠地跟上来。
好不容易把小白弄回家,关上门。再回到教室的时候,才上了十几分钟课,小白又出现了。它又探头探脑地走进教室,对着老师嘎的一声。
老师看着小白,疑惑地问:“哪儿来的鸭子?它来干吗?”
同学们还没冲我笑,小白就径直向我跑来。老师明白了,这鸭子是想来陪我上课的。
事后我和母亲反复研究,应该是小白飞过院墙出去的。鸭子也是鸟类啊。那意味着:我们关不住小白了。
“怎么办呢?”姐姐问母亲。
“要不罩住?”母亲说。
姐姐摇头反对:“不可以的,小白是朋友,怎么可以罩住?”
后来找到办法的,只能是老师——我的老师都知道了,上课一定要习惯关门。只有关了门,小白才不会跟着我进教室。
本来有老师愿意让鸭子也一起听课的,可鸭子是直肠子,课上着上着,突然一股恶臭从我脚下传来——小白还是没拦住它肚子里的东西。
老师关了门,小白就此进不来教室了。一开始,它一直守在教室门口,等着我下课和放学。但门一关就看不到我,小白很无所适从。后来小白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现,教室的另一侧窗户边,有一堵区隔学校和外面的矮墙。它于是经常蹲在矮墙上,等着我放学。
从此东石镇中心小学的矮墙上,上课时间就有只肥胖的白色鸭子一直蹲在那里。路过的人很好奇,问鸭子:“你也是在认真听课吗?”小白嘎一声。那人说:“你看看,我回去得训我家孙子,连鸭子都这么认真,他还不认真。”
自此我便有了真正形影不离的伙伴。
有小白这个朋友还是挺威风的,我走在前面,小白摇摆着肥硕的身躯跟在后面,看上去就像我的保镖。
鸭子走路本来就是一摆一摆的,莫名地有气势,像电影里那种飞扬跋扈的黑帮。只不过,电影里的人喜欢穿黑色的衣服,小白则永远一袭白衣。
某种意义上,小白确实是我的保镖。

每个人的家乡总有个乡村恶霸,于小时候的我而言,那便是邻居家养的火鸡。
在闽南,火鸡是用来看家护院的。看家护院,本来是狗的事情,只是那个经常吃不起肉的年代,狗反而容易成为被盯上的对象。起歹心的人是知道狗的缺点的:连续几天,喂些吃食,狗见到人就亲近地摇尾巴了。等狗信任了,用一个大网兜,网着就跑。
火鸡没有狗对人的信任,火鸡可能是天底下最六亲不认、好斗跋扈的动物。不要说陌生人,哪怕是喂养它的主人,它都要趁着主人不注意的时候突然一个箭步冲过去,往主人脑袋啄一下。
自从邻居换成养火鸡后,他家院子里养的其他鸡鸭,倒真没丢过。但是苦了周边的小孩。一开始,火鸡只是在自家院子里昂着头威风凛凛地宣布自己的统治,后来,看到似乎没有反抗它的存在,于是把势力范围划到了院子门外。
而院子门外,就包括我去上学和去公共厕所的必经之路。
以前母亲挑着箩筐送我们的时候,那火鸡就曾试图欺负我们。不过,母亲放下箩筐,抽出扁担,往火鸡啄过来的嘴巴一拍,如同击打棒球一般。火鸡瞬间被打蒙了,不可置信地看着我母亲。自此,它看到我母亲就悻悻地走远。
但它怕的只是我母亲,一旦我和姐姐落单,它便一定要向我们报复。事实上,现在我的头上、手上,甚至还留着那恶霸火鸡的作品。
有段时间,我和姐姐每次走近那邻居的院门,都要做一会儿心理建设,然后大喊一声“冲啊”,以最快的速度逃离火鸡的尖嘴。
邻居和我说过,火鸡也欺负小白。那天小白第一次翻墙想去学校找我,火鸡就看到了陌生的肥硕的小白,为了宣示它的统治,追着啄了小白几口。小白被啄得嘎嘎叫了几声,但它着急寻我,吞了这口气,迅速跑去学校了。
那天回家,小白跟着我和姐姐又走到这个路口。
姐姐还耐心地和小白解释,说:“小白前方危险,待会儿一听我们信号,你记得往前冲。”
姐姐喊了“冲啊”,我们三个飞快地往前跑。但火鸡还是追上来了。眼看着火鸡的尖嘴又追到我头上来了,我闭着眼睛准备承受那种熟悉的痛感,却突然听到火鸡嚎叫了一声。我一低头,看到小白用它扁扁的嘴巴拼命地夹火鸡壮硕的腿。火鸡恼怒地啄在小白后背厚厚的羽毛上,小白疼得嘎嘎叫,往火鸡腿上夹得更用力了。火鸡惨叫一声,吓得直往后退。
小白一摇一晃,如同电影里的白衣骑士,慢慢地走向火鸡。那只火鸡脸涨得通红,虚张声势地抖着羽毛,但脚终于还是诚实地往后退却了。
自此,每次我们路过那恶霸火鸡的院子,都可以晃晃悠悠地走过。当然,那火鸡不是善茬儿,后来还是偷袭过几次,只是,小白一定会让它得到该有的教训。
那段时间,我因此特别喜欢带着小白在东石镇四处晃悠,名义上是和鸭子散步,事实上是为了显摆:我有个那么帅气的白鸭骑士。
是姐姐发现不对的。按照鸭子的年龄,小白已经足够大了,大到应该要下蛋了。但小白没有下蛋。
姐姐应该是憋了很久,终于在周末阿太来的时候,谨慎、郑重且悲伤地偷偷问她:“阿太,小白不是外婆吧?阿太是不是真的在骗我和弟弟?”
阿太当时还没反应过来,问:“什么外婆?”
姐姐小心地说:“小白是公的,外婆是女生啊。”
阿太愣了一下,扑哧笑出声,看着很是失望的可怜的姐姐,安慰她说:“嗯,估计那天我没接对你外婆,我这几天去梦里再找找你外婆,问问她到底去哪儿了。”
姐姐还是失落了好些天。她以为自己掩饰得很好,其实什么都写在脸上:永远愁眉苦脸、闷闷不乐的样子。
我问姐姐怎么了。
姐姐担心我发现这个真相,和她一样接受不了,慌乱间又找不到理由,犹豫了半天,拼命挤出点笑容,说:“没有啊。”但她不知道,她的上半张脸是哭丧着的,只有嘴巴倔强地装出一副微笑的模样,那表情让人看了真难受。
终于还是我说出了口:“你是觉得小白不是外婆,是吗?”
姐姐吃惊地看着我:“所以你也发现了吗?”
“但小白不也来陪着我们了吗?”
姐姐想了想,似乎觉得有点道理,才又笑起来,只是下半张脸真正在笑的时候,上半张脸还留着刚刚不小心流出来的泪水。
“但我还是想念外婆。”姐姐最后说。
是啊,我也想念外婆。正如,我知道的,小白也在想念它的鸭子同伴。
小白偶尔还是会突然听到什么一般,抬起头,对着半空试探性地叫几声。然后定定地等待着,直到确定没有回应,它才失望地耷拉下脑袋。它有时候还是会突然像想起同伴们会不会藏在哪儿,着急忙慌地冲进母亲的床底,一寸寸地搜索,确实搜索不到,这才尴尬地出来。
我好几次追着母亲和阿太问:“小白的那些伙伴你们埋哪儿了?”
母亲一直支支吾吾,回答我的是阿太。阿太说:“我送它们回大海了。”
我问阿太:“为什么送回大海?”
阿太看着我,说得很认真:“很多我们想念的人也在那儿啊。”
她讲话总是这样,让你不知道该不该相信。
我知道阿太其实是故意在和我说什么。自外婆“离世”后,我一直没问外婆去哪儿了。这“去哪儿”,包括身体去哪儿了——葬在哪里,可以去哪里看她;“去哪儿”,也包括灵魂去哪儿了——我后来知道,人离世,之所以身体一动不动,是因为灵魂离开了身体。
我不问,是因为我一度告诉自己,只要我不去求证外婆的离开,外婆就仿佛永远在——事实上,我因此再也不肯去外婆家了。
果然,阿太还是直截了当地问我:“黑狗达想知道你外婆去哪儿了吗?”
我假装不在意地摇摇头,起身要走。
阿太说:“你外婆也在海那边,咱们这儿,往生的灵魂都会在海那边的。不信你找个时候去看看,你真的想念她,会看到她的。”
阿太的话就这样在我心里生了根,而且越长越大。我太想见到外婆了,但我告诉自己,我不能去海边,我不能承认她真的走了。
可是我知道,自己每天都在想念外婆。我太想见到外婆了。
那一天,下午最后一节是体育课,大家一起在操场准备。小白蹲在沙坑上耐心地等着我放学。
老师吹起集结哨,我往集合处跑,突然想:哎呀,我真的很想念外婆。老师又吹了吹哨子,那是催促,我心里想:我真的想再见外婆一面。
跑着跑着,我突然下定决心,对小白喊了一声:“小白,走!咱们去找外婆,咱们去找你的伙伴们。”小白也不知道听懂没有,它看到我拔腿就往校门口跑,也紧跟着跑起来。
跑出校门往左转,是石板路;沿着石板路一直往前跑,会路过外婆家所在的巷子口;继续往前跑,往右转,是一片甘蔗林;穿过甘蔗林,便是大海了。
我跑过石板路,我看到过去的记忆就在石板路上,我看到母亲挑着我和姐姐每天那么开心地去往外婆家。我跑过外婆的家,我看到那会吱呀的大门紧紧关闭,我看到以前的自己和姐姐兴奋地等着进入寻找宝藏的游戏……
我越跑越着急,越跑越难过,越跑越紧张,我能看到外婆吗?外婆真的在海上吗?
我太想看到外婆了。
穿过甘蔗林,大海反射的阳光便向我扑过来。我和小白站到堤坝上的时候,太阳微微西斜,还没准备要落地。海上一片白茫茫的,什么也没有。我失望地坐着,心想:难道是我不够想念外婆吗?难道是外婆已经走了吗?
海上的云雾在翻滚,我眯着眼,盯着遥远的海平面。我好像看到一座岛,岛上站着一个人,正向我挥手。那个人好像是外婆。
我激动地叫起来:“外婆啊……”
岛上的人似乎听到了。
我呼唤着:“我好想你啊。”
那人似乎也在对我喊着什么。
这时,身旁的小白也开始嘎嘎地叫。我想,它也看到它的同伴们了。
我笑着哭着,对外婆喊:“外婆我没事了!你走吧,赶紧到天堂去吧,我已经会交朋友了。”
小白在身边又叫了几声。我知道的,它在和同伴说:“你们放心去吧,我现在有朋友了。”
“鸭子能活到几岁?”那一天,我终于把自己的忧虑说出来。
母亲愣了一会儿,说:“哎呀,这我也不知道。”
小白就蹲在我身边,她压低声音和我解释道:“咱们这儿,养鸭子基本是为了生鸭蛋或者吃鸭肉。母鸭如果生不出鸭蛋,自然就要被宰了;而吃鸭肉的,足够大就可以那个了。”
说完,母亲还看了看小白,评估刚刚自己说的话有没有被它听到,会不会对它造成冲击。
小白显然没听懂,继续蹲坐在地上,茫然地看着我们。
算起来,小白我已经养了两年多。现在的它白白胖胖,走出去,总有人说:“你这鸭子养得真好,一看就很可……”我催着小白赶紧走,我知道,他要说的不是可爱,而是可口。比较熟的邻居则开始和我唠叨:“黑狗达啊,哪有鸭子养得这么老的,再老下去,肉就不好吃了。”
甚至那年春节,我父亲终于回到东石镇,一开门,就看到一只肥肥胖胖的鸭子在家里闲庭信步。
父亲开心地说:“真好,年夜饭有大菜了。”
母亲和父亲交涉了许久,父亲还是不太理解:“这鸭子怎么会是朋友?”
到周末阿太来了,父亲向她抱怨:“哪有人把鸭子当朋友的?”
阿太白了父亲一眼:“有啊,我还和花草树木交朋友呢。”
父亲这才闭着嘴躲到一边去。
小白就此安然地度过了闽南那么多需要庆祝的节日。
我曾认真留心过,确实东石镇上没有看到过比小白大、比小白老的鸭子。而且不知道是因为肥胖还是确实年纪大了,小白走路越来越蹒跚,真的像老人一样。有时候我走快点,它还追不上,干脆气恼地坐在地上,嘎嘎地抗议。我也因此越来越担心,小白会不会很快要离开我了。
我最终还是忍不住问了阿太。毕竟她活到八十多岁,她过的日子多,见过的生命也多,她肯定看到不止一次,有人养鸭子不是为了吃,而是交了朋友。
“阿太,鸭子最老能活多久?就是,小白还可以陪我很久吧……”
阿太看出我的忧心忡忡,犹豫了片刻,说:“这个要看品种的,最久可以活六年吧。但一般三四年就有离开的。”
我心慌了一下,阿太赶紧挑最晚的那个时间说:“所以小白还可能陪你四年。”
我则伤心地说:“小白可能最快再一年多就要走了是吧?”
阿太点点头,说:“是啊,这世界很讨厌的一点就是有生老病死。”
她又想了一会儿,说:“反正,咱们就努力珍惜啊。”
我始终没有把这个事情告诉姐姐,但自从知道这个可能期限后,我只能如阿太说的那样努力珍惜。
我把自己想得到的事情,尽可能安排得满满当当。我每周和阿太、姐姐一起陪小白到处散步,带它去集市里逛街,去菜市场讨些别人不要的小鱼吃,去河边、海边玩水,去山里找鸭子喜欢吃的草。小白也陪着我上下学,陪着我做作业,以及听我给它讲我读来的故事。
我对小白说:“以后你要离开我了,我一定会把你的故事写下来,这样我想你的时候,就可以来书里找你了。”
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小白就飞不过我家的院墙了。自此,小白只能每天窝在家里等我放学。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小白慢慢地不太愿意出门了,每次我想陪它出去走走,它总是慵懒地蹲在家门口。
那天上学前,如往常那样,我和懒洋洋的小白说:“你乖乖在家,我放学后去市场给你找点小鱼吃。”
小白却追着跑出来了,它嘎嘎地对我叫着。
我问小白:“你在说什么?”
小白又嘎嘎地叫着,像急于说很多话一样。
毕竟要迟到了,我还是和姐姐把小白送回家,关上家里的门,去上学了。路上,我心里慌张地想:小白是在向我告别吗?
那天我一直惴惴不安,几次想跑回家看看,但是又不敢。终于熬到放学,我快速抓起书包往家里跑。一开门,我还没喊小白,就看到母亲拿了把凳子坐在天井那儿。
这不对的,母亲从来不会让自己空闲下来的,也从来没有这样坐在天井小白的窝旁边过。然后我知道了,我从母亲脸上的表情知道了,小白离开了。
果然,母亲一看到我,就如同当年外婆离世时那样,走到我身边想抱抱我。
母亲开口说:“小白走了,我回来的时候,它就这样睡过去了。”
母亲说,她把小白送到大海找它的伙伴去了。
我知道小白不在了,但那天晚上,我还是下了床,偷偷给房间开了一条缝。我想,万一小白回来看我呢?等到很晚很晚,小白终究没有来看我。小白甚至没有来梦里看我。小白是那么着急去见它那些伙伴。
第二天早上,我躲在被子里不愿意起床。阿太已经如同此前的所有周末早上一样来到我家,她用拐杖捅了捅我,说:“要不要去海边看看小白?去看看你外婆?”
我们来到海边。
姐姐很认真地盯着海面,问母亲:“阿母看到小白了吗?我怎么还是没看到?”
母亲笑吟吟地说:“我看到了啊,就在那儿。”
姐姐很认真地又盯着海面很久,再次问母亲:“阿母看到外婆了吗?”
母亲凝望着大海,许久许久,她说:“我看到了。我看到你们外婆了。”
海风吹着,像一个个拥抱,把我们一圈一圈地抱着。
阿太一直微笑着看海,也看了许久许久。

我看着阿太,心想,是啊,阿太看到的人应该很多吧,毕竟她已经过了那么多日子,已经经历过太多次告别。她一直微微笑着,我想,等我长得年纪足够大了,经历过那么多告别了,我还能像阿太这样,对着这舍不得的所有微笑吗?
面对大海,阿太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过几天就可以搬过来了,以后黑狗达可不许说我骗你们了。我把自己当作补偿,赔偿你们一个外婆,外加一只小白。”
姐姐开心地跳起来。母亲则感激地看着阿太。
阿太继续说:“我得再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哦。阿太有一天也会离开的,甚至很快就要离开你们,离开这世界,阿太毕竟八十几岁了。虽然阿太一定会和老天爷讲道理,甚至大不了翻脸,尽量死皮赖脸地多活几年,多陪你们,但哪一天万一我还是得离开,你们千万不要一直难过。那样会让我很担心,甚至会让我想,那还不如从一开始就不来陪你们呢。”
是的,阿太是笑着说的:“这世界讨厌的就是有生老病死,但这一点都不妨碍,我们在离开后,还会努力陪着你们。就像你们外婆一样,就像小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