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 | 收藏 |
第三章 孤胆侠客,老母鸡阿花
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 作者:蔡崇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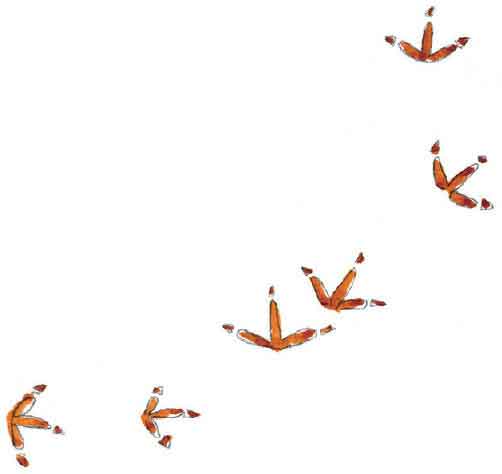
我一度非常不理解,阿太为什么要把这个混世魔王带到家里。也不理解,它怎么竟然会是阿太的好朋友。
阿太果然没骗我。那天一大早,我还赖在床上不肯起来,阿太就来了。这次她还挑着一前一后两个箩筐。我激动地跳下床,打开一个箩筐看,是衣服;再打开另外一个箩筐看,还是衣服。我欣慰地想,阿太确实是打定主意要搬来陪我们了。
送完东西,阿太便急匆匆地要赶回去。我问为什么,她说:“我那边家里还有许多东西要照顾,我得一趟趟搬过来啊。”
第二天一大早,阿太又来了,前面的箩筐里是自己的日用品,后面是一盆盆芦荟、玫瑰……我问阿太,怎么连植物都搬来了。阿太说:“那不是植物,那是陪我好多年的老朋友,我每天也都得和它们说说话。”
就这样,阿太来来回回挑了五六天,我想得到想不到的,都挑来了。阿太还早早地预告:“过几天我还要带一只鸡来。”
她特意和我们交代:“它性格不太好,你们多包容啊。”
阿太最后一趟挑的,就是她口中的老母鸡阿花。
我从一开始就不喜欢阿太的这个老朋友。
那天一大早阿太挑着箩筐进门,我照例从床上跳下来,去翻前箩筐,一打开,是和小白一样的喝水、吃饭的盆,以及一些小米。我欣喜地想,会不会也是只鸭子呢?听到后面的箩筐窸窸窣窣有什么在焦躁地动着,我忍不住要去打开。阿太提醒了句:“小心哦。”
我愣了下,为什么要小心呢?不以为意地掀开罩在箩筐上的竹篾,才打开一条小缝,就有一张尖嘴往我手上啄来。
我疼得抽回手,看到一只母鸡从那缝隙里探出头来。
我家西北面邻居有才叔家里,就养着一群鸡。公鸡顶着个红色高帽子,脸也红红的,走路威风凛凛,每天的工作就是在鸡圈里走来走去,看哪只母鸡不顺眼,就冲上去啄几嘴。母鸡没有高帽子,显得脸小小的,似乎整天都在低头翻找着地上可以吃的东西,要么就是准备去生蛋。
这般凶悍的母鸡,我倒第一次见。它歪着头,像是在细细打量我,然后头歪向另外一边,又认真地打量母亲和姐姐,最后直直地盯着阿太,像在问她:“你干吗把我带来这里?”
阿太说:“你出来吧。”
它这才从箩筐里跳出来。看来,它应该听得懂一点人的话。

从箩筐出来后,它不像当时小白它们刚来时那样,谨慎地蜷缩在角落,相反,它有种莫名其妙的孤傲感。一跳出来,先是昂着头乜着眼睛打量了我们好一会儿,这才绕着房子威严地巡视起来。走到哪里,有它不认识或者不熟悉的东西,会露出困惑的表情,看我们一下,好似希望我们向它解释为什么这东西摆在那儿。走到姐姐的房间,看到地上有一本课本,它歪着头看了我们很久,我们也困惑地看着它。它用嘴啄了几下,确定书不会反抗,于是高傲地踩了过去。
母亲问阿太:“外婆,为什么要带这么一只老母鸡来?”
阿太眯着眼睛笑:“哎呀,它脾气就是这样,不过相处久了,你就知道,它其实挺善良的。”
看来,阿太似乎不仅仅是把它当一只母鸡。
阿太还补充了一句:“对了,它叫阿花。”
阿太竟然还给它取了名字,看来,阿太确实把它当朋友了。
母亲问阿太:“咱们要把这只老母鸡的窝安在哪儿啊?还是和当时小白一样,在天井吗?”
阿太说:“阿花不用窝的,它到处睡。”
母亲有些不理解:“不需要给它在哪儿铺点布或者草吗?”
阿太说:“要不找找,你哪些柜子可以空着,都腾空就好。”
母亲还是不理解:“为什么要腾空柜子?”
阿太说:“阿花啊,喜欢到处睡,看到哪里可以当窝,就往哪里钻。你不想给它当窝的地方,记得一定关上。我家有个橱柜,里面放了些碗,阿花看中了,钻进去后拼命踢,把我的碗直接推落,打碎了一地。”
我看到母亲低下头悄悄地撇撇嘴。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因为我也是这么想的:阿太怎么往家里领了这么个混世魔王?
我家里和大部分闽南人家一样,是传统的平房格局。北边是上厅堂,厅堂两侧左右房,母亲安排我住在左边的房间,她和父亲住右边的房间。中间是天井,左右两侧两间厢房。右侧的厢房用来做厨房,左边的厢房空着。南边是下厅堂,两侧各一间房。右边的房间,姐姐住着。左边的房间地面都没铺,只用水泥简单扫了一遍,当作储藏室。
现在,阿太住在左厢房,和我的房间门对门。
那一天姐姐和我是真高兴,我们坐在门槛上,看阿太收拾东西。
阿太先是整理这几天陆陆续续搬来的各种植物。她把小一点的芦荟放在窗台,把海棠、玫瑰、芙蓉、茉莉、昙花放在天井靠自己房间的一侧。她边摆,嘴巴边言语着:“我知道你想要多一点日晒,这里应该合适”;“你喜欢多点风,这里一开门会有门廊风”……
调整来调整去,阿太似乎确定所有植物都开心了,这才拿把竹凳子坐在植物的簇拥里休息。
阿太坐在那里,像坐在一堆朋友中间。阿太的朋友真多,我莫名跟着开心。
海棠和茉莉花正开着,阿太掐了几枝插到自己盘好的发髻上。我这才突然明白了闽南的老人家头上那些簪花是从哪儿来的,明白了为什么当时的东石镇大部分人家都不算宽裕,但家家户户都养着花花草草。看来,故乡的老人们都擅长和花草交朋友。
收拾完绿植,阿太这才收拾自己的房间。衣服不多,都是那种连襟的款式,只是颜色不同。但颜色也就是灰色、蓝色、黑色这几种色调。阿太说,她从五十岁开始就只穿这样的衣服,每次穿破了,拿块布照着再裁一件。
阿太有个很精致的梳妆盒,梳妆盒里有把木头梳子,便是她最重要的家当了。每天早上,阿太都要用它很细致地梳好头,这才能盘发。虽然我那个时候年纪小,不太懂分辨价值,但看着那梳子,还镶嵌着一些很好看的玉石,就知道有许多的故事……
我看着阿太收拾自己的所有东西,感觉她像在整理目前为止的所有人生。我突然想,我只知道她是我阿太,但并不了解她的一生。我又想,其实我只知道我母亲作为母亲抚养我的部分,也并不认识全部的母亲。
于是我问:“阿太都活了八十多年了,应该有很多故事吧?”
阿太说:“当然啊。”
“阿太,那你能和我讲讲你的故事吗?”
“从哪儿讲呢?”
我想了想:“就从你认识我时一样的年纪开始讲?”
阿太半仰着头,似乎在自己的记忆里翻箱倒柜:“我五岁啊?”她努力地回想,“我五岁的时候,和黑狗达真是差不多。那时候我没有爷爷奶奶,我阿爸去讨大海出远洋再也没回来,家里就是我阿母、我和妹妹。”
“那你孤单吗?”我问阿太。
阿太又回想了很久。她在回想的时候,眼睛一直眯着,好像在看着记忆的海面上那星星点点的渔火。“是孤单过,不过还好,我很早就很会交朋友,我认识了各种花草、各种动物和神庙里很多神明。多亏我那么早就学会了啊,要不,你看,这日子多漫长啊。”
为了节省电费,我家一般五点半左右就吃晚饭——赶着天光还在,可以看见搛菜。偶尔母亲回来晚点,我们经常摸着黑吃饭,搛菜的时候,都要趴到菜跟前瞅半天。当时的菜,大部分真的都是菜,虽然有些肉渣,那是榨油剩下的。每次摸黑吃饭,没有天光照着,我和姐姐都趴在桌子上,筷子像穿山甲似的在菜里翻找着肉渣。
母亲喊吃饭了。阿太从房间里拿出一把黄黄的糙米,放进天井里老母鸡阿花的碗盆。
我们这才反应过来:“阿花呢?”从早上到现在,就一直没看到它。
“外婆,阿花不会跑了吧?”母亲问。
阿太走到饭桌旁坐下来,不慌不忙地说:“它就这性格,待会儿自己会回来的。”
阿太虽然这么说,但我们吃完饭,阿花还是没回来。我们刷牙洗脸准备睡觉了,阿花还是没回来。
我虽然不喜欢阿花,但它毕竟是阿太的朋友,我还是担心地问阿太:“咱们要不要去找找?”
阿太反倒没事一样躺到床上,说:“不用,它一定会回来的。”
我也忘记了是几点,可能晚上八九点钟,我听到咻的一声,有个影子像动画片里的忍者一般飞到我家上厅堂的窗户上,钻进来,落到庭院里,然后便安静得只剩下蟋蟀的叫声。我还在犹豫要不要起床察看,又听到天井里有什么在敲打着碗盆,爬起一看,月光下,阿花正认真啄着盆里的糙米。
阿花似乎察觉到我了,停下来歪着头看了看我。
我说:“阿花,你去哪儿了呢?”
阿花没有搭理我,转过头继续认真地啄米。阿花还是如此傲慢。
那段时间我都不确定,自己家里真的养着阿花吗?早上起床,我四处巡看,怎么也找不到它。我问阿太:“阿花呢?”
阿太说:“它出门了。”
下午放学回来,我又到处搜索。我问阿太:“阿花呢?”
阿太说:“还没回来。”
我和姐姐一般只有在周末的时候,才能看得到阿花——阿花每天中午还是会回来一趟的,把它碗盆里的食物吃掉,便又出门了,直到晚上才再回来。
我们在家里找不到阿花,但我家所在的巷子,阿花的故事却像雨后的杂草,到处疯长。
阿花随着阿太搬来的第二天,我们一家吃晚饭的时候,便听到路边有人在说着奇怪的事情:“今天中午我刚把菜做好放在厅堂桌上,转身要去厨房拿碗筷,突然听到桌上有什么被打翻的声音,追出来,看到一只什么东西,叼着菜正从我家的狗洞钻出去。”另外一个人说:“是不是土黄色的?我下午刚刚煮好一些花生放在院子里,也有一只土黄色的什么东西,咻一下子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叼上几颗花生就跑了。”
“是不是黄鼠狼?”
“我觉得不像,从屁股看像鸡,但哪有鸡这样偷东西的?”
“会不会是阿花?”在屋子里,姐姐听着外面,脸通红,小声问我。
“好像是吧……”我的脸也红得像灯笼一般。
睡了一觉,起床要去上学,耳朵边又传来新的故事。
有才叔扯着嗓子嚷:“哪里来的老母鸡!追着我家公鸡一直啄,啄出了一身伤……”
另外一个邻居听到了,回应着有才叔:“你也看到那只老母鸡了吧?我家看鸡圈的狗睡得好好的,有只老母鸡经过,突然对着它的头一顿啄,现在满头包,看上去都像得道高僧了……”
母亲、姐姐和我低着头,急匆匆往前走。
那几天,我们一家(除了阿太)过得惴惴不安。想着应该主动去和邻居道歉,但又不知道如何向大家解释这只老母鸡古怪的性格,所以犹豫着一直没去。又害怕在解释清楚前被人发现是我们家老母鸡干的,就这样每天纠结着。
流传了三四天,结合街坊的线索,大家已经笃定老母鸡基本就是我家前后左右的人养的。吃晚饭的时候,母亲紧张地说:“哎呀,快找到咱们头上了,咱们还是赶紧道歉吧。”
“要不明天早上就去?”姐姐说。
阿太说:“明天早上就去。”
第二天是周末,我还是忍不住赖床。
等我起了床,发现阿花不在,阿太也不在。我问母亲:“阿母,不是说今天去和邻居解释吗?”
母亲说:“是啊,等着你起床呢。对哦,你阿太呢?”
过了好一会儿,阿太拎着阿花的翅膀回来了。
阿太把阿花抓进箩筐里,用竹篾罩住,说:“我先和你们说发生了什么,然后再和阿花好好聊聊。”
阿太说,她一大早起来,先去菜市场买了些橘子和几个纱布罩,然后便挨家挨户去道歉。橘子是送给他们赔罪的,纱布罩是给他们以后罩着煮好的饭菜。
阿太说,这一路她一进门就和人说:“我是黑狗达阿太,我现在搬来住了。”
然后说:“抱歉啊,阿花是我带过来的。”
她一户户地听到了阿花的各种罪行。阿太说:“有人伸出手给我看,她在驱赶阿花的时候,阿花啄了她。住咱家斜对面的秀云说,她孙子正在蹲茅坑,看到阿花探头探脑,他拿起石头丢,想吓吓它,阿花追进去,对着他的屁股就啄。还有个人说,她母亲正在杀一只鸡,阿花经过时看到了,突然飞上灶台乱扫……”
这一早,阿太一户户地解释阿花是怎么有臭毛病的,她说:“我现在也给你们讲一下。”
阿太说:“阿花原来不是我养的,是我大儿子——黑狗达的大舅公养的。他当时发家了,建了个很大的房子,有个很大的花园,在花园的一个角落养着一群鸡。咱们这儿,养鸡的人多,母鸡下蛋可以吃,下的是种蛋可以孵小鸡,过年过节,可以杀几只鸡。
“我住不惯大房子,还是住在自己嫁过来时就一直住的小房子。大儿子家我就是偶尔去。那一次也忘记是什么节日,我去大儿子家,大儿媳和我说了许多家长里短,我都不太记得了,但记得她随口说的几句:家里有只母鸡很奇怪,自己下的蛋就是孵不出小鸡,就老抢别人的蛋孵。孵出来的小鸡,看得紧紧的,到处去搜罗东西给小鸡吃,甚至还敢去公鸡的盆里抢米,所以,没少挨公鸡的打。
“我一听乐了:这不和我一样吗?自己生不出小孩,便更加疼爱老天爷给我送来的小孩。

“大儿媳说,那母鸡,全身上下都是啄伤,她担心这样下去,它会被公鸡给欺负死。
“我一听急了:这可不行,那只母鸡我抱走吧。
“那母鸡便是阿花。一开始我怕阿花跑,把它养在笼子里。它估计是孤单得难受,没日没夜地咯咯咯唠叨个不停,甚至还绝食,一副倔强到底的样子。没办法,我只好把它放养,想到的办法就是隔几天放一把米,看它会不会念着我的好,偶尔来看我。
“一放开,阿花果然直直往屋外跑,连我给放的那一把米都不看,我想那也算了,尊重它自己的想法。我拿个蒲扇在门口坐着扇风纳凉,不想,过了一会儿,阿花一脸迷茫地从巷子那边走来了,看着我咯咯咯。
“我问阿花,你怎么不去找你的孩子啊?
“阿花:咯咯咯。
“我这才想起来,阿花不认识回去的路。
“那天我哄着阿花说,你吃一口米,我就带你回去。也不知道阿花有没有听懂,反正它啄了一点米,我便找来一根绳子,绑着它的一只脚,牵着它往我大儿子家走。我还是希望阿花愿意的时候来看我,所以我边走边让它记路,甚至走一段,再倒着走一段,方便它记得。
“果然,阿花第二天就从我家狗洞钻进来看我了。它咯咯咯了几声,好像是说它来了。它吃了几粒米,又叼了几粒米,便回去了。我想,阿花肯定是又叼给其他的小鸡吃了。
“阿花就此每天来看我。我是喜欢阿花来看我的,我女儿百花、我两个儿子都有自己的家,特别是二儿子,还在马来西亚。我总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虽然和花草树木说说话,但它们毕竟不会答话。阿花来了,咯咯咯几声,我就当它在和我说话。
“那五六年其实发生了许多事,我二儿子——也就是黑狗达二舅公突然回国看我,然后又突然走了,我才知道,原来他是知道自己生病快不行了,赶回来看我一眼。后来,我听说大儿子家里好像生意出了问题,没过多久,他的家就被债权人占了。我听说出事的那天,赶紧往大儿子家跑。去的时候,他家一间间房子都被各种人占了。我赶去鸡圈看,所有鸡也被哄抢了。
“我不知道自己可以干吗,一个人窝在家里。突然听到有什么从狗洞里钻进来,然后发出咯咯咯的声音。是阿花。阿花果然彪悍,那些去哄抢的人抓不到它。阿花果然重感情,想着得赶紧来陪我。”
阿太说到这儿,顿了顿:“抱歉啊,阿花那臭性格,从小就有的,这么多年就是不变。它后来就陪着我住了。还是闲不住,到处晃悠,察看谁家有小鸡,它可以帮助照顾的。然后到处找吃的,叼给小鸡。估计也是我纵着它,它胆子越来越大,再后来,就开始明抢了。”
阿太说:“所以也请你们多担待阿花,现在我和阿花好好说道理去。”
我问阿太:“阿花是鸡,能听得懂吗?”
阿太眯着眼睛一笑:“反正我尽量说,它能听懂一句是一句。”
阿太去给阿花做深度教育,我想着阿太说的那长长的故事,有些感伤。毕竟年纪小,我说不出心里翻滚的那些东西,整理了许久,最终我问母亲:“所以阿太没有自己亲生的孩子,外婆、大舅公、二舅公都不是阿太亲生的?我们也不是阿太亲生的,对吧?”
母亲想了想,说:“反正我觉得我就是你阿太亲生的。”
我问母亲:“所以人只要活得很久,就会遇到一个个人离世,对吧?就会遇到许多告别,是吧?”
母亲说:“是啊,你刚告别了外婆和小白,以后你最终也要告别阿太和我的。”
我很是悲伤:“所以我以后还是会突然间孤单,对吧……”
母亲摸摸我的头,说:“总会有孤单的时候,毕竟岁月这么漫长。”
我抬头看着正在和阿花深度交流的阿太,她满头的白发在阳光下闪闪发着光,我想:或许阿太知道岁月有多漫长、人有多孤独,才那么希望我学会和世界交朋友吧。
知道了阿花性格的前因后果,街坊大都选择尽量容忍,但三不五时地,总是有人熬不住,来家里告状。状告完了,便开始讲自家难过的事情。阿太是个很好的听众,毕竟活过那么多的岁月,阿太开口安慰人,便像她活过的所有日子在安慰人,阿太有时候会抱抱这些悲伤的主妇,便像是那么多的岁月在拥抱她们。再后来,大家其实是打着告状的幌子,来找阿太聊天。
每次我下课回到家,家里总有许多人在。我偷偷问母亲:“怎么大家都那么多事情要诉苦啊?”
母亲很认真地回答我:“因为谁的日子都藏着许多苦头啊。”
至于阿花,大家的状告着告着,倒告出许多趣事。巷子头的健康伯发现,家里的鸡圈总凭空多出来虫子、玉米、米粒各种食物,他到处说:“果然黑狗达阿太说的是真的,阿花就是想照顾它附近的小鸡们。”住我家后面第三栋房子的春枝婶说,有次她看见阿花追着一只老鼠啄:“这阿花其实是侠盗,惩奸除恶的。”
也忘记是谁第一个发现的,孤傲的阿花交朋友了,朋友便是我家后面文才叔养的猪。
一开始大家只是觉得有些奇怪,一向神出鬼没的阿花,怎么经常窝在文才叔家猪圈的矮墙上?有人路过,抬头看到阿花,问:“阿花,你待在猪圈干吗?”阿花早已经熟悉这巷子里的人家了,窝着身体眯着眼,一副爱搭不理的模样。
后来大家发现,阿花待在那儿的时间越来越多。有人好奇地往猪圈里探头,看到的是阿花啄来的各种食物。大家知道了:阿花喜欢文才叔家的猪。
说起来,文才叔家的猪圈,恰好就在我住的房间斜对面。这对我来说真是灾难。夏天还好些,风是从东南边来的,刚好把文才叔家猪圈的臭味吹走,冬天刮的是西北风,随便一阵风刮过,我房间里满满的都是猪的臭味。因此,后来我干脆把朝北的这扇窗户关得紧紧的,生怕有一丝臭味跑进来。
为了了解阿花交朋友的事情,那一天我回到家,便悄悄地把窗户开了一道小缝。我看到了,阿花就窝在那儿。阳光照着,海风吹着,它舒服地眯着眼,看上去还挺惬意。
我实在难以理解,一只鸡怎么最终会选择和一头猪交朋友。我做一会儿作业就好奇地察看一下,阿花还在;第二天起床透过窗缝一看,阿花还在。
我还看到阿花觅食回来飞到猪圈的矮墙上,那头大白猪就欢快地嗷嗷叫。阿花把叼来的东西往猪圈里扔,大白猪马上追着把阿花的礼物吃了,吃完对着阿花又嗷嗷叫了几声。阿花还是面无表情,高傲地蹲坐在矮墙上晒太阳。
阿花果然连交朋友都如此高傲。
关于阿花为什么会和大白猪交上朋友,街坊还讨论过一阵。文才叔认为,可能是阿花只有在这里才没有被驱赶,而且大白猪见到谁都一副开心的样子。健康伯说,根据他小时候养过猪和鸡的经验,鸡就是愿意和猪待在一起的。春枝婶则觉得,阿花就是想照顾人,照顾这又白又大的猪,多有成就感啊……
阿太听完我转述的各种说法,眯着眼睛笑着说:“要我看,阿花就是知道大白猪太孤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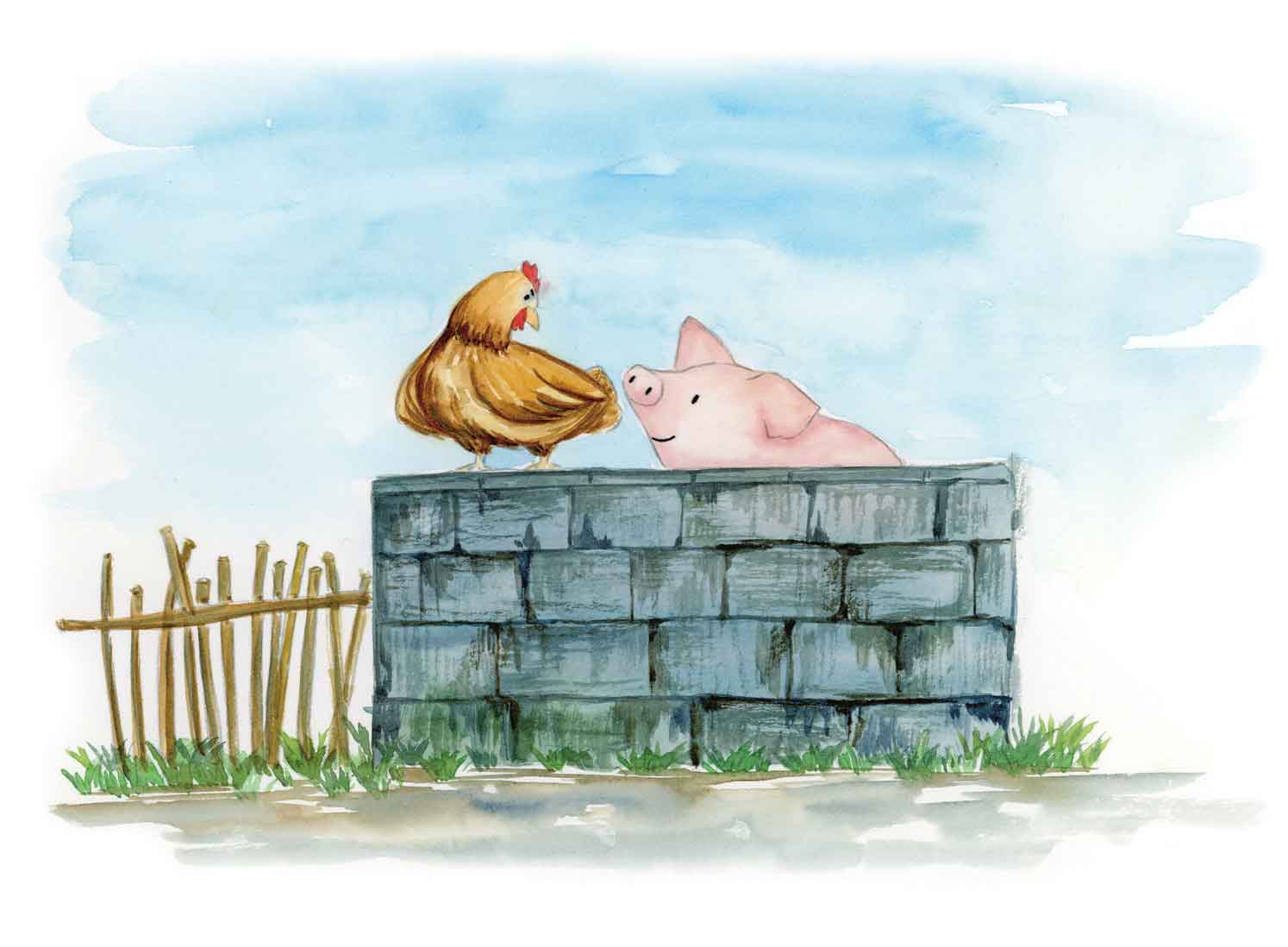
我刚懂事的时候,整个东石镇只有东西一条长长的石板路,石板路两边是店面,店面后面枝枝蔓蔓地长出一户户人家。这一户户人家,翻来覆去就那几个宗族的人相互错落。总有人家会吵架的,有的还打架了,打架了便各自要找宗亲帮忙,找着找着,最终发现,大家不都是亲戚嘛。
到我六七岁的时候,东石镇修了一条马路,通到海边。海边本来只有我母亲去工作的国营纺织厂,道路一通,各种工厂也挨着来建。工厂多了,东石镇上人自然变多了。镇上开始出现各种口音的人,有人说着河南话,有人说着四川话,有人说着东北话。街上也开始出现各个地方的餐馆,东北炖菜、湖南鱼头……热热闹闹的。
一开始,人们可喜欢这样的热闹了。这海边小镇,原本的生活日复一日,这下每天都有新鲜的事情发生。但后来人们又觉得闹心——这热闹也长出了人们不喜欢的、前所未有的新鲜事,比如盗贼。
原来东石镇是没有盗贼的,毕竟牵来扯去都是亲戚,一偷东西,被人看到,你不是某某家族的某某某吗?到他的家族一说,族规就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即使没被发现,在闽南人的理解中,举头三尺有神明,还有往生的老祖宗也在看着,怎么当贼啊。
别说贼了,平时菜市场有人缺斤短两,只要有人说,要不我去你家祠堂找你祖宗告状去?商家就会被吓得赶紧把钱退了。
巷子里的街坊邻居凑在一起讨论,确实,从盗贼的眼光来看,当时的东石镇也太适合偷了,家家户户都不习惯锁门,许多门干脆就没有锁。东石镇的人总喜欢相互走动,房子根本没有防止人进入的措施,反而都摆出一副“欢迎你随时来”的样子。
毕竟,东石镇哪想过,这世界真会有贼啊。
街坊邻居也试着理解,或许那些贼人并不是故意要当贼人的,只是外来的人一多,有些暂时还没在这小镇上找到安身的工作,吃不了饭,便只能开始偷了。但理解归理解,谁家愿意被偷呢?
先是春枝婶家南洋亲戚给的金镯子被偷了,春枝婶坐在门槛上呜呜哭。连退伍的老万伯伯家也被偷了,他珍藏的什么白酒,被贼都搬空了。他一大早醒来才发现,气呼呼地拿了把斧头,站在路中间叫骂着。
巷子里的人家,开始陆续把大门换成厚重的大杉木门,门窗都加装了石条。
母亲更是紧张,毕竟我家下厅堂只有矮矮的土墙围着,大门就是两片薄薄的木板搭着。有段时间,她甚至抱着砍柴的斧头睡觉。
后来,屋里被偷的变少了,院子里丢的却变多了。巷子头健康伯家的鸡被偷了,大家聚在一起讨论,得养些看家护院的,于是纷纷养了狗。
哪想到,养的狗反而也被偷了。
被偷的人多了,大家凑在一起核对,基本总结出了规律:盗贼大部分都是凌晨四五点作案。那时候天光刚泛出点白,又不够亮,盗贼看得到路,但又不容易被人看清楚脸。
还有受害的人家声称见到过那些盗贼,按他们的说法,那些贼全身上下涂满了黑黑的油,一来是伪装,让人看不清自己的脸,二来全身滑溜溜的,不容易被抓到。还有人说,她看到那贼人飞檐走壁的,从一户人家屋顶直接跳到另外一户人家屋顶,她说:“这身手,不比阿花差啊。”
大家凑在我家里,和阿太绘声绘色讲述的时候,阿花刚好路过。
有人开玩笑地说:“阿花,你该出手了啊。”
阿花高傲地歪着头看了大家许久,似乎在沉思,然后咯咯咯叫了几声。
大家笑着说:“阿花答应了。”
自从巷子里开始丢鸡、丢鸭,文才叔就开始担心自己家的大白猪。他见人就唠叨:“大白猪养得那么大,那些贼肯定要惦记。”听的人压低声音劝他:“别嚷嚷你家有大白猪啊。”文才叔吓得合上嘴,但还是太担心,过不了一会儿,又找人唠叨。
有人建议,要不到晚上就把猪赶到家里?“那怎么可以?大白猪整天躺在自己的屎尿上,多臭啊。进了家里我老婆肯定要揍我的。”文才叔说。
有人说,要不像拴狗一样,找条铁链,晚上把猪锁上?“那没用,你看咱们邻居养的狗,不是连狗带链子一起被偷的?”文才叔说。
最终安慰到文才叔的是红线奶奶。她边听边织毛衣,说:“你家大白猪这么重,怎么偷啊?”
“是哦,”文才叔突然自信起来,意识到肥胖就是最大的安全保障,得意扬扬地说,“我家大白猪那可是被我喂得又肥又壮。我估计咱们镇上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猪了。”
红线奶奶放下毛衣说:“何况还有阿花做保镖呢。”
出事的时间果然是凌晨四五点。我本来正熟睡着,突然听到大白猪哼哼叫的声音,我想,那头大白猪是做梦了,还是被什么打扰了睡觉?
迷迷糊糊间,我听到大白猪从哼哼叫变成嗷嗷嗷了。这叫声,一般是被文才叔打的时候才发出的。
我太困了,半梦半醒间想,怎么大白猪这么反常,文才叔不会半夜去打猪啊……我一个激灵吓醒了,难道有人偷猪?
从床上坐起来,我把朝北的窗户打开一条缝隙。透过缝隙,我看到月光下两个黑乎乎的身影,一边喂着大白猪吃的,安慰它不要嚎叫,一边正在试图把它的四只脚捆在一根竹筒上。
看样子,那两个贼是真打算把大白猪抬走。
我顿时慌张了。该怎么办呢?我不敢开电灯,摸黑走到阿太门前,轻声唤:“阿太,有人偷猪啊。”阿太屋里响着打呼声。我知道,阿太仍在睡着。我不敢叫得更大声,想了想,走到母亲门前轻声唤:“阿母,有人偷猪啊。”母亲没有回应,但翻了个身。我觉得有希望,继续唤着:“阿母,有人偷猪啊。”母亲回复了:“啊,好啊,你放下,我很快就做好了。”我知道,母亲说的是梦话。
我正在发愁,一转身,看见阿花正用锐利的眼神盯着我。我对阿花说:“有人偷你好朋友大白猪啊。”
阿花歪着头,好像没听明白。
我又说了一遍,阿花还是歪着头看着我。我急坏了,想了想,干脆模仿猪的嚎叫,做出被绑的样子。
阿花似乎明白了,二话不说(当然它本来就不会说话),一下子飞到我家上厅堂的窗户,钻了出去。
我急忙回到房间,扒着窗缝看:阿花威风凛凛地跳上猪圈的矮墙,直直盯着那两个贼。月光的映照下,阿花真的像个惩奸除恶的武林高手。
那两个贼不知道阿花此前的事迹,他们只是不在意地抬头看了看那只耀武扬威的老母鸡,继续抓紧时间绑这头又白又胖的猪。
阿花发出警告了: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我想它说的是:立刻把我的朋友放下。
贼人这次甚至连头都不抬,毕竟,一只老母鸡的叫声,有什么值得在意的?
阿花发怒了,突然飞起来,两只脚朝一个贼的肩上抓去,嘴同时往他脸上啄去。
那贼人疼得叫唤起来:“哎呀!”他放下竹筒,伸手去抓阿花。阿花早已经飞回矮墙上,然后像只公鸡一样,半仰着头不停地咯咯叫。
阿花是在宣战吧?一开始我这么想,然后我突然明白了,阿花是想叫其他人来帮忙。我犹豫了一会儿,突然鼓起勇气,跑出房间,跑到屋顶上大喊:“有人偷猪啦!有人偷猪啦!”
大白猪已经被绑好了,听到我这一喊,两个贼惊呆了,扛起猪便要跑。我站在屋顶上,看到文才叔家的灯亮了,红线奶奶家的灯亮了,健康伯家的灯亮了,我家的灯也亮了……
文才叔大喊:“抓贼啊!”另外一户人家喊:“抓贼啊……”整个巷子里一片抓贼声。我看到文才叔拿着锄头追出来了,老万伯伯拿着斧头追出来了,我看到连阿太也拿着拐杖出来了……
那两个贼抬着大白猪往巷子口跑。大白猪是四只脚被绑着倒挂着抬的,担子一晃一晃的,它疼得嗷嗷叫。
或许是情急之下的力量,那两个贼即使抬着猪依然跑得很快,眼看要跑到巷子外了,阿花又出手了。它追上去,飞起来跳到一个贼的头上,往他的脑袋上一抓,再一啄。那贼疼得想去抓阿花,一不小心,担子从肩头上滑落。

人们追上来了,那两个贼人看到情况不妙,只好丢下猪撒腿就跑。逃跑的途中,想到破坏他们好事的阿花,抓起一把石头,往阿花身上丢去。
我吓得闭上眼不敢看,在屋顶上问阿太:“阿花没事吧?”
阿太说:“你睁眼看看啊。”我睁开眼,看到阿花已经飞到一户人家的窗户上了。
偷猪贼被赶走了,大家陪着文才叔欢欢乐乐地把大白猪赶回猪圈。
文才叔对一旁的阿花说:“今天多亏了阿花,”然后掏出一把米放在矮墙上,“这是谢礼。”
阿花吃了几口,便高傲地乜着眼坐着。
文才叔开心地对大家说:“多亏街坊的帮忙,我这大白猪才保住。大后天就是我孙子的十六岁生日宴,到时候大家一起来吃全猪宴啊。”
大后天,全猪宴?我心里咯噔一下,看了看阿花。还好阿花听不懂人话,它依然歪着头,高傲地看着那些正在夸它的人。
该回去睡觉的都回去睡觉了,毕竟早上醒来,各自还要工作、上学。母亲也赶着姐姐和我回去再补一下觉。但我哪睡得着?我打开窗户,看到阿花蹲在猪圈的矮墙上,阿太正陪着它。我知道的,阿太在担心阿花。
那几天,我一直问阿太:“阿太,我们能做什么吗?”
阿太说:“猪是人家的,我们不能说什么啊。”
我说:“那我们能为阿花做什么吗?”
阿太想了许久,说:“好像做不了什么,到时候咱们多陪陪它吧。”
那天终于还是到了。一大早文才叔家里便热热闹闹,有人在烧水,有人在磨刀。听说,专门请的东石镇出名的乡厨团队,杀猪做全猪宴是一把好手。听说,按照习俗,必须赶在十点前杀好,十二点前祭祀,然后傍晚开宴席。也就是说,等我放学回来,大白猪已经成了宴席上的菜。
那天早上我慢吞吞地吃早饭,慢吞吞地收拾书包。母亲催促:“再不快点,赶不及上课了。”
我问母亲:“今天要不不上学了?”
阿太知道我在想什么,她说:“你好好上学去。我会看着阿花的。”
终于等到下午放学,我惴惴不安地往家走。
走到巷子口,我就看到阿太拿了把椅子坐在家门口发呆。海风吹过,拉扯着她的衣袖,我知道阿太很孤独,就像阿花一样。
我喊了声阿太。阿太看到我,还是习惯性眯着眼睛笑起来。
我问阿太:“阿花呢?”
阿太说得若无其事:“阿花跑了,阿花生气了。”
阿太说,今天早上文才叔和几个人揪着大白猪出猪圈的时候,阿花像当时对付偷猪贼一样,飞到文才叔头上啄他。文才叔念着阿花帮过他,虽然疼得直叫,却也只是用手驱赶它。
那群乡厨把大白猪按在地上,准备宰杀的时候,阿花跳到大白猪的身上,想护着它。但大白猪的身体对阿花来说太大了,它跳来跳去,也挡不住厨师找到一个机会,往猪的脖子上一刀。阿花眼睁睁地看着大白猪先是疼得嗷嗷叫,然后有气无力地哼哼叫,最终安静了。阿花知道大白猪走了,突然发起疯来,追着帮厨的所有人啄。好几个人手上被啄出血来。其中一人一生气,拿着正在烧火的铁棍往阿花身上抡过去。
阿花虽然飞起来了,但毕竟是鸡,不是鸟,它还是没法飞得很高,铁棍一下子打中了阿花。阿花哀鸣了一声,落到地上时,脚一拐一拐的。
“我看着难受,要去抱它回来。没想到它一拐一拐,挣扎着飞到猪圈的矮墙上,然后叫了几声,便连爬带飞地往旁边的小巷一钻,不见了。我拿着阿花的饭盆,里面放着米,沿着咱们小巷到处唤它,但它现在还没回来。”
我知道阿太难过,但一直是阿太安慰我,我怎么安慰阿太呢?我只好说:“阿太不难过。”
阿太还是对着我先笑了一下:“阿花就是难过了,我理解的,要是我,我也难过的。”
那一天阿太在门口坐了很久,孤单得像阿花一样。
天井里,阿花的饭盆里满满的都是糙米,应该是阿太加了一次又一次。
那天晚上,阿花没有回来。第二天,阿花没有回来。有街坊来家里说,看到阿花一拐一拐地往郭岑村方向走去了。有街坊说,看到有只野狗嘴里叼着一只鸡……阿太不搭话,她还是每天给阿花在碗盆里放一把米,每天沿着巷子不断呼唤阿花的名字。
过了大概一个月,一天我放学回来,看到阿太把阿花的饭盆收起来了。我知道,阿太接受了。
我担心地看着她,说:“阿太你难过吗?”
阿太缝着衣服,依旧眯着眼睛笑,但认真地说:“是难过啊。”
我问阿太:“要我抱抱你吗?”
阿太说:“好啊。”
我一抱阿太,阿太就开始呜呜地哭。
我故意笑着说:“原来阿太也会哭啊。”
阿太哭着说:“当然啊,人永远对一些事情不习惯的,多老都不习惯的。”
我说:“是啊,我发现了,外婆走的时候我不习惯,小白走的时候我还是不习惯。”
阿太突然凑到我耳朵边,压低声音说:“偷偷告诉你啊黑狗达,其实你二舅公走的时候,阿太躲在家里哭得可厉害了,我担心哭得太大声,还躲到房间蒙在被子里哭。后来你大舅公也走了,阿太跑到没有人的海边去哭。你外婆走的时候,我嘴上和你说没关系的,其实,我扛到葬礼结束后,也结结实实地哭了好多天。”
阿太边说,我边想象着那么漫长的岁月中孤独的阿太,想着,每个人终究都会迎来那么孤独而漫长的岁月吧。
我突然想到办法了,说:“没事的,阿太,我拿自己赔你一个阿花好吗?”
阿太愣了一下,然后眯着眼睛笑起来了,她摸摸我的头,说:“好啊,这样阿太就有人陪了,阿太终于也有人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