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血孩子 | 收藏 |
小说
血孩子
Bloodchild
血孩子 作者:奥克塔维娅·E·巴特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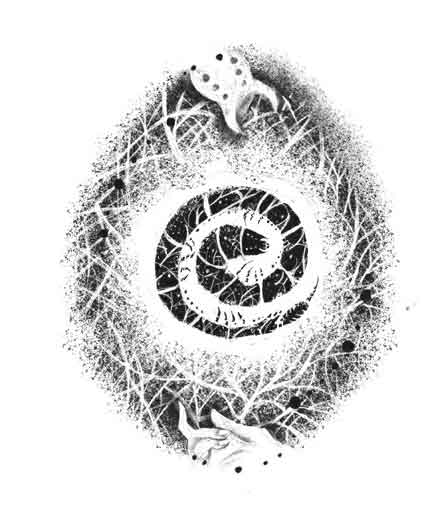
本篇获1984年星云奖最佳短中篇小说奖、1985年雨果奖最佳短中篇小说奖、1985年轨迹奖最佳短中篇小说奖。
最早刊登于《艾萨克·阿西莫夫科幻杂志》(1984)。
——编者注
我的童年结束于一次返乡。那一晚,提·嘉泰给了我们两枚无精卵。提·嘉泰把其中一枚分给了我的妈妈、哥哥、姐姐、妹妹,而另一枚,她坚持要我独享。这倒没什么。反正剩下的足够让所有人都爽一爽——除了妈妈。她不肯要,只是独自坐着,看其他人飘飘欲仙。主要是盯着我看。
提·嘉泰的肚子绵软纤长,我紧依着,随意地吸着那枚卵,琢磨着为什么妈妈偏要拒绝这种无害的乐趣。要是她肯偶尔放纵一次,白头发就不会这么多了。这些卵延长了寿命,增益了精力,爸爸就从不拒绝,所以寿命翻了一倍,一把年纪还有能耐迎娶我的妈妈,成为四个孩子的父亲。
但妈妈似乎情愿自然老去。提·嘉泰的几对足把我拽得更紧了,我看见她转过身去了。提·嘉泰喜欢我们的体温,一有机会就要好好享用。我小时候在家逗留得久,那时妈妈就总想教我与提·嘉泰的相处之道——要敬畏,要驯顺,因为提·嘉泰是提里克[类昆虫外星物种。(本书注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族的政府官员,专管人族[原文为“Terrans”,科幻小说常用词,人类、人族,对应的是外星人或神族。]保护区,直接跟人族打交道,在他们的族类中举足轻重。妈妈说,这样的大人物选了我们家,可真是荣耀万丈。嗯,妈妈撒谎时最正经、最严肃。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撒谎,甚至不明白她撒的什么谎。家里多了提·嘉泰这么个成员确实挺荣幸,但这并不新鲜。提·嘉泰和妈妈一直是朋友,提·嘉泰也不愿在她视作第二个家的地方摆架子。她只是走进来,爬上为她特制的沙发,叫我过去给她取暖。紧挨她躺着,听她一如往常地抱怨我太瘦,想拘谨也难。
“如今好多了,”她用六七只足捏弄着我,说,“你终于长胖了些。瘦弱是种危险。”足下的触感微妙地变成了爱抚。
“他还是太瘦。”妈妈突然开口了。
提·嘉泰抬起头,身子也挺起了一米多长的一截,像坐起来了一样。她看着我妈妈。而妈妈别过了头,苍老的脸上布满皱纹。
“丽安,甘恩剩下的卵,你来一些吧。”
“卵是给孩子们的。”妈妈说。
“全家都有份,拿吧。”
妈妈不情不愿,但还是顺从地接过我手里的卵,送到嘴边。弹性卵鞘[昆虫学名词,指某些昆虫卵块的包被物。]放了一阵子,已经瘪了,里面的汁水只剩几滴,但她挤捏着、吸吮着,吞了下去,片刻的工夫,她脸上僵硬的纹路便渐渐平滑了。
“真舒服啊,”她轻声感叹,“我都快忘记这种美妙的感觉了。”
“那就多来些。”提·嘉泰说,“何苦急着老去呢?”
妈妈没说什么。
“还能来这儿多好啊,”提·嘉泰说,“因为你,这儿才成了我的避难所,可你却不肯好好照顾自己。”
在外面,提·嘉泰有一众反对者。她的族群想占有、利用更多的人族,只有她和她的政派挡在我们前头。而提里克的其他族人不理解为什么要设立保护区,为什么不能与人族通婚,或直接买卖、征用我们。或许,他们其实完全明白,只是受欲望驱使,所以才毫不在乎。提·嘉泰把我们配给虎视眈眈、有权有势的提里克人,从而获取他们的政治支持。于是我们成了必需品,成了地位的象征。她监管着异族家庭之间的结合,早期那些为迎合急躁的提里克人而拆散人族家庭的制度,都由她一手瓦解。我曾和她一起住在保护区之外。在那些锁定、打量我的眼神中,我看到了疯狂的欲望。那欲望轻而易举就能吞噬我们,而在他们与我们之间,只站着一个提·嘉泰。这叫我有些害怕。妈妈有时候会看着她,对我说:“照顾好她。”我于是想起,妈妈也曾在保护区外待过,也曾见识过那样一个世界。
此刻,提·嘉泰用四只足把我推下地。“去吧,甘恩,”她说,“跟你的姐姐妹妹待会儿,趁清醒前好好享受。你几乎独自享用了一整枚卵呢。丽安,来,让我暖暖。”
不知为何,妈妈迟疑了片刻。我最早的记忆片段就是妈妈舒展身体,依偎在提·嘉泰身边,聊着我听不懂的事情;她还会把我抱起来,笑眯眯地让我坐在提·嘉泰的一节身体上。那时,她还能够欣然接受自己那份卵。拒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又是因为什么,我想知道。
她倚着提·嘉泰躺下了,而提·嘉泰身体左侧所有的足一起环住了她,松松地,但很牢。我一直觉得那么躺着很舒服,但除了我姐姐,家里没有人喜欢这样。他们说这样像囚入牢笼。
提·嘉泰确实有这个意图。她拢好那些足之后,轻轻地一拂附尾[昆虫学名词。昆虫通常没有普遍意义上的“尾巴”,只有肢(足)和节。有的种类有尾须(附肢),有的种类雌性有附尾,有感觉功能,用于寻找配偶和产卵。此处明显有关于性的暗示。],说道:“卵不够了,丽安,给你你就拿着。你现在很需要它。”
提·嘉泰的附尾又动了,上面的鞭节[昆虫学名词,指附尾上的鞭节。现实中昆虫的鞭节是触角第三节之后的部分,感觉功能敏锐。]快得看不清,要不是我一直盯着,根本发觉不了。螯刺戳进妈妈裸露的腿,吸了一滴血。
妈妈叫了起来——可能只是吓了一跳。其实挨蜇并不疼。她叹了口气,浑身松弛下来,在提·嘉泰多足的牢笼里慵懒地动动,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你为什么要那么做?”她在半梦半醒间问。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煎熬受苦。”
妈妈费劲地耸耸肩。“明天。”她说。
“是的,明天你得继续受苦——谁叫你执意如此呢。不过现在,此刻,躺在这儿吧,暖着我,我会让你好受点。”
“他仍然属于我,你懂的。”妈妈突兀地说。
“他是我的,什么都换不得、买不走。”要是她清醒着,绝不会毫不顾忌地就提起这些。
“是啊,不行。”提·嘉泰顺着她说。
“你以为我会卖掉他换那些卵吗?为了长寿?卖掉自己的儿子?”
“为了什么也不行。”提·嘉泰抚摸着妈妈的肩膀,搓弄着她花白的长发。
我也想亲近妈妈,与她分享这一刻。如果我现在去碰她,她肯定会握住我的手。享用了卵和刺,她会卸下架子,露出微笑,也许还会吐露那些长久压抑的感受。但到了明天,她回想起来,此刻的一切都会变成耻辱。我不想成为这耻辱的一部分。最好的办法就是安静地忍着,相信她在责任、尊严、痛苦的重压之下依然爱我。
“春禾[原名为“Xuan Hoa”。],替她脱鞋,”提·嘉泰说,“待会儿我再蜇她一下,她就能睡着了。”
姐姐照办了。她站起来的时候晃晃悠悠的,像喝醉了似的。回来的时候她挨着我坐下,拉住了我的手。我俩一向是个小团体,她和我。
妈妈的后脑勺抵着提·嘉泰的肚子,费力地从这个不可能看清的角度望向那张又宽又圆的脸。“你要再蜇我一次?”
“是啊,丽安。”
“那我就要睡到明天中午了。”
“这很好。你需要睡觉。你上一次闭眼是什么时候?”
妈妈恼怒地咕哝了一声:“当年真该趁你个头小,一脚踩死你。”
这是她俩之间的老段子。从某种角度来说,她俩算是一起长大的,不过在妈妈的有生之年,提·嘉泰的个头从未小到能让人族踩死。现在,她的年龄是妈妈的三倍,等到妈妈寿终正寝时,她也依然年轻。但她俩相遇相识的时候,恰逢提·嘉泰的快速发育期——类似提里克人的青春期——而我妈妈还是个小女孩,所以有一段时期,她们是同步成长的,成了最要好的朋友。
提·嘉泰甚至还撮合了我的妈妈和爸爸。虽然年龄上有差距,但他们彼此很满意,便结婚了。与此同时,提·嘉泰初涉家族事务——政治,她们见面的时间就渐渐少了。但我姐姐出生之前,妈妈曾答应提·嘉泰,把自己的一个孩子送给她。既然必须送出一个孩子,那么她宁愿选择提·嘉泰,而不是随便哪个陌生人。
时光流转,提·嘉泰各处游历,她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后来,当她回到妈妈面前,要求她兑现承诺,以此作为自己辛勤付出的回报时,人族保护区已经尽归她的势力范围。我的姐姐立刻就对她心生好感,希望自己被选中,可是妈妈刚怀孕不久。提·嘉泰另有心思,那就是选一个婴儿,观察、参与他成长的每一个阶段。据说,我出生不到三分钟,就被提·嘉泰搂进了她的多足囚笼,几天后,便初尝了卵的滋味。人族问我怕不怕她,我就原原本本地把这些说出来。提·嘉泰向她的族群推荐幼儿,而那些焦虑、无知的提里克人偏想要个青少年,我也照实讲述这段经历。我的哥哥长大后害怕提里克人,也不信任他们,但如果在他年纪更小的时候就被领走,说不定就能顺利地融入他们的家庭了。有时候替他想想,真是宜早不宜迟。我看见他瘫在房间另一边的地板上,神游天外,圆睁的眼睛在那枚卵的作用下显得呆滞。不管怎么看待提里克人,争取自己那份卵的时候,他倒从不含糊。
“丽安,能站起来吗?”提·嘉泰突然说。
“站起来?”妈妈说,“我不是该睡会儿吗?”
“过会儿再睡。外面的动静不对劲。”睡笼猛地张开了。
“什么?”
“丽安,起来!”
妈妈听懂了她的语气,连忙站起来,这才没有摔到地上。提·嘉泰三米长的身子翻下沙发,扑向门口,疾冲出去。她是有骨骼的——肋骨、长长的脊骨、颅骨,每节身体有四对肢骨。可她这样扭转翻腾、猛然跃起、稳稳下落、滑跑着地的动作,却仿佛柔软无骨,简直像是水生动物——像游弋在水中一般飘曳在空气里。我喜欢看她动起来的模样。
虽然脚下不太稳,我还是撇下姐姐,跟着她往外面走。坐在原地沉溺于幻梦当然更好,要是能找个女孩共享清醒的幻梦那就好上加好。过去,提里克人只把我们当作方便好用的大型温血动物,挑几个圈起来养着,男的女的关在一起,以卵饲喂。这样不管我们如何极力自持,他们都能确保人族的下一代绵延不绝。幸好那段时间不长,不然要不了几代,我们就真的成了方便好用的大型动物了。
“甘恩,开着门,”提·嘉泰说,“别让家里人出来。”
“怎么了?”我问。
“人族育体。”
我猛地往后一缩,紧贴着大门:“在这儿?只有他自己?”
“我猜他是想找公用电话。”她托起那人从我身边走过。他毫无知觉,像件衣服似的摊在她的足上。他看起来很年轻——可能和我哥哥差不多——远比他该有的身形瘦弱。正是提·嘉泰所说的那种“危险的瘦弱”。
“甘恩,去打电话。”她说着将人放在地上,把他的衣服往下扒。
我没动。
过了一会儿,她抬头看向我,突兀的沉默是她耐心尽失的信号。
“让奎伊去吧,”我对她说,“我留下,说不定能帮上忙。”
她的足忙碌着,抬起那个人,掀起他的衬衫蒙住他的头。“你肯定不想看,”她说,“很残忍。我没法儿像养他的提里克人那样帮他。”
“我知道,不过还是让奎伊去吧。他肯定不会帮忙的,我至少还愿意试试。”
她望向我哥哥——他比我年长、魁梧、强壮,当然也比我更能帮得上忙。他已经坐起来了,紧紧贴着墙壁,盯着地上的男人,毫不掩饰地露出了恐惧和厌恶。她也看得出来,把他留下没用。
“奎伊,你去!”她说。
他没拒绝。他站起来,身子微微打晃,但旋即就站稳了,吓得清醒了。
“这个人的名字是‘布拉姆·洛马斯’。”她看看那人的臂章,读了出来。我摸着自己的臂章,有点同病相怜的意思。“管他的是提·库姬德,把她叫过来。听懂了吗?”
“布拉姆·洛马斯,提·库姬德,”我哥哥念叨着,“那我去了。”他绕过洛马斯,跑出门去。
洛马斯恢复了一点意识。他先是呻吟了几声,接着又痉挛似的抓住提·嘉泰的一对足。妹妹终于从卵赋予的幻梦中醒来,凑近了想看看,但妈妈把她拉走了。
提·嘉泰脱下了那人的鞋子、裤子,全程任由他抓着自己的两只足。反正除了最靠下的几对,她所有的足都同样灵巧。“甘恩,这种时候我不想多解释。”她说。
我挺直了身子:“你要我做什么?”
“出去找只动物,有你身子一半大就够。宰掉它。”
“宰掉?可我从来没有——”
她一下子把我扇到屋子的另一边。不管是否露出螯刺,她的附尾都是相当厉害的武器。
我爬起来,往厨房走,后悔没把她的警告当真。用上刀子或斧子,说不定我就能杀死一只动物了。妈妈养了家畜,有一些是地球种,用来给餐桌添彩的,还有几千头是本地种,为的是要它们的皮毛。提·嘉泰应该更喜欢本地种。阿氏狄可能行。有几头大小正合适,不过它们的牙齿比我多两倍,还特别喜欢用牙撕咬。妈妈、春禾、奎伊都是用刀子宰杀它们的,而我从来没下过杀手,不管什么种类的动物都没宰过。在哥哥姐姐学着干家务活儿的时候,我把时间都花在提·嘉泰身上了。提·嘉泰说得对,去打电话的应该是我。至少那件事我办得到。
我走到妈妈存放大件家务用具和园艺工具的角柜前。柜子后面有一根往外排污水的管子——不过现在已经不用了。早在我出生之前,爸爸就改建了地下的排水管道。所以现在这条废弃的管子折叠起来,中间就能藏下一支步枪。我家不止有这一支步枪,但拿它最方便。有了枪,我连块头最大的阿氏狄也能杀死,不过那样的话,枪就可能会被提·嘉泰没收。在人族保护区内持枪是非法的。保护区刚建成后不久就出了事——人族用枪打死了提里克人,打死了提里克人的人族育体。在那之后才有了异族家庭结合,有了与所有人利益挂钩的和平共处。在我的有生之年,在妈妈的有生之年,从未有人朝提里克人开枪,但法律依然有效——据说,这是为了保护我们。有传闻称,在那个暗杀横生的年代,有些人族家庭甚至因为惨遭报复而被灭门。
我走到外面的畜笼那儿,挑了最大的一头阿氏狄打死。那是一头用于配种的漂亮雄性,妈妈看见我把它拖进屋肯定会很不高兴。可它的个头正合适,而且事出紧急,我也顾不得太多了。
我将阿氏狄修长温热的身体扛在肩上——幸好我增长的体重有一部分来自肌肉——然后扛进了厨房。我把步枪放回原来的地方藏好。要是提·嘉泰注意到了阿氏狄身上的枪伤,让我把枪交出去,那我只能照办;要是她没提,我本打算不动声色地放回原处。
我转过身,本来要将阿氏狄送过去给她,却又犹豫起来。有那么几秒钟,我站在紧闭的屋门前,不明白自己怎么突然害怕了。其实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虽然没有亲眼见过,但提·嘉泰给我看过图示和图片。她曾跟我保证,说只要我年纪到了,自然而然就能理解那种事。
可我还是不想进屋。我磨磨蹭蹭地从妈妈的雕花木盒里挑了一把刀。没准儿提·嘉泰用得着,我思忖着,毕竟阿氏狄的皮毛又厚又韧。
“甘恩!”提·嘉泰在喊我,声音刺耳,语气急迫。
我咽了口唾沫,从没想过抬脚迈步也能这么难。我发觉自己在发抖,心里羞愧不已。这份羞愧让我推门进去。
我把阿氏狄放在提·嘉泰旁边,看见洛马斯又昏过去了。现在,屋子里只有她、洛马斯和我——妈妈和姐妹们可能被打发出去了,刚好不必目睹这一切。真叫人羡慕。
可就在提·嘉泰抓起阿氏狄的时候,妈妈折回来了。提·嘉泰没理睬我递过去的刀,几对足的末端探出利爪,将阿氏狄由咽喉到肛门撕开。她看向我,黄色的眼睛紧盯着我:“甘恩,按住他的肩膀。”
我惊恐地看着洛马斯,碰都不想碰他,更不用说按住了。这跟开枪打死一只动物可不一样。不能干脆利落,因此谈不上仁慈悲悯,我希望他活下去,可那就无法一了百了。不得不参与其中,这是我最不情愿的。
妈妈走近了。“甘恩,你只管按住右边吧,”她说,“我按着左边。”要是洛马斯突然醒过来,肯定会下意识地把她掀翻。她是个娇小的女人,平日里就常常大声惊叹自己竟能生出如此“巨大”的孩子。
“没关系,”我说着按住了男人的双肩,“我能行。”她稍稍退开,还是有些犹豫。
“别担心,”我对她说,“我不会给你丢脸的。别在这儿看着了。”
她迟疑地望着我,少有地摸了摸我的脸,之后终于退回了自己的卧室。
提·嘉泰如释重负地垂下头。“谢谢你,甘恩,”她彬彬有礼,更像人族,而不是提里克人,“你母亲……她总能从我这儿自找难受。”
洛马斯呻吟起来,费力地呼吸着。我真希望他不要清醒过来。提·嘉泰凑近他的脸,让他把视线集中在自己身上。
“我已经蜇了你一下,但是不敢太重,”她对他说,“等完事了我再蜇一下,你就能睡过去,不觉得疼了。”
“再等等……”那人央求道,“求求你,再等等。”
“来不及了,布拉姆。一结束我就会蜇你。等提·库姬德来了会给你一些卵,你就能恢复了。很快就会过去的。”
“提·库姬德!”他叫唤着,使劲儿地拽着我的手。
“她马上就到,布拉姆。”提·嘉泰瞥了我一眼,一只利爪轻轻地抵住了他的腹部——中间微偏,左侧最后一根肋骨下面。他右侧的身体有了变化——很细微,仿佛在他棕色的肉体内随机地游移着某种悸动,这里凹一下、那里凸一下的,一下下地重复着,次数多了,我便看出了它的节奏,能猜到下一次悸动出现在哪里。
洛马斯的整个身体变得僵硬紧绷,提·嘉泰只是用利爪扶着他,身体的末端缠绕着他的双腿。他或许能甩开我的手,但肯定逃不开她的束缚。她用他的裤子绑住他的双手,高高推起,掀过头顶,然后让我跪着压住裤子,箍紧固定。他无助地哭泣,但紧接着她就卷起了他的衬衫,塞进了他的嘴里。
而后,她将他开膛破肚。
第一道口子划开的时候他强烈地抽搐起来,差点儿从我的膝下挣脱。他发出的声音……我闻所未闻,简直不像人族的声音。提·嘉泰充耳不闻,只管继续向下、向深处切割,并且时不时地停下来舔掉血液。她唾液中的化学成分起了作用,他的血管收缩了,出血速度减慢了。
我感觉自己是在帮她折磨他、毁灭他。我明明忍不住想吐,却不知为什么没有吐出来。我绝对坚持不到她完成整个流程。
她找到了第一只幼虫。幼虫很肥,身子内外都涨满、沾满了他殷红的血。它已经吃掉了自己的卵鞘,但显然还没开始朝育体下嘴。在这个阶段,除了自己的母虫,它不管什么肉都吃。而且,它还会释出毒素,让洛马斯难受但无法麻木。幼虫迟早会啃噬育体。等育体的血肉被朵颐殆尽,洛马斯也离死不远了——再也无法向谋害自己的东西复仇。不过,从育体出现消耗病弱的症状到幼虫真正开始喝血吞肉,还宽限出一段时间。
提·嘉泰小心翼翼地拎起幼虫看了看,根本没有理会洛马斯的痛苦呻吟。
突然,男人再次陷入了昏迷。
“行吧,”她低头看着他,冷漠地说,“真希望你们人族也能想昏就昏、想醒就醒。”至于她拎着的东西……
它还没有长出足和骨骼,大概十五厘米长、两厘米宽,没有视力,黏糊糊地沾着血,就像一条硕大的蠕虫。提·嘉泰把它放在那头阿氏狄的肚子上,它立刻就钻了进去。只要还有一口吃的,它就会趴在那儿咀嚼不停。
她在洛马斯的血肉间翻找,又找到两只幼虫,一只比较小,却更有活力。“是雄性!”她高兴地说道。他会死在我前头。在姐姐妹妹们还没长出足的时候,他就已经度过了变态期,并且会抓住一切机会繁衍。当提·嘉泰把他放到阿氏狄肚子上时,只有他一个劲儿地想咬她。
洛马斯的身体里渐渐钻出了一些浅色的肉虫。我闭上了眼睛。这比看到腐败尸体上爬满细小的蛆还要恶心。看图示和图片的感受根本不能及此万一。
“哎哟,还有呢。”提·嘉泰说着又拽出两只粗长的幼虫。“甘恩,你可能得再宰一头动物。你们人族的身子真是寄生的好地方。”
长这么大,我听到的从来都是:这是好事,是必要的,是提里克族和人族的双赢——是诞育生命的一种形式。我到现在仍然深信不疑。我知道无论如何生育都是痛苦的、血腥的。可眼下的这一切,似乎是另一回事。更恶劣的事。我还没有做好亲眼一见的准备。或许我永远也准备不好。然而,我不能当作没看见。就算闭上眼睛也无济于事。
提·嘉泰发现一只幼虫正在吃自己的卵鞘。残余的卵鞘还连着吸管、刺钩[参考昆虫学概念,“吸管”通常指成虫的虹吸式口器,“刺钩”在昆虫幼年时就具备了。]之类的东西,挂在育体的血管上。幼虫就是这样寄附在育体体内并攫取养分的。在孵化之前,它们只吸食血液,而后开始吞食富有弹性的卵鞘,最后便轮到育体。
提·嘉泰叼走卵鞘,舔掉了残血。她竟然喜欢那种味道?幼年的习性很难改变吗?还是根本就不会改变?
这整个过程都很不对劲,陌生且怪异。我从未想过她在某个层面上与我如此不同。
“我看应该还有一只,”她说,“或许是两只。真是一大家子啊。用动物做育体的时候,能保住一两只活的就相当不错了。”她瞟了我一眼,“甘恩,出去,吐干净。趁他还没醒,赶紧去。”
我踉踉跄跄地冲出门,差点儿瘫倒。在大门外的那棵树下,我搜肠刮肚地吐了个干干净净。我站在那儿,浑身发抖,泪流满面。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哭,但就是怎么也止不住。我走得远了些,免得被瞧见。只要闭上眼睛,就能看见红艳的虫子在更红艳的人族血肉上爬来爬去。
一辆轿车驶来,靠近了我们的房子。除了某些特定的农业设备,人族是严禁使用机动车辆的,所以我想来者肯定是照管洛马斯的提里克人——奎伊,也许还跟着一位人族医生。我用衬衫擦了擦脸,竭力控制着自己的举止。
“甘恩,”车一停下奎伊就喊道,“怎么样了?”他从便于提里克人出入的低矮圆形车门里钻出来。车厢另一侧也钻出一个人,没跟我说一个字就往屋里走。是医生。有了他,再加上几枚卵,洛马斯说不定能挺过去。
“提·库姬德呢?”我问。
驾车的提里克人几乎是从车里流淌出来一样,她挺起半截身子来到我跟前。她比提·嘉泰个头小、颜色浅——也许是因为她诞生于动物育体。由人族育体诞育的提里克人通常更壮实,数量也更多。
“六只幼虫,”我告诉她,“也许还有第七只。都活着。至少有一只是雄性。”
“洛马斯怎么样?”她急切地问道。她这个问题和询问时关切的语气让我有了些好感。洛马斯昏死之前,最后说出来的就是她的名字。
“他还活着。”我说。
她没再说话,径直往屋里走去。
“她很虚弱,”哥哥望着她的背影说,“我打电话时,听见有人阻拦她,说即便是为了这种事,她也不该专门跑一趟。”
我没接茬儿。我已经对提里克人足够以礼相待了,此刻再也不想开口。我希望奎伊赶紧进去——哪怕只是因为好奇也行。
“这下就算你不想知道,也全都知道了吧,嗯?”
我看着他。
“别用她那种眼神看我,”他说,“你不是她。你只是她的财产。”
她那种眼神。我现在都有能耐模仿她的眼神了?
“你怎么了?吐了?”他闻了闻四周的气味,“现在明白将来要遭什么罪了?”
我躲开他。小时候我和他很亲密。我在家时,他就任由我跟在身后团团转,提·嘉泰带我进城时,我也会带上他一起去。然而他进入青春期之后,似乎发生了什么。我一直都不知道。他开始回避提·嘉泰。他试图离家出逃——最终发觉,其实根本无路可逃。在人族保护区里如此。在外面,当然更是如此。在那之后他便只盯着自己的那份卵,只盯着我——他明显地表露出,只要我好好的,他就能安全这层意思——这只会让我恨他。
“到底怎么回事?”他追着我问道。
“我杀了一头阿氏狄。幼虫把它吃了。”
“你跑出来大吐特吐总不会是因为幼虫吃了阿氏狄吧。”
“我……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一个人被开膛破肚。”我说的是实话,对他来说这样解释也够了。我不能深谈其他的。不能跟他谈。
“哦。”他看着我,好像还想说些什么,但最终沉默了。
我们漫无目的地走着。走向屋后,走向畜笼,走向田野。
“他有没有说什么?”奎伊问,“我是指洛马斯。”
不然还能指谁呢?“他说了‘提·库姬德’。”
奎伊哆哆嗦嗦地说:“要是她也对我做了那种事,我最后呼唤的人也会是她。”
“是该呼唤她。让她蜇一下就能减轻痛苦,而且她又不会杀死你体内的幼虫。”
“你以为我在乎它们是死是活?”
是啊。他当然不在乎。那我呢,我在乎吗?
“妈的!”他深吸一口气,“我见识过它们有多厉害。你觉得洛马斯这样惨不惨?其实还有比他更惨的。”
我没有争辩。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曾看见它们吃掉一个男人。”他说。
我扭脸看着他:“你撒谎!”
“我曾看见它们吃掉一个男人。”他顿了顿,继续讲下去,“当时我还很小。那天,我去了哈特穆那儿,回家的时候,就在半路上,我撞见一个男人和一个提里克人。那个男的是个人族育体。四周都是山路,我就躲起来偷看。那个提里克人不肯剖开男人的肚子,因为她手边没有东西可以喂幼虫。男人走不动了,附近也没处歇脚。他痛苦至极,让她干脆杀了自己。他苦苦哀求,宁愿一死。最后她答应了。她割断了他的喉咙。利爪轻轻一划。我看见幼虫咬穿了他的身体,自己钻出来了,然后又扎进去大吃特吃。不停地吃。”
他的话让我的眼前再次浮现出洛马斯的身体,幼虫寄生,爬进爬出。“你怎么没跟我说呢?”我轻声道。
他吓了一跳,好像早就忘了还有我这个听众。“不知道。”
“所以在那之后你就想逃走,是吗?”
“是啊。多蠢哪。在保护区里逃跑。在牢笼里逃跑。”
我摇摇头,说出了早就应该告诉他的话:“她不会选你的,奎伊。你不用担心。”
“她会的……要是你有什么问题,她会的。”
“不,她会选春禾。阿禾她……她愿意。”要是她留在屋里目睹洛马斯遭受的一切,就不会这么想了。
“她们不用女的。”他轻蔑地说。
“有时候也用。”我看了他一眼,“其实,她们更喜欢女人。她们聊天时你真该凑近些听听。她们说女人的身体里脂肪更多,能更好地保护幼虫。但通常她们还是选择男人,把女人留下,让她们去养育自己的人族后代。”
“不过是储备下一代肉身的育体罢了。”他说,轻蔑变成了苦涩。
“不止如此啊!”我反驳道。难道不是吗?
“如果发生在我身上,我也情愿相信它‘不止如此’。”
“就是不止如此!”我感觉自己像个小孩,傻乎乎地争辩不休。
“提·嘉泰从那人肚子里掏虫子时你也这么想?”
“本来不会这么惨的。”
“本来就是这么惨的。只是不该让你看见,仅此而已。应该是他自己的提里克主子动手。她会把他蜇晕,过程就不会这么痛苦。但她还是得切开他的肚子,把幼虫拿出来。要是落下一只,幼虫就会毒死他,然后从里到外吃个干净。”
妈妈曾经提醒过我,让我尊重他,因为他是我哥哥。我走开了,心里恨着他。他这是幸灾乐祸,以他的方式。他安全了,而我前途未卜。我完全可以揍他一顿,但一想到他可能拒绝还手,还要以轻蔑而怜悯的眼神看我,我就承受不了。
他不肯放过我,迈着两条长腿越到前头去,好像我反倒是跟在后头的那一个。
“对不起。”他说。
我大步往前走,厌恶而愤怒。
“想开点,你可能不会那么惨。提·嘉泰挺喜欢你的。她会当心些的。”
我掉头往房子那儿走,急切地躲着他,几乎要跑起来。
“她已经对你做那件事了吗?”他轻松地追上我,问道,“我是说,你的年纪差不多可以植入虫卵了,她有没有——”
我一拳擂向他。我没想到自己会这么做,那一刻我恨不得杀了他。如果不是他比我年长、比我强壮,我真的会杀了他。
他本想制住我,最后还是不得已还了手。他只打了我几下,但这已经够我受的了。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倒下的,醒来时他已经走了。只要能摆脱他,挨打受疼也值得。
我站起来,慢慢地折回房子那儿。后头一片漆黑。厨房里没人。妈妈和姐姐妹妹都在卧室里睡觉——或者假装睡觉。
我一走进厨房就听见了说话的声音——在隔壁,提里克人和人族。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也不想弄清。
我在妈妈的桌子旁边坐下,等着四周归于安静。这张桌子平整光滑,颇有年头,沉甸甸的,而且做工精良。是爸爸去世前为妈妈做的。记得他干活儿时我就跟在他脚边转悠,但他一点儿也不在意。此刻我就倚着这张桌子,怀念着他。我本来可以跟他谈谈。在他漫长的生命中,那件事发生了三次。三次植入虫卵,三次剖开肚腹,三次缝合复原。他怎么受得了的?怎么有人受得了呢?
我站起来,从隐蔽处取出那支步枪,拿着它坐下。该给它清理一番、上上油了。
而我只是装上了子弹。
“甘恩?”
她走在硬质地板上,那些足此起彼伏地落地,发出噼啪噼啪的声音。一动一响,漫涌而来。
她走到桌前,挺起上半截身子,整个伏了上去。有时候她动起来非常灵巧流畅,就像一摊水。她把身子盘起来,仿佛一座小山似的堆在桌子中央,看着我。
“真糟糕,”她轻声说,“不该让你看见这些。其实不一定都这么惨烈。”
“我知道。”
“提·库姬德——现在是苛·库姬德[原文为“T'Khotgif”和“Ch'Khotgif”,“Ch”这一前缀暗示“完结”“终结”“濒死”“死亡”。]了——她就要死了,死于提里克人的固有规律。她抚养不了自己的孩子了,不过她的姐妹会照顾他们的,也会继续照管布拉姆·洛马斯。”是那个不生育的姐妹。每个人族育体都搭配一对提里克姐妹,一个负责生育,一个维系家庭。那对姐妹亏欠洛马斯的永远也还不清。
“他能活下去?”
“能。”
“他会不会再来一遭呢?”
“只要没人要求,他就不用再来一次。”
我直视着她黄色的眼睛,不知道自己能从中看见多少、看懂多少,又有多少只是出于想象。“谁也没问过我们的意愿,”我说,“你也从没问过我。”
她微微歪头:“你的脸怎么了?”
“没事。没什么大事。”人族的眼睛不可能在黑暗中看见这种肿胀。仅有的光源来自窗外,众多月亮中的一个正幽幽地发着光。
“你就是用这支步枪打死阿氏狄的吗?”
“对。”
“你打算用它打死我吗?”
我凝望着她,月光勾勒出她的轮廓——盘曲婀娜,优雅美丽。“人族的血是什么味道?”
她没回答。
“你是什么?”我喃喃道,“我们对你来说,是什么?”
她静静地卧着,头搭在盘起来的身子上面。“你比别人更了解我,”她柔声说,“你必须做出决定。”
“所以我的脸就这样了。”我说。
“怎么?”
“奎伊逼着我做决定。结果不太顺当。”我轻轻挪动步枪,将枪筒斜着抵住了自己的下巴,“至少这是决定的选项之一。”
“确实。”
“你就不问问吗,嘉泰?”
“为我孩子的性命而问?”
她一向会说这种话。她知道怎样周旋摆布,不论人族或提里克族。但这次没用。
“我不想成为肉身育体,”我说,“哪怕是你的,我也不愿意。”
她等了好久才回答我。“如今我们几乎不使用动物育体了,”她说,“你很清楚。”
“你们使用我们人族。”
“是的。我们等了很久很久,等你们出现,等你们受教,等你们的家庭和我们的家庭融为一体。”她不自在地动了动,“你知道,我们从来没有把你们当作动物。”
我看着她,没有说话。
“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你们的祖先到来之前,我们的卵在植入动物育体后,总是大量死去。”她轻轻地说,“这些事你都知道,甘恩。因为你们人族的到来,我们才重新认识了什么叫健康、兴旺的族类。你们的祖先背井离乡,本是为了逃离同族的杀戮和奴役,他们之所以能活下来,都是因为我们。我们把他们当作自己人,给他们建起了保护区,可他们却还是将我们视作虫子,恨不得杀了我们才好。”
“虫子”二字震得我一哆嗦。我完全是下意识的,她没法儿不察觉。
“我懂了,”她平静地说道,“你真的宁死也不愿生育我的后代吗,甘恩?”
我没有回答。
“那我去找春禾了?”
“好!”阿禾愿意。就遂她所愿吧。她没看见洛马斯的遭遇。她会很自豪的……不会害怕。
提·嘉泰从桌子上滑落到地板上,我一下子就慌了神。
“今晚我会睡在春禾的房间里,”她说,“今夜或明早,我就跟她说清楚。”
情况急转直下。姐姐阿禾将我带大,几乎像妈妈一样。我们仍然很亲密——不同于奎伊。她能够在追求提·嘉泰的同时仍然疼爱我。
“等等!嘉泰!”
她回过头看了看,伏在地上的身子挺起一半,一张脸逼近了我。“这是成年人之间的事,甘恩。这是我的生活,我的家庭!”
“可她是……我的姐姐。”
“你要求的事我已经照办了。我问过你了!”
“可是——”
“春禾不会这么为难。她一直期待着孕育新的生命。”
是人类的生命。是人族的婴儿。是吸吮乳汁而非血液的后代。
我摇了摇头。“别对她那么做,嘉泰。”我不是奎伊。似乎我也可以成为他那样的人,不费吹灰之力。把春禾当作挡箭牌。殷红的虫子长在她的而不是我的血肉里,难道就能让我好受些吗?
“别对她那么做。”我重复道。
她盯着我,一动不动。
我望向别处,后背对着她:“让我来吧。”
我放下了抵着下巴的枪。她俯身上前,要接过去。
“别。”我求她。
“这是法律。”她说。
“留给我的家人吧。也许某天某人会用它救我一命。”
她抓住了枪筒,但我没有松手。拉扯间我站起身,高高地俯视着她。
“把枪留下!”我说,“如果你不拿我们当动物,如果这是成年人之间的事,那就接受风险。与伴侣相处就是有风险的,嘉泰!”
对她来说,放下步枪显然很难。寒战掠过全身,她咝咝出声,痛苦至极。我突然意识到她这是害怕了。以她的年纪,必定见识过枪的杀伤力。现在,她的后代将与这支枪共处一室。她不知道这座房子里还有别的枪。在这场较量中,其他枪不重要。
“我今晚就要植入第一枚卵,”我把枪拿走时她说道,“听见了吗,甘恩?”
不然凭什么只有我能独享一枚完整的卵,而其他家人只能分享一枚?不然妈妈为什么总是望着我,好像我就要离开她,到她无法追随的地方去?难道提·嘉泰以为我仍然什么也不知道?
“听见了。”
“现在就去!”我任由她将我推出厨房,走向我的卧室。她声音里突如其来的急迫听起来很真切。“今晚你不是要选阿禾吗?”我讥讽道。
“反正就在今晚,是谁都行。”
我不顾她的急切,停下来拦住了她。“你在乎对方是谁吗?”
她绕过我,进了我的卧室。我进门时,她已经在我们常躺的那张卧榻上等着了。阿禾的屋子里没有她可用的陈设。她真要对阿禾做什么,就只能在地板上。我一想到她可能那样对待阿禾,思绪就全乱了,但和刚才的感觉不一样。我突然觉得很气愤。
然而,我还是脱下衣服,在她身边躺下。我知道该做什么、会发生什么。我从生下来就浸润在这些描述里。我感觉到了熟悉的刺痛,浑身发麻,隐隐地有种快感。她的产卵管到处试探。刺穿的那一下一点儿也不疼,不难受。进入得简单顺利。她的身子抵着我,像波浪似的起伏着,肌肉收缩舒张,将卵推出她的身体,推进我的身体。我抓住了她的一对足,蓦然想起洛马斯之前也是这样抓着她。我松了手,不经意地一动,弄疼了她。她难受地低声呻吟,我还以为她会立刻拢起几只足,像笼子似的将我围起。但她没有。我再次抓住了她,心里莫名有些愧疚。
“对不起。”我轻声道。
她伸出四只足摸摸我的肩膀。
“你在乎吗?”我问,“你在乎对方是我吗?”
她一时没有回答,过了很久才终于说道:“今晚,做选择的是你,甘恩。我的选择很久以前就定下了。”
“不然你就要去阿禾那儿吗?”
“对。我怎么能将孩子交给恨他们的人养育?”
“那不是……恨。”
“我知道那是什么。”
“我是害怕。”
沉默。
“我现在还是害怕。”现在,我终于可以向她坦陈了。
“可你还是答应了我……为了保护阿禾。”
“是啊。”我的额头倚着她的身体。她身上凉凉的,像天鹅绒一样,柔软得令人迷乱。“也是为了我自己留住你。”我说。这是真的。虽然我也不理解,但确实如此。
她欣慰地轻哼一声。“我刚才竟然误解了你,真是不可思议,”她说,“你小时候我选择了你。我相信你长大以后也会选择我。”
“本来是……可是……”
“因为洛马斯?”
“对。”
“我还没见过哪个人族目睹了整个诞育过程还能心平气和。奎伊见过,是吧?”
“是。”
“应该保护好人族,免得他们看见这些。”
我不喜欢这种论调——并且疑心她们可能真会那么干。“不要保护,”我说,“要展示。展示给我们看,从小时候起,多看几次。嘉泰,人族从来没有见过顺利的诞育过程。我们见到的只有人族育体——痛苦、恐惧、可能送命。”
她垂着头看我:“那是私密之事。一直都是私密之事。”
她的语气让我不敢再坚持——我听出来了,一旦她改变主意,第一个成为公开展品的可能是我。然而,我已经将这个念头埋进了她的思绪。念头可能会悄悄生长,最终让她付诸行动。
“不准你再看了,”她说,“不能让你总想着开枪打死我。”
和卵一起进入我的体内的少量液体让我彻底放松下来,就像享用了无精卵似的。于是,我记起了曾经握在手里的步枪,还有恐惧、厌恶、愤怒、绝望的感觉。我不用重新体验一遍就能记起那些感觉,还能描述谈论。
“我没打算朝你开枪,”我说,“不是你。”她诞育于我父亲的血肉间,当时,父亲和现在的我一个年纪。
“还是有那个可能的。”她坚持道。
“不是你。”她站在我们和她们的族群之间,保护着,弥合着。
“你是要伤害自己吗?”
我小心地动了动,很不自在。“我本来是那么想的。差一点就做到了。那其实就是奎伊所谓的‘逃离’。也不知道他懂不懂。”
“懂什么?”
我没有回答。
“现在你决心活下去了。”
“是的。”照顾好她,妈妈总是这么说。好的。
“我健康而年轻,”她说,“我不会让你像洛马斯那样遭罪的——孤苦无依,只是当个人族育体。我会照顾好你的。”
后记
有人认为《血孩子》是个鞭挞奴隶制度的故事,这让我很惊讶。不是的。不过它确实包含了很多。从某个层面上说,它写的是不同族群之间的爱。换个角度,它又是个成长故事——男孩必须吸收消化令人不安的信息,然后做出影响他余生的决定。
而第三种解读,即《血孩子》是关于“男性怀孕”的故事。我一直想要探讨:当男性处于绝不可能的位置上会是什么感觉。我是否可以写这样一个故事:不是因为好胜心用错了地方、非得证明女人能做的男人也行,也不是因为被逼无奈,甚至不是因为好奇,但这个男人就是选择了受孕怀胎。我想看看能否写出一个戏剧性的故事,写一个男人因爱而怀孕——固然周遭困难重重,但怀孕这个选择,是他自己做出的。
此外,我写《血孩子》是为了缓解自己长久以来的一种恐惧。我去秘鲁亚马孙地区采风、为“莉莉丝的孩子”系列(《破晓》《成年礼》《成熟》)做准备时,有些忌惮当地的昆虫。尤其是马蝇——在我看来,它们简直就像恐怖电影。而我打算造访的那个地区,最不缺的就是马蝇及蝇蛆。
马蝇叮咬其他昆虫,然后在它们的伤口里产卵。我由此联想开,想到蛆在我的皮肤底下存活、生长、吞食我的血肉,越想越觉得难以忍受,可怕至极。万一这种事真的发生在我身上,可怎么受得了。更糟的是,我所听到的、读到的都是建议马蝇受害者不要急于动手除掉蛆,而是等回到美国再去就医——或是静待蝇蛆度过幼虫阶段,爬出宿主的身体,自己飞走。
把蛆挤出来扔掉,看似正常的举动,其实很容易引起感染。蛆是真的“宿”在宿主身体里,如果被挤烂、切断,那么它的一部分就会留在原处,引发感染。厉害吧。
像马蝇这样一直困扰我的事,我应对的方式就是把它写下来。我通过写作解决自己的难题。1963年11月22日,在一所高中的教室里,我抓起本子,写下对肯尼迪遇刺事件的感受。无论是写日记、散文、短篇故事,还是将难题融入小说,写作总能帮我克服困难,让生活继续下去。创作《血孩子》并没有让我喜欢上马蝇,但在那段时间,它们确实更有意思了,而不是可怕吓人。
《血孩子》还做了另一个尝试。我想表达“支付租金”的主题——在太阳系外适宜居住的某处,人类孤立地聚居。往好处说,他们可能永远也找不着外援。这个故事不是什么太空中的大英帝国,也不是《星际迷航》那一类。人类迟早得与他们的——呃,主人——达成某种和解。这可能会成为某种特别的“借宿”。在那个不属于人类的世界,如果能谋得一片居处,谁知道人类会拿什么东西来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