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血孩子 | 收藏 |
马大书
The Book of Martha
血孩子 作者:奥克塔维娅·E·巴特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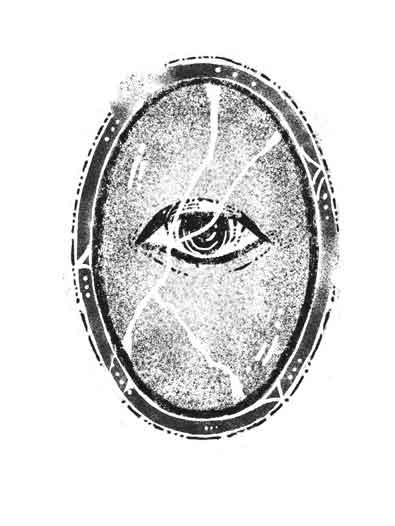
本篇最早刊登于科幻网(SciFi.com, 2003.5.21)。
——编者注
“很难,是吧?”上帝疲倦地笑了笑,“这是你第一次获得真正的自由。还有什么比这更难呢?”
马大·贝斯环顾四周,只能看见无尽的灰色。上帝就在那里。她惶恐而困惑,双手捂住黝黑的脸庞,低声说道:“但愿我能醒来。”
上帝默然不语,但他的存在是如此明晰,令人不安,即便在沉静之中,马大也感到了责备。“这是什么地方?”她问。她其实并不想知道,她不想在四十三岁就离开人世。“我这是在什么地方?”
“与我同在。”上帝说。
“真的吗?”她问,“我不是在家里做梦?没有被关进精神病院?该不会……不会躺在停尸房吧?”
“你在此处,”上帝温和地说,“和我在一起。”
过了一会儿,马大终于放下了双手,再次张望四周的灰色,再次凝视上帝。“这里肯定不是天堂,”她说,“这里什么都没有。没有人,除了你。”
“这就是你眼中所见吗?”上帝问。
这话叫她越发困惑了。“难道你不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她反问,随即压低了声音,“你不是知晓一切吗?”
上帝笑了:“不,我早就不玩那种戏法了。你想象不出那有多无聊。”
这种亲切熟悉的口吻减少了马大心里的恐惧,但她还是觉得不可思议。她记得,她本来坐在电脑前,刚结束她第五部小说的当日写作。写作一直很顺利,她乐在其中。一连几个小时,她恣意地将新鲜的故事倾泻而出,沉浸在她追求的创作带来的甜蜜疯狂中。当她终于暂告一段落、关掉电脑时,才发觉自己浑身僵硬。她的背疼得厉害,又饿又渴。已是清晨五点。她又熬了一个通宵。虽然身体上又酸又痛,但她还是很高兴,站起来到厨房去找东西吃。
然后她就到了这儿,迷茫而害怕。她的凌乱小窝给予的舒适荡然无存,面前的人如此不凡,她一下就感觉到了,他就是上帝——或者说,如此能量强大、令人震撼的人物就应该是神。他说要交给她一项工作,不仅对她,对全人类都意义重大。
要不是因为太害怕了,她没准儿会笑出来。除了漫画书和烂电影里的角色,还有谁会说这种话?
“呃,”她斗胆问道,“你为什么是个比正常人大一倍的蓄胡子白男?”她觉得他坐在那张宝座似的椅子上,就像米开朗琪罗雕刻的摩西。她记得二十年前曾在大学艺术史教科书上看过那尊雕塑的图片。但眼前的上帝比米开朗琪罗的塑像穿得更严实,从头到脚罩着基督画像中常出现的那种白色长袍。
“你的眼中是生命引领你所见的。”上帝说。
“那我想看看这究竟是什么地方!”
“是吗?马大,你眼中所见,取决于你。一切都取决于你。”
她叹了口气:“你介意我坐下聊吗?”
她转瞬就坐着了。她并没有做出“坐下”这个动作,只是突然发觉自己坐在一张扶手椅上,而刚才这儿肯定没有什么扶手椅。又是戏法,她愤愤地想,就像这一片灰色,就像那宝座上的巨人,就像她突然出现在此——都是为了让她惊讶,让她害怕。当然,这奏效了。她确实震惊又害怕。更糟的是,她不喜欢这种被摆布的感觉,因而更加恐慌。毫无疑问,那巨人能够洞悉她的心思,肯定会对她施以惩罚……
她强压着恐惧出声询问。“你说要交给我一项工作,”她顿了顿,舔舔嘴唇,努力稳住声音,“你想让我做什么?”
他没有立即回答,而是注视着她——在她看来仿佛在玩味,这长久的注视逼得她更加不自在了。
“你想让我做什么?”这次她的声音大了一些。
“要交与你的工作十分繁重,”他终于说道,“认真听好,我希望你时刻念着三个人:约拿、约伯、诺亚。将他们记在心中。让他们的故事指引你的行为。”
“好吧。”见他不再继续,马大只好开口,因为似乎应该说点儿什么,“好吧。”
她小时候去过教堂和主日学校,也上过读经班和假期圣经学校。当年,她的母亲还是个年轻姑娘,初为人母,懵懂间希望自己的孩子“向善”,而对她来说,“向善”就等于“虔诚”。所以,马大很清楚《圣经》中对约拿、约伯、诺亚的记载。她只把那些故事当作寓言,而非字面上的真理,不过这些故事她记得很牢。上帝吩咐约拿到尼尼微去,告诫那里的人改正行为。出于恐惧,约拿逃避工作,违抗神命。上帝让他遭遇海难,被一条大鱼吞进肚腹,从而警醒他,责任是逃不掉的。
在上帝和撒旦的赌局中,约伯失去了财产、孩子和自己的健康。尽管上帝放任撒旦折磨约伯,但约伯向上帝证明了自己的忠诚虔敬。之后,上帝便奖赏给他更多的财产、新生的孩子和强健的体魄。
至于诺亚,上帝命令他建造方舟,保住他的家人和世上的动物,因为上帝决意让洪水淹没世界,吞噬万物。
为什么上帝特意要她记住《圣经》中这三个人物呢?他们对她而言有何深意,尤其是约伯深重的苦难?
“这就是你要做的事,”上帝说,“你将帮助人类撑过贪婪、凶残、挥霍的青春期,帮助他们找到更无害、更平和、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马大望着他,愣了好一会儿,才有气无力地开口:“……什么?”
“如果你帮不了他们,他们就会毁灭。”
“你要再次毁灭他们吗?”她嗫嚅道。
“当然不是,”上帝有些恼火,“是他们自己要破坏地球维系生命的能力,将数十亿人送上死路。所以他们需要帮助。你要帮助他们。”
“怎么帮?”她连连摇头,“我能做什么呢?”
“不要担心,”上帝说,“我不会让你也带着人们会忽视、会曲解的信息回去。无论如何,现在那么做都已太迟。”上帝在宝座中动了动,歪头看着她。“你将借我之力,”他说,“只需巧妙运用,让人们更加友善地对待彼此,更加理智地对待环境。你将指给他们的生存之路,优于他们自己选的。我之力将借与你,你来做这件事。”他顿了顿,见她想不出什么对答的话,于是继续说下去。
“而你,完成这项工作后,便会回到他们中间,成为最卑微之人。你可以决定什么是‘最卑微的’。但不管你的决定是什么,你都只能是社会的底层,最下等的阶级、种姓、种族。”
这一次,他停下来的时候,马大笑了。困惑、恐惧、苦涩的笑意同时袭来,最终笑声挣脱了束缚。她需要笑。不知为何,笑给了她力量。
“我生来就在社会的最底层,”她说,“想必你知道。”
上帝没有回答。
“你肯定知道。”马大收起笑意,忍住痛哭的冲动。她站起来,走近上帝。“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我出生在贫苦的家庭,身为黑人、身为女性,母亲几乎不识一字,生下我时才十四岁。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有一半时间都无家可归。在你看来,这够‘底层’吗?我生于底层,却绝不会被困于底层,我也绝不会把母亲留在那里,我也不想再回到那里!”
上帝还是一言不发。他笑了。
马大坐了回去,被那笑容吓了一跳,她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在大喊大叫——冲着上帝!过了一会儿,她小声问道:“这是你选我做这件事的原因吗?我的出身?”
“我选择你,因为你是你,不是别人。”上帝说,“我本可以选择一个更穷的人,一个受压迫更为深重的人。我选择你,是因为我希望由你来做这项工作。”
马大听不出他的语气中是否带有怒意。她踌躇着,不知道被神拣选去完成一项如此重大、如此模糊、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是否是一种荣耀。
“求你让我回家吧。”她轻声恳求。她突然羞愧不已。她在乞求,可怜兮兮地放低姿态。然而,这是到目前为止她最为诚恳的一句话。
“你可以自由地向我提问,”上帝仿佛根本没有听到她的恳求,“你可以自由地辩驳、思考、检视整个人类历史中的观念和警示。你可以自由地投入时间去做这些事。正如我之前所言,你已经获得了真正的自由。你甚至害怕自由。但我向你保证,你终将完成这项工作。”
马大想起了约伯、约拿和诺亚。过了一会儿,她点了点头。
“好。”上帝说着起身,向她走去。他至少有十二英尺高,有着异于凡人的美,背后笼罩着光环。“随我来。”他说。
突然之间,他不再是十二英尺高了。马大没有看见他的变化,但他和她一样——不到六英尺高,也不再发光了。现在他看向她,他们得以四目相对。他实实在在地“看”了她。他察觉到她的疑惑,问道:“现在如何?在你看来,我是长着羽翼,还是亮着刺眼的光环?”
“你的光环消失了,”她说,“身体变小了。更像普通人了。”
“好,”他说,“你还看到了什么?”
“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灰色。”
“会变的。”
他们似乎走在光滑、平坦、坚硬的地面上,然而她低头时,却看不到自己的双脚。就像蹚在深及脚踝的浓雾之中。
“我们走在什么上面?”她问。
“你希望是什么?”上帝问,“街道?沙滩?土路?”
“郁郁葱葱的绿色草坪。”她刚说完就感到脚下踩着短茸茸的绿草。她也不觉得惊讶。“还要有大树,”她意识到自己的念头,觉得很欢喜,“阳光明媚——天空是湛蓝色的,飘着几朵云。正值五月或六月初。”
事情就这样成了。仿佛一直都是如此。他们正穿过一座巨大的城市公园。
马大睁大眼睛,望着上帝。“就是这样吗?”她轻声问,“我认为他人应该是什么样,他们就会变成什么样,而我只要……说出来就行了?”
“是的。”上帝说。
她的欢喜再次变成了恐惧:“那要是我说得不对、犯了错误怎么办?”
“这是肯定的。”
“可是……人们会因此受伤,会因此死去。”
上帝走向一棵巨大的、殷红色的挪威枫树,在树下的长木凳上坐下。马大意识到这棵树还有这张看起来很舒服的长凳,都是他片刻间创造出来的。她确信不疑,而事情顺理成章,她也没有感到不安。
“太简单了,”她说,“对你来说总是这么轻而易举吗?”
上帝叹了口气,说:“是的。”
她思索着——他的叹息,他转向树林而未投向她的目光。永恒而绝对的“轻而易举”会不会是“地狱”的另一个名字?这是不是她迄今为止最亵渎神灵的念头?她说:“我不想伤害他人,哪怕不是故意的。”
上帝将目光从树林间收回,凝视她片刻,而后道:“如果你能养育一两个孩子就更好了。”
何必呢,她生气地想,那你直接选择那些有一两个孩子的人不就行了。但她没有勇气讲出来,于是转而说:“如果我伤了人、杀了人,你会出手补救吗?我是说,我可是个新手。我可能会做出些蠢事,把别人坑了,自己事后才发觉。”
“我不会替你善后,”上帝说,“我将全权交与你。”
她在他旁边坐下,因为坐着凝望无边的园林美景,总比面对面站着问一些冒犯的问题轻松些。她说:“为什么这项工作是我的?为什么你不做?你知道该怎么做。你也不会犯错。为什么偏要我去做?我什么都不懂啊。”
“非常正确,”上帝说道,随后露出微笑,“这就是理由。”
她越想越害怕。“这对你来说只是一场游戏吗?”她问,“你觉得无趣,所以戏弄我们?”
上帝似乎想了想。“我并不觉得无趣,”他看上去很高兴,“你应该思考的是自己将引领何种改变。我们可以聊聊这些。你不必突兀地传布。”
她看看他,又低头盯着草坪,努力整理思绪。“好。我该怎么开始呢?”
“想想看,如果你只能引领一种改变,那会是什么重要的改变?只有一种。”
她再次望向青草,回忆自己写的那些小说。假设她要写一部新作,其中的人类只需要做出一种积极的改变,那该是什么呢?“嗯,”她思考片刻,说道,“不断增长的人口让很多问题雪上加霜。如果人类只能生两个小孩呢?我是说,愿意生孩子的人,无论想生多少,无论医疗技术能帮他们生多少,都只能生两个?”
“那么,你认为人口问题是最严重的?”上帝问。
“是的,”她说,“人太多了。解决了这个问题,才会有时间去解决别的问题。而且人口问题我们自己解决不了。其实大家都知道,只是不肯承认罢了。谁也不愿意由某个强势的政府机构来限制他们生几个孩子。”她偷偷看了眼上帝,见他似乎礼貌地听着。她不知道他容许她说多少。也不知道哪句话会冒犯他。如果冒犯了他,她会遭受怎样的对待?“所以,让所有人的生殖系统在生完两个孩子之后就停止工作,”她继续说道,“也不是生病,只是不能再生孩子了,他们的寿命还是和以前一样。”
“他们会继续尝试,”上帝说,“他们会将这种不孕不育视作瘟疫,并挖空心思,付出比建造金字塔、大教堂、登月火箭更多的努力,想方设法地解决它。再者,如果有人的孩子死了,或是有严重残疾呢?如果某个女人的第一胎源自被强奸呢?代孕的母亲怎么算?不认账的父亲怎么算?克隆的孩子怎么算?”
马大看着他,懊恼不已。“所以才要你去做。太复杂了。”她说。
一阵沉默。
“好吧,”马大叹了口气,放弃了,“好吧。就算有意外和现代医学,甚至克隆之类的玩意儿,只生两个的限制还是可以成立的。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实现,但你知道。”
“这确实可以实现,”上帝说,“但是你要记住,一旦选定了这种改变,就不能回到这里来修正它。你做的选择,与生命息息相关,也可以说,与死亡息息相关。”
“噢,”马大思考了一会儿,喃喃道,“噢,不。”
“人类还是会绵延数代,”上帝说,“但人口也会持续减少,最终完全灭绝。由于常见的疾病、残疾、灾难、战争、节育和谋杀,人口总数入不敷出。马大,要考虑现在的需要,也要考虑将来的需要。”
“我考虑了,”她说,“如果我把上限增加到四个孩子呢?”
上帝摇头:“自由意志与道德相结合是个有趣的试验。撇开其他不谈,自由意志其实就是犯错的自由。有时候,一组过错会抵消另一组过错。尽管并不可靠,但不少人类却因此得到了拯救。有时候,过错会使人遭受灭顶之灾、为奴为役、失去家园,因为他们破坏了土地、水域和气候。自由意志无法担保一切,但它是个颇有潜力的工具——非常有用,不能轻易消除。”
“我还以为你希望我阻止战争、奴隶制度和环境破坏呢!”马大想起了她的种族所遭受的一切,咬紧牙关。上帝对此怎能如此漫不经心?
上帝朗声大笑。这笑声令人吃惊——低沉、饱满,而且,在马大看来,这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快乐。这话题竟然能让他笑出来?他是上帝,还是撒旦?尽管母亲曾经竭力让她接受宗教教育,但马大仍然不相信这二者真实存在。现在,她不知道该怎样想、怎样做了。
上帝恢复平静,摇摇头,而后看着马大。“好了,不用着急,”他说,“马大,你知道什么是‘新星’[新星发生于白矮星和普通恒星组成的双星系统中。如果白矮星在它的伴星的洛希极限内,那么它将不断从其伴星处掠取氢、氦等气体,这些气体将聚积在白矮星的表面并且密度很大,温度很高。当温度达到2000万开时,氢聚变反应就会发生。这个过程会放出大量能量,使白矮星发生极明亮的爆发。]吗?”
马大皱起眉头。“是……爆炸的恒星。”她很愿意,甚至很渴望赶紧把注意力从疑惑上转移开。
“是一对恒星,”上帝说,“一个大的巨星[巨星光度高、体积大、密度低,是恒星演变过程的晚期。],一个小的、高密度的矮星[文中所指为白矮星,是一种低光度、高密度、高温度的恒星。]。矮星吸积[指致密天体由引力俘获周围物质的过程。文中描述的是双星系统中,白矮星掠取其伴星氢、氦等气体的现象。]巨星的物质,长此以往超过了它的控制上限,于是矮星就爆炸了。这不一定导致自我毁灭,但它的确会释放出大量过剩的物质。爆发极其明亮、剧烈。但矮星一旦归于平静,就会继续从巨星那里吸积物质。这个过程会一遍一遍地重复。这就是新星。如果发生了变化——两颗恒星彼此远离,或是变得密度相当,那么新星也就不复存在了。”
尽管并不情愿,马大还是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你的意思是,如果人类变了,他们就……不再是人类了?”
“我的意思不止于此,”上帝对她说,“我的意思是,即便如此,我也准许你放手去做。你认定人类应该怎样,他们就会怎样。但无论你做出何种决定,都将产生一定的后果。如果你限制他们的生育能力,他们可能因此走向灭绝。如果你限制他们的竞争力或创造力,他们在种种灾难和挑战中生存下来的能力就可能因此变弱。”
越说越糟了,马大心想,惧怕令她几近作呕。她转身背对着上帝,双手环抱在胸前,突然大哭起来,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哭了一会儿,她吸吸鼻子,用手抹了抹脸:“如果我拒绝,你会把我怎么样?”她想到了约伯和约拿。
“不会怎么样,”上帝甚至没有生气,“因为你不会拒绝。”
“可我要是真的拒绝呢?要是我实在想不出任何值得去做的改变呢?”
“不会发生那种事。就算发生了,只要你提出来,我就会把你送回家。毕竟,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换取这份工作的人成千上万。”
她立刻会意——这些人当中,有的出于憎恨和恐惧,很乐意消灭某个族群;有的渴望建立庞大的暴力政权,不管造成多大的痛苦,也要把所有人强塞进一个模子;还有的会把这份工作当作消遣,当作好人对坏人的电脑游戏,而完全不在乎后果。确实有这样的人。马大自己就认识这样的人。
但上帝不会选那种人,如果他真是上帝的话。可是话说回来,他为什么会选择她呢?她长大以后都不怎么相信上帝的存在了。如果这个可怕的、强大的家伙——不管是不是上帝——可以选她,那么他也可以做出更糟糕的选择。
过了一会儿,她问:“真有诺亚这个人吗?”
“没有人能应付全球性的洪水,”上帝说,“但确实需要一些人扛过较小的灾难。”
“你命令他救一部分人,其余的就任其死掉?”
“是的。”上帝说。
她不寒而栗,再次直面他。“后来呢?他们疯了吗?”她自己都能听出话里的反对和厌恶。
上帝只把这话当作普通提问:“有些人逃进了癫狂,有些人躲进了酒精,有些人放纵性欲,有些人选择自杀,还有些人长命百岁、活得充实。”
马大连连摇头,极力地想冷静下来。
“我不会再那么做了。”上帝说。
不,马大想,现在你找到不一样的乐子了。“我得推动多大的改变才行?”她问,“怎样才能取悦你,让你放过我,但又不另找他人来代替我呢?”
“不知道,”上帝笑了,他向后倚着古树,“因为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做。真是一种美妙的感受——有所期待,而非全知全能。”
“在我看来并不美妙。”马大苦涩地说。过了一会儿,她换了种语气:“在我看来,完全不妙。我不知道到底该做什么。毫无头绪。”
“你以写故事为生,”上帝说,“你创造角色和情境,设置问题,提出解决方法。我让你做的难道比这还难?”
“可你想让我左右的是真实的人。我不想那么做。我怕自己会犯下可怕的错误。”
“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上帝说,“问吧。”
她不想提问。但片刻之后她还是妥协了。“请明确些,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乌托邦吗?我不相信乌托邦。我不相信有那样一种社会,能让所有人都得偿所愿。”
“通常用不了太久,”上帝说,“有些人就能认定,自己希望邻居拥有些什么——或是希望邻居是个什么样的奴隶,或是直接希望邻居去死。不过别担心,马大,我并不是要你建立乌托邦,当然,看看你究竟能想出什么主意还是蛮有趣的。”
“那你想让我做什么?”
“当然是帮助他们。难道你不想吗?”
“我想,”她说,“但我从没帮过什么有意义的忙。饥荒、瘟疫、洪水、火灾、贪婪、奴役、复仇、愚蠢、无谓的战争……”
“现在你能做到了。当然,想要全部消除你列举的那些,非得灭绝人类不可。不过,你能够尽量减轻一部分问题。少一些战争,少一些贪婪,多一些远见,多一些对环境的关怀……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些问题?”
马大看看自己的双手,然后又看向上帝。他侃侃而谈的时候,她突然想到了一件事,可它似乎过于轻易、过于离奇,对她自己而言,也过于痛苦。真的发生过吗?应该发生吗?那样就有用吗?她问:“巴别塔之类的东西,是真的吗?你曾让人们突然间失去了互相理解的能力?”
上帝点点头:“是的,类似的事情以各种方式发生了好几次。”
“你是怎么做到的?改变他们的思维?改变他们的记忆?”
“二者皆有。不过我要做的,只是在他们拥有读写能力之前,将其彼此隔开,把一群人送往别的地方,或是给他们某种改变口型的习俗,比如在成年礼上敲掉门牙。或者,让他们对其他同类珍视或崇拜的东西心生强烈的厌恶,或者——”
马大打断了他,自己也吃了一惊:“那么这样如何?改变人们的……嗯,怎么说呢,大脑活动?这是我能做到的吗?”
“有意思,”上帝说,“也可能是危险的。不过只要你决定了就能做到。你是怎么想的呢?”
“梦境,”她说,“每当人们入睡,就让强烈的、鲜活的、无法逃避的梦境出现。”
“你的意思是,”上帝问,“让他们通过梦境学到东西?”
“差不多吧。但我真正的想法是,人们可以把精力花在梦境里。在梦境中,他们会拥有各自专属的、从各种角度来说都完美的世界。这些梦境要比普通的梦境更真实、更浓烈。人们最喜欢做什么,就在梦境里尽情地做。梦境要随着他们个人的兴趣而变化。无论他们关注什么,无论他们渴望什么,都能在梦中得到。这些梦是躲不开的。不管怎么回避——服药、手术等——都必须做梦。人们在梦境中得到的满足,要比现实给他们的更加深刻,更加彻底。我的意思是,这个满足要发生在做梦的过程中,而不是醒来之后还想着让梦境成真。”
上帝笑了:“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让他们拥有唯一的、可行的乌托邦,”马大思索片刻,说道,“每一个人,每一个夜晚,都会拥有私密的、完美的——也可能是不完美的——乌托邦。如果他们渴望冲突和争斗,那就得到冲突和争斗。如果他们渴望和平与爱,那就得到和平与爱。无论他们想要什么、需要什么,都能在梦中得到。我想,要是人们每天夜里都能上一回专属天堂,那么他们醒来之后控制他人、伤害他人的念头就能少一点。”她不太肯定,“是吧?”
上帝笑意不减:“有可能。有些人会受制于它,就像受制于成瘾药物。有些人则会在自己或他人身上与之抗争。也有些人可能会放弃生命、干脆赴死,因为所做的一切都比不上梦境。还有些人会享受其中,并且将他们惯常的生活延续下去,不过即便如此,他们也会发觉,梦境干扰了现实中的关系。大部分人会如何呢?我不知道。”他似乎很感兴趣,甚至有些兴奋。“我认为他们一开始可能会变得迟钝,再逐渐适应。至于他们到底会不会适应,这很难说。”
马大点点头:“你说得对,他们一开始会因此钝化,失去对其他事物的兴趣——包括真实的、完全清醒的性。对于健康和自尊来说,真实的性都是有风险的。而梦境中的性却可以随心所欲,还不用承担风险。在一段时间内,出生的小孩都会减少。”
“长大成人的就更少了。”上帝说。
“怎么会?”
“有些父母肯定会因为沉湎梦境而顾不上照顾孩子。爱和养育也有风险,并且伴随着辛苦的付出。”
“不能让这种事发生。除了做梦,得让抚养自己的孩子也成为人们真正愿意做的事。”
“所以你要让人们——大人和小孩——都在夜晚拥有生动、满足的梦境,但父母得把养育孩子看得比梦境更重,子女也不受梦境的引诱,渴望并需要非梦境的现实亲子关系?”
“尽量吧。”马大皱起眉头,想象生活在那样的世界会是何种感觉。人们还会阅读真正的书籍吗?也许他们希望以此反哺梦境。她还能继续写作吗?她还想写吗?如果失去了唯一在乎的工作,她会变成什么样?“人们应该仍然在乎家庭和工作,”她说,“不能让梦境带走他们的自尊。他们不该满足于窝在公园长椅上或躲在小巷里做梦。我只是希望用梦境来减速。少一些侵略,以及如你所说的,少一些贪婪。没有什么比满足更能让人慢下来,而这种满足每个夜晚都会如期而至。”
上帝点点头:“是这样吗?你希望照此发生?”
“是的。呃,我想是吧。”
“你确定吗?”
她站起来,垂首望着他:“这是我应该做的吗?这样会有效果吗?求你告诉我吧。”
“我真的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想看着一切徐徐铺展。我之前也利用过梦境,但不是你说的这种。”
上帝的愉悦显而易见,她几乎要否定整个想法了。可怕的事情似乎总能把他逗笑。“让我再斟酌斟酌,”她说,“我想自己待会儿行吗?”
上帝点点头:“如果你想聊聊就大声说话,我会出现的。”
转瞬就只有她自己了。独自一人,待在看起来和感觉上都像她家的地方——位于华盛顿州西雅图的那所小房子。她在客厅里。
她不假思索地打开灯,站在那儿望着自己的书。三面墙都是书架。她那些书以熟悉的方式陈列摆放。她抽出几本,一本接着一本——历史、医学、宗教、艺术、犯罪。她打开它们,发现这确实是她的书,里面的画线和批注都是她研究每本小说时亲手写下的。
她这才相信自己真的在家。她刚才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上帝。那个上帝酷似米开朗琪罗雕塑的摩西,命令自己想办法改变人类这个物种,消减其自我毁灭的倾向。梦境真实得令人不安,但它不可能是真的。太荒谬了。
她走到窗前,拉开窗帘。她的小房子坐落在山上,面向东方,最奢侈的就是可以越过山下几个街区,直接眺望华盛顿湖的美景。
可是现在,东方没有湖泊。窗外是她之前想出来的公园。不到二十码[1码≈0.914米。]之外,是那棵巨大的挪威红枫,还有那张长凳——她和上帝曾坐在上面交谈。
长凳上空空如也,缩在阴影里。外面天色渐暗。
她拉上窗帘,看着照亮屋子的那盏灯。有那么一会儿工夫,她感觉很别扭,因为在这虚实相交的地带,居然还亮着灯,还耗着电。她的房子是从哪儿运来的吗?还是复制品?或许,这只是一种复杂的幻觉?
她叹了口气。灯能亮就行了。接受吧。屋子里有灯光。屋子在这儿。房子在这儿。至于这一切到底有何玄妙,是她此刻最不关心的问题。
她去了厨房,找到了家里应该有的所有食物。就像灯一样,冰箱、电炉、烤箱都能用。她可以做饭。至少,这顿饭和她刚才的经历一样真实。再说她也饿了。
她从橱柜里拿出一小罐高品质白肉金枪鱼、几盒莳萝叶、咖喱粉,又从冰箱里拿出面包、生菜、腌菜、大葱、蛋黄酱和萨尔萨辣酱。她要做两份金枪鱼沙拉三明治。光是想想就更饿了。
这时她突然冒出个念头,于是大声说道:“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他们走在宽阔平坦的土路上,两旁是阴森森的树木轮廓。夜幕已经降临,树下漆黑一片,只有小路在星月的映照下仿佛一条苍白的光带。天上是一轮浅黄色的满月,又亮又大。星空浩瀚,布满苍穹。这样的夜空,她一生中只见过几次。她一直住在城市里,灯光和烟尘遮蔽了一切,只能瞥见最亮的几颗星星。
她仰望了几秒钟,然后扭头看向上帝,发现他此刻是黑人的形象,胡子也刮得干干净净。她仍旧没有半点惊讶。上帝变成了高大结实的黑人,穿着普通的现代衣服——白衬衫,黑裤子,外搭黑毛衣。他并没有比她高太多,但是比之前那个白人上帝的凡人形态高些。他完全不像白人模样的摩西了,但他仍然是上帝——同一个。这一点她毫不怀疑。
“你看见不同了吧,”上帝问,“是什么?”他的声音也变得更低沉。
她讲出了自己的所见。他点点头。“在某个时刻,你还会决定把我看作女人。”他说。
“不会的,”她说,“反正全都不是真的。”
“我告诉过你了,”上帝说,“全都是真的。只是你看见的不一定就是真的。”
她耸耸肩。这不重要——与她想问的问题相比。“我有个想法,”她说,“吓着我了,所以我才叫你出来。我之前问过这个问题,但你没有直接回答我。现在我需要一个答案。”
他等她发问。
“我死了吗?”
“当然没有,”他笑了,“你在此处。”
“与你同在。”她苦涩地接道。
沉默。
“我花多长时间来做决定,这个重要吗?”
“我说过了,不重要。你想花多长时间都行。”
这很古怪,马大心想,好吧,一切都很古怪。她冲口而出:“你想来一份金枪鱼沙拉三明治吗?”
“好啊,”上帝说,“多谢。”
他们一起向房子走去,而不是“瞬移”。马大对此很是感激。一进屋,他就在客厅里坐下,笑着翻看一本奇幻小说。而她则表现出一副用心忙碌的样子,以示为这份金枪鱼沙拉三明治尽了力。也许,努力是有用的。她其实根本不相信这些食物是真实的,也不相信她和上帝会真实地吃掉食物。
然而,三明治很美味。吃着吃着,马大突然想起存在冰箱里的起泡苹果酒。她起身去拿酒,回到客厅时,看见上帝变成了女人的模样。
马大愣住了,震惊不已,随后叹了口气。“现在你在我眼里变成女性了,”她说,“甚至有点儿像我。我们就像姐妹俩似的。”她疲惫地笑着,递过一杯苹果酒。
上帝说:“这完全取决于你,你懂吧。不过只要不惹你烦恼,我倒是无所谓。”
“确实烦恼。如果取决于我,那怎么会过了这么久,你才变成黑人女性呢?这和我一开始把你看作白人男性一样不真实啊。”
“我告诉过你,你看见的是生命引领你所见的。”上帝看着她。有那么一瞬间,马大觉得自己像在照镜子。
她移开目光:“我相信你。我只是以为我已经打破了自己出生和成长的精神牢笼——人类的上帝,白人的上帝,男性的上帝……”
“如果真有牢笼,”上帝说,“你仍然在里面,我也仍然是你第一次见时的模样。”
“不错,”马大说,“那你管它叫什么?”
“旧习,”上帝说,“这就是习俗的问题。往往没用了也依然存续。”
马大沉默了一会儿,最后说:“你觉得我那个梦境的办法怎么样?不是求你预见未来,只是挑挑毛病。如果有漏洞,就提醒我。”
上帝头倚椅背:“嗯,环境问题不太可能引发战争,所以,改善了它或许能减少饥荒和疾病。与真实的权力相比,梦中的权力无边又绝对,能够带来更多的满足感,所以人们受煽动征服邻邦、灭绝少数民族的情况也会减少。总的来说,梦境会给予人类更多的时间。”
马大不禁有些慌乱:“时间?用来做什么?”
“用来成长。成熟一些,或者至少找到某种合适的方式来度过青春期,”上帝笑道,“你有没有想过,有自我毁灭倾向的人是如何熬过青春期的?这对整个人类和人类个体来说都是值得关注的一点。”
“梦境不能实现这一点吗?”她问,“用梦境来满足他们内心的渴望,也用梦境推着他们走向醒来后的成熟,这样不行吗?不过我并不清楚对于人类这一物种来说,成熟意味着什么。”
“用愉悦耗尽他们的精力,”上帝若有所思,“同时教导他们,愉悦不是一切。”
“他们早就知道了呀。”
“通常成年后就知道了。但他们往往并不在乎。人们很容易追随恶劣但有魅力的领袖,养成能带来快乐的不良习惯,从而忽视迫在眉睫的灾难,因为那不过是一种可能性——或者只会发生在别人身上。这类想法正是青春期的表现之一。”
“那,梦境能教会——或者至少是推动——人类醒着的时候多多思考吗?能让人类更多地关注现实后果吗?”
“如果你想这么做,也是可以的。”
“我想这么做。我希望他们在睡着的时候尽可能地享受梦境、满足自己,而醒着的时候更清醒、更机敏,不要轻易相信谎言、同流合污、自欺欺人。”
“这些都不能使他们完美,马大。”
马大站起来,低头望着上帝,生怕自己漏掉什么重要的东西,也怕上帝明明知道,却还是一心看乐子。“还是有帮助的吧?”她问,“利大于弊?”
“是的,有帮助,但无须怀疑,也会有其他作用。我不知道那会是什么,但副作用不可避免。任何事碰到人类都不会一帆风顺。”
“你不就喜欢这样吗?”
“我最初并不喜欢,人类属于我,可我完全不了解他们。你不会理解这有多怪异,”上帝摇摇头,“他们是那样熟悉,就像我的一部分,却又并不是。”
“让那些梦境出现吧。”
“你确定吗?”
“实施吧。”
“那么,你准备回家了。”
“对。”
上帝站起来,面向她:“你想走,为什么?”
“因为我不像你那样觉得这种事有趣。因为你的方式令我害怕。”
上帝笑了——笑声不再那么叫人不安了。“哦,并不吧,”她说,“你已经开始喜欢我的方式了。”
马大沉吟片刻,点了点头:“你说得对。我一开始确实很害怕,但现在不怕了。我已经习惯了。我只在这里停留了这么短暂的时间,就已经习惯了,还渐渐喜欢上了。这才是真正令我害怕的。”
上帝仿佛在镜子里一般,也点了点头:“其实,你真的可以留下来。时间不会在你身上流逝。时间会绵延向前。”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在乎时间。”
“你一开始会回到记忆中的生活。但很快,你就得另谋生路了。以你这个年纪重新开始可不容易。”
马大望着墙边整整齐齐的书架:“阅读也会受影响,对吗?至少是休闲放松的阅读。”
“对——至少暂时是的。人们会为了获取信息和观点而阅读,但他们将创造属于自己的幻想世界。你做决定之前想到这一点了吗?”
马大叹了口气,说:“是的,我想到了。”过了一会儿,她又说,“我想回家。”
“你想记住自己曾经来过这儿吗?”上帝问。
“不想。”冲动之下,她走上前,拥抱了上帝——紧紧地拥抱,感知着熟悉的女性身体,还有那仿佛来自她自己衣橱的蓝色牛仔裤和黑色T恤。马大意识到,她其实是喜欢上了这个有魅力的、孩子气的、危险的家伙。“不想,”她再次说道,“我害怕那些梦会造成意想不到的伤害。”
“长远看来,想必是利大于弊啊。哪怕如此也不想记得?”
“对,不想,”马大说,“我怕终有一天会发觉是我导致了伤害的发生,是我亲手终结了自己唯一在乎的事业。我恐怕承受不了。知道这一切,迟早会把我逼疯的。我害怕。”她向后退开,而上帝已经变得模糊、透明,最终隐去。
“我想忘记。”马大喃喃说道。她独自伫立在自家客厅,茫然望向打开的前窗,望向华盛顿湖和萦绕水面的薄雾。她想了想刚才的自言自语,心里觉得奇怪,不明白到底要忘记什么。
后记
《马大书》是属于我的乌托邦故事。大多数乌托邦式的作品我都不喜欢,因为它们一点儿也不能令我信服。似乎不可避免的是,我的“乌托邦”可能是别人的“地狱”。所以我让“上帝”吩咐可怜的马大,托她去构想一个可行的乌托邦。可是,除了在每个人自己的、私密的梦境里,哪有行得通的乌托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