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错失之爱 | 收藏 |
班级聚会
错失之爱 作者:兹旦内克·斯维拉克

说实话,对参加高中同学的聚会我并不热衷,虽然曾几何时,我也满怀期待去过几次。对于那种毕业四五十年之后的聚会,教育部真该明令禁止。我何苦要去摧毁自己曾经渴望和心仪的姑娘在记忆里留下的美好印象呢?我又何苦非得去见证那些自己曾经羡慕不已的健硕少年如今变成了何种模样?这比戴上眼镜看镜子里的自己险些石化的感觉更加糟糕。
可是没隔多久,我就收到了同学拉迪•布尔班发来的聚会邀请函,他召集B班的同学再次相聚以追忆美好的学生时代。面对邀请我无力拒绝,因为这次我们的聚会不在餐厅举办,而是设在班主任科拉切克家里,这样还免去了舟车劳顿。况且,倘若我不到场的话,科拉切克老师会感到遗憾和难过的。
那栋建于五十年代末的别墅,前厅格局偏小,地板上堆满了各式鞋子,班主任没料到会进来这么多学生。换上拖鞋之后,大家便在铺着秃了毛的波斯地毯的客厅里走动起来。
科拉切克热泪盈眶,亲热地欢迎每个人的到来。就连他家那条老狗也是泪汪汪的,身上发出不好闻的气味。学生时代大家就跟班主任没大没小,直接叫他“罗曼”,现在更是无所忌惮。沙发上方挂了一大幅油画,画的是他二十年前去世的妻子克薇塔,此刻她正与我们相对而望。这个肤色晒得黝黑的美人曾让我们艳羡,她深得丈夫的宠爱,常被带入我们的课堂,自豪地看丈夫挥斥方遒。
今年的晚会一开始就裹挟着一丝神秘,如同一个无法揭晓的谜底。聚会上出现了一个男人,谁也不认识,他坐在女生们中间,膝盖上铺一块纸巾,正往嘴里填塞三明治。
“那个人是谁?”在阳台上抽烟时,我向布尔班打听。
“我也不知道,也许是罗曼的朋友吧,或者某个女生的丈夫。”
赫鲁达同学认为,那个汉子肯定是同我们上了一学期课后就消失了的德富勒。然而,平时老瞪着眼珠子看人、现在已戴上眼镜的丽布舍•乌尔班科娃赌咒说,肯定不是德富勒,也不是我们班任何一位女同学的丈夫。
“据罗曼说,那人是赛义德。”有人搭腔。
“赛义德!如果他是赛义德的话,那我就是教皇!”布尔班决绝地反驳。
“先生们,可别忘了,如今的我们都今非昔比,模样大变。斯拉维克•赛义德从来没有参加过聚会,我都不记得他长什么模样了。这么些年,那个可怜虫可能真的大变其样呢。”赫鲁达望着那位陌生老头感慨。
“你们看我的!”布尔班竖起食指,透过阳台的门缝冲客厅里招呼道,“斯拉维克!”
老人无动于衷,可见他并不是斯拉维克。
安多谢克把杯里的白葡萄酒一饮而尽,鼓起勇气说:“我去当面问他吧!”所有人都拥进了房间。大家屏住了呼吸。
“嘿,不好意思,”安多谢克向老人发问,“我们想不起来了,请问您是?”
“赛义德,”老人回答,“我是斯拉维克•赛义德的兄弟,他的腿骨折了,我替他来的。”
这样的玩笑谁都始料不及,整个晚会的气氛在这一刻释放开了。就如同腿上打了石膏的斯拉维克,让自家兄弟前来证实:鲜活的他,正有血有肉地站在我们中间,痛快地喝着酒,吃着面包。
“斯拉维克现在过得怎么样?他退休了吧?”我们的班主任满怀好奇。
“他的腿骨折了。”那位嘴里塞满食物的兄弟嘟囔了一句,此外没再多言。
我一边看着眼前这位素不相识的远道而来的替代者,一边用手在狗的耳朵之间摩挲,它感到格外惬意。
我在课堂上无数次描摹过的曾经胸部坚挺的史捷潘卡•罗索娃,从厨房里端出了热乎乎的小泥肠。
“朋友们,快来,趁热吃!”她边说边舔着油腻腻的手指头。
我刚想上前拿一根来吃,突然意识到之前抚摸了狗,于是先去洗手间。洗手间里的塑料马桶盖已经开裂,粘贴着透明胶布。镜子黯然失却了光泽,有年头的洗手盆也锈迹斑斑。排风扇在歪斜的轴承里摇摇晃晃,吹得黑色的蜘蛛网苟延残喘。唉,一个老鳏夫的浴室。我拿起肥皂洗手时,下决心今天一定请班主任解答几个疑问,不然就永远得不到答案了。
罗曼•科拉切克刚当我们班主任的时候,是个穿灯芯绒制服的小伙子,满脸稚气。之前他教低年级班,我们是他接手的第一批初中生。几堂俄语课和公民教育课下来,我们便发现这个人很好对付。比如说到“军队”在俄语里是战争的意思时,史捷潘同学马上会举手请求:“老师,您再给我们讲讲您以前当兵的故事吧,像上次那样。”
“对啊,再讲一遍吧!”其他同学也齐声附和。
科拉切克扫了一眼腕表,思忖在此插入是否有些不恰当,然而唤回那段在边防值守的记忆是他乐意至极的事儿,因为那是他迄今最为光鲜的人生经历:“在一次异常艰辛的野外实战训练中,我们占据了波什涅克山脚作为射击点。指挥官莫尼克中尉,一位干练的军人,顺便提一句,是他给我们展示了刚纳入我军战备的新型望远镜。这款望远镜的特点是,士兵以卧姿进行瞄准射击时,双目镜能自动屏蔽视野周边的杂草,就像在无草环境下瞄准一样清晰。”
“真是不可思议!”史捷潘感叹。
“当时我也完全不敢相信,然而莫尼克中尉将望远镜递给我,我用它瞄准茂密的草丛时,确实清楚地看到了山的全貌。”
我们全班都震惊了,渴望有朝一日也能试一下这种望远镜。拉迪•布尔班这个总是异想天开的小子,举起手回应说:“既然我们提到了望远镜,我联想到夏天在祖母家阁楼上发现的一架德国产的望远镜,它的特点是,用望远镜的一端看出去时,你和所视物体之间的距离非常近,而当你用另一端看出去时,景物又离你很远,变得非常小。”
布尔班的叙述使全班炸开了锅。
我们的老师无助地环顾全班,说:“现在我也被搞糊涂了,布尔班同学,你不是在拿我开玩笑吧?还是以前你真的没有摸过望远镜?”
“那是我拿到手的第一架望远镜,它确实具有那样的功能。”布尔班带着发现者的激动回答,还想滔滔不绝地展开话题。然而坐在他身后的赫鲁达一把将他拽到座位上,提醒说:“够了,傻蛋。”
科拉切克老师不知情,而我们全班同学都心知肚明,如果对那架不同寻常的德国望远镜发表高见的人是史捷潘,那就不仅是故作幼稚,更是心怀叵测地考验教师的耐心。然而拉迪•布尔班,他的确是没有任何意图的天真、善良。
说起我们班,当初留给其他人的印象似乎是班上的同学不把班主任当回事儿。不尊重也好,尊重也罢,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便我们B班最顽劣的那几个学生,也一致承认班主任是个好人,对学生有恻隐之心,因此没有必要故意找老师的麻烦。班主任时刻为我们着想,这无疑提升了他在大家心目中的分量。
譬如他会这样宣布:“穆西尔,我在哈珀尔老师那里替你说情啦,有可能,我再重申一遍,有可能你的数学成绩不至于不及格了。”这是非常了不得的举动,因为要让哈珀尔教授服软——我在后面还会提到,至今尚没有一个人做到呢。
另外,他在那个“日光浴”事件中为我们班“和稀泥”的事儿,也足以彪炳学校史册。事情跟我们的化学老师居立奇工程师有关。那个秃子,无趣又乏味,苍白得没有灵魂,不知谁给他起了个“山羊屁”的绰号。他本该留在利特威诺夫化工厂里,不该跑到学校来教书育人的,因为他不具备半点儿天赋。而且他嗓音低沉,只有第一排的同学听得见,其他同学只能听天由命,投入课堂之外的娱乐。他还是个混蛋,当我们招呼其他老师,称他们为“先生”或者“女士”时,老师们倒无所谓,只有居立奇以这是非同志式的称谓为由,建议扣除学生的德育分。
在他的课堂上,我唯一想得起来的是他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谁不懂化学谁就是白丁一枚,因为整个世界的发展是一个化学进程。或许这就是我至今依然无法理解这个世界的原因吧。
有一天,这位“门捷列夫”怒气冲冲地走进教室,因为他又一次被排除在滑雪旅行名单之外,而他那个饱受化工厂“熏陶”的肺,比其他人更迫切地需要进山疗养。
“他们从山里疗养回来,皮肤都晒成了棕褐色,跟风吹日晒的原始人一样,只有我一脸苍白。”他愤懑不已。作为老师,居立奇不应该吐露心声,因为这句话激发了我们的同学赫鲁贝什的灵感,他灵机一动,冒出了帮老师进行日光浴的鬼点子。
第二天我们立刻按照山上的光照强度更换了讲台上的灯泡。为了免受辐射影响,一些同学用绿色的透明尺遮挡住自己的眼睛。这是多此一举,因为讲台上的灯只能罩住居立奇的秃瓢儿。果然第一堂化学课下来,他就拥有了健康的肤色。第二堂化学课之后,他已经晒脱了皮。只是没等赫鲁贝什及时把灯泡撤换掉,A班的学生和他们的化学老师魏索娃就陆续进了教室。魏索娃嗅出了辐射的味道,她马上下令拆下整个灯头,送到居立奇的办公室。据说她还添油加醋地挑拨说:“现在你明白,为什么你的脑袋晒得像熏肉了吧。”她一出门,那位“山羊屁”原始人就冲到门外,在走廊里叫喊道:“你们听好了,某些人将被开除出校!”
这时我们的班主任科拉切克向他保证说,他一定设法找到罪魁祸首,并昭示于众人。老师进行了严密调查,肇事者却始终无法查实。我记忆犹新,当时他这样跟我们说:“你们对居立奇同志的所作所为,非常可耻并且危害健康,即使本着‘让同志晒日光浴’的初衷,你们的这种行为也是不值得肯定的。主谋这个事件的那位同学应该感到羞耻!同时也要感到庆幸,我们班无人参与!我重复一遍,没有人知道这是谁的鬼主意,学校可以开除一个学生,但开除全班,这是不可能的。”
借由这几句“金玉良言”,赫鲁贝什同学中学顺利毕业。
赫鲁贝什此刻就坐在我们老态龙钟的班主任身边,刚从老师手里拿过一副老花镜,以便看清一张6厘米×6厘米的黑白缩印照片,以前的老照片都是这种规格。
我必须去找班主任科拉切克,过一会儿他又该迷糊瞌睡了。通常他只能保持两小时的清醒,之后便会闭上眼睛进入梦乡,任由我们自己聊自己的。
脑海中浮现出另一个场景,在此我不妨讲给大家听。班级聚会的特别之处在于,大家知无不言,没有秘密,在交谈中尽情回忆,畅所欲言。于是,我插话说:“大家是否还记得,斯大林去世时,布尔班同学当时发表了什么高见?”
“呵,有意思啊,你讲讲看。”有人对此饶有兴趣。于是我开始讲述1953年发生的事。那一天,报纸上刊出了斯大林逝世的讣告,整个布拉格阴沉一片,被黑幕笼罩,如同童话里恶龙吃掉了美丽的公主那般,全城黯然失魂。广播里日夜播放着哀乐,播音员以悲伤低沉的声音播报说,无产阶级伟大领袖斯大林的遗体将被运往红场陵墓,安放在列宁同志的遗体旁,供后人瞻仰。整个和平阵营举国哀悼之时,在我们的一堂公民教育课上,一位督导突然走进了我们班级。
“你可千万别提那段历史了,当时我三宿都没合眼。”班主任抢过话头,然而看得出来,他愿意听我往下讲,否则他不会把一只手罩在耳朵上,生怕漏听了什么。
我接着描述,督导的脖颈上系着一条黑色领带,神情严肃地在讲台后坐了片刻,然后站起来,对我们老师说:“科拉切克同志,请允许我提几个问题。众人皆知,伟大领袖的逝世是无法挽回的损失。你们有人知道吗,斯大林同志的遗体将如何安置?”
台下鸦雀无声,在死一般的寂静中,科拉切克用恳求的目光望向我们。突然布尔班举起了右手,神情急切,而我们班主任的眼睛里浮现出了恐惧和不安。
“请你来回答。”督导发话。
“斯大林同志的遗体不会被埋葬在普通的坟墓里,而是放到红场上的……蜡像馆里,用于展览。”
大家都觉得可笑,然而这一次没有人笑出来。
督导没有说话,他转向班主任,眼神里充满疑惑。
“你想说的是陵墓里吧?”科拉切克补充道。
“是的!”布尔班回答。
“但是,你刚才说的是蜡像馆。”督导提高了嗓音。
“是的,是我口误了。”布尔班解释。
“你叫什么名字?”督导一边问一边从胸兜里掏出一个黑色记事本,小本的一侧插了一支黑色铅笔。
“拉迪斯拉夫•布尔班。”
“你的父亲从事什么工作?”
“我父亲是画家。”拉迪回答。
“那我们就得研究研究了,画家……”督导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仿佛一切在预料之中,随后在记事本上写下什么。
“我父亲是刷墙的画家。”布尔班补充道。他还不如不解释呢。
“督导同志,”科拉切克的额头渗出了汗珠,他鼓起勇气说道,“布尔班患过脑震荡,疾病对他的表达能力造成了一定伤害,导致他有时词不达意。他的父亲是玛尔比特合作社的劳动模范,在放假期间还抽空为我们粉刷过教室呢。”
我们怔住了。因为我们从没有听说过拉迪得过脑震荡,也不知道他的父亲为我们粉刷过教室。
督导半信半疑地将教室的墙壁扫视一遍,啪的一声合上记事本。
“这是一个严肃的时期,”他声色俱厉,不是针对我们,而是朝着科拉切克老师,“这就意味着要谨言慎行,否则会大祸临头。”
班主任示意我们全体起立,目送缓缓踱着四方步的督导从教室离去。
“很有意思呀。”赛义德的兄弟笑了起来,他是当时唯一不在场的人。他表示下一次的班级聚会他依然愿意参加,不想错过。
我回忆完斯大林逝世那一段往事之后,米拉•穆西尔示意我一起去阳台抽烟。我们自然而然地聊到了数学兼几何教师罗伯特•哈珀尔。一提起他,我就联想到棋手,因为哈珀尔是下象棋的高手,屡次参赛,战绩不俗。
这位安静、瘦长的先生,印象里始终穿着考究。只要他一出现,不安的情绪就会无形地在教室里弥漫,对此我一直疑惑不解。在他的课堂上,令人恐惧的气氛压抑得人喘不过气来。然而他从来没有过激的言辞,相反他很害羞,几乎不敢直视女生的眼睛,不像面对男生那样自然。当他问某个女同学问题的时候,往往将两眼望向天花板或者地面。他那双褐色的眼睛里和那张紧绷的脸上找不到一丝笑意。鸦雀无声是他的数学课堂的主旋律。只有当他背对我们在黑板上书写时,才有同学在底下窃窃私语,而当他转过头来,传递一个无声的眼神,教室里就会瞬间无声无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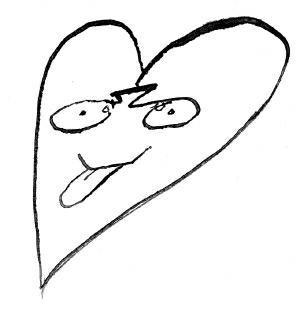
记忆中,哈珀尔老师似乎只展露过一次笑颜,然而这在我们的脑海中已经变得有些模糊。
那次穆西尔被叫到黑板前。因害怕数学考试不及格,他失去了正常的逻辑思考能力,语无伦次,浑身战栗。他在哈珀尔面前,如同小老鼠面对眼镜蛇,在黑板上演算时折断了粉笔,用抹布擦黑板时,汗湿的手掌心擦掉了刚写上的算式。最后他放弃了演算,用无奈的眼神望着老师。
“回座位去吧。”哈珀尔发令,面无表情。
穆西尔听到这话之后,并不想恶意搞怪,然而身体却如同被催眠的老鼠,一屁股瘫坐在了黑板前的讲台上。
班里的同学终于忍不住,哄堂大笑起来。哈珀尔先生此时转向黑板,背对我们,望着窗外。我敢发誓,他在强忍住笑,因为他的肩膀在轻轻起伏。唯独那次,那个铁面男人在我们面前流露出人性的一面。
还有一次是在毕业考试的时候,我在解答一个等式问题。哈珀尔先生就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我把2a从等式的一侧移到另一侧,却忘记了改变运算符号。这时,我感到有人在踩我的右脚。我不敢相信,事实确是如此:哈珀尔先生在课桌底下提醒我把加号改成减号。
这两次经历说明,罗伯特•哈珀尔先生并非不苟言笑,只不过在课堂上,他仅把严厉的一面展现给我们。
还有一件关于哈珀尔的小事,始终令我们疑惑。谜一般的一个词。哈珀尔先生在讲解数学的时候,班主任会不时走进教室,通知迫在眉睫的事项,诸如开家长会,或者采摘啤酒花、打理干草的义务劳动。说完之后,班主任会礼貌地为他打断了课堂教学表达歉意。在离开教室的时候,他每每悄声笑对哈珀尔说:“筷子!”哈珀尔也会干巴巴地回应:“筷子!”并且脸上掠过一丝神秘的微笑。
“筷子”这个词我们曾揣摩良久。有人说,他们说的是“三个杠铃”[捷克语“筷子”和“三个杠铃”发音近似。],可这根本解释不通。在教绘图的几何课上,哈珀尔先生会手持三角板和圆规走进教室,他把那些道具定在黑板上,用粉笔给我们示范在黑板上绘出如同在三维空间里呈现的直线。
我和穆西尔抽完烟,准备回屋。这时,那条老态龙钟的狗从房间里来到阳台,科拉切克跟在它身后。
“你们在这里吞云吐雾,谈什么呢?”
“我们在聊哈珀尔先生。请问罗曼老师,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逗趣吗?”我发问。
“罗伯特吗?他实在是个有趣之人。我本不该告诉你们的。你们知道他曾发表过什么高见吗?他说对于老师而言,三尺讲台是舞台,教员休息室就是化妆间。教师在化妆间里可以卸下伪装,展现本色。他是一个性欲极强的男人。”
“什么?哈珀尔,性欲强?”穆西尔惊愕得屏住了呼吸。
“嗯,那是。对他而言,教高中的学生是对意志力的考验。我记得,他上完课回到休息室,把办公包扔到桌子上,跟我感叹道:为什么丰满的史捷潘卡•罗索娃偏偏坐在第一排?你不能给她换一下座吗?谁能受得了?这哪里是在上课,简直是在表现英雄主义气概。”
“你们在说我吗?”罗索娃的声音从房间里传出来。她现在叫科瓦西洛娃,正给大家传阅六个孙辈的照片。
“没有!”穆西尔回应,一边掩上了阳台门。
“罗曼,你们彼此打招呼的暗号有什么含义吗?你们说的是‘筷子’还是‘三个杠铃’?”我不解地询问。
班主任笑了起来,踌躇了片刻,说:“嗯。我们都是男人啊,可惜哈珀尔已经驾鹤西归了……那是在教师节的一次庆祝活动上,哈珀尔一时兴起,给我讲了他最难忘的性爱经历。你们都知道,他是个出色的象棋赛手,去各地参加比赛。有一次他收到了邀请函,邀请他参加在科尔奇[位于布拉格南城的居民区。]别墅举行的象棋锦标赛,并且在按别墅门铃时,需要报上暗语‘开局让棋法’。罗伯特如约而至,他刚迈进门,里面就把门锁上了。他发现,这一次活动女性棋手远远多于男性,而且那些女人连开局让棋法是什么都不知道。因为她们不是象棋手。总之,哈珀尔陷入了一场性爱聚会。”
“群交!”穆西尔错愕地命名。
“是的。在那里他深深地迷恋上了一个女孩。在集体翻云覆雨之后,罗伯特悄声地在她耳边请求,希望他们两人能够私下幽会,在别的时间,在别处,就他们俩。女孩回答说:和你嘛,悉听尊便[捷克语“悉听尊便”和“筷子”发音近似。]!”
“随时随地的意思?”我想确认。
“是的。罗伯特对这个词烂熟于心,后来我们便以这种方式彼此问候。”班主任朗声笑着,打了个哈欠。
我们回到客厅里,阳台上的瓷砖因为失去了阳光的照拂,凉意透过袜子沁入我们的脚底。罗曼坐回到沙发椅上,一歪脑袋睡着了。我为自己深感庆幸,没有错失这次班级聚会。
夜半时分,我们轻轻唤醒了班主任,与他道别。
屋外繁星灿烂。
我们的班主任罗曼站在楼门前,目送我们离开。谁也不曾料想到,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相见。
“罗曼,明年还在你这里聚会!”拉迪•布尔班挥手喊道。
“悉听尊便!”班主任回应,同样朝我们挥了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