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错失之爱 | 收藏 |
体面的出租车司机
错失之爱 作者:兹旦内克·斯维拉克

布拉格市政厅大概不知道拿蓝色油漆派什么用场,变戏法似的在街面上画出了许多蓝道道,弄得人找不到地方停车。为此您也许会特地购置一辆斯玛特车,它车身短小,像是刚从游乐场赛道上下来,哪儿都能挤进去容身。虽然如此,一旦您把车随意停在了蓝线之外,那个以拖车公司为名的饥饿秃鹫便闻风而至,一口把您的爱车叼走,拖到维索羌尼[布拉格的一个偏僻城区。]自己的巢穴里。这下您就得跋涉两小时,气喘吁吁地赶到那里,心疼地掏出2000克朗,求他们仁慈地归还您的爱车。
只是,尊敬的市政议员们,从我家到公交车站,疾步而行也需要二十分钟,我的膝盖对此断然拒绝,不予配合。身为自由职业者,我得四处出击去搞配音、朗诵、试镜、主持企业文娱晚会,对着电台麦克风胡说八道,反正我必须奔波忙活,你们理解了吧?早晨我还有一个毛病,恋床,迟迟出不了被窝。我可以对自己说上一百次:起床了,阿尔诺斯特,您可以轻松出门,悠然踱步,顺道欣赏街边绵延不尽、风格一致的连体别墅,然后上坡,爬上一走动便摇晃的过街天桥,到达主干道对面的公交车站。话虽这么说,我就是起不来,而我在香甜的十五分钟睡眠和搭乘丑陋不堪的公交车之间举棋不定之时,公交车早就开走了。于是,我只得约出租车。
针对这种情况,同事亚麻籽为我建言献策,他说找一个固定的出租车司机,非常划得来。因为固定的司机可靠,不会绕道,待人恭敬,而且那个人知书达理的话,还可以有分寸地陪顾客聊上几句。有时他会保持缄默,因为他深知此刻的顾客需要清净。话毕,亚麻籽马上把自己的司机奥特鲁巴先生推荐给了我。据他说那人举止得体,会让我惊愕得眼珠子掉出来。
迈出家门口,一辆出租车已在恭候。坐在方向盘后面的司机,正埋头读一册厚实的线装书。见到我,他立刻放下手里的书,下车朝我迎来。他年纪在四十五岁上下,身材魁梧,中等个头,握手坚定有力,双目直视我的眼睛。
“日安,我叫弗拉斯基米尔•奥特鲁巴。您愿意坐在前面,还是后面?”他问。
前排座位上放着他那本书,于是我坐到后座上。
车里很洁净,没有打开收音机,这一点令我满意。后视镜上也没有垂挂晃荡不停的玩具熊或足球运动员人偶之类的东西。仪表板右侧贴有营业执照,旁边是一片塑封的枫叶。
“您在读什么书呢?”车子启动后,我开口。
“《在公爵庭院》和《世界天堂》,伊拉塞克[阿洛伊斯•伊拉塞克(1851—1930),捷克现实主义作家,历史小说和戏剧作者。]两部长篇的合订本。”司机一边回答,一边用右手翻开了书。
“铜版纸印刷,阿道夫•卡斯帕尔提供插画。很精美,是吧?”
为了看到书中的彩色插图,我俯身凑近前座椅背。
“嗯,插图很美。”我说。此时,我已经领悟到出租车司机奥特鲁巴的雅致所在。他说一口标准的捷克语,完美,凝练,无可挑剔。
“我注意到,您车子的右侧挡泥板上有擦痕。”我没话找话。
奥特鲁巴回答:“没错,右侧挡泥板。我已经约好了钣金工。”
“您是摩拉维亚人吧?”我判断,否则我无法解释。
“我在卡尔林长大,霍谢克先生。”他使用了第五格呼格称谓,这种表达在当今几乎已绝迹,“哦,上次我载了两位姑娘,她们也以为我是摩拉维亚人呢。”他回过味来,“那俩姑娘说连电视播音员也不会如此表达。”
“伙计,您说的是纯粹的书面语。”我打趣道,“我猜您以前当过语文教师或类似的文职。”
“我毕业于电气工程技校。”他面带笑意作答。
“技校能教授您如此完美的捷克语?”
“是的。”他说。
就这样,我时常约上奥特鲁巴先生的出租车出门,耳朵里灌入了大量标准的母语。他是一个让人信赖的人。当我在夜深时分从岩石酒吧给他打电话,只须说:“弗拉斯基米尔,我在帕拉茨基大街。”他便在电话里回应:“帕拉茨基大街?我现在莱特纳一带,交通路况良好,十五分钟之内我将到您那里。”每每他都能如约而至。
奥特鲁巴优雅的谈吐在眼下混乱的通俗语表达中显得高贵而令人意外,这就好比在倾倒的垃圾堆上长出了玫瑰,然而有时难免矫枉过正。有一次,他告诉我说,在电视上他看到了博•波莱夫卡[捷克当代著名演员。]。我说:“弗拉斯基米尔,你夸张了。那个人的名字叫波利夫卡,你不能叫他波莱夫卡。”
“真不好意思,阿尔诺斯特,我弄混淆了。但是波莱夫卡听起来更为悦耳。”他说。此刻他正对一个因鲁莽过马路而差点儿闯入我们车轮下的老妇告诫道,“小心点儿,女士,要当心!”
“我说,弗拉斯基米尔,既然我们聊到了波利夫卡的名字,你是否也改过姓名?”我突发奇想。
“是的。”他羞涩地承认。
“真是难以置信。那么,你正常情况下应该姓沃特鲁巴[沃特鲁巴Votruba。在不标准的通俗捷克语中,为了便于发音,在元音O开头的单词前添加上V。主人公的姓氏Votruba实为正常词,但他为了避嫌不标准的通俗捷克语,更名为Otruba。]?”
“对。”
“你是怎么做到的?更名的依据是什么?”
“我就说我的姓氏令人厌恶,同时给女办事员准备了一盒高级巧克力。”奥特鲁巴如实作答。
细心的读者也许留意到,我们俩已经以“你”相称。没错,我跟这个特殊的男人迅速拉近了距离。糟糕的是,他的谈吐太具有感染力了。当他问我,在我的乡间别墅是否装有饮用水时,我在他的标准语影响下,居然愚蠢地回答:“有下水道[捷克语“下水道”为“vodovod”,作者信口说出“odovod”,去掉了首字母“v”,这个词便失去了意义,属画蛇添足之举。]。”
下水道,你们看明白了吗?我恨不得抽自己一个嘴巴。
但是,无论我如何打探,皆不得其解,眼前此人的语言差异源自哪里。
“弗拉斯基米尔,”我不依不饶,继续打探,“请不要跟我说,你,卡尔林区长大的普通男孩,打小就这样完美地说话,那还不被你的同伴们往死里揍。”
“打小倒没有,那是后来的事。”坐在方向盘后面的奥特鲁巴咧嘴乐了。
“因为什么?”
“到电气工程技校之后才发生的。”他脸上的笑容黯淡了。
“你从来不说脏话吗,伙计?”我好奇。
弗拉斯基米尔摆摆手,说:“有时,我也会咒骂。”
“你怎么咒骂的?”我的好奇心爆棚。
“比如我会说‘无聊’‘差劲’,或者‘见鬼去’……”
“这可不解气,伙计。你这种替代词管个屁用。”
“在我被气得七窍生烟时,我甚至会说‘他娘的’。”奥特鲁巴承认。
自然,我不会天天打电话约车,那种奢侈得让我把裤子赔上。我一周内用他两次车,便如同享受了昂贵的珍馐佳肴了。
那一天,我又睡过头起晚了,我的出租车司机只有三十分钟时间,把我送到坐落在卡尔林区的瑞吉娜广播电台。他使出浑身解数,迂回穿梭抄近道,在日兹科夫区拐入了施吉特尼街,在那里,我们遇见了拖车服务队。他们赫然挡在我们面前。
“他娘的!”我骂道。
“的确令人不悦。”奥特鲁巴说罢转头往后看,想倒车撤离。不幸的是,我们的后头已排上一列车阵。我们被堵在那里动弹不得,只好无奈地观望起眼前上演的无情“猎车”游戏。那些人在劫持每一辆遭殃的汽车之前,先拍照,然后铲起车挂上吊钩。
这时,后面某个暴躁的司机大肆鸣响了喇叭。
“猎人”中一个身量不高的年轻人,仿佛被蜇咬了一口。他站在拖车平台上停顿了一秒钟,然后把目光投向我们的车,扔下手里的缆绳,摘去工作手套,迈出缓慢的步伐——向人昭示:有别于我们,他有的是时间。走到我们车前,他猛地一把拉开驾驶室侧门,脱口呵斥道:“摁什么喇叭,畜生?找抽是不是?”
不出所料,我的司机没有跟他一般见识,而是面带微笑说:“你弄错了,先生,不是我摁的喇叭。”
“少废话,傻蛋,出来!”他文过身的爪子揪住司机的西装衣领。我怒了,跳下出租车,冲他嚷起来:“怎么说话呢,你这混蛋?!”
“你闭嘴,老家伙!”他一把将我推倒在地。那一刻,从我们后面的一辆车里晃出一位壮汉,他站到那小个儿面前,居高临下、面无表情地发话说:“是我摁的喇叭。想抽我,来啊。”
邪恶的小子权衡了一秒钟,往地上啐了口唾沫,嘟囔一句:“这鸟活儿!”回到了自己的拖车平台。
待我们的车终于开动时,我说:“弗拉斯基米尔,我搞不懂,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这种侮辱,你怎么依然能像在豪华餐厅里用餐那样说话?语言,嗯,它是一种工具,就如同配备了大量寄存器的管风琴,譬如一个音栓代表酒吧,第二个代表家庭,第三个办公室,第四个演讲,第五个卧室……而你呢,总在一个寄存器上演奏。伙计,你过于单调刻板了,你这种无菌的语言无法撩拨任何一个女人,让她们兴奋起来。你跟妻子在床上也这么交流吗?”
“当然。”他说。
“万一她高潮时满嘴粗话呢?很多女性都会这样。”
“那我鞭笞她。”他笑了起来。
“你使用鞭子?”我希望自己终于发现了他的某些变态。
“没有。我就是比喻而已。”他淡淡地回答。
一个温暖的春日,奥特鲁巴身穿短袖T恤在驾车,让我深感惊讶的是,他臂膀的肌肉丰满隆起。
“你常去健身房吧,胳膊如此健壮?”我问。
“不去,我在家锻炼。以前练过搏击。”
“你,搏击?”我毫不掩饰地狐疑。
“对于司机这个职业,搏击很能派上用场。我已经展露了两次身手。”
“遭遇抢劫了?”
“对。每一次都在黎明时分。这个时间段现金一般都在身上。”
“是啊。他们以为,一个说话跟牧师似的彬彬有礼的司机,一定不会伤人。”
“对,但他们都失算了。”奥特鲁巴开心地笑着。
“结果呢?”
“第一次我弄折了那人的手臂。第二次让劫匪的右肩脱臼,很痛苦的,所以我立刻开车把他送到了斯特肖维策医院。”弗拉斯基米尔沉浸在回忆之中。
“厉害呀!”我伸出拳头试探着砸向他的二头肌,“那你之前为什么不教训一下拖车行的那个小子呢?”
“迫不得已我才出招,”他说,“当时还没到极端时刻呢。”
之后,我拿到了一单活儿,去赫鲁迪姆城为一家企业主持晚会,对方支付交通和住宿费。我打电话约了奥特鲁巴。晚会结束后,我们俩点了一瓶绿维特利纳葡萄酒,品鉴后一致认为,葡萄酒口味醇厚,连着又要了两瓶。我们惬意地吞云吐雾,而酒精,人类的祸害,这一次展现出它温柔善良的一面,让我们向彼此敞开了心扉。在这种时刻,我忍不住吐槽自己失意的爱,我给弗拉斯基米尔描述我与美人娜迪亚的恋情,她是我心头无法愈合的伤痛,是她无情地将我一脚踹开,如同门将在球门前一脚将球踢离,踹到了远远的中场。我的叙述显然触动了弗拉斯基米尔的心弦,他端起酒杯,透过清亮的维特利纳酒液望着我,一饮而尽,然后开口说道:“在技校的最后一年,新来了一位女老师,教我们捷克语,名叫伊丽莎白,二十六岁。恕我不透露她的姓。她长得那么美,为此我生了一场病。”
“请做一下描述。我难以想象。”我请求。
“我不能。那是一种糅合在一起的美,你明白的,遥远空灵的眼神,倾侧的脸庞,轻盈的步态,还有嗓音,那嗓音,为她令人窒息的魅力锦上添花。”
“那她的身材,是修长还是纤巧?”我按捺不住。
“纤巧。她身上的一切都精致小巧,手,鼻孔,让人忍不住想象她纤细的鼻孔是如何呼吸的。还有耳朵……她的耳朵露在外面,因为也许为了显得高挑,她的头发往上梳起。给我们做听写时,她在课桌之间徜徉,她身上奇妙的香味便在教室里弥散开。那不仅仅是香水,阿尔诺斯特,里面融合了她的体香。当她在我的课桌旁停下脚步,往我的练习本上端详时,我几乎晕厥。
“‘写啊,奥特鲁巴,你为什么不写了呢?’她的手轻轻放在我的肩胛骨之间,我的身体在颤抖,她一定感觉得到。”
“她叫你奥特鲁巴?”
“是的,虽然当时我还叫沃特鲁巴。这是她给我开的一个玩笑。我的捷克语开始出类拔萃,其他科目却几乎都不及格。我一本不落地通读了她推荐的文学作品,而且是高声朗读,至少读出声。妈妈受不了,在她房间冲我叫喊:‘弗拉斯基塔,你就不能像别人那样默读吗?’
“我如实相告说,我不能,因为出声读小说,我才可以模仿她说话的样子。令我激动不已的并非小说情节,而是她在对我说话,如同出自她的嘴唇,你明白吗?”
“明白,弗拉斯基克,我能理解。”我说。
奥特鲁巴等酒吧女招待开启了另一瓶葡萄酒,目送她远去后,继续叙述:“她让我魔怔了!有一次,我在学生食堂故意磨蹭到最后。她坐到我的旁边,对我说:‘弗拉斯基塔,在课堂上你别那样盯着我。那会打扰我讲课。’
“‘好的。’我说。她感激地笑了,轻柔地捏了一下我的肩膀,离去了。多少次我回味她的这番话!这意味着我的痛苦她心知肚明,这也意味着她并非无动于衷。当她负责的校图书馆需要一名志愿者时,我第一个报名。我在那里填写索引卡片,编号和整理图书。我坐在图书馆里她的办公桌后面的座椅上。你不会相信,阿尔诺斯特,那个小男孩能在椅子上爱欲膨胀。”
“怎么不能呢?我的朋友,是她坐过的椅子呀。男人会妒忌那把椅子!”我说。
“对!”我的感同身受让弗拉斯基克倍感欣慰,“她不在的时候,那把椅子,那个她坐过的座位,我一遍又一遍地抚摸,嗯,类似一个恋物癖。”
“如果她在场呢?”我想知道,女教师是否允许他有所冒犯。
“有一次,我坐在她的椅子上往图书里面标注登记号。她从我身后走来,靠近椅背,我完全被她的馥郁包围,她说:‘弗拉斯基塔,一旦你坠入爱河,就不会移情别恋,对吗?’
“‘是的。’我说。
“‘你不会介意?年龄的差异……可我的职业禁止发生这样的事,你不介意?’
“‘不介意。’我回答。
“她的手抚摸着我的脖子,柔声说道:‘不能。我们不能这样做,尽管我们很想要。在生活中,在大多数的情形下,我们无法随心所欲。’
“她从后面迅速亲吻了一下我的脖子,离开了。”
“然后,什么也没有发生?别告诉我你们之间就这样草草结束了!”我迫不及待地问,点燃了一支烟。
“你知道吗?那句话昼夜不停地在我的脑海里回放!‘尽管我们很想要’,你明白吗?‘尽管我们很想要’!这意味着她有同样的欲望!”弗拉斯基克的眼睛直直盯着我,酒精让他的眼神涣散,他在企求我的认同。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表白,你这个傻瓜!”我说。
“学年的最后一天到来了,那是一个明媚的六月天。”弗拉斯基克嘘了口气,叙述慢慢趋向尾声,即使酗酒也没有影响他标准语的表达,“我在西里尔和迪乌斯广场买了三枝含苞待放的玫瑰。把成绩单塞入衣兜,手持鲜花,我敲开了学校图书馆的门。
“她把鲜花插入花瓶,转身说:‘我为你摘下了一片枫树叶。’她递给我一张叠成四方形的纸,这样枫叶不会卷起。
“‘您哭了?’我问,凝视着她的眼睛。
“‘有一点儿。’她羞怯一笑。
“我记得,学校的庭院里传来阵阵鸟鸣。鸟儿凄厉的悲鸣回荡在建筑大楼的四壁,仿佛那里聚合了更多的鸟儿,庭院容不下了,仿佛鸟儿拼命想飞出院子,却无能为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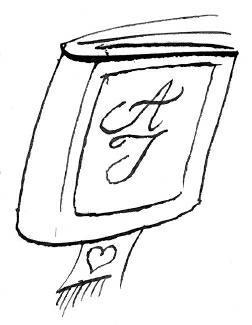
“‘为什么不往上高飞呢,既然它们有翅膀?’我说。
“‘不知道。’她摇了摇头,泪水潸然而下。
“然后,她闭上眼睛,我们拥抱在一起。那么默契,阿尔诺斯特!就像一个物体的两半,之前开裂了,现在黏合在一起,断点上所有的裂纹都嵌入凹槽,重新融为一体。它就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们俩倚靠在小说栏的书架上,书脊上的作家名字有:阿尔弗雷德•加利、兹德涅克•耶洛特卡、雅罗米尔•约翰、詹姆斯•乔伊斯、约瑟夫•容格曼,出现最频繁的名字是阿洛伊斯•伊拉塞克。我紧紧抱住我的捷克语老师,一动不动,胸口感觉到她娇小的乳房,她的双腿紧紧贴住我的膝盖。没错,我不敢动弹,希望就这样到永远。后来有人从教室窗户往院子里扔鞭炮,惊得鸟儿们扇动翅膀往天上飞去。而我,阿尔诺斯特,即使没有动弹,也感觉跟鸟儿们一起一飞冲天,甚至飞到了无法预想的高度,直至眩晕。这种感觉我后来跟别的女性,再也不曾体验过。”我的出租车司机坦陈。
“别扯了!你想说,这是故事的全部?”我不信。
“没错,这正是我想说的。”弗拉斯基克言罢,饮了一大口酒。
“然后呢?”
“暑假结束后,我在学校门前守候了几次。后来别人告诉我,说她在那年夏天嫁给了一个外国人,移民到了加拿大。后来我再没有见过她。”
至此,关于我那位体面的出租车司机的故事可以收笔了,那样的话你们就无法得知我们俩在斯梅奇卡大街上的遭遇了。奥特鲁巴在这条单行道上载着我,前往奥普莱塔尔街。前方出了交通事故,显然,我们被困住了,短时间内挪动不了。弗拉斯基克不安地搓着双手,又揉搓几下膝盖,然后跟我说,他需要出去方便一下。
“能憋住吗?”我问。
“很急,感觉膀胱都要炸了。”他边说,边擦了一把额头渗出的汗珠。
我告诉他,在我们右手边的那家酒店,顺前台往里走就是洗手间。奥特鲁巴疾步进了酒店。看他好一会儿不回来,我拔下插在点火器里的钥匙,锁上车,进入了酒店。在玻璃门外我就听到了酒店大堂里传出来的争吵声。
“这样有何意义呢,伙计?难道您从来没有内急之需吗?”出租车司机奥特鲁巴在质问,两眼绝望地盯着酒店大门上戴高帽的金娃娃。
“我第五次警告您,这里不是公共厕所,我们的洗手间仅对酒店客人开放。”那个魁梧、微秃的混蛋保安,叉开两腿挡在奥特鲁巴面前。
然后,我亲耳听到弗拉斯基克说:“先生,待人且和善些,你他妈的一边见鬼去!”
这句令人难以置信的话之后,他一把推开保安,那人倒向了服务前台。
当弗拉斯基克的身影消失在洗手间后,那个保安野牛般跟了过去,想阻止他方便。这时我插话说:“伙计,难道您不认识内政部长吗?”
“你胡扯!”他气鼓鼓地说。当奥特鲁巴从洗手间回来,保安举起了手致意,直到我们出了酒店走上人行道。
“我运用了你给我建议的寄存器,阿尔诺斯特。真是解气啊。”我体面的出租车司机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