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婚前一年 | 收藏 |
13
只有爱情的婚姻是走不下去的;没有爱情的婚姻也是走不下去的
作者:李柏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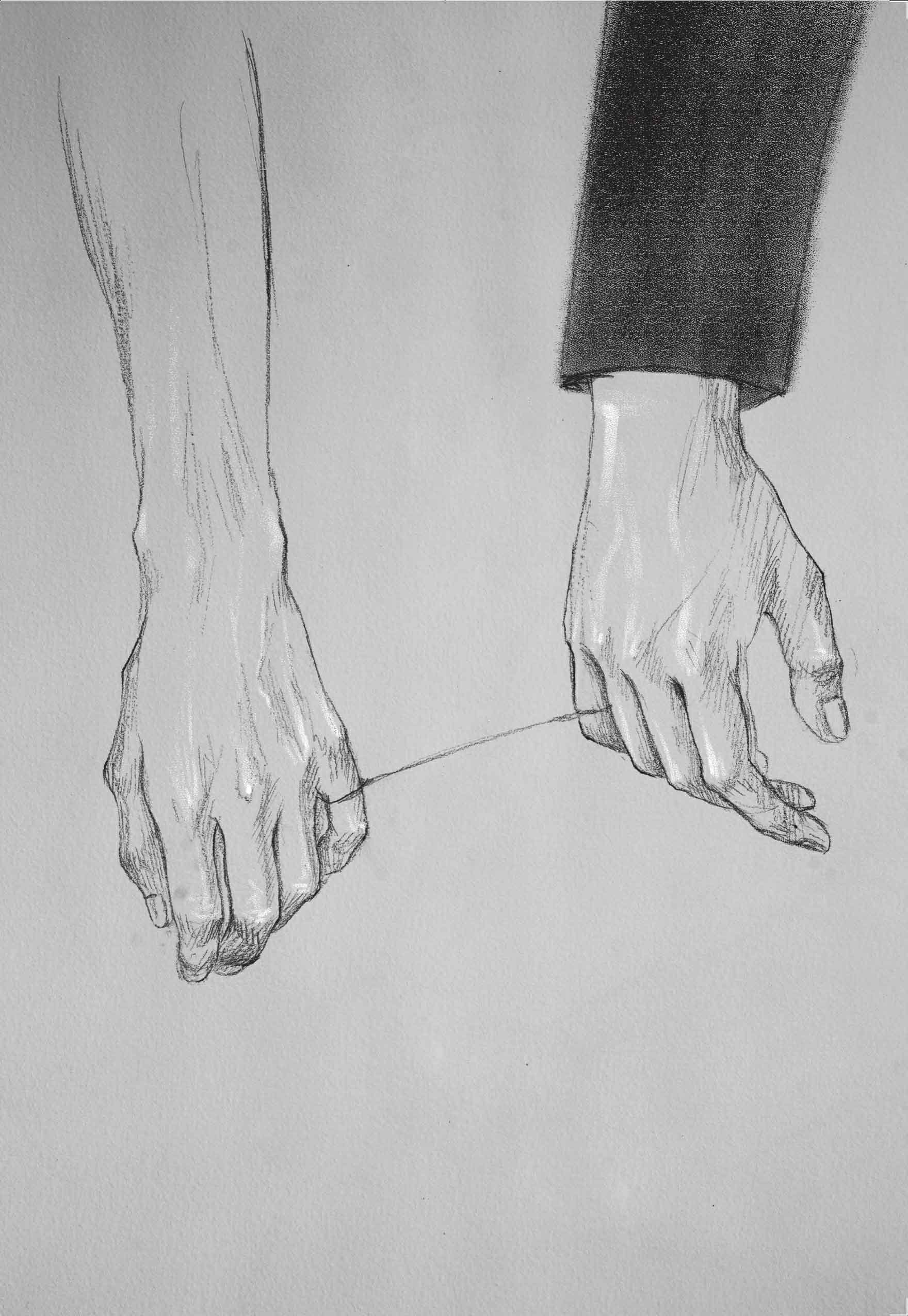
“我那时候是真的打算和徐千帆走一辈子的,我以为我可以。她性格很好相处,外向、喜欢往外面跑交朋友,我比较内敛一点,可以帮她处理家务;我们都想要有个家,都想要有小孩,都打算在美国留一阵子然后回台湾。重点是,我们都不那么爱对方,也不会要求对方为彼此付出太多,就是一对伴侣基本的陪伴,建立社会上的门面,其他空间就是自己的。嘿,那时我觉得我们简直是天作之合,但后来我发现太天真了,婚姻比我想象的难太多了。”
菜头学长为茶壶中注入热水,缓缓地说:“以前几任分手经验让我觉得,婚姻要面对的现实困难实在太多了,所以只有爱情的婚姻是无法长久的;但与小帆走过这一回,我也了解,也正因为婚姻要面对太多现实的困难,没有爱情的婚姻,也是走不下去的。学弟,这是学长十年来的人生体悟。”
当我告诉二马与阿本我的“劫孩见父”计划时,两人都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这犯法吧?”二马说。
“没有吧,我没有引诱,是他来找我的。”
“绑架?‘儿少法’?反正我觉得不大对啦!”二马说,“为什么要为一个小孩子以身试法?”
“因为我欠他一份冰激凌。”
“什么?”
我告诉他们我之前在攀岩场遇到艾登,给他名片,答应请他吃冰激凌的事。
“那就请他吃冰激凌啊!干吗要做那么危险的事?”
“因为这是男人的承诺。”我说,“不是啦,一个六岁小孩半夜打电话给你,哭着说要找爸爸,你舍得跟人家说不要吗?”
“对女人心软,对女人的小孩也心软,为你点首《心太软》好了。”二马说。
我看向阿本:“怎么样,要不要加入?跟你当事人利益应该没有冲突吧?”
阿本想了一下,说:“但是怎么做得到?我老实说吧,菜头学长之前试过去找他小孩,但都没有办法,徐千帆防得密不透风。你要怎么把一个六岁小孩带走但不让他妈妈知道?”
“只有我们三个臭皮匠当然做不到,”我说,“我们需要特别的帮手。”
“什么特别帮手?”
我清了清喉咙,高声说:“女士们先生们,欢迎特别来宾,郑水澄小姐!”
包厢门推开,穿着长大衣的郑小姐踩着猫步走进来,在屏幕前站定,食指自额间往上一挥,然后向前划个小弧度落下,向包厢内众人说:“感谢您。”
我觉得一阵尴尬,我跟她说我可以用正常方式介绍她给二马阿本认识的,她坚持要学凤飞飞。
“这位是……?”
“徐千帆的妈妈。”
“原来是徐妈妈!”冯二马用夸张的声调说,“太年轻了啦,难怪都认不出来。”
徐妈妈开心得眉开眼笑,直拍着二马说:“你就是彼个[彼个:那个。]二马嘛,若是艾伦嘛像你嘴遐[遐:那么。]甜,当初就袂[袂:不会,不能。]给阮家千帆走去[走去:离开,走了。]了。”
徐妈妈是个充满反差感的女士,不说话的时候是位低调气质贵妇,衣着朴实、妆发平淡,只有银质细链上那颗钻石标志她“百亿郑家长公主”的地位。不过她一说话就是个搞笑谐星,还是很老派的那种。
那天我和艾登打到一半电话就被徐妈妈抢过去,弄清楚我的身份后,她便对我大吐苦水,说艾登每天想爸爸,又不敢跟妈妈说,只有来阿公阿嬷家住时才敢偷偷跟阿嬷哭,只是没想到他还会偷偷打电话找外援。
“恁拢[恁拢:你们都。]这么大了,阮老岁仔[阮老岁仔:我们这些老人家。]也不用说什么了。女儿交男朋友,当然嘛好;分手,没关系啦,还会再有;想欲结婚,好啊,管待[管待:理会、理睬、答理。]是啥人;现在讲欲离婚,当然嘛支持。”
徐妈妈喝了口威士忌,叹气说:“恁大人忙就忙,苦都是苦到囡仔……唉,阮看阮艾登是愈看愈不忍心,年纪那么小,又那么懂事,想爸爸不敢讲,自己目屎[目屎:眼泪。]吞落腹内,阮这做阿嬷的,唉,心痛啊!”
阿本问:“徐妈妈,你为什么不自己带小孩去找他爸爸啊?”
“呃……阮会惊[惊:怕。]啦!”
“惊徐千帆哦?”
“对啊,恁嘛知影徐千帆那个性,做母的也会惊。”
根据徐妈妈提供的情报,小帆并没有请保姆或陪玩姐姐,艾登每天幼儿园下课,小帆亲自去接,带他去上攀岩、画画之类的才艺课,之后便回家,隔天再亲自送他去幼儿园;周末小帆则会带艾登去动物园、博物馆。简单来说,除了上学时间外,小帆与艾登总是形影不离。
至于幼儿园呢?艾登上学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八点半到下午四点半。那是间高档的私立幼儿园,门禁森严,凭证件接送,而且因为人数少,老师都认得家长。
阿本补充说,菜头学长之前就试过去幼儿园见艾登,但被园方挡了回来,说是妈妈特别交代的。
这样看来,确实如阿本所说,想趁小帆不知不觉将艾登带走几个小时,似乎是绝无可能的任务。
“但是哦,囡仔顾久也是会疲劳啦。”徐妈妈说。
小帆照顾艾登虽然力求亲力亲为,但她总是有工作的人,时间没有办法永远安排得刚刚好,先前一个月大概有几天,小帆会因为其他事情请徐妈妈去接艾登下课,至于留艾登在阿公阿嬷家过夜则是极少数的例外(艾登就是趁那几个晚上打电话给我的)。这个月开始,每隔周星期四晚上五点到八点,小帆要去上EMBA课,因此将由徐妈妈去接艾登下课,晚上八九点再送艾登回小帆家。
“阮也讲艾登会使在阮家困啊,伊嘛会当稍休一下,伊就毋爱,讲隔天还要上幼儿园,一定爱转去厝里。[阮也讲艾登会使在阮家困啊,伊嘛会当稍休一下,伊就毋爱,讲隔天还要上幼儿园,一定爱转去厝里:我也说艾登可以在我家睡啊,他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但他就不要,说隔天还要上幼儿园,一定要回家。]”徐妈妈说。
因此现在艾登可以去见爸爸的时间,就只有周四下午四点半到七点半,大约三个小时而已。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请菜头学长到幼儿园附近,徐妈妈先将艾登接出来,送去给爸爸,他们父子俩就可以享受三小时的二人时光。
“不行,这样会违反保护令。”阿本说。
阿本说,大概是受到菜头擅自去幼儿园找艾登的刺激,小帆拿先前的验伤单跑去申请了暂时保护令,正式命令还要等法院决定。根据保护令内容,菜头学长不得接近艾登的住所与幼儿园,也不能与艾登为“非必要之联络”。
因此菜头学长不能出现在幼儿园方圆一百米以内,就算在禁制范围外,只要菜头学长出现的目的是要和艾登见面,也可能被认为违反保护令。
阿本说,菜头学长唯一合法见儿子的方法,就是艾登主动去找他,而菜头学长在事前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儿子“巧遇”。身为菜头学长的律师,阿本能做的最多就是在行动当时帮我们确定菜头学长的所在地点而已,再多做都会陷菜头学长于不法。
喝完三瓶威士忌后,“劫孩见父”的行动纲领总算成形。行动当天由二马开车,停在一条街以外的黄线区,避免引起园方注意;我则等在幼儿园围墙转角处,避开接送室视线。徐妈妈接出艾登后,带到转角交给我,我再带艾登上二马的车,这时阿本传来菜头学长所在的地点,我们就可以带艾登去看爸爸了。
我们又讨论了很多突发状况,例如下大雨、突然要跑步、二马车抛锚之类,讨论到徐妈妈都说难怪我们会是律师,要是用我们这种方法做生意,大概一颗螺丝都卖不出去。
行动当天我特地请了半天的假,提早来到幼儿园附近熟悉地形,只见二马那辆BMW大七已经停在黄线区,二马坐在里头啃着热狗堡。我隔着车窗跟他指了指头顶的蓝天,比了个大拇指;他让引擎空转几声,回我一个大拇指。
下午四点十五分,我在围墙转角处就定位,看见徐妈妈下出租车,与我交换个大拇指后便往接送室方向走去。我在原地耐心等待,但直到四点四十分仍不见徐妈妈与艾登过来。我开始焦虑,心想是不是出什么意外了。我又等了五分钟,终于忍不住,将身体偷偷探出墙角,只见徐妈妈牵着艾登,一旁跟着显然是幼儿园老师的女人,正有说有笑地朝我的方向走过来。
我心里呐喊:计划不是这样的啊!老师要是怀疑我是爸爸而联络小帆怎么办?
我正要缩回墙角,却见吴正非大步地从幼儿园大门方向走来,他超过徐妈妈与艾登,与我正好打个照面。吴正非满脸意外与尴尬(我猜我也是),顿了一下才向我打招呼说:“艾伦,真巧,你也来接小孩啊?”
吴正非这一招呼,事情就毁了,艾登看到我立刻向我跑来,边跑边说:“要去找爸爸吗?”我打手势要他小声已经来不及,我看到那位老师一脸怀疑地看向我这儿,然后不理会一旁拼命解释的徐妈妈,拿起手机便打。
“艾登,我们走!”我拉起艾登的手便走,身后却响起老师高声呼叫保安的声音,我回头一看,只见一名一百九十厘米、肩宽至少六十厘米、身穿黑皮衣、脸戴黑墨镜的彪形大汉从幼儿园中冲出,直线向我跑来。我二话不说抱起艾登便往前跑,心中庆幸之前有沙盘推演到“跑步”的环节,所以我现在穿的是轻便的运动服运动鞋。
我没命地往前跑,跨过一个路口,二马的车已近在眼前,我大喊要他发动,同时也感觉后方追兵的手指已经碰到我的背。我身体往前挺,再加快脚步,但毕竟手上扛了个二十多公斤的孩子,加速有限,才没两步,那保安的大手已经搭上我的肩,一个粗豪的声音说:“不要跑!”
就在我感到绝望的时候,那手松开了,粗豪的声音喊着:“喂……你在干什么……放开我。”我回头一看,只见徐妈妈整个人跳到保安身上,双手遮住他的墨镜,同时用一种电影慢动作的表情喊着:“快──走──”
我没有停下脚步,甚至没有半分犹疑,我抱着艾登跳上车,在二马踩下油门之际,关上车门。我挣扎着爬起身,看向后车窗,对着被保安扣住双手的徐妈妈做了个凤飞飞“感谢您”的敬礼。
车子钻进车流中,我们二大一小仍惊魂未定,二马惊恐地问刚刚那个是谁,我说是幼儿园保安,他问为什么幼儿园要请个魔鬼终结者来当保安。
我叫二马废话少说,问他阿本有没有确认菜头学长的所在地,他说有,在北投的某个公园,阿本还说他叫菜头学长别问原因,在原地至少停留三十分钟,这是阿本能做的极限了。
“三十分钟够吗?”我说。
“都够我们吃顿下午茶了。”二马说着油门一踩,车子如子弹般射出,在新生高架上一“马”绝尘。
我稍稍放下了心,瘫在椅背上重重地喘着气,艾登递给我他的手帕和水壶,霎时间我觉得为这孩子上刀山下油锅都值得。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小帆打来的,我二话不说直接挂掉,她又打来一次,我依然拒绝接听。过了一会儿,手机又响了,是蒋恩打来的,我接起来。听见蒋恩用高八度的声音喊:“杨艾伦你是不是把徐千帆的小孩带走了?你是有什么毛病吗?绑架人家小孩干吗?小帆吓死了,她问我你是不是恋童癖,还说你是要报复她把你解除委任。”
“我只是要带小孩子去见他爸爸。”
“蔡得禄叫你弄的?”
“不是,是小孩子找我的。”
“找爸爸跟他妈妈说不就好了?”
“说得通就不是徐千帆了!”
我们很快地来到温泉旅馆林立的北投区,根据导航,离目的地公园只剩下五分钟车程。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辆警车在我们车后拉响警笛,并用扩音器念出车号,要我们靠边停车。
“哇,是警车耶!”艾登趴在座位上兴奋地说。
二马显然更兴奋:“这样就被警察吓倒,要怎么当律师?全部给我坐好!”
车子陡然转弯,我和艾登随惯性向左边倒,然后向右边倒,再向左边倒,再向左边倒得更低一点。
“好了,甩掉了。”二马说,“想追上我‘蟾蜍山的藤原拓海’,还早得很嘞!”
“叔叔好厉害,好会开车,我爸爸都开得慢慢的。”艾登开心地说。
我只能说小孩确实是复杂的生物,温良恭俭让的艾登对于我们的“速度与激情”情节显然乐在其中。
“喂,二马,还是小心一点啦,我们又不是重大要犯,不要搞得……”
“又来了,坐稳!”
一阵贴背感,然后又是如云霄飞车般的左摇右晃,二马显然是豁出去了,开着大七在北投街头喋血飙速,但这回警笛声并未消失,更糟的是还多了另一辆警车。
“没办法了,出绝招。”二马方向盘一转,车子驶进一条较小的街道,我的身子还没回正,又是一个急转弯,车子已开进一条狭窄的暗巷中,并且贴着墙边停下。二马快速地关灯熄火,并要我们趴下。我听见警笛声掠过巷口,慢慢远离。
“从成龙电影里学的,帅吧?”
“叔叔超帅的!”
二马又自吹自擂一番,然后重新启动引擎,缓缓往巷口驶去。
此时,一辆警车堵在巷口,扭开远光灯。
虽然是现实生活,但我想我和二马当时的心中都响起了“噔、噔”的音效。
二马切动排挡,沿巷子倒车,但另一端巷口也出现警车,并同样以远光灯锁定我们。
两辆警车自两端慢慢逼近,二马前前后后试探几回后,下决心似的拉起手刹,指着一旁阴暗的防火巷,以悲壮的语气说:“这条巷子走到底就是公园了,你们快走,这边我来扛!”
我将车门推开一条细缝,与艾登尽可能压低身子下了车,并往暗巷内没命地跑。我偶然回头,只见二马高举双手下车,脸上带着平静的微笑,一名警察冲上来将他压制在车上,进行盘查。
我没有停下脚步,唯有以更快的步伐,向光荣牺牲的战友致以最高的敬意。
我和艾登沿着防火巷跑着,他的速度比我所想象的六岁男孩要快许多,我几乎是要全力奔跑才跟得上他。防火巷不仅阴暗,而且堆放杂物,我们得停下来搬开挡路的馊水桶才能继续前进。就这样跑了一阵子,前方天空渐渐开阔,天光洒下,虫鸟渐闻,人声渐响,然后就是……一道两米多的砖墙封住防火巷口。
而后头警察追赶的吆喝声正快速逼近中。
我跳起来试着攀上墙头,但跳了两次都不成功,只好去将刚刚那个挡路的馊水桶拖过来,一抬头只见艾登已经蹲在墙头上,我问他怎么上去的,他说他会攀岩,又说警察追过来,要我快一点。我赶紧将馊水桶推至墙边,站上馊水桶,双手刚攀上墙,左脚已经被人抓住。
“快跳!”我向艾登大吼,同时两脚乱踢,趁着警察松手,我一鼓作气攀上墙,然后纵身一跳,在柔软的公园草地上打了个滚,正要起身,只感觉背上一阵沉重的压力,左手被人抓住往后一扭,巨大的疼痛与绝望令我惨叫出声。
“爸爸!”
“艾登!”
我从土壤与草丛中挣扎着抬起头,只见艾登与菜头学长抱在一起,一旁站着J.J.那个高高瘦瘦的CFO。
“我那时候是真的打算和徐千帆走一辈子的,我以为我可以。”菜头学长苦笑着说,同时将第一泡茶水倒掉。
现在的菜头学长已恢复成当年我所认识的那个菜头学长,原本坚硬的肌肉线条全松软了下来,语气也回到原先的温柔和缓,双眼水汪汪的,似乎随时含着泪。他慢条斯理地沏茶,印度尼西亚裔CFO阿玛德则在一旁将凤眼糕盛入小盘分送给大家,一切是如此宁静与和谐,好像今天下午的一场闹剧从未发生过一样。
“婚姻中有太多的现实困难,没有爱情的婚姻是走不下去的。”
菜头学长饮下第一杯茶,长长地呼了口气,如吟唱俳句般做出他的人生体悟总结。
我们所在的是间老旧的平房,斑驳的木门开向一条车子开不进来的蜿蜒小巷,庭院窄仄,只容得下几株山茶,外墙瓷砖剥落,铁窗锈蚀,室内倒收拾得窗明几净,一尘不染,老旧的木制家具在细心磨洗后映出温暖的光泽,果然是菜头学长的风格。
我们坐在开向庭院的和室中,外头庭院飘起山边特有的细雨,空气中混合着濡湿泥土与榻榻米的气味,矮几上开水咕嘟咕嘟滚着,艾登则躺在房间一角,早累得睡着了。
菜头学长看着我说:“我哥过世了,车祸意外走的。走的时候他才刚结婚,在科学园区工作几年,计划生小孩,结果一个酒驾的浑蛋就这样带走了他。”
学长低头擤了擤鼻子,说:“我帮我哥守灵的时候一直痛骂自己,我发现……我比较难过的竟然不是我哥走了,而是我这辈子再也没有做自己的机会了。很丢脸吧?艾伦,那时候我还跟你说什么要真诚面对自己,结果那么多年过去,我还在指望我哥生小孩……我真的很没用。
“那时候我告诉自己:我要自立自强,我靠我哥一辈子了,不能再靠别人了,我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水沸腾了,学长缓缓地注水、沏茶、出汤、斟茶,同时向阿玛德用英文翻译他刚刚说的话。阿玛德轻拍着学长的后背,像在安慰他的丧兄之痛。
“我到美国的第二年遇到阿玛德。”菜头学长为艾登加了件毯子,说,“阿玛德读管理学院,我们是滑雪认识的。因着同样的困扰和遭遇,我们成为挚友。”
“相当痛苦的经验,幸好当时有阿玛德在身边,我差点儿想杀了自己。”学长说,“那时候我只是学着当一个有‘男子气概’的男人而已,我和不同的女生约会,最后会跟徐千帆在一起,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客观条件符合做的理性决定而已。
“刚开始一切都很好,我和徐千帆处得不错,艾登出生,我很高兴,我们彼此都有事忙,就没太多时间去想东想西,反而是小孩慢慢长大,我们开始需要真正地面对彼此,才发现我们之间的隔阂比想象的还要难跨越……一切就是这样了。”
“你回台湾是计划好的?”阿本问。
“对,那时候觉得很完美,隔着太平洋大家就可以互不打扰,‘我老婆带着小孩在美国’,超完美的挡箭牌,只是我没想到徐千帆也找了台湾的工作。嘿,世事难料,早知道应该去马达加斯加的。”
我在心中比较着菜头学长与小帆的说法,怎么说呢?像两个人共乘一艘原本就破了底的船,只是比谁先跳船而已。
“学长,”二马突然说,“杨艾伦说你在工作的时候很挑剔,他上次开会差点儿要揍你,有这回事吗?”
我抗议说:“我没有说要揍人。”
学长笑着说:“真的吗?其实我是学你的耶,艾伦。我是有意识地学你说话走路的方式,学你挖苦别人的口气,还有你那种笑起来很嚣张的样子……不像吗?”
“我?我讲话哪里有那么油?”
二马说:“你就是那么油。”
阿本说:“有时候更油。”
学长继续说:“我以为我学得还不错嘞,我一直觉得……徐千帆会接近我,是因为在我身上感觉到你的影子。她没有跟我提起过你,但我知道她心中一直有你。”
“你怎么知道?”
“第六感吧……哦,还有这个……”学长从一旁的包包中拿出一支钢笔摆在桌上,是上面刻有“L&F”的那支。
“这是你和徐千帆的对笔,对吧?其实我完全可以理解徐千帆今天的愤怒,因为当我发现她将这支笔送去维修的时候,我也非常生气。那家店离我们家一百多公里,她来回跑了两趟,一趟还下着大雪──平常下雪她几乎是不出门的。那时候艾登才几个月,她骗我说是去跟教授开会,结果是花一整天去修理这支几千台币的钢笔。”
菜头学长在指间转动着钢笔,继续说:“我是在垃圾堆中翻到收据才知道这件事的,当时我非常火大,火大到……我做了很幼稚的事。我假装在她的书桌上发现这支笔,惊喜这是她要送给我的礼物,上面还刻了我们名字的缩写!我看她一脸心虚,想解释又不敢解释的样子,就觉得自己赢了!……蠢吧?我觉得蠢透了,根本不知道在气什么,也不知道赢在哪里。那时候我自己也搞不懂,我和徐千帆又不是‘那种关系’,她心里有别人我没理由生气,或是说……我有什么资格生气。
“一直到那天阿本告诉我,你跟他说,婚姻是承诺,我才豁然开朗。”他摇摇头,苦笑说,“所以这么多年,我其实根本没把这段婚姻当一回事,是我对不起徐千帆,她要从我这边讨走什么,我都无话可说。”
“但你还是不同意公开道歉。”
“我可以公开道歉。”学长说,“我会想办法安抚我妈妈,虽然我还没想好什么方法,但总会有方法的。我需要时间,只要一点时间就好,我会尽力满足徐千帆的要求。”
“男人。”
一个女声从我背后传来,我转身,只见徐千帆拉开和室拉门走了进来,她身后跟着蒋恩。
“天啊,这房间里关系超乱的。”二马低声说,我笑不出来。
小帆没有理会起身相迎的菜头学长,她直接跪坐在艾登身边,端详孩子的睡颜,然后像松了口气般笑了笑,亲亲孩子的额头。
“对不起,帆,是我叫他们把艾登带来……”菜头学长说。
“不要乱道歉,这样会让道歉变得很廉价。”徐千帆抬头说,“我妈都跟我说了,如果艾登真怎么样,要杀我也是杀杨艾伦。”
我抖了一下,只差没磕头大叫“娘娘饶命”。
“抱歉。”菜头学长低头说道。
小帆站起身,肩膀发颤,脸部表情痛苦,我看得出来她有意思殴打眼前这个人,但不知道怎么下手。许久,她才用一种勉强平稳的声调说:“这房子哪里找的啊?”
“租屋网站。”菜头学长说,“空了很多年了,租金很便宜。”
“怎么会找这种地方?我们刚刚找了半天都找不到门口。”
“比较清静吧。”学长说,“现在这种老房子也不多,很宝贵的。”
“你应该帮艾登包尿布,他尿床会毁了你的榻榻米。”
“他不是早就不包了吗?去年就停掉了。”
“对,可是最近又开始尿床,可能是因为压力太大。”说到这里小帆突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菜头想去抱她,她将菜头推开,瘫坐在地上,越哭越大声。
“帆,对不起,一切都是我的错,我一定会尽全力弥补你……”菜头学长跪在小帆身边拼命道歉,但止不住她的崩溃,她趴在地上,哭到全身抽搐。菜头学长着急地看向我,二马与阿本也看向我,甚至连蒋恩也看向我。
我走上前去,轻声说……
“妈妈不要哭。”
艾登不知道什么时候醒来,他爬过来,抱住小帆的头,说:“妈妈,对不起,我不应该自己跑出来的,害你担心,对不起。我只是很想很想爸爸,艾伦叔叔很保护我,我们很安全的。妈妈,你不要生他的气啦,你也可以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啊,像……你可以跟二马叔叔结婚啊,他开车很厉害耶,我想再坐他的车……妈妈,不管你跟谁结婚,我都不会离开你的,我会一直跟你在一起,我真的很爱你。”
小帆抬起头来,抱着艾登又哭了一会儿,然后说:“谢谢你,艾登,但可以不是冯二马吗?他车开得超烂的。”
那天我们留到很晚,将离婚协议书签妥。一群律师一起拟一份离婚协议书超没效率,七嘴八舌,连要签名还是盖印章都有不同意见。最终小帆与菜头签了名,二马与蒋恩则签了见证人。之后还得去户政事务所办登记,那是后话了。
小帆离开的时候,在我面前停下脚步,轻轻说了声“谢谢”,我以为她会给我一个拥抱──友情的或爱情的,但她没有,她跨进驾驶座,和大家再说一次再见,红色本田发动引擎,两盏车尾灯缓缓地消失在雨雾之中。
我想,以后大概不大有机会再见到小帆了吧。
第二天天气晴朗,上班尖峰时刻车潮汹涌,行人脚步匆促,都市生活一样忙碌而平凡,昨天的冒险好像只是梦一场。
我进办公室,财务人员跑来找我,说收到一笔二十万元的汇款,汇款人是徐千帆,标注的是我的名字,问这笔钱是什么原因。我告诉他案件编号,然后将关于这个案子的文书、电子文件整理一番,连同银行汇入汇款通知转寄给汤玛士、廖培西与秘书,表示案子结束,可以办理结案。
廖培西三分钟不到就跑来我办公室,关上门问案子怎么结的。我将来龙去脉告诉他,听得他惊呼连连,直说我们胆大包天,他又问警察那边怎么摆平,我说哪有什么方法,当然是排成一排拼命道歉,徐千帆又在电话里说不追究才没事……其实有事啦,二马超速、蛇行被罚了七千元。
汤玛士接近中午的时候才回了个“做得好”,也不知是在指什么。
汤玛士的回信倒让我想到升合伙人的事。依惯例,事务所调整人事的时间固定在五月左右,如果今年真的要升一个受雇律师上去,那现在应该要有动作,至少知道候选人有谁,甚至候选人应该已经面谈过了,但目前连个风声都没有。
我借着拿文件给汤玛士的秘书时探了探她的口风,她说农历年前好像有开过一次会,但也没交代秘书准备什么。
我直接跑去问布兰达,她也说农历年前合伙人们有开会,但好像在人选问题上卡住了,可能之后会再开会讨论吧,但也有可能今年就不升合伙人了。
“会担心吗?”布兰达问。
“还好啦,”我耸肩说,“领到钱就好,合伙人就是个头衔而已。”
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是违心之言,除非接案状况太差,要不然合伙人领的钱还是多出受雇律师一截,而且还能参与事务所的管理;当然有些人习惯当闲云野鹤,钱赚够就好,专心做案子,不想掺和政治,那就不会积极争取升职,但我觉得既然有升上去的机会,就应该拼看看。
前年做非讼的一个合伙人离职,艾瑞克便问过我有没有升上去的意思;这年我接进来台磁这件大案,按说“业绩”是够了,但布兰达却说升职人选难产,难道说真的是……
这问题一直盘旋在我脑子里,乃至于我吃饭超过午休结束时间才回办公室,一进门秘书就喊说艾瑞克找我。我心头一喜,进了艾瑞克的办公室,却见蒋恩、布兰达都在。
“跑到哪里去了?一直在找你。”蒋恩说,“台磁说J.J.美国总公司的CEO下个星期到台湾,要找台磁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