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井中影 | 收藏 |
俄国大撤退
井中影 作者:马塞尔·埃梅
小多雷在草稿本上做动词变位,将“我对我的老师和同学缺乏尊敬”(Je manque de respect à mon maître et à mes camarades)一句的动词变为虚拟式未完成过去时。他写得不慌不忙。老师罚他在课间休息时写动词变位,但并没有指定额外作业的长度。同学们在操场上打弹子,掷球。小多雷不时抬头,听一听熟悉的欢叫声:
“我的手碰到你啦!”
“暂停!”
“我保卫寄生枝和医学……”
他看见因为没上好历史课而受罚的学生,从窗前一再经过:他们受罚比他轻些,课间休息时列队,静静地绕操场跑圈。这根本管不住莱翁·雅尔,队列中的他,透过窗户缝儿向小多雷示威:
“我们,起码还能在外面走走。这就让你知道对我们缺乏尊敬的后果!”
“我总比你这样傻走聪明。”小多雷反击。
他举起折纸玩具[原文为une saliere en papier,类似中国折纸玩具“东南西北”。——编者注],表明自己在愉快地打发孤独的时间。等莱翁·雅尔追上小队之后,小多雷藏起折纸玩具,又拿起笔。他刚写完虚拟式未完成过去时的句子,又乘兴把它改成个将来时的句子:“我将对我的老师和同学缺乏尊敬。”因为,小多雷做什么也不后悔,该说就说,如果老师挑刺,他就不得不承认,外露了对智慧的忠诚。出了这种事情的确怪诞,老师倒是情有可原:他并不了解莱翁·雅尔卑劣的行为如何激发了历史课的意外事件。其实,全怪雅尔这个大傻瓜,他的过错由来已久了……
小多雷一头棕红发,极为活跃,在瓦尔普瓦当地,唯独母亲叫他的名字:皮埃尔。
小多雷在公民教育课、历史课和地理课的课堂上,表现出了早慧。在拼写方面,很难掌握的复数,他也很少有迟疑的时候。他还会心算法。
“这个皮埃尔·寿代,”老师常说,“还不满十一岁,就有能力拿初级教育修业证书了。”
同学们未免有点嫉妒,尤其是莱翁·雅尔,十三岁的一个瘦高个儿。他特别高傲,只因他腋下长出了绒毛,腹部下方三角部位也有了苗头。他特别起劲地嘲笑小多雷头发的颜色。
“多了一堆烧柴,”他常说,“他这脑袋着了火。”
小多雷一头棕红发,并不觉得羞耻,他甚至认为这是一种特别的发色。不过,他还是出于谨慎,更愿强调智力胜过暂时的外表,从容不迫地反驳莱翁·雅尔的嘲笑:
“我的头发,可能就是棕红色的。但是可以肯定,听写我成绩最好;你要是能像我这样,记住你那些省份的书写,恐怕你得熬白了头发。还有一种说法:一个人生来蠢笨,那就要蠢笨一辈子。”
小多雷的反驳,往往会引发一场有关教育受益的争论。莱翁·雅尔不相信教育有什么用处,极为反感将学习的成果同田间劳动扯在一起。
“表示复数时,马字要加一个S,”他说道,“你知道这个有什么用呢?!你懂得这个,并不能帮你驾驭一匹不听话的马。”
“人也不是一天总驾驭劣马。”小多雷指出。
“我知道哇,有时候要去会金发姑娘,尽管你这头棕红发,同这种事挨不上边。总之,就算行吧。假设你约会一个姑娘,你总不会给她背诵乘法口诀吧。”
小多雷承认这一点。不过,他本可以质疑,向大雅尔表明,受了良好教育,在姑娘面前就能有几分自信。他也可以向大雅尔讲述,每星期四,他常去树林,同玛丽·布洛一起玩耍,她是小学女教师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她会不知疲倦地听他背诵《得了瘟疫的群兽》,或者
父亲,这位蔼然微笑的英雄……
然而,这类事情同他没有关系。
就在今天早晨,上学的路上,小多雷还受不了大雅尔那副自负的劲头,真想以树林里这类休憩为论据,透露出一些秘密。
不料,大雅尔却嗤之以鼻,用居高临下的怜悯口气说道:
“果然,你是班上第一名,你用三率法做题,你了解一八七〇年的所有战役,可是,女人有什么用,你却不知道。”
小多雷脸红了,竟然怀疑他这么无知,不免被刺伤。他冷淡地回敬道:“我清楚女人用来生孩子。”
“这已经不错了,”大雅尔肯定,“不过,还是多亏了我告诉你的;如果只听老师讲的话……那么男人呢,你知道他们有什么用吗?”
“这不算个问题。”小多雷咕哝一句。
“为什么这不算个问题?”
“男人,就是男人。”
“当然了,你不可能知道:一个棕红头发的人,跟别人就是不一样……”
离上课时间还有十分钟。大雅尔决定舍弃一些打弹子的时间来启蒙小多雷,并且向他证明不存在无因之果。他的论据完全有道理,小多雷心里翻腾起来。事情异乎寻常,引起的后果,他预感到很严重。他胆怯地问道:
“所以,老师……”
“当然了,”大雅尔肯定,“既然他跟女老师结婚。哼!他不会炫耀的……”
上课的时间快到了,隔着树篱,可以望见学校有二百米远。
这工夫,大雅尔抢在小多雷前面几米,开始跑起来,同时嚷道:“后到校园的是傻瓜!”
小多雷急速起步,但是每次他都得输,自然是后到达,因为大雅尔腿很长。然而他心里明镜似的:头脑想要仗恃奔跑的优势,这一点儿道理也没有。他本可以向大雅尔证明这一点,而且不乏论据;不过,抵达目的地时,他比他的同学仅仅落后五六米,嘴上什么也没有说,心中很得意,接受了打赌的结局,并不强调自己虽败犹荣的理由。
这天早上,要么是大雅尔奔跑不上劲儿,要么是小多雷全力以赴,他们二人同时到达了校园。同学们反响热烈,跟随着他们奔跑,当两名赛手跑出树篱路时,所有人都叫喊起来:
“加油,小多雷!加油,加油……到了,红头胜啦!红头胜啦!”
其实,二人同时触到了校园尽头的那棵大洋槐树,然而,过分冲动总要导致闻所未闻的情况,打破惯例的人才能争得荣耀。小多雷这次真的跑赢了,大家不断地高呼:“红头万岁!”大雅尔气疯了,他趁相对安静一点儿的时候,高声说道:
“在起点,我至少让他先跑出去了十米,如果我想要……”
可是,没人听他的。小多雷趾高气扬,乱蓬蓬的头发成了一团火,他在早晨清新的空气中,嗅着自己光荣的肌肤汗气蒸腾的香味。他反驳大雅尔:
“你刚才对我讲了那么多蠢话,不后到达才怪呢……”
所有人都赞同他的说法,也不管大雅尔讲了什么蠢话。莱翁·雅尔气喘吁吁,乜斜着眼看他,心里盘算如何报复。
老师出现在教室门口,示意上课。
学生按成绩排列座位:最优秀的学生挨近老师。莱翁·雅尔排在最差的学生中间,坐在教室后方,而小多雷则坐在第一排。
等全班同学都坐下了,老师点名,然后对小多雷说:
“皮埃尔·寿代,去收作文本,放到我的讲台上,都翻到作业那一页。”
收作业本是一种信任的表示,总派给好学生。这种差使经常交给小多雷,他也特别引以为豪。不过,他这种好学生的意识,并不阻碍他宽待同学。如果有哪个同学未做作业,挤了挤眼睛,小多雷会意,就略过去,不收有过错人的作业,然后再巧妙地掩饰,不让老师发觉。
走到最后一排,看大雅尔那张愁苦的脸,小多雷就明白他没有写作文。小多雷很高兴能高抬贵手,放这个对头一马。这种小伎俩再次成功了。他将一摞作业本放到讲台上,当老师问他,作文本都收齐了没有,他便肯定地回答:
“是的,先生,收齐了。”
恰好这时,大雅尔站起身,声调沉着地提醒:
“先生,我没有写作文。”
全班一阵窃窃私议,对大雅尔这种卑劣行为,大家都很气愤。
老师扶了扶眼镜,默想片刻。莱翁·雅尔没有写作文,他并不怎么感到意外,不过他要严肃对待小多雷的行为,他本应该告诉自己这一问题。
“皮埃尔·寿代,”老师说道,“站起来。我当场抓住了您说谎。您辜负了我的信任。今后,再也不用您收同学们的作业了。”
小多雷气得脸蛋儿热乎乎的,很想辩解。老师一个手势制止他说话,又对莱翁·雅尔说:
“我感谢您的坦率,莱翁·雅尔,因此,我不惩罚您。您瞧,讲实话总会有好处。我要问一句,您为什么没有写作文呢?”
“昨天家里杀猪了。”
“我倒是没有听说,”老师指出,“看来,你们家经常杀猪。不管怎样,既然没有写作文,您一定有时间看历史课了。给我讲一讲俄国大撤退的史实吧。”
莱翁·雅尔的历史知识,只是一些大概的印象,他回答拿破仑是个伟大人物。这样回答也还是一种印象,老师再一追问,他就不能用史料来证实了。老师就罚大雅尔抄写一章历史,这是向他预告一种凄惨的未来,生活在懒惰少年的追悔中:想想这一辈子,因无知和愚蠢而与世隔绝,只能怀着羡慕的心情,听听有学问的人谈话,悔恨当初不知接受开明政府给予他的关怀。然而,大雅尔听着这种警告,叉着手臂,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毫无要掩饰的隐秘不安。老师气馁了,耸了耸肩膀,又问别的学生,也没有得到多少满意的回答。
大家清楚,法国人和俄罗斯人之间发生过战争——在法国历史上,除开少数的一些怪人,如爱玩比尔包开球戏[一种玩具。小棒一端装有一托盘,棒上用长线拴一小球,玩时将小球抛起,再用托盘接住]的亨利三世[1551—1589,法国国王(1574—1589)。],或者爱做咖啡的路易十五[1710—1774,法国国王(1715—1774)。],所有人都在战争中度过时光;大家甚至了解,在远征俄国的过程中,大雪纷飞,天气相当恶劣,但是,他们得不出决定性的结论。
老师十分不悦,认为俄国大撤退这段历史没有受到应得的重视,就决定集体惩罚:没有学好功课的所有学生,到了课间休息时,都去绕校园跑圈。
这工夫,小多雷显得躁动不安。莱翁·雅尔背信弃义,气得他浑身颤抖,胸口怦怦狂跳,他在座位上坐不住了,以为询问结束,便用手指打响,连声说道:
“先生,我可以出去吗?”
老师审视小多雷,那神态有些吃惊,近乎难过。在执教生涯中,他早已观察到上课的时候,总是差生请求上厕所,而好学生很容易就能憋到课间休息。小多雷何以这样急切,他要找出一种解释,心想毋庸置疑,他最好的学生正走上歧途,打算逃脱俄国大撤退。他不以为然,还是点头允许了。然而,教室后面却叫嚷起来:大雅尔不干了,他说他在皮埃尔·寿代之前就请求上厕所。老师不免狐疑,但又怕有失公正。
“好吧,”老师说,“你们两个,快去快回。”
小多雷和大雅尔真够气人的,他们冲到门口,挤在一起,各不相让。大雅尔占了上风,先出了教室。全班同学都盯着门口,津津有味地观赏这场闹剧。老师非常气愤,想提醒两个淘气鬼规矩一些,但是他们听不见这话了,他便凭借这起坏事例做出决定,告知全班,今后,上课时间,谁也不准上厕所。
到了院子里,小多雷大肆发泄怒气,痛斥大雅尔:
“全班同学都算上,没有一个能干出你这种事。”
他还数落大雅尔是告密者,混蛋,卑鄙小人,流产儿。
大雅尔倒很平静,笑嘻嘻的,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接受所有指责,最后突然翻脸。
“流产儿?你再说一遍,如果你不是一个……”
小多雷清楚,自己没有他强壮,于是忍住,咬紧牙关。大雅尔嘿嘿冷笑,那神态让人受不了。
二人一同挤进狭窄恶臭的厕所,相互瞪着眼。沉默了一分钟之后,大雅尔火气十足地指出:
“我撒尿比你射得高。”
他说得对,他的优势不容置疑,不过,他那炫耀的傲慢劲头,让小多雷无法容忍。小多雷耸了耸肩,反驳道:
“这能证明什么吗?还不是因为你比我大两岁。”
“不是这码事儿。撒尿高度的问题,同年龄毫无关系。我有证据,我撒尿同我哥哥一样高,他从部队回家探亲时已经二十一岁了。”
这话的恶意显而易见,小多雷毫不犹豫,回击如此明目张胆的吹嘘。
“这不可能,你瞎说什么呀……同你哥哥一样高!那也许是他没想比试。不管怎样,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谁也不会反驳,就是年纪越大,尿射得越高。我始终坚持这种观点。”
“你说这是年纪大的问题?”
“我说了,也可以重复。”
“你若是这么认为,那么,一个人到了六十岁,为什么撒尿不会越过房顶呢?假设一下,就说老师吧,他撒尿为什么不会越过学校呢,嗯?”
小多雷考虑如何回答,可是,拥有如此严谨逻辑的一个论据,实在难以驳倒。用归谬法进行的这种论证,一时让他目瞪口呆。他觉得算术似乎背叛了自己,不再切合实际。他深信比例的价值,现在受辱,便怀疑起自己的智力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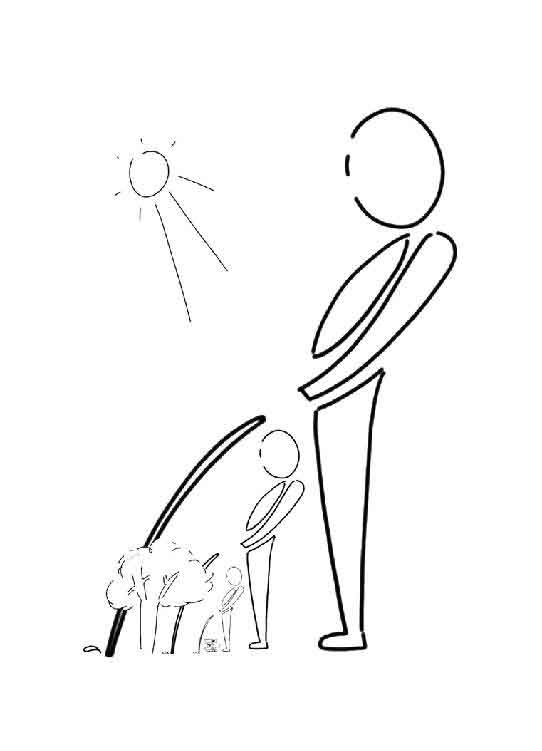
“你明白了吧。”大雅尔得意扬扬。
他又补充一句:
“棕红头发的人,撒尿永远也射不高,这谁都知道。”
说罢,他跑回教室。小多雷缓步跟随,坐到他刚才获胜的大洋槐树脚下,开始厌恶地注视教室的窗户。他感到,猛然间,老师的学问被厚厚的黑暗淹没了。
上帝啊,学会除法、拼写,还有那么多复杂的事物,究竟干什么呢?心算课,或者地理课,为什么要取得优胜呢,既然这么多知识也根本对付不了一个莱翁·雅尔的嚣张的恶意!眼看着真理受逻辑的嘲弄,折辱,又无力抗辩,那又何必做个勤奋的学生,得意地同强大的智力交往呢……
他愤愤不平,站起身,拖着脚步走向教室门。
老师对他很严厉:“皮埃尔·寿代,您向我请求出教室,就是为了去坐到树下吗?”
小多雷回到座位上,一反常态,甚至不屑于说他头疼。老师见他以沉默相抗,十分恼火,他又让全班作证,以讥讽的威胁口吻说道:
“看来,寿代先生拉长出去的时间,必是期望逃避,免得陈述他在俄国大撤退这段历史上的个人观点……”
同学们都附和着笑起来,大雅尔尤甚。小多雷双臂交叉,放在课桌上。他鄙视将这种没头脑的嘲笑引向他。因一种悲伤的气愤,他的脸色苍白,乳白色肌肤上的雀斑更加显眼了。
“好了,”老师说道,“回到俄国大撤退的正题上。我听您讲,皮埃尔·寿代。您起来。”
小多雷离开座位,看也不看老师一眼,开口说道:
“一八一二年九月十四日,拿破仑进入莫斯科……”
他说到大火、哥萨克骑兵、别列津纳河及其架桥兵,大雪,冻伤的双脚,吃战马肉,他什么都没有漏掉。但是,他叙述的声音很单调,毫无热情。往常,老师说他背诵得有声有色。而今天,他的声调总那么平平淡淡。一副厌烦的神态,眼睛茫然地望着窗框框住的那棵大洋槐。
“士兵同军官混杂在一起,没人服从命令了。然而,还有一些将领,如维克托元帅和内伊元帅……”
话说到半截,小多雷停了一下。热血涌到脸上,他直起脸,注视他的老师。
“当时有内伊元帅。他非但不逃,还操起一杆枪,他是最勇敢的人。正因为如此,拿破仑称他勇士的勇士。内伊元帅在大革命中战斗过。他出生在萨尔路易,有一头棕红发……”
同学们相互捅臂肘,纷纷窃笑,老师也难免露出一丝微笑。
这时,小多雷那棕红发往后一仰,脑袋猛一挺,就仿佛在向一队哥萨克骑兵挑战,他转向大雅尔,朗声抛去:
“内伊元帅有一头棕红发,在全军,他撒尿比谁射得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