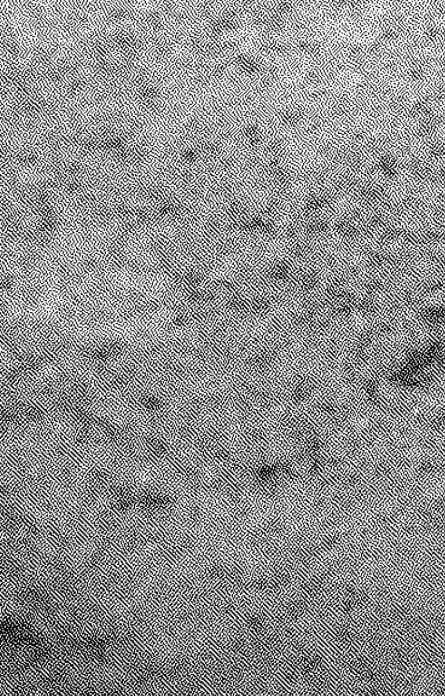| 逝物录 | 收藏 |
地狱谷
萨切蒂别墅
亦称萨切蒂侯爵的皮涅托别墅逝物录 作者:尤迪特·沙朗斯基
* 受朱利奥和马尔切洛·萨切蒂兄弟委托、建造于1628-1648年间的萨切蒂别墅是建筑大师皮埃特罗·达·科尔托纳最重要的早期作品。
† 17世纪末,宫宅已现颓势。18世纪中期,两座翼楼坍塌;建筑废墟最终于1861年被拆。
一如每位君王,这座城也有两个身体。有死之躯倒卧,仿佛被亵渎的尸体,或大理石已在炉中烧成灰的采石场。不藏化石的苍白脉岩,本就是远古之印,是一大块受伤的记忆。不死之躯却从外邦人想象的净化空间高耸而出,他们做梦般在废墟前驻足,因敬畏而目瞪口呆:一整群高贵的骄子,在画家、雕刻家和文学家的率领下侵入城中,围攻了西班牙广场四周的旅店。年复一年,北方纬度上的艺术家们从覆满尘土的邮车里走出,皮夹里装着显赫世家的推荐信、资助者的捐赠或某个学院的奖金——确定的则是一位同胞的地址,多年前的一个冬天他来到此地,留了下来。
他们崇拜废墟,就像崇拜圣髑,祈盼其复活,迷醉于消逝的、不知餍足的辉煌。总是缺了点什么。眼睛看见,大脑补充:残垣断壁变成建筑,死者的功业栩栩如生,比当年所为更雄壮、更完美。当年,罗马元老院决定,留存那千余年不倒、纪念图拉真及其胜利的多里斯柱,只要世界还在,它就完好,企图破坏者,不论是谁,都将受到最重的惩罚,那一刻,此处,在这神圣之城、历史之都,纪念物保护被发明出来,全民皆称继承者。罗马未亡,往昔未逝,只是未来已经开始。此地牵绊在一个个时代、一种种建筑风格间,它们在世界剧场的半圆里争奇斗艳,讨好着从那时起就蜂拥而来的观众:罗马的方形教堂与沉入沙中的凯旋门,中世纪三角墙与巴洛克教堂的立面,灰白的文艺复兴别墅与熏黑的金字塔——死生交错的材料构成的庞大有机体,受制于偶然与必然,还有太阳的法则。
没有栅栏隔开废墟和居民们可悲的营生,他们宠辱不惊,过着随处可见的日子:半裸的乞丐在拱廊中闲逛;鱼贩在砌死的廊门阴凉中兜售易腐的货物;妇女们在古温泉里洗着亚麻布;牧人把羊群赶进发霉的神庙,曾用于祭祀的牺牲于是在异教圣坛前吃起了草;日工把一块块多孔的黄白钙华从弗拉维安斗兽场的地下墓穴中挖出,那是野兽和不屈的基督徒骸骨的安息所。可使用的,都被拆出、运走。古建筑零件的交易蓬勃发展。废墟是纯粹的资本;并非待打捞的宝藏,而是应开采的半贵重矿物,就像阿尔巴尼亚山区的铜。
少有人关心罗马遗存的维护,却一定没有谁像威尼斯迁来的乔瓦尼·巴蒂斯塔·皮拉内西那样暴烈好斗,他会和每个欣赏他、资助他的人闹翻。所以,这个厌恶人类社会而更愿意与石头相伴的男人,居然在生命的第33个年头找到一位能够忍受他、并给他生出5个孩子的妻子,简直就是奇迹,哪怕他把她并非不可观的嫁妆全都投进了大宗的铜板货存。乖戾易怒又孤注一掷的性情让这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双眼幽光闪烁,那些声称在他身边一刻钟就会虚弱的人不明白,这位眉头阴郁的暴君正忍受着怎样的痛苦:废墟对他说话,仿佛发着烧,夺走他的宁静和睡眠,它们不停召唤出画面,他认为那些景象一定要牢记,以证明所有后辈和无知者一派胡言,他们竟胆敢声称古希腊的艺术远远胜过古罗马。他像热恋中的情人,坚定地抨击无脑的当代,他在不断更新的小册子里写道,当今可悲的幼稚定会让每个知晓往昔之雄浑大美的人绝望。而皮拉内西知道它、见过它,因为,自从儿时在一位罗马历史作者的编年史中读到古典的种种,它们就占据着他的梦,那是在叔父那间被泻湖的微光照亮的小屋里,他是位工程师,致力于维修防护堤、以抵御纠缠不休的亚得里亚海。
当今就像珊瑚,总在沉积中的事物上繁殖,把那并不古老、却已装腔作势的身体磁力般推入深处,推入地球内部,向下沉入拱顶地窖和地下墓穴,向外进入城门外主路旁被湮埋的墓地,那是古罗马人驱逐亡灵的地方,因为世上再没什么比普鲁托的冥府更让他们畏惧。他们在那里造了大公墓,无数次战争教导,尸体只有烧光,才能不被敌人凌辱,此后他们便只埋葬死者的骨灰。
于是皮拉内西用斧子和火炬凿穿丛林与黄昏,点火驱赶蛇蝎,裹在黑斗篷里沐浴晨光,就像未来小说里的人物。他把锄铲挖入土层,暴露出底座和石棺,挂念着古工事和风化桥梁的墩垛,考察砖石结构的接合与柱式,研究立面和地基,破译灵骨塔的铭文,复制柱体凹槽和拱门横饰,为湮埋的猛兽笼和斗兽场、为杂草蔓生的庙宇和教堂速写平面及正视图、横断与纵剖面——用停不下来的手画出建造那些森然大物所必需的杠杆和横梁、挂钩和链索、摆锤和支架。对他而言,没有石头太沉默,没有砖墙太破碎,没有断柱太残缺,他总能从中辨认出曾让城市力量充盈的肢干和肌肉、为之给养的血脉和器官:桥桁和公路,高架渠和蓄水池,尤其是古罗马迷宫般多臂的马克西姆水下河道,被他评断为建筑艺术的巅峰,虽然、或正因其调控着最基础的需求,他鉴定说,它的伟大,超越了世界七大奇迹。
就像百年前解剖学家维萨里在手术台上切割受刑罪犯温热的尸体,他也支离着半已塌朽的建筑之躯、拆卸着在他眼中无辜毁灭的昔日帝国的残骸。
终生未造一屋的建筑师,从意味深长的废墟中设计着他梦寐以求的过去的蓝图,它也同时是全新创作的愿景,它在铜版画上迷住的人,远多于任何固着于地面的建筑。每当他在工作室里附身于抛光的冰冷金属上,目光便自由无阻地穿透沉淀和材质,把赭红的草图交给腐蚀涂料,无数点划钩折、斑驳形状和颤抖的线条,它们极少交叉,虽然在每个细处都改变着方向,好像要另辟天地。他把铜板浸入池中,每次重复都覆盖一些区域,其他地方则一滴滴沾湿,让酸液继续蚀入最精微的凹处,永远固定下他不想忘、忘不了的东西。
待轧辊释放出纸张,太阳便在版画上无情闪耀,阴影软似丝绒、黑如遗忘,灭点几近无穷,视角如梦如幻,即使俯瞰,残垣断壁依然气势磅礴。纪念碑放肆地耸立在起火的天空前,凌驾于那群身形微茫、挥舞着手臂、笨拙小丑般的小民之上。一定是巨人们建起了这座城,那些创造力正值中天的罗马独眼怪赛克洛普们。
皮拉内西的版画很快就作为古代生活的解剖图流传于世,虽然大多板子仅仅讲述了死亡。它们展现着坟室的内景、陵墓的平面图、端坐在大理石基座上的石棺或是一条从铺路石中间切开的、通往焚化场的廊道截面。皮拉内西成了祭司,他所谙熟的死亡秘仪遍袭整块大陆,每个星期都催促着新的年轻人去马峰后大师的家中朝圣,他退隐于此,以寻找他在那间被全世界骚扰的、繁华的科尔索工作室里求而不得的清静。每当那些黄毛小子哀求进入,他就大吼:“皮拉内西不在家,”直到他们悻悻放弃,一眼都没瞥见偶像。
唯有一次,初夏一个异常闷热的下午,敲门怎么都不停。当皮拉内西像往常一样骂骂咧咧地扯开门,那里站着一位穿着优雅的年轻人,他半长的鬈发仔细打理过,在颈后用带子扎了起来,面部线条柔和,小小的圆眼睛闪闪放光,在一个过时的大幅鞠躬后,形状漂亮的嘴巴里传出带着文雅法国口音的话,“我的先生,冒昧打扰。我是休伯特·罗伯特。我像您一样热爱废墟。请您带上我吧,不论您去哪里。”
两年后,1760年的一个阴郁的秋天早上,休伯特·罗伯特来到天使门前,沿一条干枯小溪的蜿蜒河道走入山谷,在它最后一个多荫的隐蔽处,如人们对他所说,破落着一座庄园的主宅。乌云密布的天空下,色彩惨淡地发出微光,他呼吸着潮湿的空气,想甩掉疲惫,那是一种已纠缠他多时的铅似的倦怠,虽然本质上与他毫不相干。
他年轻,27岁,法兰西艺术学院的奖学金获得者,一位巴黎宫廷侍从的儿子。父亲曾在凡尔赛宫服侍一位公使,六年前,他随公使之子,经巴塞尔、圣哥大和米兰来到了罗马,作为众多天资卓越者之一,画下那些不隐藏、反倒几乎傲示出时间标志的纪念碑和建筑物。这年春天他才来到那不勒斯,参观了海湾附近刚刚挖掘的墓群,见过波佐利和帕埃斯图姆,在蒂沃利画了虬枝错结的橄榄树,它在一座西比拉神庙破败的内庭里把枯干的枝桠伸向红铜色的天空。他再也不想过罗马的夏天,那发烧般的炎热一年前差点要了他的命。回来后他似乎变了。古怪的厌倦折磨着他,把他对所有古代文物的兴致连根毁掉,一种欲望袭来,他渴望寻找当今的废墟,——那座萨切蒂别墅,现在,走过在沙质大道尽头继续逶迤的小路,它终于从柏树枝后浮现出来。
他离开小路,走近院落,坐在干硬、枯黄的草中,看着。然后他开始画那半塌的庄宅,迅速而精准,就像第一冬在罗马的那些漫漫长夜、在科尔索大道上高高的学院画室里画一个意大利人结实的肌肉。他果断地把石墨笔擦过纸面,很少抬头看,几眼就对此地了然于心:野草丛生的花园沿坡扩张至三层;破败的建筑,立面宽阔、有两个弧形石翼的亭宇安立在斜面基座上,中央是高高的半圆殿,三层梯台各有一处水景:喷泉,鱼塘,柱廊后光影交错、带有多利斯壁柱的宁芙窟。楼梯裸露,直通朽脆的砖墙。顶架塌毁,栏杆破碎,殿堂上方隔成方块的拱顶布满裂隙,喷泉枯竭,由两个半鱼半人的海神守护的贝状水池干涸得露出石地。连入口上方的楣石也沉落下来,仿佛地震过后。
罗伯特画下一切,不忘为这荒凉景象补充点缀的人物:于是,纸面上出现了一个头顶平衡着水壶的少女,一个女人把婴儿紧抱入怀,另一个牵着孩子走上台阶,狗跟着看不见的足迹,井边站着一头牛和一头羊,驴子把头低向水满至缘的池子。
休伯特·罗伯特看了看他的画,卷起纸,穿过曾是入口甬道的杂草丛生的小路,走上断裂的台阶,跨过荒废在墙角的泥渣。入口已被瓦砾湮没。他从窗洞爬进去,一个并不算太大的凉爽房间,一定是曾经的沙龙。空气散发着霉味。地上堆着碎砖和朽烂的梁木,拱顶几无支撑。方格天花板的中央裂了洞,如同巨大的伤口,灰白的云层透过它微微泛光。只是在边缘,破碎的灰浆下,还能看出被真菌侵染变黑的顶画残迹,褪色场景上幽灵般的人物中,唯一能辨认的,是一个被刺穿的、瞪大双眼的脑袋——恐怖惨相,让罗伯特想起维吉尔《埃涅阿斯纪》里的一行诗:Unum pro multis dabitur caput。一头换多命。
他盯着那毛骨悚然的脑袋,直到一个念头突然袭来:当今无非是未来的过往。——当一阵腐败的气味钻入他的鼻子、还魂了上一个夏天的记忆,他不寒而栗,走出废墟,以少见的敏捷重回到室外,那是八月,暴雨过后,台伯河大水泛滥,一如既往地溢出河岸,无法忍受的恶臭霾罩般压住整座城,只在黄昏时分才短暂散去,与所有人一样,他利用此时散步,以从白日的酷暑中恢复生机。后来,医生,那个谨小慎微、经验丰富、尤其相信放血疗效的男人,告诉他,他一定是在某个鬼魅般清新的傍晚染上了很少有人能挺过的疟疾。他的身体状况陡转直下,加上随之而来的精神错乱,谁都——不论女房东还是他的朋友们——不相信罗伯特还能康复。在八天内第十次切开血管后,从失血昏迷中又一次醒来的他自己也认了命,相信事情已不可挽回,甚至当症状已经消失时,他还在等着他的死,至今仍惊讶于大病夺生。
他再次转过身去,观察着现在似乎已发生了变化的房子。墙垣里抽出绿芽,苔衣覆盖着大理石神像,红景天从裂缝中涌出,常春藤强韧的根死死抓住石头,野葡萄装饰着拦墙,用多臂的藤蔓缠绕着风化的漩涡花饰,它泄露着屋主,仍还展示着萨切蒂的王章,那白底上的三条黑杠。
一百多年前,朱利奥·萨切蒂被任命为红衣主教时,让人修造了这栋别墅,高高的中殿如望景楼一般雄奇壮观——亭榭在地狱谷中,那是马里奥山和梵蒂冈之间多沙的洼地,是教皇国附近尘雾蔽日、高松瘦柏遮天的深渊。他家财万贯,是罗马最富有的红衣主教——前途一片大好。他能从夏宫的卧室看到圣彼得大教堂的穹顶。他曾两次希望被选为大祭司,1655年的秘密会议上差点就如愿以偿。可教皇,另有其人。
一年后,他最后一次站在乡宅窗边,眺望着他未能实现的梦想目标,骨瘦的手中握着装有草药、酸橙和柠檬皮的嗅囊,不断把它压在鼻子上。瘟疫在城中肆虐——又一次,却猖獗得经年难遇。街道上处处是裹着烟雾、带鸟嘴面具的生物,他们试图用没药、樟脑和旋覆花的芳香氤氲驱散疾病——并用棍棒赶走病人,那些可怜的家伙丧命得那么快,竟使他,朱利奥·萨切蒂,控制疫情的教皇顾问,无能为力,只能让人把可怜的死者埋到城墙之外——尽可能迅速,无需任何宗教仪式,抢在尸体开始腐败、散发出人人都相信会烈性传染的恶臭之前。瘴疠尤爱侵袭这座偏僻的山谷,那些在死水的浅岸和泥泞斜滩上发酵的潮湿浊溷,沉沉低垂在土层之上——散发出的腥秽气如此恶心,只能让人认为它有邪毒、致溃烂。朱利奥·萨切蒂知道,每本疾疫手册里都写着:污染的土地将永远废弃。此后,他又在城内的府邸接待起客人。修造几十年后,萨切蒂别墅无主堙废。
先是砖顶下沉,然后大理石柱在穹拱数吨的重压下弯曲变形,水很快从绽裂的砖块间成股流下,渗入梁架和弃屋,瓦解开始了。曾被年轻的建筑大师在绘图板上用直尺一笔笔量画出来的房屋构造,渐渐失去轮廓,它面目全非、支离破碎。曾被打磨雕凿、一层层堆砌成建筑的石料,变得脆碎易折,无力抵御植物生长和寒暑更迭,直至再也分不清凝灰石和砖块、大理石与山岩。唯有亭宇厚重的外墙,还能在夏月的每次暴雨倾盆后,抵挡一阵冲下山的大水,仿佛世界到了末日。
相反,在巴黎,欧洲的另一个都城,必不可缺的污秽比波旁王室更久长——那是屎和尿的刺鼻气味。特别是夜里,当排污管再次升出粪坑,整个住宅区都臭气熏天,为省去开往堆尸场的路,排泄物被倾倒进下水沟,拂晓中,浓稠的酱汁沿街道向塞纳河流去,几小时后,岸边的取水者们毫不知情地装满他们的罐子。
过早的衰弱将让他们得到救赎。神主之宫为他们每个人都准备了床,这家古老的医院坐落在迂回曲折的老城,那张床,他们要与其他四个人分享。除了孤儿,那里还住着精神病人和老人。产妇和刚动过手术的患者在尸体楼上,病人躺在垂死者之间。破屋潮湿,走廊憋闷,即使在夏日,钻入窗洞的也是永远的昏暗。孩子们发了馊,女人是腐烂的甜,男人闻起来满身冷汗,医院朽败的浊气萦绕着一切——它预告着死亡将至,与不停地抚捻衣被同样可靠无疑。1772年12月30日也是如此,当夜,点蜡时燃着的火跳过木梁、落到枝叶繁茂的绿地上。两星期之久,医院大火熊熊。当观众们兴致勃勃地欣赏着红光冲天的壮观城景,怒焰却蔓延得越来越远、毁掉了城市中世纪的心脏。
黑色的天空前,留下被休伯特·罗伯特记录在若干素描和油画中的烧光的骨架。他八年前回到巴黎,赢得了“废墟罗伯特”的名号。废墟被渴望着。谁等不及时间完工,就制造或画出它。建筑的坍塌能吸引许多人来凑热闹,几乎就像砍头。于是,罗伯特画着古庙中祈祷的僧侣、地下河码头边的洗衣妇、圣母院桥和兑换桥上桥屋的拆除;他画马车如何从废墟上拉走瓦砾,人们怎样把残骸装上长长的平底船,日工在城市翻新的战场上寻找着可重复利用的材料、将其堆垒起来卖掉,以推动那永恒的循环。于是废墟成了工地,在罗伯特笔下不再彼此区分。甚至在他的画布上,医学院的基坑也像极文物的发掘地。他把歌剧院的大火画成火山喷发,六月夜空前的火海、火柱和烟云,以及次日清晨熏黑的建筑外壳,还有默东城堡的拆除,斐扬教堂的轰炸,巴士底狱的攻占,被毁前的黑色要塞——滔滔不绝的迷人画面:落石堆入护城河,烟云缭绕,如同古代的战利品。这幅画在说,新生,要求旧物无情毁灭。自此之后,每天都有纪念碑消失,每个星期都有骑兵雕像阵亡于熔炉。新的废墟之城,叫作巴黎。宫殿被占,堡垒夷为平地,教堂惨遭蹂躏,坟墓中挖出了国王和王后、修道院长和主教、血统最高贵的王侯的尸骨,他们的铅棺铜椁在专门设立的铸造厂被加工成子弹,遗骸被弃入匆匆挖出的坑穴、撒上生石灰,以遏止尸臭、加速腐败。罗伯特以编年史家冷眼冷心的无动于衷画下目标明确又漫无目的的毁灭全景,若有谁当时问他,支持哪一方,将会得到的答案是:“艺术。”
在他的画上,亵渎百年陵冢成了家常便饭,已无法判断,某些东西是毁是存。画布未干,他就被捕了。他和许多其他贵族的宠臣一样,落入圣-拉扎尔,那座古老的、变成监狱的麻风病院。在那里他也要画,画发放牛奶,监狱庭院内的球赛,透过栅栏窗、在远方闪烁的克里希近郊和教堂,还有耸立天边的蒙马特四周的荒田——起先画在陶器和门板上,直至后来他被允许拿到画布和纸。他每日在内院锻炼,不远处,裹黑衣的女侯爵在巨大的木十字下祈天垂怜——恢复“主是主,仆为仆”的旧秩序。
1794年3月的一个傍晚,四层走廊里传来阵阵笑声。又是一席常见的全道宴,上了梭子鱼和鳟鱼、水果和酒。一只小猴子在牢房间窜来窜去。埃米尔,一个囚犯五岁的儿子,用一根绳子开开心心地遛着兔子。两位被关押的女士忘情地弹奏着羽管键琴和竖琴,乐器静下来,罗伯特就开始讲,年轻时他如何登上斗兽场、差点摔死,又如何鼓足勇气拜访皮拉内西。他怎么跟师学艺,怎么随着他一起画地下的墓穴。萨切蒂别墅的骇象,他只字未提。像往常一样,他穿着及膝的紫袍,袍下身体的胖瘦只能被隐约猜到。他的高额头上刻着两道深深的皱纹,几粒麻子点在红光焕发的脸上。黑色的浓眉已经和他稀疏的头发一样,变得灰白。虽然上了年纪,又一身肥膘,监狱里的抓人比赛他却总是能赢。连那双小眼睛也一如既往地满是欣喜。大笑时,他肉乎乎的下唇就抖起来,下巴上浮出两个小小的酒窝。他举起酒杯,愉快地宣布,他是圣拉扎尔最不倒霉的囚徒。他的快乐安如磐石,其原因在于,他将和这里的所有人一样,注定死于断头台下,然而他对此守口如瓶。——“世人皆有始与终”(Stat sua cuique dies),他一再引用维吉尔,笑着他富有感染力的大笑,让人以为他从未遭遇过不幸。尽管他的四个孩子全死了,都被疾病夺了命。他已经准备好了一切。他画过自己的坟,用废柴做了架微型斩首机,以弄明白工具的操作原理,很快它也会把他的脑袋干净利索地从躯干上切下来。每隔几天,他的牢房就会回响起阵阵鼓声,它宣告着黑马车的到来,囚犯将会被带走、送上法庭。
几个星期后,1794年5月的一个寒冷、明媚的清晨,他站在集合于内庭的囚犯当中,被点了名。他明白,最后的时辰敲响了。他正要出列,却有另一个人走上前去,他被命运赐予了同一个姓氏,并将替代他被刀锋砍中。休伯特·罗伯特自由了。多年后,他才在卢森堡新街的工作室里死于中风。他倒在地上,手里拿着调色板。
罗伯特死后一年,1809年7月,两位建筑师在一位医生的陪同下,开入罗马附近那座窒闷的荒谷。还没抵达目的地,马就受了惊,重鞭之下,仍然拒绝把车子拉到再也走不了的大道尽头。他们没办法,只能徒步走完最后一段路,直至站在马里奥山脚下的萨切蒂别墅面前。罗马的每位占领者都曾在那座山上扎营,包括拿破仑的军官,那是1797年2月,他下令抢夺人们认为有价值的所有艺术品,将其运往法兰西共和国、那自命的自由之国,送至全宇宙的学府巴黎。于是专员们倾巢出动,把教皇的宝库洗劫一空,剪碎拉斐尔的挂毯,锯开壁画和油画,砍断雕像的手足四肢。
父辈们曾来此惊赞,他们却来掠走被赞之物。教堂的每片金属、每块理石都被拆出、卖掉,圣人的陵墓被翻得底朝天,圣髑盒、圣体光和神龛被拍卖,连哥特人都手下留情的主祭坛被捣毁,所有贵族的权力标识全部从市容中清空:罗维雷的橡树、波吉亚的公牛、美第奇的药丸、法尔内塞的百合、巴贝里尼的蜜蜂。而萨切蒂的三条黑杠,只是在此处城外的地狱谷中才幸免于葬身怒火。
先生们走上摇摇欲坠的台阶。他们在为死者寻找一块地方,一个所有人都能安息的公墓。两位建筑师想把废墟改造成小教堂,把庄园开辟成通风良好、高墙环荫的宽阔大墓园。因为,在教皇被捕、珍奇猎物般被绑去法国后不久,奥勒利安城墙内的所有葬地均已封锁。罗马的宝贝消失了,阿波罗,拉奥孔,甚至贝维德雷的躯干,都被当作战利品,与非洲的骆驼、狮子和一头来自伯尔尼的熊,共同上了月桂叶装饰的战车,在两天的凯旋游行中,在阴沉如铅的天空下,被公牛从植物园、经万神殿、一直拉到练兵场。第一日傍晚,天放了晴,这让骄横的记者有机会评论说,太阳战胜了云,就像自由的力量战胜了暴政。
只有沉重的图拉真柱,仍伫立在素日所在之处。罗马人口几乎少了三分之一;住宅多于居民。宫殿和修道院成了破壁残垣,教堂的墓穴中散发出熟悉的、甜丝丝的朽败气息,虽然医生们在公告和演讲中一再警告腐尸的危险、迫切建议将其葬在城门之外。从现在开始,卫生法生效,取代传统的仪式。可罗马人拒绝,不愿把他们的亡人草草埋入地狱谷光秃秃的地下,他们要被安葬在石屋里,在陵墓和地穴中,靠近着圣人的尸骨,一如既往。
公墓从未开放。斗兽场长出悬钩子。集会广场上施了工。别墅在洼谷中沙化,羊在大道上吃草。松柏发出幽幽清香,很长一段时间,还将有画家再来,直至最后一点残迹也沉入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