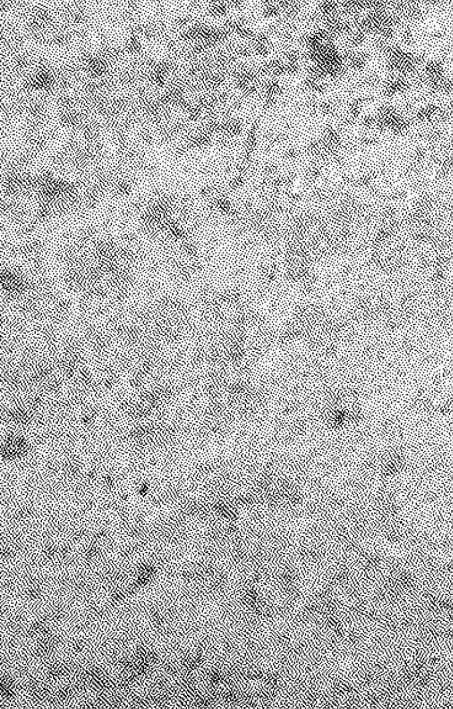| 逝物录 | 收藏 |
曼哈顿
蓝衣男孩
又名《死亡玛瑙》逝物录 作者:尤迪特·沙朗斯基
* 弗里德里希·威廉·茂瑙的电影处女座拍摄于1919年2月,拍摄地在明斯特地区的维希林水上城堡及柏林市郊。故事最重要的道具是一幅画,它模仿了托马斯·庚斯博罗的《蓝衣男孩》,原作中男孩的脸换成了茂瑙的男主角、由恩斯特·霍夫曼扮演的托马斯·凡·韦尔特。对剧情发展有不同说法,但一致的是,主人公是家族的最后一个成员,破落、孤独,与一位老仆生活在父亲的城堡里。他经常观察一位祖先的肖像,常因与之酷似而感到某种神秘的关联。他是他的转世吗?年轻的蓝衣男子胸前带有一枚不断给家族带来灾祸的著名的死亡玛瑙。为摆脱厄运,有人藏起了这枚绿宝石。一天夜里,托马斯梦见,“蓝衣男孩”从画中走出,带他去了藏宝之处。醒来后,托马斯果然在那个地方找到绿宝石,老仆苦苦哀求他扔掉,他却置之不顾。这时,一个巡游剧团来到城堡,夺走了他的一切:宝石被偷,城堡失火,肖像被毁。托马斯生了病,但幸亏一位漂亮女演员纯粹的爱和无私奉献,他活了下来。
† 这部无声电影的首映至今无法证实。因为当时的评论家无人提过它,很可能它从未被当作正片播放。人们认为它下落不明。该片35个短片段的硝酸胶片被染成五种不同颜色,现存于柏林的德国电影资料馆。
显然感冒了。流鼻涕。鼻塞过吗?根本想不起来。这让她很纳闷。毕竟她很在意健康。该死的舒洁纸巾又哪去了?刚刚还在这。真倒霉。没纸巾她无论如何不出门。哈,这呢,镜子下面!嗯,提包里干干净净,带上帽子和墨镜,关门,去邮局。走廊里又是什么怪味儿?哦,对了。抹肥皂的星期一早上。皇后区的清洁团一大早就来了,像群发疯的猴子擦起来大理石,天还没怎么亮,她就被硬生生吵醒。整栋楼都没人像她起得这么早。这种清洁女工的怪味至少到周三都不散。又得想想搬家了。没完没了!要哭了。至少电梯来得快。服务生也有了点礼貌。没人告诉过他在伺候谁吗?装得好像没认出来似的。没人和他讲过,该怎么和她打招呼吗?小屁孩,已经彻底学坏了。娃娃脸上不知想什么歪门邪道。起码没别人。还真觉得缺点什么。可还是慢得要死。怎么说都说十八楼。总算到了。至少门卫懂规矩,从传达室出来,给她开了门。谢啦。天!空气干净。看不见狗仔。没人注意她。肯定是新墨镜的原因。好吧。她不挑,遇到谁算谁,就那个穿灰色法兰绒西装的男人吧。他真不怎么优雅。但还是个好货。他急匆匆地往东区赶,带她挤来挤去,给她了方向、节奏。就不错了。有时他消失在人群里,但她又很快追上去。她毕竟是个有经验的行人。这是唯一她在点行的学问。其实是她唯一的乐趣,她的信仰。需要时可以放弃健美操,遛弯可不行。逛街看橱窗,到处乱走,离开计划路线。每天至少一个小时,两个更好。通常往下到华盛顿广场公园再回来,有时候也往上去77街。开始的时候跟踪一个陌生人比较好。后来就随便了。反正走不丢。岛的好处。
比想得冷。至少对于四月太冷了。哪怕在东岸。这座城市,要么冻死,要么热死。为什么住这,真是个谜,讨厌的漏风天,不感冒都难。一到三月,就该马上去加利福尼亚。和以前一样。三月是真好,就是三月!虽然那没什么事干,无聊得能死人。但毕竟,天气完美:空气干净,阳光充足。能整天光溜溜地到处跑。好吧,至少理论上行。该死的是,施利斯基不愿意。所以她全得自己操心:订飞机、司机、甚至住处,因为房子卖了、马布里路上的也没了。那已经待够了。她在找一件正经的毛衣,找了好几个星期。应该是开司米的。脏玫瑰色,她最爱的颜色。她喜欢的颜色:鲑鱼红,丁香紫,桃花粉。但都比不了脏玫瑰。另外她还有安排,愚蠢的约定。大部分都推了,可还是折腾。塞西尔总试图,显然他自以为,能给她建议某个时间和地点,或,更可怕的是,从她这问出来。可她哪会知道,明天或三天后饿不饿、渴不渴、有没有兴趣见他?再说她状态也不稳。她的健康向来不好。虽然她真的很小心,总是穿得够暖,从来不坐在马桶圈上。真的是:来阵风,她就能倒,不知怎么就惨兮兮着了凉。上次中招是和梅赛德斯喝茶。她只是靠着打开的窗稍稍站一下。晚上喉咙里就开始痒得要死。虽然她像往常一样穿着两件羊毛衫和羊毛裤袜上了床,第二天醒来还是病得一塌糊涂。几个星期才好一半。事实上,更容易说她什么时候没病。还有莫名其妙的该死的潮热。太可怕。她急需新内裤。去年秋天在伦敦,她的确见过及膝的淡蓝款。塞西尔写信说,莉莉怀特只有品蓝、猩红和浅黄的。但他还会去哈罗德看看。反正他保证会找到几条。现在她自己也得上上心。也许应该见他,就为内裤。
咦?灰西装怎么了?干脆跑偏,往右边漂,靠近玻璃墙。去死!他该不是要……就是,别!不会是真的吧!他径直走过去了。真就消失在广场酒店的旋转门里!她刚刚才适应他。至少是华尔道夫酒店啊!十匹马也不能把她拉进广场酒店。它的后门全城最破。这么高级的酒店竟能臭成那样。她对后门了如指掌。是啊,要是她什么事都能像后门这么了解就好了!垃圾桶,或盆子,装满臭烘烘、脏兮兮的衣服,还有泔水味的工作人员电梯。怎么这么倒霉!还没到十点,就来了第一次失望,还不算电梯里的服务生。干脆就不该指望任何人。
现在她站在这,鼻子滴着水。鼻涕淌出来。没人拦住她。多惨!没人关心她。在乎她、认出她、帮助她。所有人都匆匆走开。经过她。一个戴着手套、手指在包里乱翻的女人。该死的舒洁,就像被吞到地底下了。连军团广场的喷泉都没开。所以就结束散步,两个街区都没走完?好吧,那就干脆把鼻涕吸回去,下一轮绿灯过街,别搞什么实验了,沿第五大道走一段,去麦迪逊。灰西装是个错误。又错一回,仅此而已。再来。没什么奇怪的。她不停犯错。可怕。但不是总这样。以前不是。那时候她从不犯什么恶心的错。总是准确知道,要什么,要多少。小手可真准。不会多想。多想一点用都没有。想得多,就永远下不了决心。深思熟虑真他妈可悲,只能长皱纹。她这辈子还从没认真想过什么。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斟酌。反正智商是零。什么都不懂。根本没受过教育。也没读过书。学到过什么?脑袋的姿态有不同的意思:往前低着脑袋,就是听话,往后仰相反,稍稍前倾的脑袋是支持,抬得高高的是镇定、抗拒。居然能记住,真是怪了。她从来没记住过什么。一无所知,但有种梦游似的直觉!很可靠。还是小男孩的时候,她就知道想要什么。反正以前是。现在没了,糟透的直觉。稀汤寡水。她把自己塞进那件畸形的游泳衣的时候,她那有名的直觉哪去了?眼见她往火坑里跳,在镜头前面。纯粹是自杀。顶上空气少。一往下看,就完蛋了。会怕得要死。然后就都没了。
先流鼻涕再鼻塞,还是反过来?典型的病到底他妈的怎么来?待会儿要给简打个电话问问。简明白这些事。至少她装得很懂,都一样吧。虽然她也不知道今天晚上怎么办。夜里有急事当然可以给好朋友打电话!她可是真的惨。一直在想蠢事,烧坏脑子的梦。受不了。现在清楚是什么:进行中的感冒,可今天夜里,也可能是中风、肺炎或癌。到底有没有鼻癌?大概叫别的吧。感冒,也不是不可能鼻窦炎,鼻涕流成这样。可晚上也没洗头啊。见鬼,到底为什么没洗?哦,对了,塞西尔,叽叽歪歪的老阿姨,又打来电话絮叨。就应该给他转接出去!一凑过来就立刻惩罚。娘娘腔的老男人比梅赛德斯还烦。除了抱怨就是情话。难怪她后来偏头痛。要是没接电话就洗头了。至少办完这件事。又是鼻子。真他妈晦气。总在红灯的时候。那又是什么?相机,那边,对着她。那么。的确是。后面有个女人,小丫头,真是个大奶子。她没有吧?不会是真的!现在她擤着鼻涕被拍了。光天化日之下。太可怕!什么倒霉事都躲不开。女摄影师已经走了。街上挤满人。能杀人的热闹。拿着纸条和手风琴的救世军护士,推着热狗小车的可怜虫,卖报的在他那堆分币和一大捆纸后面。人人都有事做。就她没有。她连报纸都不读。里面什么都没有。《生活》封面上那个小心肝是谁?哈,来看看吧!那个小矮子梦露,眼皮半吊着,头发金灿灿,露着肩——一半荡妇,一半瓷娃娃,但也不是没型。她还真是有两把刷子。好莱坞的话题。真厉害。终于到处都在传,这个小蹄子不错。几年前她就预言过。大炮。什么呀,炸弹。为那个被道林·格雷拧断脖子的少女,配上完美的演员。天啊!本来应该是!梦露是西比尔,她自己是道林。复出的完美角色。电影里有一个地方:梦露什么都没穿!要是这样就好了。其他都是浪费。本来就是!高大的嘉宝,被矮小的梦露毁了。表演艺术的胜利!该死的狗屎,本来就应该这样!她早就知道。是的,就是知道。只是没人懂。但那些白痴,他们从来都不懂。总拿来那些女性角色。为真爱而死,或这类悲惨的废话。那具塞纳河的尸体,傻兮兮地咧嘴笑,靠当死人面具搞出了名堂。如果是面具,那就对了。她本想演小丑,男性小丑,妆和绸裤子下面却是女人。所有崇拜他的少女都不明白,他为什么不作答。可比利也不懂。他和所有人一样是叛徒。现在所有酥皮饼都反胃上来。他竟敢一口气把她所有撤掉的默片念一遍。好像她已经被划掉,已经死了!真卑鄙。反正她无条件信任的导演只有一个,可他早就死透了。为了他,她连小夜鬼也演,小夜灯都行。他让她干啥都成。一切!可他不想。那时候她已经喜欢上了他,在伯杰那。他对她也是,晒得黑黑的,就是他的样子。刚从南太平洋回来,一如既往地又高又瘦。穷得叮当响,却带着牧羊犬住在米拉玛海滩。不可思议地骄傲,霸道得完美。从来都搞不清楚他到底什么意思。他告诉她,几个世纪以前他家从瑞典移民过来。直挺挺地杵在那,好像这就能证明什么似的。简直太迷人!后来在台球桌上,他又变得那么温柔。也难怪,两人都那么醉醺醺的。他机灵的棕色眼睛,红头发,抽动的嘴巴,总是一阵阵荡漾的声音。就是她的菜。可是不!又是结束的开始。五个星期后,他死了。和所有真正对她重要的人一样:阿尔瓦,莫耶,还有茂尔。本来可以好好地。起码他不是没兴趣。他迷男孩子也不是问题。相反:她也从来不是什么小姑娘。就像塞西尔开玩笑说的。来吧,你可从来不是什么男孩。后来他挖出来一张她的照片,看到了什么,一个还看不到未来的时刻。她暮色中的童年。该死的贫穷,索德尔灰色的日子。爸爸在房间角落里弯腰看报纸,妈妈在另一个角落里,补着什么衣服。总是浑浊的空气。那时她确实希望塞西尔碰碰她。尤其是:在她喊出Nicht machen![德语:别!]前——用德语——别离开!施利斯基从不碰她。他的手大得像马桶盖。可悲。
时装沙龙的橱窗也有品位得多。可究竟能从哪搞到锦葵紫的地毯?这个颜色的家具她又是在哪见到的?唉,她的房子也只能继续无聊的要死。一个能看到中央公园的讨厌的窟窿。里面没有她喜欢的东西。可怕。她必须再搬一次。居无定所,逃亡的生活,旁白。永远一个人,伶伶仃仃。像鸡似的天黑就睡。很少看戏,只看电影,不排队的话。无事可做。据说处女座什么都搞得定。可她能做的一切,就是搬家。C'est la vie[法语:这就是生活。]。不,生活不是这样的。她自己是。塞西尔说得对。她浪费了最好的年华。要是有谁为她而活,用他的血养她。可会是谁?今天夜里连简都不耐烦起来。都这样了!她还要算一算打过多少次电话,太过分了!十次?就算是又怎样!先是塞西尔阴阳怪气的指责,然后发现她今天再没力气洗头。然后是简的冷酷。可惜塞西尔现在这么黏,真可怜。几乎和梅赛德斯一样糟。只不过那只老乌鸦还给她带来晦气。她推荐的那个脊椎按摩师。狼医生,名字就是个坏征兆。本来只是手腕有点问题。他却把她的背和胯搞得咔咔响。整个骨架都被他错了位!之后不止胯骨脱臼,连嘴都歪了。他差点杀了她。
是不是应该喝杯咖啡?可去哪喝?在市区走得太远了。该死。怎么没早点想到!她得去保健品店!上个礼拜就应该去拿荨麻茶了。竟然忘了这么重要的事!不愧是她。她可有事做,有目标。保健品店在莱辛顿大道和57街的街角。她毕竟生病了呀。也许又是那个小小的、风趣的布吕内特。算不上大美女,但是那种感到亲切的好看。一切都会好的。多美妙的主意。她会给她一包新纸巾,也可能调一杯混合维他命。然后可以给简打电话,约她去殖民地酒店吃午饭。再给她一次机会。或者干脆自己去三冠吃北欧烩菜。这次不要无聊的蒸蔬菜,不要烤鸡。然后去孔雀画廊痛快地来杯威士忌,抽盒金健烟。还可以去男装裁缝那儿,给自己订做一条新裤子。是的,她甚至可以给塞西尔打电话,让他搞来一件脏玫瑰色的毛衣。他甚至有可能弄到的。他那么活跃,那么八面玲珑,有那么强烈的兴趣——对物和人。她摸不透,他到底为什么会愿意和她一起消磨时间?她最了解自己多么不可思议地无聊。毕竟她不得不一直忍受自己。哪怕受不了,也不能干脆挂掉。没法和自己分开。可惜这根本不可能。唉,她多想从自己这儿放个假。成为另外一个人。该死的拍戏就好在这儿。还有剧本,挺实用的。施利斯基不是特别有天赋的作者。不过差强人意的小货色也比什么都没有强。目前男人也不少。起码有两位数。女人不算。她们是另一码。可能就是塞西尔吧。她还是喜欢他的。还有谁能让她这么说?他只是没有一把抓住她拉到婚礼圣坛上去。是个白痴反倒在等那句愿意。他不懂,她得被强迫幸福。她需要的,就是屁股上被踢一脚!她忘了愿意怎么说。她当然想拍电影。但也要等好角色。游泳衣那场灾难之后,怨她自己。只是不太容易看出来,什么是:好角色。《魔山》里的琦琦夫人?玛丽·居里和伦琴射线?直觉没了。它完蛋了。那个殷勤的怪物施利斯基虽然能在半夜给她搞一辆车和一瓶伏特加,这些事儿他可帮不上忙。当然,他很霸道。那是他身上可爱的地方。对他的小矮个儿来说,他有双很大的手。他能用那双手把所有其他人搞得团团转。不用大声。所有人都他妈的怕他。地狱狗赛普鲁斯还是赛普洛斯的,不管叫什么。但他是个根本不知道想要什么的人。有时候他那样看着她。那双冷冷的鱼眼睛,好像她根本不存在。
那儿,自助餐厅旁边就是了。她的目标,她的灯塔,她亲爱的保健品店。很幸运。矮小的布吕内特在。她已经把茶捧在了手里。她能信得着。她弯腰的时候,白大褂可真合体。她为什么这么奇怪地看着?“天啊,嘉宝小姐,您看起来可不怎么好。”怎么会?“什么?我变得那么厉害?”她多么奇怪的看着。“不不,并没有。”她现在冷静下来,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这她可没想到!上帝啊,必须立刻离开。赶紧喝茶。已经交过钱了。然后就出去。怎样一场灾难。该死。她显然看起来很糟糕。至少比平时差。她必须检查一下。可是在哪儿呀?橱窗里的镜子。该死。这算是什么?果然,她看起来简直就是可怕,恐怖。红眼睛,红鼻子,皱纹,从没有过这么多。脖子松弛。到处都是急着变成皱纹的线条。哎呀,褶子,嘴边儿的裂纹像沟一样,该死的烟。没有化妆师能打腻子抹平它们。大理石碎了。所有还在的轮廓,都会模糊掉,渐渐消失。死人面具的角色倒是应景。谁死得早,至少还有这个。茂尔的她还留着。
为了这张脸,她什么没做过?烫直发根,矫正牙齿,改变发型和发色。那些狗仔以为,这张脸属于他们,也难怪。她只需要动动睫毛,整个世界都会去解读。她的微笑,女巫般的。她的眼睛,充满预言。她的颧骨,天神一般。去他妈的。任何崇拜都是结束的开始。然后就只有僵化和牺牲。真他妈的该死。哪有女神。所有这些年,她就是个化妆的屁股。她也可以演一个好男人。英俊高大,宽肩膀,大脚大手。
可现在她知道了!根本不是游泳衣!和她一直以为的不一样,那根本就不是问题。不是泳衣,而是该死的泳帽。下巴上那条晦气的小皮绳,在皮肤上勒出了印。那时候肉就软了,有点儿松。衰老很早就开始。实际上一出生就老了。反正现在一切都晚了。去他妈的。无所谓。现在来根烟就好了。快拿这些死亡小棍来。爸爸总是说:明天就好了。然后他就死了。这十年很难。下个十年也只会可怕。她厌倦了一切。甚至厌倦了厌倦。其他人有丈夫、孩子或记忆。她什么都没有,该死的名气和糟透的钱,惩罚她在四月的星期一不需要上班,不用去市区的办公室,不用去——脏兮兮的工作室,哪都不用去。真相是,她的一生结束了。一个有过去的女人。一个没未来的女人。没有舵的船,永远孤零零。可怜的小嘉宝!没救了。不是拉车的马,而是没有主人的狗,一天天在曼哈顿闲逛,穿过城市的阴沟,它在四月就发出垃圾的恶臭。她又能去哪儿?在整个世界上,她就是一张脸。哪怕带着渔夫帽,或是裹着拖地的海狗皮大衣,也迟早会被发现。到处是狗仔。只是时间的问题。不,结束,很好。那是她终点。从某一时刻起,输的比赢的多。她努力工作过。从来没有时间。现在有了时间,却屁事儿都没有。东河太脏,可不想在那淹死。很多女人发了疯。可惜她没有。她只是病了。也许她也早就精神错乱,只是自己不知道。甚至已经死了?谁知道,可能死了好多年。她曾经年轻过吗?记不住了。也不是新鲜事。她什么都记不住。只有那种一切都见过、经历过的感觉:成堆的邮件,聚光灯嗡嗡响,闪光灯,所有那些可怜的装腔作势。洛杉矶是场独一无二的噩梦。世界上再没有更无聊的地方。一个没有人行道的该死的城市!我的天。有多少次,她让人往北开五小时把自己送去圣芭芭拉,只是为了在那散散步,却发现还是哪都去不了,连喝茶都没地方。那里也到处是埋伏。她只想自己待着。可为什么没人关心她?她究竟为什么没有丈夫和孩子?所有她爱的人,都死了。她还欣赏的人,都老了。和她一样老。茂尔会让她怎么办。卖掉一切,永远消失。也不一定是太平洋。他回来,意味着结束。逆行的载重车,一丛灌木。其他人都没事,司机和坐在副驾驶上的小个子菲律宾人。牧羊犬干脆跑了。它可能还在山谷里乱转呢。茂尔好看的后脑勺,压得稀碎。可他躺在殡仪馆里,一点都看不出来,他穿着灰西装,高贵、傲慢的脸画得花里胡哨,就像娘娘腔的柏林老同性恋。一具干瘦的、盛装打扮的死尸,在栀子花的花圈和十字架之间。这个地方连死人都会被化成彩色片。到处都是谁也不想坐的空空的花园椅子,带着那些蜡印的彩花布垫。毕竟还有几个心腹。最后能信任的人。火葬还是土埋还是问题。到那时候还没定。要是能把钟调回去,让她怎么着都成。别错过结局,结婚,或者就拍部电影!她愿意!甚至试过镜了。在拉布里亚把台词说得漂漂亮亮,头发里鼓着机器的风。所有人都没了,不是吗?詹姆斯不是对她说过,嘉宝小姐,您仍然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他是认真的。就在不久前。两年还是三年?差一点。又是什么?一个女公爵,爱情失意,成了修女。随他妈的便。她也是个修女。虽然和塞西尔在一起也不错。同性恋其实是更好的情人。他抓住她的头发,扯得生疼。有时候,他就是知道她需要什么。就差那么一点。所有蠢事她都玩过。张开屁股,甚至练了上臂。可,不,每次她以为,现在行了,就会有什么事发生。就像中了邪!施利斯基总是说,她和杜丝一样。她也隐居了十一年,然后重返舞台。前所未有地大获成功。现在是哪年来着?1952年,真他妈该死。现在也已经十一年了。自从全世界都看到她在游泳池里、嘲笑她,都过去该死的十一年了。现在,现在她是什么?一个什么都诱惑不了的女人。失业的演员。活着的化石。夜里的鬼,大白天在市中心乱转,找一件脏玫瑰色的开司米衫和鬼知道是什么的意义!僵尸,被活埋在这高耸着红砖楼、荒凉笔直的深渊大街里。她什么没试过!占星,通灵,甚至心理分析——在草包博士那,整个西好莱坞唯一的瑞典分析师。几周后,他告诉她,她有自恋障碍。可真厉害!一出去,公路上就挂着她的海报,比人还大。怎么能没障碍?她再没去过。反正她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灵魂切成片。塞西尔怀疑,她根本没灵魂。很可能他就是对的。很可能她真就是个坏人。是的,就是她:不懂礼貌的坏人。改不了的。他当真相信过,她能当他的妻子?无非就是个角色。最后一个。现在什么都晚了。可她是从什么时候老的?没多久吧。该死的变老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当她开始盼着春天的时候。毕竟,它以前没法打动她。以前她只念着冬天。那棵孤零零的、单薄的死树,在她圣维森特大道的公寓后面,她的冬天树。她多少次想象过,是寒冷夺走它的叶子,很快就会下雪,盖上它光秃秃的树枝。当然没下过雪。又怎么会?在该死的加利福尼亚。圣诞节后下的是雨,哗哗地尿,峡谷都满了。什么都能忘:父母,语言,国籍,但放不下小时候的气候。尽管:四月开玫瑰,橙花甜甜的香气。马布里路上潮湿的、雾蒙蒙的日子,海滩的清晨,唯一能散步的地方。所有逃离气候的尝试最后都失败了。她在哪落了脚?一座散发着甲醛、汗臭和垃圾味儿的城市。第一次来这,她还是个黄毛小子。是夏天,热得要死,出不去门。她想,她死了。晚上她合不上眼,因为院子里正在剁垃圾。就躺着,听那台轰隆隆响的地狱机器令人恶心地砸嘴,救火车的警笛,汽车喇叭,那种毁神经的噪声。她最想把自己淹死在浴缸里,可房里没有。现在呢?现在这个城市的窟窿是她唯一的家。她没死。她知道,死人不擤鼻涕,至少。不,她活着。还活着。这就是问题。所以,加利福尼亚。还是欧洲?这待不下去了。也许先从小事开始。一件接着另一件。先回家,沏茶,给简打电话,洗头。接下来也许是加利福尼亚。绕路去棕榈泉。夏天才是欧洲。尼斯应该是个漂亮的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