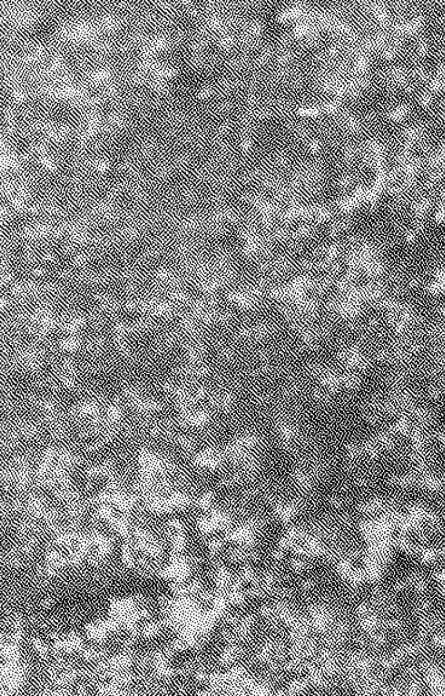| 逝物录 | 收藏 |
莱斯博斯岛
萨福的爱之诗
逝物录 作者:尤迪特·沙朗斯基
* 萨福的诗诞生于希腊古风时期,约公元前600年,在爱琴海东部的莱斯博斯岛上。
† 萨福死后,她的诗可能很快在莱斯博斯岛上以某种可演奏的形式被记录下来,然而,其音乐伴奏的曲谱已荡然无存。公元前3世纪和2世纪,亚历山大学者曾把她散落于不同雅典版本及文选中的作品结集出版为评注本,也许,在此之前,曲谱早已遗失。公元1世纪,加达拉的菲洛德穆有一句注疏表明,在他的时代,妓女们常在宴席和调情时吟唱萨福的诗。
她的作品大概在拜占庭时期消失——纯粹的忽视和针对性破坏的共同结果。12世纪上半叶,哲学家米歇尔·伊塔利克斯还曾以某种方式提及萨福,据此推测,他熟悉她的作品。同一时期,学者约翰·策策斯却说,她的诗已经失传。有些人认为,它们在1073年被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焚毁,或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期间毁于君士坦丁堡的大火;另有人推测,早在公元4世纪她的文本已被销毁,还有其他人认为时间更早,因为此后的文法学家再未引用过她的诗。
近来对规模庞大、但残缺不全的莎草纸的评鉴将使文本剧增。
当尼布甲尼撒二世洗劫耶路撒冷、梭伦执政雅典、腓尼基水手首次环航非洲大陆、阿那克西曼德还在猜想一切存在源于某种说不清的元物质、而灵魂本质上是气状的时候,萨福写道:
他好似神,
他对你坐,
他近你身,
他听你言如蜜
你牵魂一笑
我就胸中心怯:
我凝眸一瞥,
就哑然失声。
我舌瘫成结,
我微火侵肤,
我眼不能视,
我耳中呼啸。
我汗下成瀑,
我战颤欲折,
我枯似草,
我形如尸。
万般不忍,唯当……
佛陀和孔子尚未出世,民主观念和“哲学”一词还没被想出,可厄洛斯——阿芙洛狄特的侍童——已开始了毫不留情的统治;不只是最古老、最强大的神,是症状不定、晴空劈下的病,是汹涌崩塌的自然力,是翻江倒海、甚至连根拔起橡树的风暴,是急遽扑来、无法制服的狂暴野兽,点燃压不灭的欲望,引发铺天盖地的折磨——既甜又苦、蚀骨噬心的激情。
存世的文学作品,古于萨福之诗者寥寥无几:厚如大地的吉尔伽美什史诗,最初几首空灵的梨俱吠陀赞歌,荷马源源不竭的史诗,赫西俄德枝杈阔远的神话,它说:缪斯无所不知。她们知道,曾在、现在、将在的一切。她们的父亲是宙斯,母亲是女提坦、记忆神摩涅莫辛涅。
我们一无所知。起码所知甚少。甚至不清楚,是否真有过一位荷马,不清楚,那位我们不得已而冠名为伪朗吉努斯的作者是谁,他在残缺的、关于崇高的传世文稿中引用了萨福描写厄洛斯威力的诗行,这才为后人、为我们把它们保存下来。
我们知道,萨福来自莱斯博斯,这座爱琴海东部的岛屿如此靠近小亚细亚主陆,视野晴好时人们竟以为能游过去——游到当时富不可测的吕底亚岸边,再从那里,今天的土耳其,游向今天富不可测的欧罗巴。
某处,在赫梯人沉落的帝国,一定能找到她特殊姓氏的起源,其隐蔽的意义,或是“神圣”“净洁”“纯粹的源泉”,或是——据另一种推衍——古希腊语中蓝宝石和天青石的变异。
她应出生于埃雷索斯,也可能是米蒂利尼,约在我们纪年前的617年左右,或许还要早13年或再晚5年。她的父亲叫斯卡曼德罗斯或斯卡曼德罗尼摩斯;但也可能是西蒙、攸梅诺斯、埃瑞吉亚斯、埃克里托斯、塞摩斯、卡蒙或埃塔科斯,这是《苏达》所记,那部滔滔不绝、但并不怎么可靠的10世纪拜占庭辞书。
我们知道,她有两个分别叫查拉科斯和拉里科斯的兄弟,或许还有第三位攸吕吉亚斯,她出身高贵,因为她最小的弟弟拉里科斯是米蒂利尼国宴厅的司酒官,也就是担任着一个留给贵族男孩的职位。
我们相信,她的母亲叫克莱伊丝,她的一个女儿同名,虽然这个词也可能指女奴,因为她曾在一首诗中以此称呼她心爱的少女。
萨福从未提过丈夫。《苏达》认为“安德罗斯岛的凯克拉斯”是他的名字,可那只能是古代喜剧作者的下流笑话,偏偏为她捏造出一个名为“男人岛之阳具先生”的丈夫,他们一定在以此取乐。传说她对一个叫法翁的年轻船夫怀有不幸的、甚或自我毁灭的爱情,这也定然出自那个时候,奥维德还在《女杰书简》中对此添油加醋。
我们从公元前3世纪的一部编年史铭文中得知,她曾乘船逃到叙拉古——具体何时,帕罗斯岛的大理石碑上并未记载。我们可以从另一处文献推断,此事发生在克连阿克梯德家族掌握岛屿命运之时,约公元前596年。
七八年后,待僭主庇塔库斯统治莱斯博斯时,她逃亡归来,并在米蒂利尼建立了一个圈子,我们并不知道,它算是崇拜阿芙洛狄特的神秘宗教团体,是彼此之间有色情关系的女伴酒会,还是贵族小姐们婚前的预备学校。
再没有哪个古希腊早期的女人被如此丰富、如此矛盾地讨论过。文献多么贫瘠,传说就多么五光十色,而区分二者的尝试几乎全都无望。
每个时代都创造着它自己的萨福,有些甚至杜撰出两个她以逃避叙事的矛盾:于是,她有时是女祭司——献身于阿芙洛狄特或缪斯,有时是妓女,有时是女淫棍,有时是爱到发疯的两性人,有时是仁心的教师,有时是风流的荡妇;有时无耻堕落,有时贞洁纯净。
她的同胞和同代人阿尔卡埃乌斯说她不可亵玩,紫罗兰般迷人,且甜笑如蜜,苏格拉底说她美,柏拉图说她智慧,加达拉的菲洛德莫斯称她是第十位缪斯,斯特拉波说她是珍贵的尤物,贺拉斯说她阳刚,而他究竟指什么,再也无证可循。
一份2世纪末或3世纪初的莎草纸却宣称,萨福丑陋、矮小、黝黑,是令人憎恶的女性的情人。
她的容貌曾在青铜像上广为流传;时至今日,银币还显示着她头戴月桂花冠的侧颜,一个波留克列特斯学派的水壶上画着她阅读卷轴的苗条身影,一只公元前5世纪的黑釉花瓶上有她的高挑体态,她手执八弦琴,似乎刚结束演奏,或正要开始。
我们不知道,用词首不识送气音的伊奥利亚语吟诵萨福诗行听之如何,当那种古老至极、繁复至极的古希腊方言在婚礼、盛宴或女人的圈子里响起时,弦乐器会被奏响相和,低音时弹拨福明克斯或专用于节日的基塔拉、巴尔比通或竖琴般的派克提斯,高音处则以二十弦的玛伽蒂斯或闷响的龟背琴为伴。
我们只知道,萨福死后三百年才被亚历山大学者造出的“抒情诗”(Lyrik)一词源于其中的一种乐器的里拉(Lyra)。他们为她整理出一部八卷或九卷的全集,那是莎草文卷上的几千行、按格律分类的数百首,我们只完好拥有其中一首,而它之所以还在,是因为奥古斯都时代生活在罗马的修辞学者哈利卡纳索斯的狄奥尼修斯在他的文稿《论文学布局》中将其作为可赞叹的典范完整收载。那位人称伪朗基努斯的学者至少护存下四段连贯诗节;另一首诗的五节可从三份不同的莎草纸碎片中拼合而出;1937年发现了第三首诗的四个诗节,它们被一个公元前2世纪的埃及学童随意乱写在手掌大的陶片上;第五首和第六首的片段保存在一卷中世纪早期的破损羊皮纸上;前不久分离出的莎草纸条能补充出第七首和第八首的大部分内容,它们来自存放埃及木乃伊或包书的硬板,虽然对其中一首诗的破译专家们仍各执一词。
大规模的中世纪抄士手稿流传下来的,是文法学者如阿特纳奥斯、阿波罗尼奥斯·狄斯克罗斯、哲学家如克律希波斯、词典编撰者如尤里亚斯·波勒克斯等人,为说明某种风格、特殊词汇或以她命名的格律而引用过的只言片语,——其余只是碎屑:几段零散的诗节,一两行残缺的诗句,剥离文脉的语词,孤零零的音节或字母,词首或词尾,长不及句,更遑论意义。
…
…
…我去往…
…
…若…
…
…因…
…和谐的…
…合唱,…
…声音清澈地…
…
…一切…
…
省略符在歌声消逝、语词阙如、莎草卷破碎朽烂处出场,先伶仃散现,后成双成对,很快成为一种隐隐约约的三节拍模式——静寂之声的乐谱。
这些诗歌沉默下去,成了文字,成了借取自腓尼基语的希腊字符:深暗的大写字母——被学童笨拙的手刻入黏土,或被孜孜不倦的专业人士用羽毛管转录到木质禾本植物的草浆里;纤细的小写字母——写在被浮石磨光、被石灰漂白的小绵羊或死产山羊的皮上:莎草纸和羊皮纸,——一旦暴露于天日之下,就会在某一时刻像所有死尸那样分解的有机材料。
…
…并不…
…渴求…
…突然…
…花朵…
…渴求…
…喜悦…
这些残诗仿佛表格,渴望着填充——被阐释和想象——或那些散落在奥克西林库斯垃圾山中其他莎草残迹的破译,那是埃及法雍绿洲上的亡城,它把这些石头般坚硬、被蠹虫蚀蛀、因多次卷折而脆裂、皴皱、撕破的碎片保存在数米深的干沙层里几近千年。
我们知道,密密麻麻写在莎草纸卷上的一列列文字没有间隙、标点或线格,即便是保存完好的段落仍难以识读。卜筮——那种在古代神谕艺术中通过观察鸟的迁徙和释梦而预言未来的天赋,在今天的莎草纸学里则另有所指,它被用来命名读出一行文字的能力——在隐约只有古希腊字母的吉光片羽上。
我们知道,碎片是浪漫的无限承诺,是依然有力的现代理想,素来无任何文学体裁如诗艺这般,与意味深长的空缺、与滋养着投影的留白息息相关。省略符恍似与语词长合的幻肢,宣告着一种失却的美满。萨福完好无损的诗会让我们感到陌异,就像涂满刺目色彩的古代雕塑。
流传下来的诗歌和片段,不论多么短促,多么零乱残缺,总计不足600行。计算表明,萨福的作品约有7%留存至今。计算还表明,女性中约有7%只被、或主要被女性吸引。可没有计算能够证明,此中是否存在关联。
符号史熟悉几种未知和不定、缺席和缺失、空白和虚无的代表:古巴比伦谷物清单上的零,代数方程中的字母X,话语戛然而止时的破折号。
… … …
牧人 欲望 汗水
… … …
…玫瑰…
…
我们知道,顿绝,话语的中断,是一种修辞格,伪朗吉努斯那部关于崇高的文稿也一定有过相关论述,这部分内容却因图书馆理员和装订者的疏忽遗失。谁被情感击溃,语言因其纯然的宏大而失灵,谁就会停止说话,就会开始支吾吞吐,甚至喑哑失声。感觉无法转化为语言,亦不会投降于可用的词句,省略号则把每篇文本开向这浩瀚不定的觉知帝国。
…我的爱…
我们知道,艾米丽·狄金森写给她的女友及日后的嫂子苏珊·吉尔伯特的信,曾被她的侄女、吉尔伯特的女儿玛莎删节,为出版之故她天衣无缝地清理了一系列激情段落。在这些被审查的文段中,1852年6月11日的一句是:若你在此——哦,若你在此,我的苏西,我们就不用说什么话,我们的眼睛会为我们轻声耳语,有你的手紧紧在我手中,我们就再也不需要言语。
一如不可测的情感滔滔不绝的誓信,无言、盲目的理解,也是爱情诗固定的话题。
萨福的句子,但凡可读,就明确清澈,正是句子应有的模样。它们又同时慎思、澎湃,以每经一次翻译才能苏醒复活的消亡语言讲述着天穹的力量,纵然过了二十六个世纪,其惊世骇俗依然毫发无损:那急遽、美妙又残酷的转变,让一个人成了欲望的客体,让他无法抵抗,让他不惜离开父母、配偶甚至孩子。
厄洛斯再次震摇我,那肢体的溶化者,
苦而甜,无法制服的爬行兽。
我们知道,按主角属于同性还是异性来划分欲望的观念,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很是陌生。关键的反而是,参与者在性行为中的性别角色是否符合其社会角色,成年男性主动,相反,孩子、未成年人和女性举止被动。行为中掌控和顺服的分野不在于性别,而在于进攻及占有者与被进攻及被占有者之别。
在存留的萨福抒情诗中,男子无名而现,具名者是众多女子:阿班缇斯,阿加丽斯,安娜格拉,安娜克托莉卡,阿尔夏娜萨,阿丽格诺塔,阿缇斯,狄卡,多莉夏,艾拉娜,尤内卡,贡吉拉,格尔戈,吉瑞娜,克莱伊斯,克利安缇斯,麦加拉,米卡,姆娜西斯,姆娜西狄卡,普莱斯托蒂卡,特蕾西帕。她们是萨福歌唱的人,以倾心柔情或熊熊欲火,以焦灼的妒意或冰冷的轻蔑。
我说,有人会想起我们,
即使在遥远的时空。
我们相信,萨福曾是一位女教师,虽然第一份认定她如此身份的文献是一块公元2世纪的莎草纸碎片,它在她死后700年记述说,她曾为爱奥尼亚和吕底亚出身最好的少女授课。
在萨福留存下来的抒情诗中,找不到任何能推测出教育背景的线索,虽然诸残篇描写了一个女子们来来去去、常常述说离别的世界。它似乎是过渡场。希腊的少年之爱有案可稽,很容易想到,把萨福诗中的世界解读为其女性的对应物。这种读法亦有优势,可把诗中无法否认的女女情爱的存在归入课程为那个真正的、公认的顶点所做的准备:婚姻。
我们不知道,汉娜·怀特和安妮·盖斯吉尔的关系是何种性质,她们在1707年9月4日缔结的婚姻被不加任何解释地记录在英国西北部塔克萨尔教区的登记簿中。可我们知道,基督教缔结婚姻时的常用辞令出自旧约,那是守寡的鲁特对婆婆拿俄米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
我们还知道,1891年,一家苏格兰女子寄宿学校的两位主管——如一位女学生宣称——相互犯下不得体的罪行,诉讼过程中,她们引用了琉善的《妓女对话》,才使得女性之间的性爱终于有可能浮出水面。书中,妓女科罗娜里翁向基塔拉琴师雷阿伊娜询问她与一位莱斯博斯富家女的性经验,特别是催促她透露,具体怎样做,用什么方法。雷阿伊娜回应说:别指望从我这里得到细节!那是不可说之事。向阿芙洛狄忒起誓,我不会对你讲一个字。
这一章在此结束,问题没有得到回答,女人之间做了什么,既未说,也不可说。不论如何,两位女教师被无罪释放,因为法官得出的结论是,指责她们的罪根本不可能:没有工具,就没有行为,没有武器,就不会造孽。
在很长时间里,女人之间只有模仿男女媾和才算作性、才会被惩罚。阳具标志着性行为,缺少它,则不过是尚无符号强调的空白,盲点、缺口,一个应被填满的窟窿,就像女性的生殖器。
在这空白之上久久阴魂不散的幻象是从1世纪到19世纪流窜在男性文本中的“特里巴德”,这个行为男性化的女人借助怪物般膨胀的阴蒂或类似阴茎的工具与其他女人交媾。据我们所知,从未有任何一个女人自称为特里巴德。
我们知道,词句如同符号,意义会发生变化。很久以来,书写线下方三个连贯的点一直标识着遗失和不明,不知何时起它们也意味着未曾说和不可说,不仅是去——和无——,也是开放的留白。于是这三点变成了符号,它要求把暗示思考到底,敦促着人们想象阙如,它代表未曾明言、秘而不宣,它代表伤风败俗,代表归罪和臆测,代表着省略的一个特殊变种:本真。
我们也知道,省略的古代标志是星号——直至中世纪那颗小星星才担任起连接文本标记处与相关批注的职能。所以圣依西多禄在他成书于公元7世纪的《词源》中写道:星号——作为字体排印中文本缺漏的标记——被插入某物省略之处,以便让缺席者通过这个符号醒目起来。今天使用这个星号,有时是为囊括尽可能多的人及其性别身份。从省略变为参与,从缺席变为在场,从空白变为意义的填充。
我们还知道,动词lesbiazein,“像莱斯博斯的女人那样做”,在古代是“亵渎”或“诋毁某人”的一个词,它意指口交,因为人们认为,是莱斯博斯岛上的女人发明了这种性技巧。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在他的古语大全中把这个希腊单词译为拉丁语的fellare,“吮吸”,并在结束该词条时批注:概念虽然犹在,但我认为,此种行为已被彻底根除。
不久后,16世纪末,布朗通领主皮埃尔·德·布尔代耶在他的色情小说《风流女士的一生》中提及:据说,在这门手艺上,莱斯博斯的萨福是很好的老师;甚至有人说,是她发明了此道,并将其沿传至今。此后,空白不仅有了地理上的来处,也有了语言的故乡,虽然直到近代,莱斯博斯之爱仍然常常用于表达女性对年轻男子的徒劳爱慕。
我们知道,1904年暮夏,两位年轻的女诗人娜塔莉·格里芙德·巴妮和勒妮·薇薇安实现了久违之梦,她们同游莱斯博斯岛,却大失所望。终于抵达米蒂利尼港口时,一部留声机尖叫起刺耳的法国香颂。女诗人曾在自己的诗中反复吟咏此地,可不论岛上居民的形象、还是他们方言的粗俗,都与她们崇高的想象相去甚远。即便如此,她们还是在橄榄林里租下两座相邻的房子,在月光和日光中长长地散步,让她们经年冷却的爱复活,并计划在岛上建立一所诗和爱的女子同性恋学校。
当第三个女人宣布来访时,伊甸园的静好结束了,——善妒而占有欲强烈的女伯爵与薇薇安暧昧不清,却只需一封电报就能被拦下脚步。巴妮和薇薇安分了手。返回巴黎,两人共同的古希腊语老师继续充当着她们秘密信件的传递者。
我们知道,2009年,莱博斯岛上的两位女居民和一位男居民试图实施禁令而未果,她们想禁止并非来自岛屿的女人自称或被其他人称作蕾丝:我们抗议家乡的名字被那些特殊的人滥用。
审理此事的法官驳回提案,下令三个莱斯博斯人承担法庭费用。
谁还熟悉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陈述的莱斯博斯原则?对于那些一般律法不适用于具体情况的案例,建议参考莱斯博斯的建筑师,他们使用的铅尺能适应石头的形状。在具体情况中有一种弯曲但有效的尺度,要好于追求平直却无用的理想。
谁还熟悉萨福体的诗节,那种四行的颂诗格律前三行相同,由十一音节构成,插入扬抑格间的扬抑抑格位于第三位,最后是一行阿多尼斯韵脚,这使得行首无一弱音而铿锵有力,行末则阴柔婉约,此韵律典型的庄重肃穆于是最终在宁静甚或欢愉中弥散开来。
在神学家、法学学者及医学家的手册里,“特里巴德”“萨福主义”或“莱斯博斯主义”很久都被用作大致相仿的同义词,虽然它们有时意味着反自然的性行为或有伤风化的习俗,有时又成了异常肥大或心理疾病。
我们并不清楚,“莱斯博斯之爱”的说法为何经久不败,我们只知道,这个词及其相关的秩序,与所有过往之物一样,晦暗不明。
L是舌尖音,e是随后发出的元音,s是种嘶嘶作响的警告声,b是冲开闭唇的爆破音……
在德语词典中,“莱斯博斯”紧跟在“可读”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