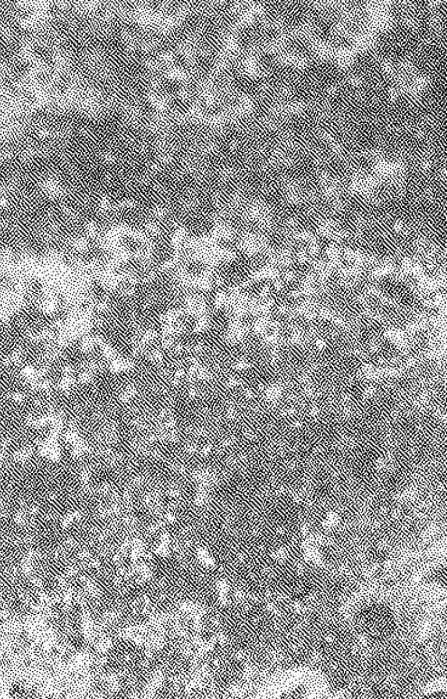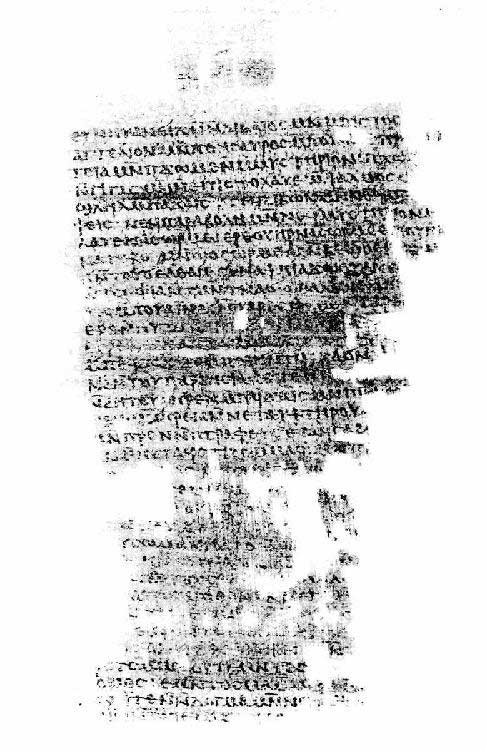| 逝物录 | 收藏 |
贝伦霍夫
冯·贝尔宫
逝物录 作者:尤迪特·沙朗斯基
* 古老的冯·贝尔家族因其纹章形态亦被称作“天鹅颈之家”,该家族的古茨科系自14世纪起就在波莫瑞的格赖夫斯瓦尔德附近拥有布斯多夫的大部分土地。
1804年,此地在瑞典-波莫瑞政府的批准之下更名为“贝伦霍夫”的施特拉尔松。经遗产信托,骑兵上尉约翰·卡尔·乌尔里希·冯·贝尔把他的农庄转移给了孙子卡尔·菲利克斯·戈奥格,并规定永远采取长子继承制。
后者在庄园后方修造了两层楼高的新主宅,这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由辛克尔-舒勒斯·弗里德里希·黑茨希设计,于1838年完工。1896年,此处被1877年晋升为普鲁士伯爵的卡尔·菲利克斯·沃尔德玛扩建,两侧的单层门廊被拓宽并加建了新楼层。
最后一位伯爵、帝国地方长官、德意志国国会常任议员卡尔·弗里德里希·菲利克斯·冯·贝尔的遗孀梅希蒂尔德·冯·贝尔伯爵夫人,于1936至1939年间,在认信会主宅中举办讲座。神学家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应是当年的常客。
† 1945年5月8日,主宅失火。当地居民利用烧毁建筑的砖瓦建造了新农舍。
今天,方圆9公顷、由皮特·约瑟夫·勒内设计、修建于1840到1860年间的风景园得到了文物保护。
我还记得那扇打开的窗。夜里,空气凉爽。一扇开在夏夜的窗。天上没有月亮。只有路灯弥散的光。有泥土的气息。也许下过雨。我不知道。
妈妈说,是7月31日。她很确定,因为克尔斯汀阿姨7月31日过生日,那天傍晚她也庆祝过,在对面长工的老房子里。妈妈还说,肯定没下雨。晴朗的一天。全天太阳,就是七月。
天气记录也说那天很热,毕竟是极其干燥的暖夏。
1984年夏天。是我的第一个记忆,我知道,我以为,我宣称。我可以给克尔斯汀阿姨打电话。她还活着。妈妈和我的两个爸爸也是。一个生了我,一个会在后来那个夜里冰敷我的腿、为它们缠上纱布。
我在葱茏小山间的墓园里玩。我藏在大石块和墓碑后,和蓝白闪烁的小花一起蹲在植物之间。一个因驼背走路而变矮的老太太把枯花和干花环扔进堆肥。她在生锈的水龙头下放了一只铁皮水壶,从黄杨树篱后消失了。
我弯下腰,手指划过光滑的石头,摸着那些凿刻字母的粗糙凹陷,等待着不可能的事情。我等待着被发现。我希望。我害怕。
整个童年我们都在乡下,典型的农庄仔细藏起它们更辉煌的过去。那时候也住在村子里,离当地唯一的公交站仅几步之遥,紧挨没有钟楼、野石圣坛高耸的教堂,那是司事的老房子,在上面一层。我们的院子就在坟场旁。甚至没有篱笆隔开两边的堆肥。记忆里,我总是一个人。自己在墓地,自己在围着红色高墙的果园里,自己在石头堆上,妈妈说,我每天都从上面一次次跳下来。
可没人来。奇迹,一如既往地,并未发生。于是我在小小的苗圃里摘几朵花,拔出地里的三色堇,从尖尖的、插入土中的塑料花瓶里抽出一支支郁金香。
我有所预感,却一无所知。至少不知道,花属于缺席者,属于装入木盒、烂在地下的死人。当我把花束带回家,妈妈骂了我,但什么都没解释。
我还不了解死。人会死,有一天我自己也会死,这超出了我的想象力。后来,当表哥对我透露这个秘密时,我根本不信。我确定,他像往常一样,只是偶然听错。他咧开嘴笑了。他确定他说的事。
我晕了头。穿过我们现在住的新房子,跑去厨房问妈妈,是不是真的,人到底会不会死,是不是我们所有人都将在某一天死去,我也一样。她点点头,说是,耸了耸肩。我看向垃圾桶,不知为何,我想象死人会掉进里面,成为皱巴巴的东西,被垃圾车运走。虽然没人说话,我还是堵住耳朵,跑进了走廊。黄光透过波纹玻璃窗,落到楼梯间落满尘土的绿色植物上。
我闭着眼睛,在邻村年市的鬼屋车里。凉风吹过我的皮肤。能听到啪嗒啪嗒的声响,车子在摇晃、滚动,尖叫。我感觉到眼睑的皮肤,仍死死闭着眼,有一刻屏住了呼吸,我哼歌,等待。简直是永远。
不知过了多久,有人拍了拍我。妈妈的声音说:完了。我睁开眼。我们又在外面了。我一直闭着眼睛,我骄傲地说。我骗过了它。我赢了害怕。可惜了钱,妈妈说,把我从车里抱出来。
我在公园里的苹果树间玩。我摘了许多小黄花,用蒲公英汁染指甲。在堆肥前发现了一个有刺的球。它呼吸。它活着。
妈妈把一小碟牛奶放在球前面,它变成了神奇的动物。我们蹲下去。圆圆的乌黑的眼睛盯着我。我感到妈妈的手摸着我的头。尖尖的鼻子在找牛奶。粉色的小舌头一闪一闪。动物呼噜呼噜地咂吧嘴。它的刺晃来晃去。
我对生活满意。我没什么期待。妈妈在期待一个小孩。但我不记得隆起的肚子,或是抚摸那弧线的男人的手。日期表明,她一定怀着孕。照片显示,她正在怀孕。那个七月之夜并不会凉爽,我的弟弟应该在一个月后来到世界上,我的外婆,接过医院的电话后,穿着暗蓝的晨衣站在卧室门口,第一次说出了他的名字。
我坐在外婆的床上,听着那个对我没有任何意义的名字,又玩起了口红,那是一堆不可思议的闪亮的小圆筒,外婆把它们藏在床头上方的扁盒里。
卧室开着窗,可房门关了,紧锁着,钥匙没挂在钥匙板上,也没放在餐桌上。我醒了,爬下带栏杆的儿童床。打开卧室门,把房子看了个遍。所有房间都黑漆漆的,所有其他窗子都关着:客厅半圆的老虎窗,厨房的天舱口,无窗小屋乌黑的窟窿,我的爸爸在那里搞了个小作坊。
再没房间了。浴室在楼下的底层。我们和顶楼的薇欧拉阿姨共用。我们共用厕所、咕咕响的快热炉、四脚浴缸和挂在前面的篾席。薇欧拉阿姨在学校食堂工作,那是以前的马厩,公园北端的一栋黄砖房,入口上方左右两侧有石刻的马头。在过去马吃草的地方,我们现在吃每天的午饭。我们排长长的队,幼儿园的小孩,学校的学生,老师,和半个村子。薇欧拉阿姨有染成金色的头发,画成紫罗兰的眼睛,和一个当货车司机的丈夫,他星期六回来,星期日又离开,一个看不见脸的大高个。学校在公园后,两栋新楼,有着一排排长长的窗。我的父母在那教书,还有克尔斯汀阿姨。公园很大,属于已经没有了的宫殿。克尔斯汀阿姨和薇欧拉阿姨都不是真阿姨。只是这么叫。
宫殿也不是真宫殿。是主宅,延伸很远的两层楼,农庄的中心,旁边有一个马厩、一个羊圈和一个牛棚,还有事务房和两座仓库。石雕熊的大门后一条菩提树大道紧接着乡路,它穿过禁止村民入内的北园、直接通往主宅。我的幼儿园所在之处,曾经一定是气派的上坡,敞开的大门前是绿油油的圆形花坛,它同时也是车道入口,上方高悬着八根柱子支撑的露台,窗子在三角山墙下,立面爬满了野葡萄。
窗子开着,可房门关了,锁前闩了插销。我伸出手臂,抓住门把手,往下拽——可门仍然锁着。
我记得客厅里装有组合立柜的高墙,安安静静放在炉角的玩具,摇椅好像突然定住,一个超大尺寸的清空的娃娃屋。只有卧室开着窗,外面空气凉凉的。
教堂就在正中,可所有人都从它旁边走过。谁都不关心红砖墙里面,谁都不去看坟冢和十字。只有几个驼背的老妇人,穿过吱嘎作响的大门,向公墓走去。我们紧挨着教堂住。但它毫无意义。用雕凿的花岗岩和粗石修造的高大建筑没有意义,斜对面的牧师房没有意义,平地上的木钟架没有意义,礼拜日的钟声没有意义,教堂院子里歪歪扭扭的锈十字没有意义,锻铁门后伯爵们风化的陵墓、蕨类植物中的十字、半浮雕里的石刻天使也没有,它们在没人坐的破长椅上方飞,还有写着箴言的板子,虽然有一次妈妈给我读了上面的话,我还是不明白:爱无休止。那是过去的残迹,而过去,似乎已永无出头日。
村子得名于一个古老的贵族世家,是古茨科伯爵及波莫瑞公爵的封地——一封古老的采邑受封书上写,他们是英勇、亲爱、忠诚的骑士。
那是童话的词句。写在挤巴巴的竖栏里,家谱树的枝桠从这里远远分叉出去。冯·贝尔家族,他们是乡绅和膳务总管,宫廷侍从和行政官,修士长和教授,县、市议员,学监和司令,贵族教师和骑兵指挥官,宫廷和皇家侍童,士兵、元帅、少校、上尉、中尉——在波兰战争中,在地方民兵里,在瑞典禁卫军、丹麦或法国的军队中。有方济会修女和女修道院院长,有船长的妻子,甚至女诗人,重要的是,他们是此地的拥有者,他们的采邑,他们的家业,谷苗、动产和牲畜统统在内。这块贵族地产不能继承,而是直接落回古老的主脉,长子比后出世的弟弟重要得多,女儿们则几乎什么都不是。他们有货物,要变卖和交换、抵押和购入,要为之缴税或借贷。他们有时签署采邑书,把印章敲在厚厚的纸上,黏糊糊的一团,红得像公牛的血:一头跳舞的熊在两只天鹅间。
我母亲的祖先是农场主,牲口或木柴贩子,运货商和屠夫,一个守林人,一个扳道工,一个水手。我生父的祖先是磨坊工和裁缝、车匠和木工,一个步兵,几个医生,一位女缝工,一位渔夫,一位火车乘务员,一位化学家,一个建筑师,一位工厂主,一位战后成了墓园花匠的军火商。
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只住了一年,但那是我记得的第一年。妈妈说,我们院落紧邻的,不是墓地,而是公园。她补充说,那还有一段残墙。
有些人说,宫殿是战后炸毁的,另一些说,战争结束前它就烧光了,连同所有财产:迎宾大厅中华丽的枝状吊灯,两个沙龙的水晶玻璃门,昏暗的家具、书、银餐具和瓷器,金镜子,古地图,还有祖先画廊里巨大的肖像,先生们目光严肃、骑着高头大马。
我们没有古物,没有遗产。只有我们住的老房子。每晚都听得见屋架上的鼬。我的父母在等天鹅湖后面的板式楼。三房,中央供暖,还有一个能流出热水的浴室。他们在排队。时间很紧。小孩很快就会来。
老房子常常很脆,一夜之间倒掉也不奇怪,就像去年秋天的供销社。屋顶直接塌下来。早上费了好大劲儿才撞开门。我还记得聚集在前面的人群,售货员和顾客们,穿花罩衫的女人提着购物网兜,男人赶来,从废墟里刨出瓶瓶罐罐。他们把满是尘土的货物装入推车,把罐头、面粉袋和牛奶车送来的瓶子堆进我们楼左前方鼓出来的阴暗、霉臭的房间。甩卖开始了。整天亮着灯。我们在楼上的房子里都能听到钱箱的叮叮当当。
我穿着无袖的麻纱连体衣,带橙色的小花图案。松紧带箍在腰上。我记得那扇打开的窗,温吞吞的空气,因为不凉爽,不可能凉爽,连一丝新鲜的风都吹不进,因为是七月,克尔斯汀阿姨过生日,薇欧拉阿姨为什么没来看我,我不知道。我三岁半了,几乎四岁。四个手指伸出来,几乎就是整只手。
我不记得有一摞砖,不记得院子里有一堆石头,不记得我每天爬上去,越爬越高,再一次次跳下来。我只看到那扇打开的窗。窗台到我胸口。我想爬上去,可太高了。我后退了几步,想:尤迪特,你不傻,然后说:尤迪特,你不傻。我一遍遍重复这句话,先是悄悄对自己,然后大声说了出来。这句话把我带到厨房。我抓住餐椅,在地砖上推它。吱吱声很响。我把它拖过门槛,生拉硬扯地从客厅的橙色地毯上拽过去,经过父母的大床,一直到了那扇打开的窗边。我想起童话里那个淘气的小海沃尔曼,可我的睡衣不是帆,我的栏杆床没有轮。它整晚都在炉边。我透过栏杆往外看。我站在窗腰边。我是海沃尔曼,总用妈妈的声音问我有完没完的月亮,却消失在一朵云的后面。云边闪着光。我谁也拦不住。我爬到椅子上,脚上穿着居家鞋。是深蓝色灯芯绒做的。我爬上窗台,蹲下去。鞋尖朝外面。我不等。我什么都不等。不看路灯。不看苹果树。只是下面。石铺路。灌木丛。
妈妈从医院回来,没有小孩,在新的村子乘了火车,那不只有公交站,还有火车站。她经过教堂,仙鹤在上面喂它们的宝宝,她经过供销社,那座新楼前的水泥广场上有自行车的停车架。围裙们早就站在那里。看着她的方向窃窃私语:贝伦霍夫的女教师,现在住在新房里。她们相互眨眼睛,问孩子是不是死胎。她们用普通话和土话问:他一下生就没了?
一个老妇人找到我。她拄着拐棍,弯下腰问:你在干什么傻事,孩子?
妈妈回了家,没有小孩。她根本没回家,因为我住在外婆家里的那个星期,我的父母搬进了邻村的新房,七千米外,远得没边。千米是最大的单位,和年一样无法想象。我三岁半,几乎四岁,我知道,只是因为,在我四岁生日前不久,我的弟弟看到了世界的光——其实是格赖夫斯瓦尔德妇产科医院的日光灯——随后就是治皮肤黄疸的紫外灯。房子有浴室,但没有中央供暖。地下室还有前租客的煤。还有很多。
脐带像蛇一样缠在小孩的脖子上,推迟、阻挠他来到这个世界,最后那么危险,手和嘴唇都已经发青的婴儿,活着生下来简直就是奇迹。
我还记得一个噩梦,我在水下,沉得越来越深,头顶是一层冰。我记得一部电视卡通片,有个女人跳进空空的游泳池,像娃娃似的,把四肢摔得粉碎。那个画面至今仍让我不寒而栗。
我不知道,死是什么感觉。我问了新幼儿园的保育员,她是个有好多卷发的高大的女人。
她摇摇头。说,我不知道。我还没死。
我想知道,地里的死人怎么了。烂了。这个词,我不懂。
就像皱巴巴的苹果,迟早会长出虫子和蛆,被它们吃光。她解释说。
我不得不想到厨房里的垃圾桶,这时她又说:你根本感觉不到。你已经死了呀。
邪恶是,热牛奶上的皮,冻住的村子池塘上薄薄的冰层,院子里十几条黑闪闪的蛞蝓。死亡是穿着花围裙的老妇人。命运女神们戴头巾,走路拄拐,说土话。她们询问生下来就死去的小孩,询问傻事,耙平她们早死的丈夫的坟。
冯·贝尔家的人曾是英勇、亲爱、忠诚的骑士。有些人说,他们的宫殿烧光了。另一些人说,它是炸毁的。俄国人来了,老伯爵夫人逃跑,于是村民们亲自抢空它,然后点了火,这是一个老妇人说的,她一定知道。她也拿了能拿走的东西:迎宾大厅中华丽的枝状吊灯,两个沙龙的水晶玻璃门,昏暗的家具、书、银餐具和瓷器、金镜子、古地图,还有祖先画廊里巨大的肖像,先生们目光严肃、骑着高头大马,带有伯爵纹章的银烟盒:灰牌上是一头站立的黑熊,前掌抬起好像在敬礼,牌子的头盔上有两只曲颈相背的天鹅。
我落在荨麻丛里。脚上还套着居家鞋,腿上一阵抽痛。麻木。荨麻火辣辣地烧着。路灯灯光里,有一个驼背的老妇人的轮廓。水泥路面闪着光。下雨了。
不久前我读到,有人居住的地方,荨麻无处不在,墙壁上,垃圾堆里。一如所有长针刺的植物,它们自古就被认为能驱魔。老普林尼写道,如果挖荨麻的时候叫出病童的名字,再补充说他是谁的孩子,荨麻根就能治疗小儿的玫瑰疹。
我不知道,我是谁的孩子。
是卧室刺眼的灯光,光滑漆面下有木纹的柜子。我仰面躺着,像甲虫一样把腿伸向高处。是我的父母,比平时更高大。他们不看我,只盯着我缠了纱布的腿。腿很痛,脚是木的。他们的脸是有发型的亮斑。
什么都没断。X光片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这一点。没人说这是奇迹。妈妈没说,县城的医生也没说。护士为扭伤的脚踝缠了锌糊绷带。在我的接种证明书上敲了章,它的第一页贴了三条胶带。上面用粗体的大写字母写着我的名字和铁道边村里的新地址,是妈妈的笔迹,清晰易读的教师体。
什么都没断。可我好多个星期都不能正常走路。我一瘸一拐,张开双臂。妈妈抱起我。我叉开腿,环住她的腰,后面的肚子里是尚未出生的孩子。
后来,我的父母常常说起,我这一跳给他们带来多少麻烦。但只字不提运气或奇迹,因为在那个时代、在那个国家,不存在奇迹。
我不知道什么上帝或天使。第一次在彩画上看到时,我已经上学了。彩画在一个老妇人床上方的玻璃后,她的床短得不可思议。那是上个时代的遗迹,和所有长工房一样昏暗,有山墙和粗石基座,遥远得像另一个世界,月光清澈的夜色中,孩子们被一个长发、仙鹤翅膀的男人领过吊桥,他们穿着五彩衣服,脸蛋发光,金色鬈发,眼睛亮晶晶。
吃晚饭的时候,我盯着看了妈妈很久。她真的是我的妈妈吗?难道不可能,她只是宣称生下我,像她一再强调的,疼了好几天?不是也很可能,她只不过在某个地方找到了我、带回来,甚至是从我原本的、真正的妈妈那里抱走了我,而她还在某个地方等着我,和小汉斯的儿歌里一样绝望?
我看着她给我抹面包,切成小块,放在我的小餐板上。我观察她棕色的眼睛,她隐藏着什么心事的嘴巴。我跑进浴室,站到两面镜子之间,看着无限复制的画面,寻找相似之处。
有一个谜,可我连问题或提问都不懂。问题是一扇打开的窗。答案是一扇打开的窗。从四米的高处跳下。
几年后,我在外婆家中病倒。是假期。客厅没有暖气。我发着烧,浑身疼。他们叫了医生。一个高大的男人,把他苍白的手放在我的脖子上,用悠长、坚定的目光打量着我。他声音柔和。眼睛那么深,好像有人把它们推回眼窝,从里面看出来也因此更加迫切,并被眼镜片奇怪地放大了。那是一种想要对我说什么的目光。手从钱夹里抽出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小腿紧绷、穿白袜的小孩,手里拿着一把巨大的伞。我点点头,什么都不知道。有一个谜,可我连问题或提问都不懂。照片上的小孩是我。医生是我的爸爸,他不是。
三十多年后,一个料峭的春天,我拿折尺比量着翻修的司事楼立面,惊讶地发现,居然有四米,精确到厘米。楼上的窗现在更宽了。斜对面牧师的老房子在出售。从那里阳台上能看到一望无际的田野,平坦辽阔,草场,沙质粘表土的耕田。一个人来了,透过毛玻璃指了指。他说,起硝了。听起来就像死亡判决。现在我才发现墙上一块白色的、硬化的盐花。看上去就像传染病。
我第一次进了教堂。圣坛北面的墙上画着地狱敞开的深渊。蛙、蛇和人坠落其中,被诅咒的灵魂,将会被火焰吞没。前面宝座上端坐着猪脸的地狱王,手执权杖和闪电。
跳出窗是我的第一个记忆吗?我问妈妈刺猬。刺猬出现在一年前,秋天,妈妈说。可我记得刺猬,这只能意味着,我的第一个记忆不是七月夜,而是那个奇妙的动物。
石雕熊仍还立在公园入口处抹了灰泥的柱子上,前掌中举着风化的牌子,最后一位公爵的纹章。菩提大道通进公园。鹅卵石几乎陷入土。园内有许多杜鹃花、欧洲栗、木兰,两棵山峰榉,甚至一棵红栎和鹅掌楸。地上铺着染白的毯子,那是怒放的雪滴花、雪莲花和银莲花。
我在运动场边缘发现了一堵及腰高的墙,石头上长满青苔。它一定是宫殿的残迹。一定是主宅的残迹,只剩地窖拱顶时,它才成为宫殿。公园南边,一对天鹅,浮在池塘里,在两座假山间,就像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