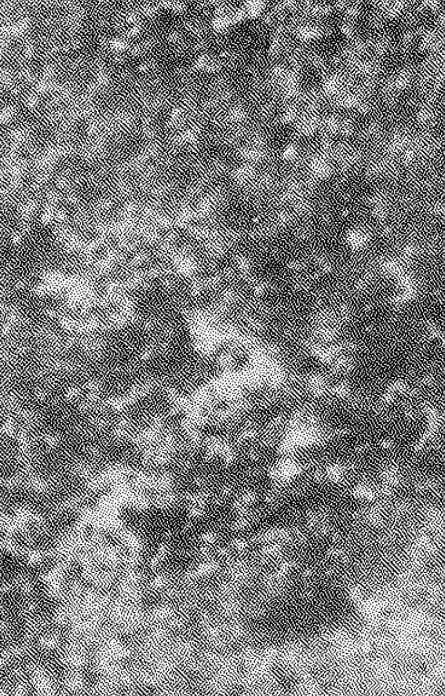| 逝物录 | 收藏 |
巴比伦
摩尼七经
逝物录 作者:尤迪特·沙朗斯基
* 216年,摩尼出生于巴比伦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泰西封附近。摩尼的父母均为波斯人,他随父亲在幼发拉底河下游的一个犹太基督教净洗派中长大。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受到天启。24岁时,他离开厄勒克塞派教团,开始布道,寻找信徒、树立敌人,他在全巴比伦、米底、甘扎克和波斯传教,也遍迹于印度人和安息人的国土,并曾远行至罗马帝国的边缘。
摩尼得到萨珊王朝统治者沙卜尔一世及其子奥尔密兹德一世的支助,却因琐罗亚斯德教教士的怂恿被其后继者巴赫拉姆一世于276年或277年投入监牢。他在囚禁的第26天死去。尸体被肢解,剥下的皮被悬挂在贡德沙普尔城的城门上示众。
摩尼教远播至两河流域以外的整个地中海地区,直至西班牙和北非、小亚细亚和中亚,并沿丝绸之路传入印度和中国。因此这种融合性的教义与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西方的灵知派基督教、东方的佛教均有关联。古代后期,在三大洲均有信众的摩尼教是世界宗教。
† 关于摩尼教的没落鲜有记载,古代及中世纪的所有文献均已被毁,各地的信仰活动和信徒均遭受打压或迫害。在西罗马帝国,自382年起,信仰摩尼教可致死刑。该教在中国至843年才被禁,但它在几个地区一直延续到13世纪,在中国南部甚至存活到16世纪。
以东阿拉姆语写就的摩尼经虽有所有传教语种的译本,如希腊语、拉丁语、科普特语、阿拉伯语、安息语、中古波斯语、粟特语、维吾尔语、汉语等,但这些文本无一留存。传世的只有《生命福音》开头、《信简》的残遗、《大力士经》的片断以及用中古波斯语撰写的教义书《沙卜拉甘》的零星残章。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能根据迫害者及后世阿拉伯百科全书提供的证据复原摩尼教义。
直至1902年,才在中亚绿洲吐鲁番出土了保存不佳的摩尼原稿残片。1929年在埃及绿洲法雍附近发现的科普特语摩尼教藏书,大部分进入了柏林的博物馆。部分手稿,包括一卷摩尼书简,在“二战”后运往苏联的过程中再次散失。
倘若神圣之物真的只对神圣之人开显,那么此地——在正午高悬的荒原骄阳悠悠颤动的天光中,在蓬乱的椰枣树下,在汹涌多叉的幼发拉底河蜿蜒的支流旁——暮春时节它会因北方高山上的大量融雪暴涨为浩浩汤汤、间或断岸决堤的泛滥大河,把汹汹洪流泵入灌溉系统的壮观沟渠,它远之又远,枝杈愈发精微,侵入缺雨或无雨的洼谷,灌满围堤的凹槽,浸透休耕的荒地,让水轮转动、让谷苗繁茂,保证每年两季的收成,以此奠定这片土地的富饶和美名:谷物,堆成山的石榴,无花果和椰枣,它们在数百艘筏子上顺流而下,直至水体在泥泞的三角洲流域与其孪生的兄弟河汇聚,血脉偾张地向它们的入海口奔流而去。
此处是鸿蒙之地,文明之滩,始祖曾带着他沉重的头颅和已获自由的手迁徙至此,把他宽颌、鼻孔怒张如马、眉毛上方忧郁隆起的堂兄驱逐到更远的北方,使他蜷缩在彼处的洞穴中——以石制工具和啃光的骨头为武器——死于他那不被哀悼的死。族群四处游荡,他们在崎岖多折的迁移中形成了一种模糊的秩序,部落成了民族,依蜿蜒流水顺序而居,仿佛一颗颗珍珠串于编织精美的长线。每一处均自成帝国,开始分配工作和薪酬、收成和收益的芸芸众生——缺乏石头、木材和铁,他们就为自己创造出一个黏土的世界:涂泥浆的草屋和简单的圆形建筑给不穿鞋的平民,四方的宫殿给胡须鬈曲的帝首,有风呼啸而过的堡垒和防尘的金字神塔,蓝釉砖铺就的豪华街道被牛首人和长翅膀的狮子守护,温柔凸起的浮雕上是长袍、叉臂的祭司,泥板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符号,纤细如湿沙上的鸟迹。
当那些亚当的族人还在野山羊的皮毛中摸索着羊毛内衣,当单粒小麦从禾杆中抽出穗,当二粒小麦的颖壳被收集在彩绘的陶碗里,当弯弯的锄头在每一轮新的播种前掀开土壤,物也定居下来,堆垒成储备,被宣告为财产,牛被篱笆圈起,野马被驯服,土地首次被测量,收成将会分配到未来的年份。宗族经济随宗族集体而来。蜂蜜流淌。灵魂流浪。石头的时日即将结束。青铜幽幽,铁器闪烁,时代才刚刚镀上金,就灰暗下来。那些民族定居得越稳,求索就越是汲汲皇皇,追寻真理和意义的冲动,一种内心的不安,崭新得就像看到永远相同、夜夜吞下太阳的地平线。他们凝视黑暗,看不见任何土地,只有眼睑后跳跃的幻影和无底幽冥,它被灼灼亮点刺穿,湮没靠近它的一切。世界是昼和夜,是寒和热,是饥、渴和餍足,是精进自旋的陶片,是木车轮,是芦苇尖,它耕作潮湿的黏土,就像犁地的牛。
太初,能确定的只是,功,伟大永动机的轮转,它——一旦开启——获存能量,就让河流高涨入海,抬水升天,以致大循环,以致四季更迭,以致概念对的轮回,自历史之始它们便成双出现,去扮演天地、父母、兄妹,一对天神,两个怪物,水火不容。初始前荒凉的虚空似乎比对立的单调法则更丰富,后来它就像笼罩人类的诅咒,让他们此后必须在采集和打猎、耕田和放牧、拨火和通往水井的道路上抉择。没人说得出,彼处,深处,在存在之根本,有什么正等待领悟。太初弥漫着骇然混沌还是开裂的虚空,是二者同在还是均不在;作为天神竞争、新旧世代相斗的结果,创世的发生是漫无计划还是目标明确。
从此处开始的宇宙论,不计其数,又彼此悖谬。将它们统一起来的,是此世不完美的观念。有一条无可争辩的鸿沟,一道令人痛苦的深渊,横亘在神明与被抛入此世的人类之间、永恒无瑕的灵魂与易腐因而堕落的肉体之间。问题古老,却从未如此紧迫:何为人,他从何而来,他将归何处,这个世界何时、如何担负起罪孽。
因为,不愿结束的干旱证明,它有罪。种子二三十倍地发芽、每场春雨都会把荒原变成花海的时代,已一去不返。水在淹没的田野上淤积不动,庄稼腐烂,不知疲倦的河流把越来越多的沙冲向南方的岸,大海渐渐退落,只留下开裂的沼泽。雨有时降落,有时不见影踪。若水位上涨,只高出平素一肘,洪流便提早泛滥,淹没洼地,撕裂堤坝,摧毁庄稼,大河只滋养饥饿和苦难——还有那场大水的记忆,翻天覆地的骇浪上,一艘以不幸印封的木舟,载着几个天选之民,向新的万古之世漂去,在那个时代,一位神战胜了其他诸神,帝王般颁布律法:没有无条件的缔盟,没有无契约的信任。
可那位神的心绪多变如河道,矛盾如先知的预兆,他们读取的未来源自抽搐的羊肝和闪烁的星辰。因为此处,这有着大风吹过的荒野和多产河谷、这很久以前图像便凝固为文字的广阔平原上,一切都充满要破译、要阐释的符号。是命运的消息,是天的音信,那无穷无尽的荒野之天,现在开始说话:以它是灵,以它为风或呼吸!天使开口时,就应倾听。于是,在幼发拉底河下游的一个棕榈林里,一个孩子翘首听着那声音对他说的话:“你是光的使徒,最后的先知,塞特、诺亚、以挪士、以诺、闪、亚伯拉罕、琐罗亚斯德、佛陀、耶稣、保罗、厄勒克塞的后继者——他们所有人教义的完善者。”这是妄言般的启示。天使撒了弥天大谎。孩子怎么办?他怕了,要求证明。于是天使做了天使应为之事。他安慰男孩,送去征兆和奇迹,让棕榈树以人的方式说话,让菜蔬婴儿般哭喊,并向他揭开了世界此前一直隐藏的秘密:世界的大戏是光明和黑暗之争,而此在无非是两个时代间的过渡。
谁愿意,就会明白。男孩摩尼愿意。他愿意占据那个分配给他的位子,成为辉煌的终点——站在伟大的先知序列之末。可从来没有人信一个孩子,所以,要等。一个时候未到的当选者要怎么办?他准备。他研究前人的传世之作。无一例外的伟人,苦行者,先知,半神。他们都有大成就,却一定都失败了,所以现在,他领受天命,完善他们的作品。
人人皆可苦修,弃绝世界,抵挡魔鬼。许多人曾闻神语,也有不少将其公之于众。可风连天使的福音也吹散。若时间使之零落,有朝一日,谁来搜集它们、传布智慧?善言流于闲谈,实相沦为梦幻。天使说,欲成真理者,必要写下。摩尼想,欲存真理者,必要写下。只有文字会真正遗世不朽,重如收摄它们的材料,黑色的玄武岩,烧硬的泥板,莎草压实的纤维,或是棕榈僵硬的叶片。
一年年过去。知识开出路,面纱被吹开,内容推动形式,手艺逼就艺术,语词促成记录。一种突如其来的清晰形式踏入摩尼的意识,圆满得仿佛出自圆规,完美如他的教义,融合着始和末,协调了循环与线性之思。
已是仲秋,摩尼的时代终于到来。幼发拉底河静卧在它发源的冬季河床上,无力的小溪在宽阔、凹洼的沙质河床中渐流渐逝,让人忘记,曾是它的水,通过不倦转动的螺旋泵,供养着空中花园的七层高台。
摩尼动身北上,去往底格里斯河左岸他出生的城市,穿过长翅膀的石雕守护的城门,混入涌来此地的人群,提高声音,说出了先知们自古就在说的话:“你们是土里的盐。世界的光。谁跟随我,就不会在黑暗里流浪,就将有生命的光。”
人们站住了。很难说为什么。也许是炎热劝他们停下来,或者,是摩尼那既迷人又让人厌恶的形象,即便只是擦肩而过,目光也会停留在他歪斜的身影和萎缩的腿上。也许,竟或是他带来的消息,在它的光里,一切阴影都散去,一切都成了黑或白:灵魂善而迷失,物质恶而堕落——人是二者的连线,渴求救赎和净化。它是一种创造澄澈、许诺纯粹的对比,它黯淡了如其所是的世界,同时让遥远但确定的未来熠熠生辉,而未来宣称,它只是要恢复那已消逝的完美的从前。它是一条喜讯,在这充满喜讯的国度里,是一份福音,在这不乏福音的时代中,它是许许多多问题的答案。现在,在太阳正至中天、在接近午休的时辰,摩尼从许许多多的脸上读出了那些问题。他知道,在这片土地上,谁懂得从头说起,谁才会被人听到,于是他开始讲述,万物如何开始:太初,世界形成之前,曾一切安好。柔风芬芳,光照斑斓,一派祥和恬淡。统治那帝国的神是永恒的善神,是伟大的父亲,光明的主人。这天堂曾安宁永在,无人自扰于黑暗在南方的喧嚣小国,在那里各地王侯自古相争相斗。两种势力毗邻而居;光明自明,黑暗自毁,各守其道,各司其职。直至某一天——无人知晓具体何时——黑暗侵入光明,二者混战,灵魂与物质,不共戴天。第二个中间时代开始了,世界大戏,正是把人类囚入其中的,此时、此地、此刻。
摩尼讲东方的阿拉姆语,可他的话切肤分明、不容反驳:世上的一切,他再次重复,均为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灵魂与物质的混合,这些两相对立的天性,如生死般泾渭分明。因此,不应以此世为家,甚至不应造屋、生子、食肉,更不应委身肉欲。一切所作所为应局限于最不得已的必需,以尽量减少与物质的接触。因为耕犁田地、剪切菜蔬、采摘果实,甚至踩踏草茎,都会让闭锁其中的那一息光明疼痛。
他停下,倾听他话语的效果。好的演说者知道,什么时候必须沉默。
于是他不久后隐居起来,在半荒野上先知们栖身的洞穴中,曲左腿而坐,把那条走路时不愿听从他、从小就被他托在身后的右腿支在身前,上面架起木简。他解开绳子,翻开书简,把羽毛管放在空空如也的纸上,开始写字——无需任何辅助线,那是他发明的无瑕笔体:如此纤细、精致,乃至千年之后,其残存虽无法用肉眼识别,在放大镜下却纤毫毕现、历历分明。
摩尼翻过页,把毛笔放在莎草纸上,画出黑暗的晦盲否塞和世界的初创:光明之主如何剥下被杀诸魔的皮,以之铺覆天穹,以其碎骨造山,以其枯肉为土,把争战中释放的光亮变为日月,他还画了那位启动寰宇、将天体一一置入轨道的神使。然后摩尼又翻过一页,勾勒出颠乾倒坤的景象:那是黑暗的统治者,他模仿神使相貌、从惨淡余光中塑造出第一对人——并赋予他们结合与繁衍的凶险欲望。第一对人相拥相缠,两个赤裸、苍白的形象,生出一个又一个孩子,光随之四散,碎成越来越小的粒子,回归天国之日于是愈发遥不可及。
摩尼将金箔剪为细屑,胶于莎草之上,再以新色反复涂覆,直至整面流光。晨。昏。一日日,一周周。摩尼不停地画:旋转、庞大、不倦不休的宇宙之轮渐渐提炼出全世界的光,在它乘璀璨渡舟重返银河、摆脱生死循环前,会被信守盈亏的月亮——幽幽天青石的夜空上一轮金色的瓷盘——收集起来、净去尘间浊秽,一个光的灵魂,可以停止存在。
最后,他抓起松鼠毛制成的笔,补画出神使的衣褶,生命之母的眼眉,太初之人金灿灿的铠甲轮廓,众魔的山羊鬼脸。连黑暗统治者的胡须、他被鳞双足上的利爪,也画得精心备至,那是艺术家的周到,他一视同仁地爱着他林林总总的各色造物,甚至忘记了,恶从不曾善,既非善之同族,亦不是善的后代,不是坠落的天使,也不是叛变的提坦,恶之恶无法解释。摩尼的缩微图里有一个自我毁灭的怪物,龙身、狮首、鹰翅、鲸尾,自时间之始它就在蹂躏着它自己的帝国——蛮烟瘴雾、腐臭熏天的战场上,死树的残桩满目,猩红鼎沸的渊穴遍野,铬黄的焦烟从其深处蒸蒸腾起。摩尼教义虽是黑白,他的经书却光怪陆离。谁拥有这些经书,就不再需要庙宇或教堂。它们自身就是皈依、智慧、祈祷之处:木简堂皇,壮丽的书芯裹着未鞣制的生皮,覆以由打磨纤薄的玳瑁和象牙制成的精巧压花,轻便的十二开本封面镶金箔、嵌宝石,还有护身符般大小的微型经书,能藏在握起的拳头里。石榴和灯炱制成的墨水,在白垩漂染的莎草、色泽清浅的丝绸、柔软的皮革或幽光隐隐的羊皮纸上,同样乌黑油亮。只有题名,被雕画得几不可读,环绕着炫目花饰,以朱砂点镶边,那是救赎与毁灭之色,是世界大火的颜色。赤焰熊熊,照亮一千四百六十八年,它点燃宇宙,若不烧光整座世界大厦、释放出最后一粒光,就不会作罢。未来的雄奇景象流光溢彩,在那锌白与金箔仿造的天国光明世界里,善恶再度分离,黑暗的所有成分都被征服、沉降、没落,一大团被活埋之物。而光明的所有成分都高升入月华,被星辰的旋转提纯、澄净。谁愿意,就信。许多人愿意。
琐罗亚斯德有无数弟子,佛陀有五个比丘,耶稣有十二门徒——而摩尼,有七部经书,它们用许多种语言把他的教义传向世界,去统一巴别塔所离间的,去前古未有地分别:那些追随他的,和那些诅咒他的。人们称他为摩那,善的容器或恶的容器,天国食粮或蒙昧者的鸦片,人们称他为摩尼,飞翔的救世主,或摩内斯,瘸腿的恶棍,普照者摩尼,出世以拯救世界,或颠妄者摩尼耶,出世以败坏世界——摩尼,甘露,摩尼,瘟疫。
当殉教之时来临,摩尼对他的子民说:“照看我的经书!也写下我时时言说的智慧,使它们不被你们遗失。”
烈焰灼灼。饕餮怒火吞没摩尼教徒的神圣经文,纯金从中横流而出。可它不是世界之火,不是火光冲天的宇宙,而是敌人的柴堆。任何异说都不被容忍,任何怀疑都要遭受惩罚。因为,信民所在处,便有无神者,虔诚所在处,便有异教徒,真教所在处,忠实信众的妒火便会立即点燃,他们严格区分对错,一如摩尼严格区分光明和黑暗。火从不挑剔,虽然有人说,火焰只毁不真之物。
彼时与摩尼教徒的神圣经文一同烧毁的是什么?世界毁灭的算式,大量的巫术书,驱魔咒,无数相异的此在哲学,成千上万部犹太法典,奥维德的所有作品,论述神圣的三位一体及灵魂有死、论述太空无穷和宇宙的真正规模、论述地球形态及其在星辰结构中位置的文章。审讯持续数日,柴堆燃烧了千年。火温暖了无所不知者的心,加热着亚历山大、君士坦丁堡和罗马的浴室,直至眼睛再也骗不了理智、自然教诲起书籍。真理究竟多么可怕?它的光竟能遍照所有被黑暗歪曲的错误。新的望远镜把远方移至迫在眉睫的近处,造出它后,界限必移位,视野必扩大:天穹成为球行星簇星云、涡旋星云和星系的一轮轮椭圆轨道,从六颗行星变成七颗、八颗、九颗——又成八颗,神话蜕变出物质,其诞生史的古怪毫不亚于摩尼的宇宙观——诸多太阳把行星固定在它们的轨道上,黑洞撕碎并吞掉了星星,星云发出的光将无人在遥远的未来接收。不论多少数字和公式描写过宇宙,不论多少知识参透其本质。只要时间有效——谁又会怀疑时间?——任何解释都只是讲述,讲那个吸引与排斥、始与末、成与坏、偶然与必然的著名故事。宇宙在生长、扩张,把星系彼此推开,就好像,在种种理论试图抓住它之前,就逃之夭夭。想到逃逸、想到这无根虚空的恣肆生长,就不禁毛骨悚然,似乎更甚于想到收缩、回归古老的痛点,万物从那里开始,一切力和物质、所有时间和所有空间都在那里熔融、密聚,先是一点,然后是成团,活埋:爆炸,不断外延的空间,灼烫、拥攘的状态,扩展,冷却,原子从中诞生,光和物质分离,太阳、分子云、尘埃、宇宙蠕虫创造出——虽然如此不真:可见的世界。问始即是问终。是否一切都在扩张、加速,或将在某一天反转、重新收聚,是否一切都被囚禁在不知生亦不知亡的循环里。我们知道什么!能确定的只是:世界末日将会到来,也许暂时,却是可以想象的最阴森的骇事:太阳膨胀为巨星,吞没水星和金星,地球上空,除了太阳,一无所有。它恐怖的热将使海水全部蒸发、石头融化、地壳掀开,内外颠倒,直至寒冷降临,时间结束。
可太阳还在华丽的深蓝天空上,大小如球,照耀着四千年的土地,那片妄自以为与人类本身一样古老、只晓得两个极端的土地:赐死的沙石荒漠和赋生的尼罗河水,每年夏天它都泛滥百日,把滩涂变成茫茫大海,留下让大地丰饶的黑土肥泥。可自从人们用巍峨高墙截住大水,将其围进数千堤坝的迷宫、逼入由堰闸调平的水道,使之全年灌溉侵入荒原越来越远的田野,甚至从沙地上抢出两季收成,尼罗河的饫沃滩涂便一去不返。古老、定居的法拉欣世代以骨骼健壮的公牛和木犁耕地,无奈之下只好把孩子送入荒原,在废弃居民点的瓦砾堆上寻找塞卜巴赫,那由古城土墙的风干砖块瓦解而成的氮肥。
那是1929年异常炎热的一天,三个半大的少年在麦地那-马地附近填满黄沙、半沉入地下的废墟中闲逛,在一个拱顶里发现了一只脆裂的木箱,它在阳光下立刻粉碎,露出几包朽烂的莎草。纸页虽挺过无数世代的蠕虫和蚂蚁,却曾经被水泡透,于是细腻的盐晶取代了动物蚕食而入,这让那几个不久后在古董商的小铺子里手持古卷的男人起初犹豫再三,不知这些边缘发黑、皱缩的书芯能否换钱。连最终鉴定其中一包腐物的修复人员也不相信,远古的秘密竟会在某一时刻对他开口。
工作数月后,他才在一块斜面和微型镊子的帮助下把一张张纸页分离开来,它们那么纤薄、脆弱,只要他打个喷嚏就会瞬间碎成尘埃。称之为偶然或天意!当柏林的文字专家拿着放大镜和镜子、弯腰研究着一块压在玻璃板下、蚕丝般光泽、显然神圣的文字残片时,物理学家弗里茨·兹威基正在离洛杉矶不远的山脊上把加利福尼里亚天文台直径200寸的反射望远镜对准后发座的方向。本是星系的星云疯狂膨胀,在观察它的运动、并与他自己的计算做出比较的时候,他豁然开朗。
可见的物质永远都不足以维系这个星系团。太空中一定有某种不可见的庞然大物,只能通过它产生的引力才能断定其存在。它开始结聚时,比其他物质提早了一刹那,它的引力因此留下一条万物均需追随的痕迹。神秘力量,天空的新权威,因其不为人知的本性,兹威基称之为“暗物质”。
与此同时,柏林的文字学者整理出保护在玻璃后的碎片,开始破译鬼斧神工的笔迹。残章预言了摩尼教团的没落,画出信徒遭受的残暴虐行。可它们也宣告:
千万经书将获救。流入正义与虔诚者之手:《生命福音》与《生命宝藏》,《钵迦摩帝夜》与《秘密经》,《大力士经》与《书信》,《诗篇》与我主的《祈祷》,《图经》与他的启示,他的寓言与他的秘仪——无一遗失。多少失传,多少毁灭?千万失传,又有千万回到手上、终被重新找到。人们将亲吻它们说:“伟大的智慧啊!光明使徒的铠甲!你曾迷失何处?你来自何方?他们在何处寻到你?我欢呼,经书去到他们的手中。”你将与他们相遇,听他们诵读,宣告每部经书之名,宣告书主之名,宣告倾尽所有、使经书得以写就者之名,宣告写书者及置入标点者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