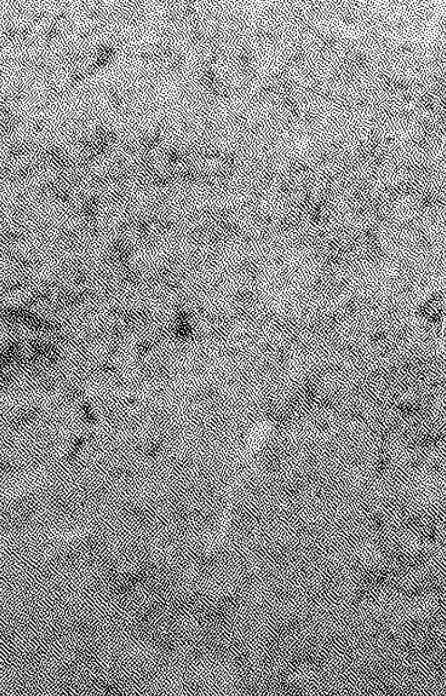| 逝物录 | 收藏 |
莱克河谷
格赖夫斯瓦尔德港
逝物录 作者:尤迪特·沙朗斯基
* 1810至1820年间,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画过他出生的城市格赖夫斯瓦尔德,帆樯林立的港口挤满小货船、双桅船、快艇等帆船。这座古老的汉莎城市,通过可行船的莱克河入波罗的海的入海口,连接着各大贸易中心。然而当时河道宽阔得多的莱克河已多次面临沙化的危险。
† 自1909年起,这幅94厘米高、74厘米宽的油画归汉堡艺术馆所有。1931年,它被出展于慕尼黑玻璃宫举办的“德国的浪漫主义者——从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到莫里兹·冯·施温德”主题画展。6月6日玻璃宫失火,3000多幅画作被毁,包括特展的全部展品。
寻找源头不难,难的是将其辨认出来。我站在一块草场旁,手里拿着帮不上忙的地图。面前有条沟,水不深,水道至多半米宽,水面覆盖着黄绿色浮萍的镂空地毯。岸边蒲草丛生,黄白如干草。绿苔只在水明显从地内涌向表面的地方聚居。我期待着什么?汩汩冒泡的泉源?指示牌?我又看了看地图,寻找那条蓝色的虚线,它在蛋壳青的空地中起始于标绿的林区下方。很可能,真正的源头要在上方找,在那几栋房子背后铺展开的森林里,是房子让这一块斑点成为我能对出租车司机讲出名字的小镇。他当然想知道我来这里做什么,何况是复活节前的周六,可在这个地方,单单好奇不足以诱使任何人开口。此地的人严肃而冷漠——仿佛埋入无名苦恼——与这片土地一样,应付得了沉默寡言。
也许,这条极不起眼的细流真就是我要找的东西:莱克河、古老的希尔达河之源,它向海流去数千米,注入格赖夫斯瓦尔德港,随后宽广地、几乎是壮观地在博登泻湖的浅湾丹麦维克湾入海。我看着左边布满裂隙的斑白木篱桩、两排生锈的铁丝网、后面草地上无数新翻的土堆——那是孜孜不倦的鼹鼠的作品,开始照计划,往西南方向追溯水源。
云层远而宽,沉沉低垂在我头顶。天空在远处亮起来,释放出一抹浅淡的粉红。几棵宽肩的橡树耸立在牧场上,那是早已被开垦的荒野的遗迹。积满雨水和融水的洼地阔大如湖,映照着橡树的枝杈。灰黄枯草如灯芯草般在淡蓝的浅泡中亭亭而立。一只白鹡鸰穿水跃过,屈膝沉下尾羽,又展翅高飞而去。
硬结的、不足三日的三月残雪闪烁着,在草地背阴的角落里,在拖拉机的深车辙中,在裹着白塑料、干草于其内发酵成青贮饲料的圆草捆顶上。翻倒的水槽在岸边生着锈。上方伸展出山楂树的冷枝,树皮上布满硫黄斑。这时响起鹤的鸣叫,凯旋之声高亢如号角。水沟对面,两只铅灰的鸟展开它们过于庞大的翅膀冲入高空,只为不久后降落时把身体屈成弧状——以绝对的协调,两腿伸向地面——三次急促扑翅后停稳站定。好一阵子,它们的鸣叫声仍盘旋不散,直至最终被东风吞没。风从海上怒啸而来,扫落身前夜蛾灰的橡树叶。耕田滑腻。棕黑的黏土块暴露出来,在表土上渐渐变软。油菜籽从垄沟中发出芽,叶缘已被农药的毒染金。色泽晦暗,光恹恹无力,似乎黄昏马上就会降临。
一群狍子在已变为沼泽的凹地背风面吃草。我走近时,它们便闪着亮白的尾根快跑回林后。水洼边缘,一块迷彩布在高高的架子上飘扬。不远处,长满青苔的水泥楼板堆在黑莓、接骨木和黑刺李的无叶树篱前。生锈的金属箍从钢筋孔中伸出,最便宜的钢材,裸露着,任凭日晒雨淋。多孔的大石块密生着藻类般发黑的苔藓。后面,在光秃秃的灌木保护下,黏滑的绿水塘静静躺在冰川时代的洞窟中,那是蟾蜍、青蛙和铃蟾的产卵处,它们正暗中等待繁殖的信号。衰草枯成蜡黄,被冬天脱了色。只有毛茛,菠菜般青翠地刺破黑色的湿土。
我回到水沟,跟着走,直至它消失在地下水泥管中。风车空空的螺旋桨在天边转动,活机器。我想起儿时见过的黑色马头泵,阴森、淡漠,砸入地内的撞击。上个冰川期造就了此地:莱克河谷的低凹,冰碛丘陵缓坡中的冰蚀湖,地块和水塘边那些在沙质沉积物与冰川水中磨圆的巨大漂砾。
西南几百米外,白桦的灰树皮泄露出水之后的流向。我穿过田野,到达现在稍稍宽一点的河床。土埂在耕地和沟渠间狭窄地蜿蜒,宽不及两米。有些地方表层的植物被掀开。泥炭土湿润地闪烁着。是野猪挖的。云雀啁啾,一飞而起,她的歌急促地宣告着似乎遥不可及、甚至难以置信的春天。现在第一次听到水声。它轻笑着流向林地,迷失在榛丛之中。我潜入林内熟悉的静寂。这里,土壤仍负荷着前一年未受咄咄东风侵害的沉黯枯叶。矮林含土发灰,只有回心草绿得像香菜。已准备好绽放明黄花朵的菟葵展叶挺立着。树林开始疏朗时,我发现了一具——在枯枝、云杉松塔和蓝黑色泽的野兽粪便之间——蜕掉的鹿角。深棕的骨结构很重。我摸了摸它有舒适纵梭及珠状凸起的皮质硬面和角叉的光滑末端。曾着冠于额骨骨茬上的环状突起仍粘着兽毛,角一定是刚刚才掉。在应是断裂的位置,能摸到白如石膏、结痂粗糙的骨组织,锋利得就像珊瑚岩。脱角一定很耗力。四周的云杉树伤痕累累。挂于伤口的乳白树脂仿佛凝住的血。饥饿的赤鹿已啃光一些树干的树皮。
一阵风划过树冠,天亮起来,苍白的日轮透过云层闪现了片刻。它没有投下影子,空气却立即蠢蠢欲动,鸟儿更响了:喜鹊机械的沙沙声,苍头燕雀不倦的歌曲,乌鸫的粗糙哨音和知更鸟的忧郁吟唱。
走出森林时,一只乌鸦飞了起来,嘎嘎叫着滑翔在被冬麦缀满绿意的田野上空,又一次次落下,却从不曾间断嘶哑的叫声。景色显现出变化,平静,有序。一条柳丛镶边的笔直土路随沟通向下一处居点。水中飘着烈酒瓶,已不再生产的牌子。小路左侧,黑莓红灰的枝条从枯萎的灌木丛中弯曲着伸出。鸟巢悬挂在光秃秃的树篱。一丛山楂树下有几十个灰白的、砸烂的蜗牛壳,还有石头,乌鸫和画眉曾在上面把柔软的肉凿出铠甲。黏土被拖拉机轮胎撕裂、被雨和融水浸软,在我脚下的每一步塌陷。水坑吸收了环境的色彩。是湿土和浊泥浆的赭红,一种蜡质的、很少反差的单调。只有黄花柳边缘泛着春绿的枝条及其银色的初生柔荑花在料峭空气中微微颤抖。它丝滑的皮毛刚刚才剥去粘荚。
水道在村口牌子前不远处分了叉。我追踪着最不显眼的一条,它深深藏入不情愿的田埂,一条被爆竹柳包围的小溪。从喀斯特矮林中升起的树木像笨重的、倒挂在冲蚀斜坡上的怪物,树冠截断,被寒暑风雨挖空的树枝畸形怪状。发霉的木心从胀破的内部鼓出。
不久后,一道流水路与此路交叉,在地图上它已被冠以所寻之河的名字。它没有弯转,直直地东流而去,脱离了周遭背景,在两块围以篱栅的牧场间形成天然的界限。贫瘠的河岸地面上,倒伏着一束束被雨水压弯的莎草。流水无声地追随绘图板上画出的轨迹,不断为南北分支的新的排水沟供水。开阔的土地冻僵在那里。一切都很远,一切都已被占据,耕田,为仍挤在棚中的牛提供饲料的草地。只有风在呼啸,切断呼吸,暴雨般拦住我的脚步。天边密聚起肌肉似的重云。模糊的远方有车流的轰鸣。
这样过了好一会儿,目光再次被挡住,山茱萸和黑刺李的路堤围起农田,使之免受坚硬的东北风之害。一群灰棕色、乌鸫般大小的鸟儿飞过耕地,一次次聚拢休息,又因最轻微的干扰一哄而散。是田鸫,老式菜谱书中身被灰斑、在地中海地区过冬的鸟儿。很快,黄鹀也飞过耗竭体力的空气,轻擦出染料般的黄。沟渠不知不觉地充满水,水位上升,水道开阔,波面粼粼地流过机械水堰的开放地闸。
最后,当一条路来到近前、横跨过沟渠时,光滑的锡灰色柏油路面已让我感觉陌生。汽车穿梭而过。北边,透过白杨树栅,闪现出水泥灰的马厩、脓绿的青贮房和灰白的裹着玻璃纸的稻草金字塔。农机不知在何处轰轰作响。一片片雪花静悄悄地飘落在泛黄的牧场淤泥上。
我在岸边草丛中找到一枚鸡蛋大小、有棕色麻点的河贝。它内部散发着珠母的光泽。不远处有野鸭在水中觅食,它们比城里的亲戚更易受惊,我一走近,就粗鲁地嘎嘎大叫,扑簌簌飞走,停聚在近旁的休耕地上。它们的脚掌橙光闪烁,鸭头在田地灰色的小径前释放出耀眼的孔雀蓝。在过去几个小时的单色调后,鸟儿绚烂得几乎吊诡。
然后,我为自己的第一段行程选择的终点到了。这个小村庄叫荒凉的埃尔德纳,几乎只有一座翻修过的庄园和一排砖褐色的农工房。除破旧不堪的消防局和几个倒塌的马厩外,所有房屋都似乎住着人:帘子挡住窗,车停在入口,鸡在棚屋的篱笆上匆匆踱步。荒疏笼罩此地。它的名字是空洞的宣告。它指的是位于莱克河河口的西多会修道院,那是格赖夫斯瓦尔德初建时的古老核心,三十年战争后便已沦为废墟。
手机又有了信号。我拨下号码,当出租车在大路尽头出现时,下起了绝决的厚重的大雪片。
三个星期后,世界划分为不再、已在和尚未。四月末。别处均已春意盎然。我从火车上看到青绿斑驳的矮树篱和黑刺李的白花泡沫。可在最东北端的此处,郁积的寒凉仍遏止着萌动。太阳照着,但日光苍白。尚未暖起来。连翘一如既往地最先展示出它的四萼花序,却还不是硫黄火焰。乳白的雾霭笼罩着村庄,在一片茁壮的杨树围篱后,它很快与花园和小棚屋消失在嫩绿的草场中。僵冻已解,土里的冰化了,大地沉静,几乎是羞怯、笃定。爆竹柳和白桦仍然光秃秃地立着,只有一层细腻的绒毛覆盖着树枝的骨骼。刺篱微微泛青。黑刺李的绿漾出淡黄的莲座状基生新叶。去年夏天的干浆果还零星挂在枝上。它们的柔影下蜷着常春藤、立着毛茸茸的嫩荨麻。一株小栗树露出它刚刚从漆光芽苞中绽开的皱叶。汽车和农机在草皮上留下两道沙质的、被碎石固定下来的车辙,它们与田间小路一同沿着沟渠的方向伸展出去。麻雀在山茱萸和黑刺李的树篱中竖起羽毛。乌鸫高声抱怨,黑顶林莺笛声悠扬,苍头燕雀鸣唱着永远相同的诗段。不知何时起,篱笆全都不见了。缠着烂叶的断芦苇露出水面,而那浅浅的水,几乎是清澈地躺在基底锈棕的河床里。一层层伏在岸边淡绿草丛上的芦苇则泛着稻草般的微光,秋风曾吹倒它们,在干燥而松脆的时候。
柔软的卷云遮住高空,被渐渐衰败的飞机尾迹打乱。灰绿的森林界定了东边的天际。南边,大地在星罗棋布的居民点、一棵棵树木和浅水泡之间散裂开来。北边,浮尘随着一台耕作的拖拉机飞扬。泛蓝的庄稼在近旁的农田里发着芽。粪肥味充斥着空气。
田埂上,白屈菜、蒲公英和蜡质心形叶的驴蹄草盛开着铬黄的花。棕褐色的荨麻蛱蝶在前面翩翩飞舞。一只大黄蜂嗡嗡嗡地寻找着食物。野芝麻的骄傲茎秆向上伸展。紫花的唇瓣高耸在雄蕊花柱的上方。
在左侧几乎觉察不到的小山上,一片小森林躲在因寒暑淬炼而刚硬的松树和布满青苔的漂砾壁垒后。一排排顶端有尖头、羊肚菌似的棕色孢子囊穗在前方钻出地面。那是幼年的木贼,是早已逝去的地质时代的残迹,是所有农民的敌人。路当中,小小的龙胆草怒放出淡紫的华丽。更远处,清澈的高空中盘旋着几只鸢,它们升降、旋转,在侦察飞行时恣肆地俯仰悠荡。金灰色的光渲染着风景。大地似乎在缓慢轻柔地呼吸。水的反射面下,多臂的眼子菜在无声的水流里摇曳。一只尾扇蓝灰的苍鹭猛地从湿处窜入空中。水在它的翅膀下泛起涟漪,它绕着大圈缓缓升高,缩回扁头,飞向大海。继而又归于星期日的宁静。小径随沟蜿蜒,在看不见的起落里从容流淌。水终于积聚到泵站的进口池中。降下的木闸前,不祥的绿汤纹丝不动,静卧在芦苇和浮萍半腐的清漆之下。标牌提示禁止洗澡或入内。如今清澈的水沟已宽阔如河,窄铁桥通向另一侧,在彼岸的阔野和点缀着鹅黄的山坡后,大片森林继续铺展而去。
绿油油的草里坐着一只大蟾蜍。它右手小小的拇指放在一根草茎上。半闭的沉重眼睑下,铜红色的眼睛盯着模糊的前方,只有皱巴巴的、玛瑙棕的身体在有节奏地搏动。它全身布满疣和沙粒。
人们似乎从虚无中乍现。一个男孩开着四轮车飞驰过空地。一条西班牙猎狗跟在他后面狂吠。大人牵着小孩子走过此地,没打招呼就消失在河堤后。我停下来,尝试在地图上定位这纷乱的景致。空气清爽,有一刻我甚至以为尝到春天的滋味。地图不知岸边小径,也没有森林的入口。所有标记出来的路,都从森林内部才开始。
我想随水进入柳丛,可沟渠转了个弯,后面出现了发酵的湿黑沼泽。浸透的泥土啪嗒啪嗒地抗拒着每一步。地面越来越软,我越来越深地陷入泥泞的裸土。无底的黑水洞从低地深处闪出微光。我看出,这里走不下去,只能回头。于是我笨拙地穿过斑驳浅绿的河边林,用手臂推弯拦路的新枝,往南走了好长一段路,藏在树叶下的地面才硬实起来。在褪色的枯叶地毯下,缺少光照的银莲花从凉凉的林土中涌出一团团白。啄木鸟敲着树梢。柔和的光落在榛窠、幼山毛榉和单薄桦树的瘦枝上。此时地面因铺满鳞状松塔和枯黄针叶而有了弹性,高大的云杉很快让它暗下来,直到它在橡树和山毛榉的树冠下再次明亮。
到处都有动物的踪迹,被野猪拱起的发红、松散的腐殖土,树根下狐狸或獾子窝的黑色入口,齿小蠹虫幼虫在裸露树墩上画下的象形文字,最后还有红腹灰雀的清脆声音。对它欢快的单音节啼叫,我几次作答。后来,当我在一个小丘柔软的草地上躺入松树斑斑点点的半荫时,那只鸟儿冒险走出它的掩护,坐到我正头顶的树枝上。它胸脯的朱红色明亮耀眼。我又开始回应它,几个回合后,它突然唱起一支婉转的、我没听过、也模仿不了的五节曲子。
我闭上眼。缠结的树枝又一次映在亮着红光的眼睑上。远处传来猛禽刺耳的尖叫。
再上路时,太阳高挂天顶,它毫无遮蔽的光让我在多尘的林中空地上恍惚间感到夏日微微颤鸣、有着灼沙味道的炎热和海的呼啸。红腹灰雀有节奏的循环歌声时不时再次响起。我漫行穿过新老树木并存的禁伐林区。模糊的沙地上盘旋着鸢鸟幽灵般的影子,开裂的、迸出新叶的鹅耳枥叶鞘闪闪发亮,散发着蜂蜜的香甜。
当我回到开阔的天空下,前方仅仅几米处,一只野兔从它藏身的黑麦苗中弹出,在农场路上绕了个弯,消失在耕田里。东边,一群老鸦嘶哑干咳着,飞过低垂的电线。一只鹳展开大翅膀,擦过它们,滑翔入巢,高过附近居点所有房子的山墙。另一条水沟在森林边缘的阴影中干涸了,它的两侧镶着干草沉积的灰白条带。一定是漫溢的水把它们冲上了岸,还有肉质指状叶的沼泽鸢尾和大量灰紫的软体动物,就像化石,搁浅在干燥淤泥上。
莱克河沟本身北流而去。我想抄近路,就从电篱笆下面钻进去,取直线横穿牧场。可湿土很快就挡住了脚步,不论踩到哪,地面都会下陷。再往北,莱克河终于汇入水量丰沛的莱茵河。在微微拱起的堤坝保障下,向一个村庄流去。远远地就能看见一栋板楼。我最终抵达岸边时,天上悄悄地出现第一只海鸥,黑头,即将繁殖。空气瞬间有了咸味。村道经过一座横桥。一声警笛的尖叫。郁郁葱葱的地平线上,深蓝天空染了雾蒙蒙的白。
三个星期后,当我跨过同一座桥时,沟岸已长出及膝高的草。天空铅灰。鼓腹的厚云让此地一片阴沉。只有我身后,天际西边的裂缝中,挤出一抹象牙白的光。
我沿着参差不齐的枯苇丛,随水向东。一匹哈福林格母马带着她的小马驹在浓绿的牧场上吃草。莺鸟啁啾,在披挂新叶的矮篱中,在一浪浪高高的荨麻后。电锯的啸声从一个农庄传来。它起起落落的尖叫伴我在透着黄花茅一缕缕紫灰的小堤上走了很久,与南岸绿染的白柳丛中布谷鸟脆铃似的啼声错落相和。当我应答它充满回声的鸣叫,它竟像怒猫一样嘶嘶呵气,为寻找对手从一棵树飞上另一棵。在它头上,更高的高空,三只苍鹭曲起一动不动的翅膀,在重力作用下滑向浅湾。几片水鳖叶零落在起皱的水面上,白腹毛脚燕忙不迭地躲避着它们。羽扇豆雍容地托起淡蓝的烛状花序。蓍草蕨叶状的小嫩芽以及开着蓝紫小花的草本婆婆纳,反倒弱不禁风地纤细。纤维质的宽叶车前草之间腐烂着一条鲈鱼的后半身,蓝鳞闪烁,一定是鱼鹰剩的。高高窜起的碎米荠为褥草草场画出桦白色的虚线。焦糖胸脯的草原石䳭唧唧喳喳地在草茎间飞来飞去。苇莺高亢的叫声穿透颤抖的芦苇,不久后,附近林中便传来黄鹂响亮的笛声。
我徒劳地尝试找它。反倒在东边远处发现了一只黑白相间的动物,它从水中升起,展开硬板似的翅膀。单因纯然庞大就显得古怪,几乎超自然的。我停下,伸手拿望远镜。鱼鹰?不,甚至可能是白尾海鸥,现在它降入田野深处,以瞭望姿态准备着下一程追猎。离它不远处,长满毛茛花的草地后面,闪耀着油菜的信号黄。再后面,又升起风力机灰色的螺旋桨。除了一个全都静止着。再往东,喷水车正灌溉大麦田。
因为发生在另一岸,一切都显得那么远,人群也是,尽管我们只被一条沟隔开。他们叉着手臂,站在大水箱的拖拉机旁。一条圣伯纳狗在他们腿边蹭来蹭去,嗅着垂下来的红色软管,向蓝白漆的水泵跑去,回头大叫起来。他们在取水?还是把什么东西导入莱克河?数十年来,新挖的排水沟一直在抽走沼泽的地下水,以便把湿草地变成农田。果然,我很快就看到一条支沟,它在相邻森林多刺的灌木边缘中失去踪迹。矮林中郁积的黑泥汩汩冒泡。弱光穿过树冠。现在彻底安静了,再也听不到鸟儿。但只过一会儿就又亮了,因为人们为高压线在林中开出了通道。数米高的虎杖密集丛生,它们长着巨大的椭圆形叶子和左右摇摆、竹子似的茎秆。我继续走,沿第一条支沟走到外面。
树林边缘,无数嗡嗡嘤嘤的山楂花滚起浓密的泡沫,——草地被盛开的三叶草泼白,当中立着药用白前和紫色盔状花序的红门兰,它宽阔的叶片上布满红棕色的斑点。在岸边树篱和远处斜堤之间,格赖夫斯瓦尔德大教堂现身片刻,它正前方,是圣雅各比塔砖红色的棱锥。
沿沟有一条几乎看不出的小路。现在两侧都围起堤坝。轻盈光亮的桦树在枯草栅后踮起脚,新鲜的叶子闪耀着,像小小的三角旗。芦苇在它前方摆荡着流苏。黄鹀重复着它们单调的歌,一只苍头燕雀猛地冲了出来。对岸很快出现另一个较小的泵站。立面上涂鸦刺眼。一个钓鱼的女人从房前抛出鱼竿。她身边趴着两条棕色的大狗。此后不久,一只铜色的大鼹鼠丘从燥土中耸出,正好挡住我的路。它看起来就像牛的股骨。耳柳丛中花穗直立,鹅黄郁积。长满断木和苇草的莱克河已经看不见了。芦苇沙沙作响。蓝豆娘在枝间嗡嗡地飞,或坐在早熟禾的茎秆上,虹彩色的后腹部卷如马蹄铁。
现在能听到一种无法定义的噪音,没有回声的金属敲击急促地重复着。然后,一个斜坡后面,刚割好的草坪上展开高尔夫球场,人造山紧贴迂回旁道,一直伸向路堤。人们带着浅色鸭舌帽在空中击球。而我旁边的茂密树篱中,一只歌鸲开始了啼叫,比夜莺还响,但同样精湛。
刚刚还树篱茂盛,脚下就铺开蜂斗菜的地毯。蜗牛把它大黄般大小的叶子蚕食得千疮百孔。一条小径穿过车桥下生长的沼泽柳树,然后重新通到人行桥上。我紧靠栏杆,凝望着平静、褐色、约三到四米宽的流水,从此处,在城市的边界,它才开始真正叫“莱克”这个名字。萍蓬草叶漂在河边。
天空一下子晴朗起来,太阳晒着我的脖子。我走上南岸的小堤坝坝顶的沙路。开着黄花的草地后开始了市政公墓的坟场。对岸排着一座座独栋住宅。地图对这个居住区一无所知。一定是不久前才建的。在一棵被虎杖团团围住的山楂树桠杈间,闪烁着一块锈红色的斑点。那是金翅雀,它身旁一掌处,是更大、颜色更暗的雌鸟。可还不等我仔细观察,两只垂直飞起的鸟儿就消失了。不久后,莱克河再次藏入芦苇,只有远处蓝色的铁路桥才暴露出它的流向。
我的路继续引我向南,经过刺铁网围起的灭火池和开粉花的苹果树。一棵柳树的树干上长有大量赭黄的黏菌。看起来就像建筑泡沫。高大的杨树夹着布满裂隙的柏油路通入城中。马在围场中吃草,不久,在一条小溪后,公寓楼区拔地而起。花园里有塑料滑梯和蹦床。路的另一侧,一座大仓库在多孔的铁丝网后破败着。很快,我到达了有狭窄的粉彩老房子的格里姆街,走过农庄,经过超市的停车场。在一个石匠铺着地砖的前院里,两条罗威纳狗在高高的篱笆后威胁地打着呼噜。它们口中衔着橡胶咬环。唾液从唇上滴下。莱克河远了。直到我拐进动物园绿化带的矮墙,才再次在废弃的铁轨后看到它系着芦苇带的河床。我沿着铺设的小径散步下去,经过我出生的旧诊所大楼。河水在施特拉尔松公路桥的后加宽,流入一个约七八十米宽、数百米长的梯形盆地,——格赖夫斯瓦尔德港。加固的北岸停着两艘餐厅船,南岸是一些桅杆高耸的帆船。板楼从后面投下长长的影子。
我在南岸坐下。对面是一排排低矮的建筑和木棚、造船厂和划船俱乐部,年少时我曾在那里训练过一个春天。盐矿一定位于后方某处,在莱克河与巴贝罗湖之间的罗森谷里,矿和河,就是此地垦林、在沼泽地上建立集镇的原因。微咸的水里飘着一条死去的鳊鱼。雨燕在波浪起伏的水上来回穿梭,鸣声尖利。三只家燕停在帆船的舷栏上。狐狸红的喉部在夕阳中闪闪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