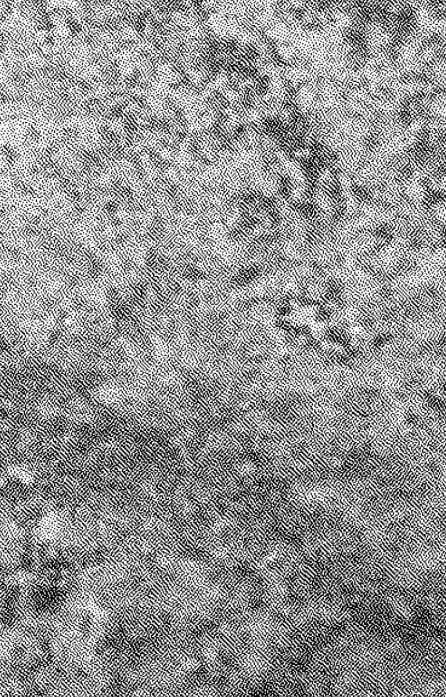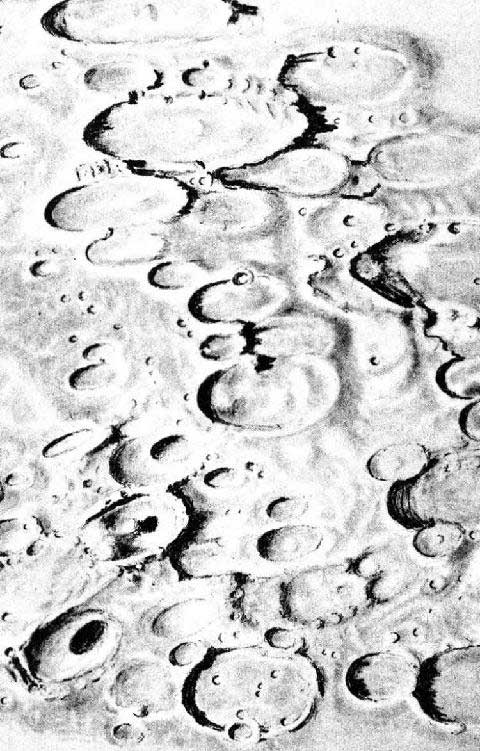| 逝物录 | 收藏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共和国宫
逝物录 作者:尤迪特·沙朗斯基
* 这座在海因茨·格拉冯德尔的领导下、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筑学院集体设计的代表性建筑,被修造在所谓的“马克思-恩格斯广场”上,所在地为炸毁于1950年的柏林城市宫旧址。在32个月的修造期后,1976年4月23日,共和国宫作为“人民大楼”落成。
拉长的五层平顶建筑以其反射铜镜饰面、白色大理石镶边的立面为最显著特征。大楼内部有一个可容纳近800人的人民议会会议大厅与一个上限至5000人的活动大厅,除此之外,还设有多个会议室及工作室、十三间餐厅、八个保龄球馆、一个剧院和一个迪斯科舞厅。
它是党和国家领导的社会中心,德国统一社会党党代会所在地,人民议会驻地,重要的国内、国际会议会场以及文化、休闲中心。最受欢迎的聚会场所是“玻璃花”,它是40米宽、80米长的双层前厅。其中悬挂着由著名爱国艺术家创作、以“共产党可以梦想吗?”为题的16幅巨画。
† 为使建筑能承受柏林冰蚀谷的地下水压力,人们浇筑了一个长180米、宽86米、深11米的混凝土凹槽当作地基。围绕八个混凝土芯,诞生了包裹着石棉水泥的钢梁骨架结构。石棉的使用得到特殊豁免条例的批准,虽然这种建筑方法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自1969年起已被禁止。
1990年8月23日,人民议会在宫内决议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一个月后,9月19日,同一组议会成员决定,鉴于石棉污染,立刻关闭此宫。1992年,德国联邦议院要求拆除该建筑。1998年至2003年间,专业公司处理了大约5000吨建筑用石棉,此后才有可能拆除并改造建筑。清除致癌物质后,共和国宫处于无装潢状态。
自1991年起,该地点被称作“宫殿广场”。经过几轮关于此地未来的建筑竞赛,联邦议院于2003年决定拆除宫殿。2004年春到2005年底,被毁宫殿再次对公众开放,以举办临时的文化活动。
建筑的最终拆除被数次推迟——各方的强烈抗议亦是原因之一。2006年6月,建筑终于被夷为平地。基本结构所用的瑞典钢材被融化,出售给迪拜建造哈利法塔以及在汽车工业中继续用于发动机制造。重建历史上的柏林城市宫的工程,于2013年启动。
她从购物网兜里取出一捆芦笋,打开包着的布,把茎秆放在餐桌上。然后去冰箱边,从放在阴凉角落的纸盒里捧出土豆,两手满满。有些已经发绿了,几个甚至长出来胖胖的短芽。箱子显然不够暗。当然最好是放在地下室,可那样就总会有一点煤味。她拿来一条灰色的擦碗布盖在盒子上,就像是块桌布。
洗衣机在第二次漂洗衣物。幸运的话,今天还能干,因为中午出了太阳。阴了一上午,好像随时都会开始下雨。
她削土豆,发青和长芽的地方挖得深一点,把它们洗净、切半、放在炉子旁的碗里。她想尽可能把一切都准备好。午饭她只抹了点黄油面包,虽然是周日,可她从来不喜欢给自己一个人做饭。不值得。
刚开始清洗芦笋上的沙,门铃就响了。她迅速抓起手巾,走进过道,打开门。
“嗨,马琳娜,能打扰一下吗?”
是利珀。他住在她斜下一楼。
“当然啦。快进。我还得去下厨房。”
利珀看起来有点疲惫。他是个和善、不拘小节的家伙。有些晚上,他们所有人还会坐在一起,喝上一杯,虽然最近很少了。
“霍尔格不在,是吧?”
他迅速看了一眼客厅。
她摇摇头。利珀和霍尔格一样,学的是军医,可他的重点是口腔科。
他还站在进门处。
“哎呀利珀,你干脆就穿着鞋吧。”
“那怎么行,别。”
他耸耸肩膀。
“小家伙睡了?”他朝卧室方向动了动脑袋。他看起来真是好累。也许和卡门有关?
“是呀,又沉又死。可累坏了。空气好。和她转了个大圈。”
一吃过午饭,她就拉上窗帘,把小家伙放在了栏杆床里。开始孩子还嘟哝着什么,可很快就安静下来。其实她还想备课。上午全忘了。
“唔。”他把手插到裤袋里。“尤勒也睡了。周日这么休息,也值了。”
她把芦笋一根根放在干的洗碗布上。
“喏,还为芦笋排队?”他把手从口袋里掏出来,抱着双臂,咧开嘴笑了。
她只能笑。她不是唯一一个从小花园后面的地里偷笋的。绿芦笋。商店里她还从来没遇见过。传言说,直接去柏林了,送到共和国宫里。
“是呀,希望没人告发。”她在手巾上擦干手,解下围裙。
“喝什么?”
他还光着脚站在门口。利珀比霍尔格矮一点。他留着浓密的深色胡须,发际线后退了。他皮肤发白,几乎是苍白。
“别,别。别费劲。”他摆摆手。“我想马上下楼去花园。”
利珀特和她,还有这栋的其他几户,都在新楼后面分到一块种菜的田。他们得用锹铲去草皮、抖干净,才能露出一层薄薄的表土,然后种上土豆,以防止杂草长出来。为了收成好一点,利珀甚至在农产品合作社搞到粪肥、搭起暖房。作物在他们这里其实是稀稀拉拉的。但什么都让她高兴。豌豆、小红萝卜、胡萝卜、豆角、香菜。甚至还有草莓。一小碗,但毕竟有。
“来,咱们进客厅去。”
他让她穿过过道,她关上卧室门,走在前面。
门左边自制的架子上摆着鱼缸,现在太阳把一束光打了上去。是霍尔格的鱼缸。古比鱼,黑摩丽,霓虹灯,和唯一一条鲶鱼,大部分时间它都钻在洞里。最初他们只有一层,但霍尔格总是削新木头、锯板子,然后就有了上面稍小的第二层,最后甚至有了紧顶上更小的第三层。像个金字塔。鱼缸前安了栏杆。
利珀坐在沙发上。他的格子衬衫有点绷在肚子上。袖子卷了起来。小臂上一层深色的毛。
“马琳娜,我们……”
他深吸一口气。
然后移上前,把手叠放在大腿上。
“我们想了很久,是不是应该和你说。”
他一个人坐在她面前,却说“我们”,奇了怪。
他犹豫着。
“就是……”他重新开始,“我们就在柏林,昨天,你知道吧。卡门有一场报告,我和尤勒也一起去了。很好的一次外出,但也不太一样。”他的右手在空气里比划着。
“嗯,是。”她全忘了。
“然后,我们想享受一下。”
他看向窗子。逆光里的仙人掌看起来脏脏的。得浇一次水了。
“所以我们在共和国宫,特殊一点,你知道的。”
他光着脚,踩在她的地毯上,脚趾毛茸茸的,不怎么体面。她看着茶几雕刻精致的桌腿。霍尔格前段时间在邻村的一个破房子里发现了它。一件发霉的旧家具。能清楚地看到虫洞。那些洞永远都变不了。他们一起,穿过林子的沙路,用自行车把它运了回来。
“就是,马琳娜……”他又开始说,挺直了背。
“我们在那看到了霍尔格。和另一个女人。”
现在他看着她。
“在那种明确的状态。”他稍稍抬起下巴,手摸摸脸,又缩回去一点。
“我们只想让你知道。”听起来就像道歉。
“卡门一开始认为,这和我们没关系。”他的舌头蹭着牙齿。
“可是今天早上,我对她说:如果马琳娜在什么地方看到我和其他女人在一起,但什么都没说,你会怎么想?”
一种明确的状态?一种明确的状态。可怜的利珀。多好的人。比卡门好多了,她那扎得紧紧的辫子和嘴巴左上方的美人痣,就像画上去似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翘了翘右脚。“也许你想和卡门谈谈?女人之间那种?”
卡门是药剂师。从没和她热络起来。
“另外,我认为,他没注意到我们。”他又说。
桌子是绿的。她亲自刷的。她觉得说不出的好看。
“谢谢。”她说。她也不知道为什么。
利珀站起来。“那我走了。”他在裤腿上擦了擦手。
她听到,他在过道里匆匆趿拉上鞋,关上房门,下了楼。灰尘在光里跳舞。其实桌子根本没法看。
他转过身,从后座上拿起手提包,放在腿上,打开拉链。在他的衣物之间有一个灌了水的球,给孩子的礼物。他把它拿在手里。
“好看”,阿希姆说。“她会高兴的。”
绿莹莹的水晃来晃去。小鸭子笑着。霍尔格把球塞回包里,掏出面包。
“你吃不?”
他拆开油纸。
阿希姆稍稍转向他,摇摇头。
“不要,算了。”他又看向车道。路上没什么。
“我可不想用它搞坏我美好的饥饿。”
霍尔格咬了一口。茶肠。面包吃起来老了。昨天早上涂的黄油,马琳娜和孩子还在睡。怕吵醒她们,他到外面楼梯间才穿鞋,像往常一样一步两个台阶,走了一千米到公路上。已经过去了好久。他把面包放回去,又包在纸里。
“想吃好的,对吧?”
阿希姆打了方向灯,踩一脚油门,超过一辆世文自行车。
霍尔格蹭了蹭膝盖。现在他才意识到,自己有多累。他脑袋里嗡嗡作响。他很少喝酒。根本受不了早起和锻炼。他还穿着运动短裤呢。阿希姆催着要准时出发。他可能等不及回去见老婆了。颁奖之后,连好好和布里吉特道别的时间都没有。老实说,对于他这倒是蛮好的。
“能靠下边不,我得上厕所。”
他不喜欢告别。永远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过去了总是很高兴。
“天啊,你的膀胱就跟个姑娘似的。”
阿希姆不错,壮得像熊。不是最快,但投垒球总是超过其他所有人。站姿,一个仿佛慢镜头下的动作。他命中率在50%以上。
阿希姆看了看后镜,让一辆车超过去,挂低档,打方向灯,往没铺柏油的小路里开了一段。然后停了发动机,把手从方向盘上拿下来,转过来对着他。
“好啦。快去。”
霍尔格下了车,站到一丛灌木旁。一股尿对准荨麻。绿树篱蔓生着虎杖。刺树篱中挂着没熟的黑莓。高压线在田埂后穿过野地,径直进入一座孤零零的砖砌农庄,厚木板搭的仓库边立着没有旗帜的旗杆。庄稼还绿着,在风中摇晃。一切看上去都那么安宁。可联合收割机迟早会来。他感觉到晒着脖子的太阳。
他不由地想到,中学一毕业就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他多么开心。那种从今往后什么都不会搞砸的感觉。还有荣誉板上他的名字。用哥特字母写的,就像在证书上。他的记录还没被打破呢。
现在呢?几只蚊子绕着他飞。他赶走了。如果没有意外,三年后他就会成医生。很靠谱。
尿啊,哥们。
布里吉特当然反复地问,什么时候再见。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忍不住打起哈欠。然后提起裤腰,走回车上。
阿希姆启动发动机,又上了路。霍尔格从后座拿过来训练夹克,塞到靠椅和窗框间,把脑袋靠了上去。他观察着阿希姆。他的额头上有几颗汗珠。阿希姆总是准确知道他想要什么。但话不多。
霍尔格转向窗。从车上看一切都不太一样。这一段他只坐火车走过。
他们开过一个小镇子,街上铺着粗石。他观察着外面的人。一个戴围裙的老太太在她的花园里,手插在两边。一对年轻的夫妇在村道上推着婴儿车。两个骑自行车的男孩,松开手,在人行路上拐来拐去。
然后他闭上眼睛。车子震动起来。他试图放松。他去过宫里,和他的父母一起。新兵宣誓后不久。甚至穿着制服。但他已经记不太清了。虽然所有人都谈论过。说那些旗子、镜面玻璃、大理石、长长的队。
他不知道,是他还是布里吉特有了这个主意。反正就这样了。他们也没排队。甚至在酒馆拿到了位子,能看到施普雷河。一个周六的晚上。一切都很轻松。他给她摆正椅子,她坐上去,好像没什么大不了。他们穿得都不太合适,但他们也都无所谓。布里吉特觉得要庆祝一下。虽然他们根本没赢。在他认识的女孩里,只有她剃腋毛。
他睁开眼睛,看着压碎在挡风玻璃上的昆虫。障碍跑其实最糟糕。结束这一项,难的就过了。水沟和地形跑简直就是散步。
他坐直,摇下窗,把手肘直到外面,开车时的风很舒服。
田野和森林在外面滑过,电话线杆,巨大的废弃机车库,一条没完没了的林荫大道。他可是医生。至少半个。
他把手臂交叉在脑后。
小孩站在儿童床里,睁大了眼睛。一只手胖胖的手指抓着栏杆,另一只手越过护栏,朝她的方向比划。小牙齿从大笑的嘴巴里闪着白光。
她把小家伙抱起来,放在双人床边的五斗柜上,先给她脱下连脚裤,然后尿布裤,最后是湿透的尿布。
孩子咿咿呀呀,小拳头在空气里打来打去,光着的小脚丫不停踢她的手臂和乳房。填了棉花的衬垫上印满黄色的泰迪熊:一个举着气球的,一个摇着雨伞,另一个骑在小马上。换着花样。
她抱起小家伙,放在尿罐上,去厨房,把水壶搁上灶。然后打开壁柜,取出咖啡罐,往杯子里加了勺粉末。
再回到卧室时,孩子正嚼着被子的一个角,它从婚床上滑了下来。她小心地从孩子嘴里拉出来浸透了口水的布片,把钩织的小蘑菇塞到她手中,把被子推回床上去,抻几下弄平。然后她又把小家伙举到衬垫上,用湿毛巾擦了擦她的屁屁。
她正要把折成三角形的尿布塞到小胖腿之间,水壶开始在厨房里尖叫起来。蘑菇掉到地上。她三下五除二地绑好尿布,提上尿布裤,抱起小孩,跑进厨房。
她关掉煤气,把开水浇到咖啡粉上。孩子抓住她的衬衫,头顶住她的脖子。她能感觉到胸口上攥紧的小拳头。她把孩子抱到客厅的婴儿围栏里,试着松开她的手。
“好啦,”她说,“好啦。”然后抽出身来。
接着她回到卧室,端着尿罐进了卫生间,倒进马桶,冲干净,把马桶圈放下来,坐上去。
窗斜开着。外面,一只球被孩子们踢来踢去。他们的叫嚷充斥着新楼区。她站起来,把窗帘拉到一边,看出去。一个小男孩脑袋朝下、在攀爬架上晃悠。头发一根根挂在空中。一个她还没见过的金发、戴眼镜的女孩,自己坐在跷跷板上。她紧抓着把手,站起来,板子翘起,她就坐下去,撞到从沙子里露出来一截的汽车轮胎。她又立刻再站起来,翘着脚尖,再让自己坐下去,一遍又一遍。她迅速拉上窗帘。衣服一定早就洗好了。
她打开滚筒,拽出湿涝涝的东西,塞进浴缸上面的甩干机。右手压住盖子,左手推下控制杆。甩干机动起来。几波水涌进浴缸,起先很多,然后变少,一股细细的水流慢慢地枯了。最后只是滴水,她关上发动机。
橡胶圈又滑了下来。她把它按回去,打开盖子,开始把衣服一件件取出甩干机、挂在斜拉过浴室的绳子上。主要是尿布、内衣和手巾。这辈子都不可能第二天就干。就在上周,她还得每天早上撤床单,因为霍尔格尿床。难以置信。
她合上甩干机的盖子。
她正想把尿罐送回卧室,目光却落到奖牌上,它们挂在过道的椭圆镜子边。田径、十项赛、军事全能。悬在彩色饰带上晃荡的金属。她还这么年轻呢。她这么年轻。
她一把扯下他的奖牌。它们叮叮当当地落到地上。镜子晃了晃,但还挂在那。
她把尿罐放在栏杆床前面,斜开了窗,回到过道,从厨房取出咖啡。把杯子端进客厅,放在绿桌子上,倒在沙发里。
孩子叉腿坐在围栏里大哭。她的脸憋红了。一条口水挂在嘴边。在一个打着黄光的鱼缸里,一群蓝幽幽的霓虹灯鱼嬉戏追赶。小气泡升起来。古比鱼消失了。泵平稳地嗡嗡响着。黑白理石纹的鲶鱼用它的大吸盘嘴啜着玻璃壁上的水藻。它白边的眼睛看起来就像死了。卧室门砰地一声关了。
她的目光,从玫瑰枝花纹的毯子滑向赭黄的炉子,经过装着壁柜的墙,墙上有电视和地图、有两卷本的词典和画册,是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再看向虎尾兰、窗台上的仙人掌和抱枕套,上面的花卉图案是她怀孕时绣的。沙发上方挂着两幅带框的小画,画着帆船,是印刷品。桌子上摆着果盘,霍格尔做的。
咖啡还在杯子里。她一口都没动。
她站起来,走向婴儿围栏。
红灯很远就闪过来。那是莫科夫山电视塔的路口。然后他们开进林子,他太熟悉不过。一下子天就凉了。霍尔格摇起窗。阿希姆打开方向灯,在公路屋前面的公交站右侧停下。
“喏,明天见吧。”
他手指抚过方向盘。它套着闪银光的绒布。
“谢啦,阿希姆。”
霍尔格抓起他的包,打开门,下车,推上副驾门。
深蓝的拉达车打着闪光,拐回公路上。霍尔格在后面看着。他想记住车牌上的字母和数字,但没成功。汽车最后画了条弧,消失在林中。
他转过身,走上窄窄的柏油人行道。进居民区的路,只在中间有一盏路灯。已经开了,虽然天才刚刚发暗。路堤的小石子在灯光下微微闪烁着。
还没到居民区的入口牌,就开始了一系列独户及双户房。房前小花园里盛开着玫瑰和飞燕草。在如今被用作车库的马厩入口上方,有一套旧马具挂在生锈的铁上。环路后污迹斑斑的车站附近,几个半大少年像平时一样,吸着烟,骑车闲逛。两个抬头看了一眼,对他几乎察觉不到地点点头,又缩起脑袋。至少还和他打过招呼,虽然他住在军队楼。他换到路对面。能听到小溪在树篱后轻轻流淌。河水总能提供方向。很靠谱。需求明确,一切就简单多了。
他过了桥,走上坡。拐进教堂后面的路。供销社前停着一辆黑色女自行车,套了网织的辐条护罩。居然还没关门。后面浮现出学校楼房的轮廓。社区办公楼刷了黄色,左窗里有块窗帘被拉到旁边。现在也能看到三个新楼区,都装修过。几扇窗通亮。柏油路在这里结束,沙路开始了。突然就凉了。他站住,取下肩上的训练夹克穿好。
游戏场器具之间躺着一个脏兮兮的瘪排球。攀爬架下面几条梁已经掉色,虽然还很新,不到两年。他抬头看向家。厨房亮着灯。浴室黑着。他在等么?他也不知道。
他打开门,爬上二楼,一个一个台阶地走。利珀家开着电视。他的脚步发出了回声。施雷特门前有炖豌豆的味。
他去院子穿的鞋放在脚垫边。粘着土,落了层薄薄的灰。脚垫斜了。他把它踢正。门牌上有他的名字,她的名字,刻在黄铜里。他真是累了。
虽然他知道,钥匙塞在提包前面的格子里,还是按了门铃。能听见家里关冰箱门的声音。过了好久,她才开门。
她已经穿了睡衣。他拥抱她,她随他,然后转头走了。他任她离开,把包放到衣柜下,蹲下脱鞋。
“小家伙睡了?”
他抬起头看着她。
马琳娜快速点点头,消失在厨房里。黑漆漆的,只有厨房桌上的台灯把圆形的亮光打在桌布上。
他趿着居家鞋,打开卧室门。孩子安然躺在床里,两个胳膊伸在脑袋边。她的呼吸慢而稳。他把食指放到她半张开的小手里。她看上去多么满足,不可思议。然后他拉了拉被子,离开房间,轻轻关上门。提包还在衣柜下。他拿了起来。
取出那包面包的时候,他碰到那只有小鸭子的球。把它拿进厨房。
马琳娜坐在厨房桌边,仰着头。
“我们没赢,但我给小家伙带了礼物。”他把球放在她眼前的桌上。然后去冰箱,打开门,看了一下,又关上。水池边是削好的土豆和绿芦笋。他很想沏一杯甘菊茶,但不敢用水壶。
他走到桌边,拉出椅子,坐下,碰碰她的手臂,却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就缩回了手。
现在她才看他。他耸耸肩,深呼吸。她的眼睛,几乎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