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上 | 收藏 |
四月八日 于阿盖
水上 作者:莫泊桑
“好天气,先生。”
我立刻起床,走上甲板。时间是清晨三点钟;海上波平浪静,辽阔无边的天空好像一个巨大无比、撒满了火种的阴暗屋顶。一阵微风从岸上吹来。
趁热喝了咖啡之后,我们一分钟也不耽搁,赶快趁着顺风开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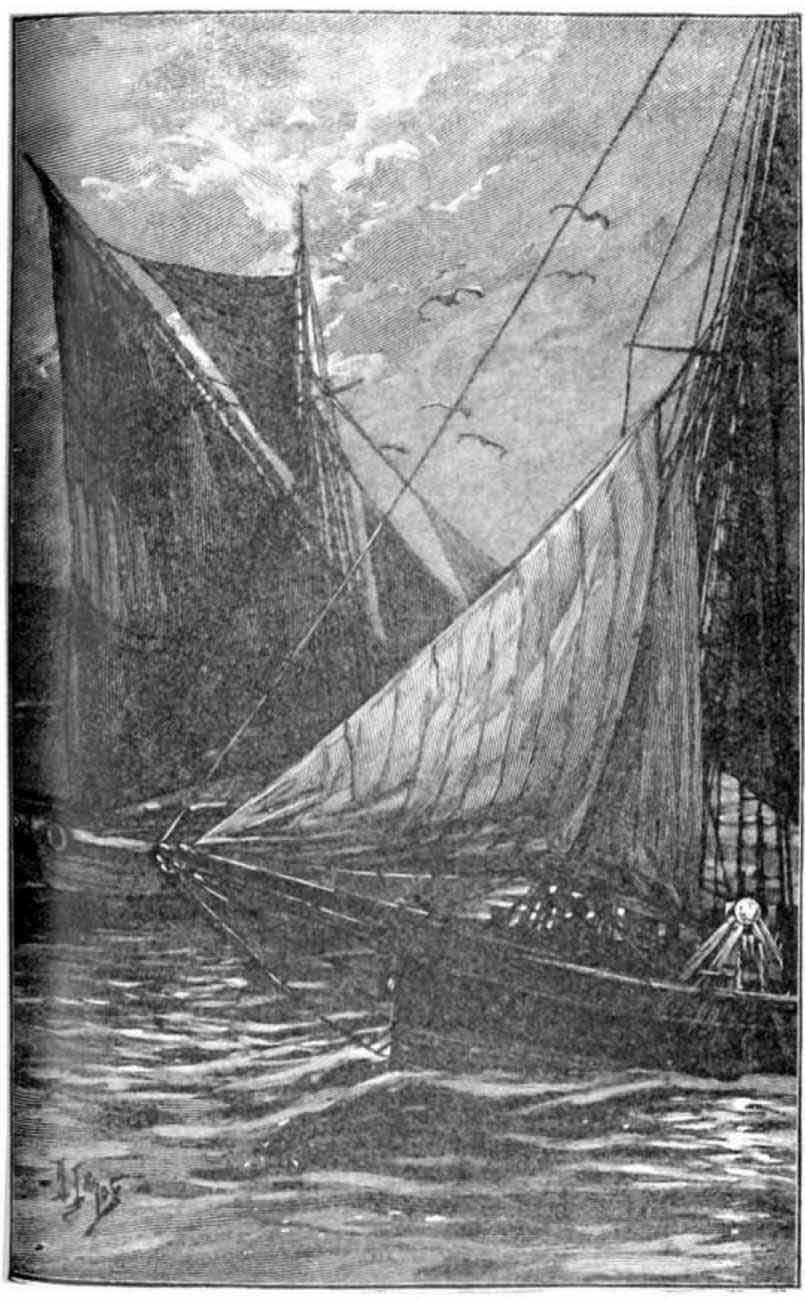
我们在水上滑行,驶向汪洋大海。海岸慢慢看不见了;在我们周围,只有一片黑暗。沉没在这空空洞洞的深夜里,在这万籁无声的寂静中,在这远离一切的海洋上,既能使人感到心烦意乱,也能使人尝到心醉神迷的滋味。我们仿佛离开了世界,永远不会到达任何地方,不会再看见海岸,不会再看见白天。在我脚下,一盏小提灯照亮了指示航路的罗盘。不管起什么风,我们在日出之前,至少也要在海上行驶三海里,才能安全绕过褐色海岬和德拉蒙山。我叫他们点着了方位灯,左舷红灯,右舷绿灯,以免撞船出事。我如醉如痴地欣赏着这销声匿迹、逍遥自在的离世远游。
忽然,我们听见前面一声喊叫。我吓了一跳,因为喊声离我们很近;而我什么也看不见,只见面前一堵黑暗的厚墙。我们的船头刚刚冲破了一点黑暗,黑暗又在我们后面合拢了。雷蒙在船头瞭望,他对我说:“这是一条向东去的帆船;偏过来一点吧,先生,我们从它后面绕过去好了。”
突然,近在咫尺之间,出现了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朦胧阴影,那是一张高耸入云、迎风飘动的巨大帆篷。说时迟,那时快,我还没看清楚,它已经一掠而过了。在半夜的海上,还有什么比瞥见这种倏忽消失、神出鬼没的阴影,更令人胆战心惊,更吓得人魂不附体的呢?海上的渔船夜里不点方位灯,要等到你和它交错而过,才能看得见它,这会使你心惊肉跳,仿佛遇见了世外之物似的。
我听见远处的飞鸟啼鸣。它飞过来了,飞过船旁,又飞远了。要是我能像它一样自由翱翔,那多好啊!
柔和的曙光到底慢慢出现了,天上没有一片云彩,接着而来的是白天,一个名副其实的夏季的白天。
雷蒙说是会起东风,伯纳却总是说会起西风,并且劝我改变航向,让帆篷从右舷吃风,向着矗立在远方的德拉蒙山驶去。我接受了他的意见,在奄奄一息的微风吹动下,我们慢慢接近了埃斯特勒山。一条长蛇似的红色海岸,在海上投下了它的倒影,使蓝色的海水看起来也成了紫色的。海岸奇形怪状,险峰林立,引人注目,沿岸有数不胜数的海角和海湾,婀娜多姿、变幻莫测的岩礁,真是千变万化、赏心悦目的山景。在山坡上,松林密布,万绿丛中露出花岗石的山峰,既像堡垒,又像城池,也像正在你追我赶的石人石马。山脚下的海水清澈透明,有些地方甚至可以看得见海底下是沙子还是水草。
的确,有些日子,我对现实中的一切讨厌得要死。我觉得风景也好,人物也好,人的思想也好,全都千篇一律,毫无变化,使我痛苦无比。宇宙的平凡无奇使我惊讶、反感,事物的渺小使我憎恶,人生的空虚使我颓废沮丧。
但是,另外有些日子,恰恰相反,我和别的动物一样,对什么都能尽情享受。如果说我那动荡不安的心灵,由于工作的缘故而畸形发展,总是向往人类不能实现的希望,等到发现希望化为泡影,又反过来觉得万事皆空,没有什么值得放在眼里,那么,我像其他动物一样的肉体,却总是沉醉在终日行乐的生活之中。我像飞鸟一样喜欢天空,像野狼一样喜欢树林,像羚羊一样喜欢岩石。我喜欢厚厚的草地,以便像野马一般在上面翻来滚去,或者尽情奔驰;我喜欢清澈的海水,以便像鱼儿一般在里面自由游动。我感到各种动物的天性,各种低级生物的模糊欲望,或多或少地都在我身上蠢蠢欲动。我像动物一样,而不是像你们人类一样喜欢大地,我喜欢它并不把它抬高,也不把它美化,更不会乐而忘形。我用动物内心深处那看起来算不了什么、实在却非常高尚的感情,来喜欢活着的一切,生长着的一切,看得见的一切,因为这一切:白天、黑夜、小河、大海、风暴、森林、曙光、女人的眼波和肉体,不会扰乱我的心灵,却能使我眼花缭乱,心花怒放。
海水轻轻抚摩岸边的沙砾,或者冲击海中的岩礁,都会使我感动,使我忧伤。当我随风漂泊,随波逐流时,我又会感到阵阵欢乐的侵袭,因为我又回到了原始的初民生活,在听任宇宙间无情的自然力摆布。
当天气像今天这样美好的时候,我感到血管里沸腾着生性放荡、到处漂泊的老羊神的血液,我不再是人类的弟兄,而是一切有生物和无生物的伙伴了。
朝阳在天边升起。微风像前天一样平息了,伯纳预报的西风也好,雷蒙预报的东风也好,都没有刮起来。
在十点钟以前,我们一直是一动不动地在海上漂浮,好像是一艘沉船的残骸;然后,海上吹起一阵微风,我们又继续前进;但是海风吹吹停停,仿佛在拿我们开玩笑,在惹帆篷生气,在不断地许空愿,似乎真的要起风了,但是风并不来。来了也算不得什么,不还是嘴巴呵的气,扇子扇的风;不过,这已经够使我们不至于留在原处不动了。在我们周围,海豚好像是在海上表演杂技:它们突然一下跃出水面,仿佛要飞上天,它们经过空中,比闪电还更灵活,然后又翻身下海,再在远处飞出海面。
将近一点钟的时候,阿盖已经在望,微风却完全停了。我知道,如果不用小划子把游艇拖到海湾停泊处去,那就只好在海上过夜。
于是我就要他们两个到小划子上去,在我前方三十米,拖着游艇前进。狂热的太阳直射着水面,晒得甲板都发烫了。
这两个水手用非常缓慢的节拍划桨,好像是两把旧得几乎转不动了的曲柄,还在勉为其难地继续不断起着机械的作用。
阿盖停泊处是个美丽的内湾,两边都有屏障:一边是陡峭的赤壁,山顶上高耸着一座信号台,赤壁一直伸向汪洋大海,构成了因金黄颜色而得名的“黄金岛”;海湾另一边是一字长蛇似的水平岩礁,尽头有一个刚刚露出水面的灯塔,标志着海湾的入口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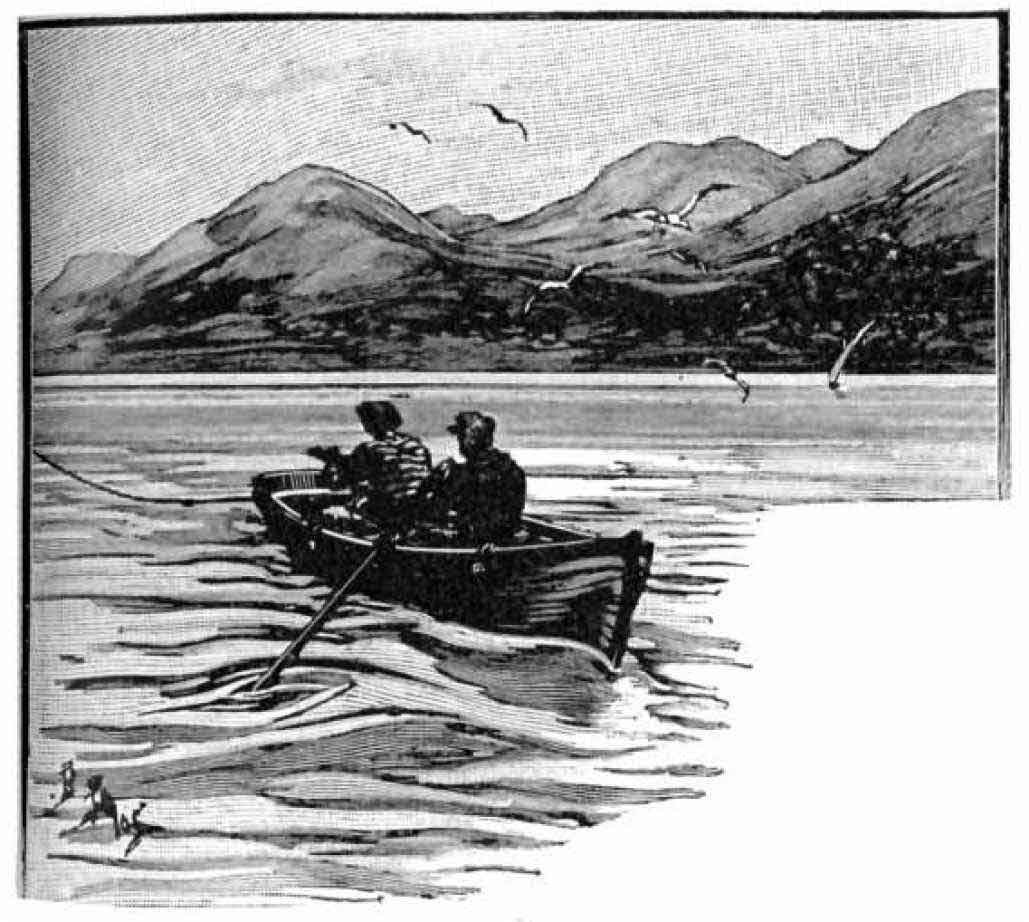
在海湾最里边,有一个小旅馆接待避风的船长和夏天的钓鱼客;有一个火车站,每天只有两班火车经过,但是并没有人下车;还有一条美丽的小河深入埃斯特勒山中,一直通到马兰费梅峡谷,谷里长满了夹竹桃,好像非洲的山沟。
内地没有一条大路可以通到这个幽美的海湾。只有一条羊肠小道,经过德拉蒙山的大理石矿,通到圣拉斐尔;但是这条小路不能走马车。因为这里已经是深山了。
我打定了主意,在天黑之前,就在这条乳香、黄连木和岩蔷薇夹道的小路上散散步。这些树木发出了野生植物的香味,浓郁芬芳,弥漫空中,和树脂的气息融成一片,满山遍野的森林似乎都给闷热压得娇喘吁吁了。
走了一个小时之后,我到了斜坡上一片稀疏的枞树林中。紫红色的花岗岩,这些大地的骨头,似乎也给太阳晒红了。我慢慢地走着,简直像壁虎爬在灼热的石头上一样开心。忽然,我看见山坡上来了一对情人,他们心醉神迷,并没有看见我。
这真美丽,真吸引人,两个人胳膊挽着胳膊,心不在焉地走下这光影交织、五彩缤纷的斜坡。
她显得既雅致又淳朴,穿了一套灰色的旅行装,戴了一顶娇艳新颖的毡帽。他呢,我没有看清楚,只觉得他正派大方。我坐在一棵松树后面,瞧着他们两人走过。他们并没有发现我,还是互相依偎,默默无言,继续走下坡去,他们是多么相爱啊!
等到他们走得看不见了,我忽然感到一种无名的悲哀压在我的心上。一种我从来没有尝过但却能够猜到的、最难得的幸福和我交臂而过了。这时,我觉得心力交瘁,懒得再散步了,就转过身来,向着阿盖海湾走去。
黄昏之前,我一直躺在河边的草地上,快到七点钟的时候,才回旅馆去吃晚餐。
我的水手已经告诉旅馆老板,叫他等我。在一个粉刷一新的、天花板很低的餐厅里,已经为我摆好了餐具。在旁边的一张餐桌上,有两个人在用晚餐,他们凝眸对坐,正是我刚才碰见的那一对情人。
我坐在那里妨碍了他们,觉得不好意思,仿佛做了一件不识相的错事似的。
他们打量了我几眼,然后还是继续他们的喁喁情话。
旅馆老板是我的熟人,他拿了一把椅子,坐到我的身边。他对我谈野猪和野兔,好天气和坏天气,还谈到一个在他旅馆里住过一夜的意大利船长。然后,为了讨我的好,他说我的游艇真棒。从窗口可以看到我那艘游艇的黑色船壳和长桅,桅杆顶上挂着我的红白两色的三角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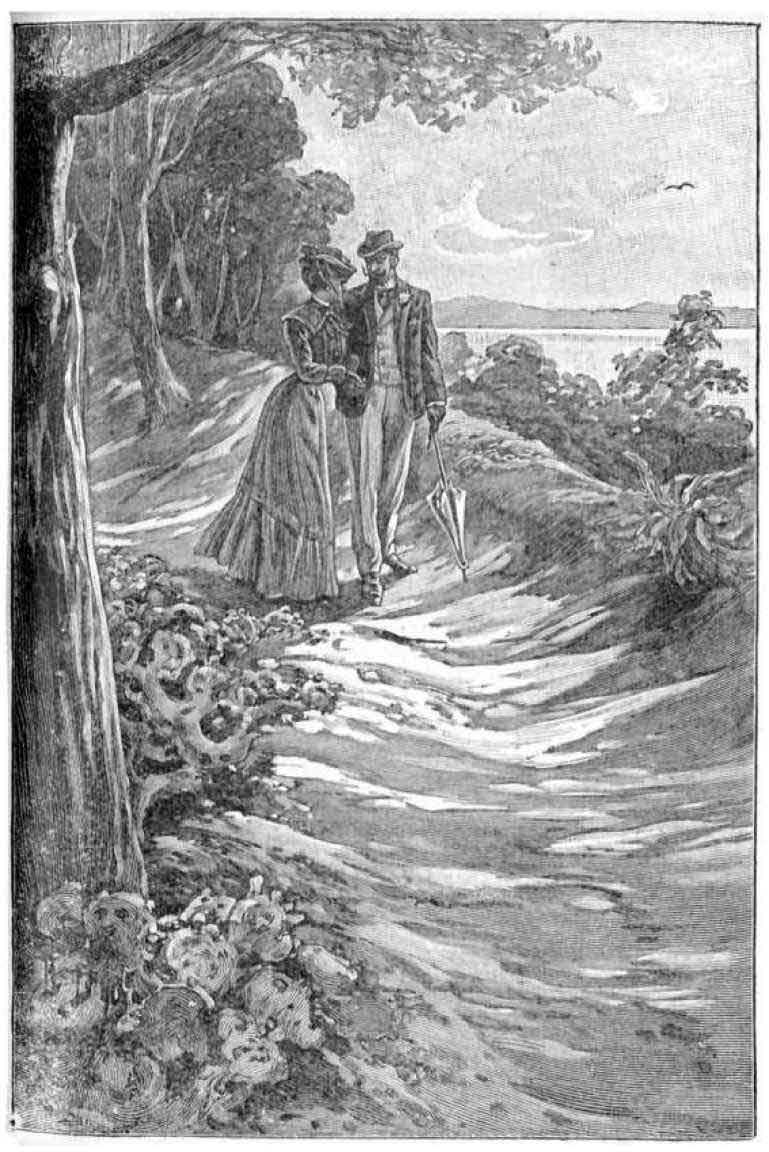
我旁边那一桌的客人吃得很快,吃完就出去了。我呢,我却待在那儿,瞧着一弯新月在小小的海湾里洒下的点点银光。我一直等着我的小划子,看着它划破了平静的水面和惨淡的月色,来到岸边。
我走到岸边去上船的时候,看见那一对情侣站在沙滩上,对着大海凝眸。
我在急促的桨声中离开了海岸,但我一直看得见他们在海滨并肩而立的俪影。海湾、月夜、天空,到处都充塞着他们的影子。无限的爱情从他们的倩影中散发出来,一直扩展到了天际,使他们的影子变得无所不在,意味无穷。
我回到我的游艇,在甲板上坐了很久,心里不知为什么充满了忧悒,充满了无以名之的懊伤,我打不定主意到底下不下船舱去,仿佛要多待一会儿,好呼吸他们散发在空气中的柔情似的。忽然,旅馆的一个窗口亮了,我看见了他们俩在灯光下的俪影。那时,我的孤独感压得我难以忍受。在这温暖的春夜里,听着海浪轻轻吻着沙滩,瞧着月光吻着汪洋大海,我感到心里如饥似渴地需要爱情,几乎苦恼得要高声大叫。
然后,我又忽然因为自己太脆弱而感到惭愧,但不愿承认自己是一个和别人一样的凡人,我就只好怪月光扰乱了我的心情。
再说,我一直相信月亮对人的头脑能起一种神秘的作用。

月亮能使诗人心神飘荡,能使他们变得有趣或者好笑。它对恋人的爱情能起的作用,就像龙考夫[龙考夫(1803—1877),德国机械学家,在法国工作,一八五一年曾设计感应电圈,使低压的断续电流变为高压的断续电流。]的感应线圈对电流的作用一样。一个在阳光下规规矩矩恋爱的人,在月光下却会爱得神魂颠倒。
有一天,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士不知怎的对我谈起:月光造成的创伤比太阳光更危险一千倍。她说,有人在美丽的月夜散步,受了伤都不知道,并且永远也治不好;他一直如醉如痴,如疯如狂,虽然不会发作,不必关进疯人院,但他总是含情脉脉,与众不同;不论是什么事,他的想法都和别人不一样。
的确,我今晚给月光一照,一定是受伤了,因为我感到自己失去了理智,在胡思乱想;这小小的一弯新月落下大海,却使我激动,使我忧伤,使我痛苦。
这个月亮,这个老态龙钟、死气沉沉的星球,在天空中露出了淡黄的脸孔,发出了惨淡的光辉。她有什么迷人的魅力,能使我们心神恍惚,漂浮不定,若有所失呢?
我们爱月亮,难道是可怜她失去了生命?正如诗人阿罗库[阿罗库(1856—1941),法国诗人、小说家。]说的:
然后是风和日暖的黄金时期,
月亮上喧嚣鼎沸,洋溢着生气:它有过无数的河流、无底的海洋、
城市、牛羊、泪珠、欢乐的笑声、
爱情;它有过艺术、法律、天神,
但却慢慢变得暗淡无光。
我们爱月亮,是不是因为诗人用无穷无尽的幻想美化了生活,用月光下看到的各种景象使我们心醉神迷,教我们带着兴奋激动的心情,以千变万化的方式,去欣赏月亮在世界上留下的千篇一律而又温柔甜蜜的印象?
当月亮在树林后面升起,当它震颤的银光倾泻在小河的流水上,当它穿过树枝,照着小园芳径的沙砾,当它形单影只,爬上阴森森、空荡荡的苍穹,当它慢慢地沉入大海,在波涛起伏的水面上,洒下万丈流光的时候,那些伟大的梦想家在它启发下写出的令人陶醉的诗句,能不涌上我们的心头?
如果我们夜行的时候心情舒畅,看见圆圆的月亮好像一只黄色的眼睛,不偏不倚地栖息在一个屋顶上,瞅着我们,那时,缪塞[缪塞(1810—1857),法国浪漫主义诗人,作品有《罗拉》《罗朗查丘》《一个世纪儿的忏悔》等。]的不朽名作就会在我们的记忆中吟咏起来。
难道不是这位游戏人间的诗人,通过他的眼睛,使月亮一下就出现在我们眼前?
暮色苍茫古塔黄,
明月高挂古塔上,好像
一竖上面加一点。
月啊,哪一个神仙
用根银线在暗中转动
你的正面和侧面?
如果我们在一个心情忧悒的晚上,在月光照耀下的海滩上散步,我们几乎会情不自禁地吟诵起下面两行如此崇高而又如此凄凉的诗句:
形影孤单的月亮漂泊在海上,
银色的泪珠洒进黑暗的波浪。
如果我们一觉醒来,忽然看见一线月光从窗口射到床上,难道我们不会恍惚看见卡杜勒·孟德斯[卡杜勒·孟德斯(1841—1909),法国作家及诗人,他的诗深受巴那斯派美学的影响,强调“为艺术而艺术”。]提到过的白衣仙子从天而降,向着我们冉冉而来?
她来了,每只手拿着一枝百合花,
踏着一线月光,顺着银流而下。
如果我们在乡下夜行,忽然听见农家的狗发出凄惨幽长的哀嚎,难道我们不会立刻想起勒孔特·德·李勒[勒孔特·德·李勒(1818—1894),法国诗人,青年时代思想上接近空想社会主义,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后放弃政治活动,拥护“纯艺术论”,成为巴那斯派的主要代表。]的绝妙诗篇《嚎声》?
孤独的、苍白的月亮,排开乌云,
像昏暗的灯光,在凄凉地摇晃。
这微露恨意、毫无怨言的月亮,
这陨灭了的星球飘零的残片,
从冰冷的球体上投下了一线
阴森的反光照着北极的海洋。
在一个和情人相会的晚上,你慢慢地在路上走着,紧紧地抱着爱人的腰肢,握着她的纤手,吻着她的额头。她有一点疲乏,又有一点激动,走的步子也有一点蹒跚。忽然,一条长凳出现在被柔和沉静的光波浸润着的绿叶之下。
那时,这两行引人入胜的诗句,难道不会像一首意味深长的情歌一样,突然涌上你的心头,震动你的心弦:
唤醒睡在长凳上的月光,
请她让出一点坐的地方。
当我们看见一弯新月,像今天晚上一样,在无边辽阔、星光灿烂的天空中,勾画出自己的侧影,我们能不想起维克多·雨果那首杰作《波阿斯[波阿斯,以色列国王的曾祖父,伯利恒的财主。摩押人路得,在丈夫死后随婆婆回到伯利恒,得到亲戚波阿斯的照顾,后嫁给波阿斯,这里是描述路得在波阿斯地里拾麦穗,夜宿场上抬头望天的景象。]睡着了》的最后几行:
……路得一动不动,
半开半闭地睁开眼睛,心中问道:
哪个上帝,哪个永远在夏天里
收割麦子的人,走时粗心大意,
在星野里丢下了这把金镰刀?
描写风流蕴藉、对情人体贴入微的月亮,又有谁能超过雨果?
黑夜来了,火光熄了,一片静寂;
在阴暗的树林里,泉水如诉如泣;
夜莺隐蔽在黑暗的窠里歌唱,
唱得像个诗人,唱得像个情郎。
大家都在绿荫深处成双成对;
不论男的女的,笑着互相追随;
怨女拉着痴男,一同走进林荫;
他们迷糊得仿佛在梦中惊醒,
感到有什么渗进他们的灵魂,
渗进他们的情话、如火的眼神,
他们的心、五官和脆弱的思想,
啊!那是弥漫大地的蓝色月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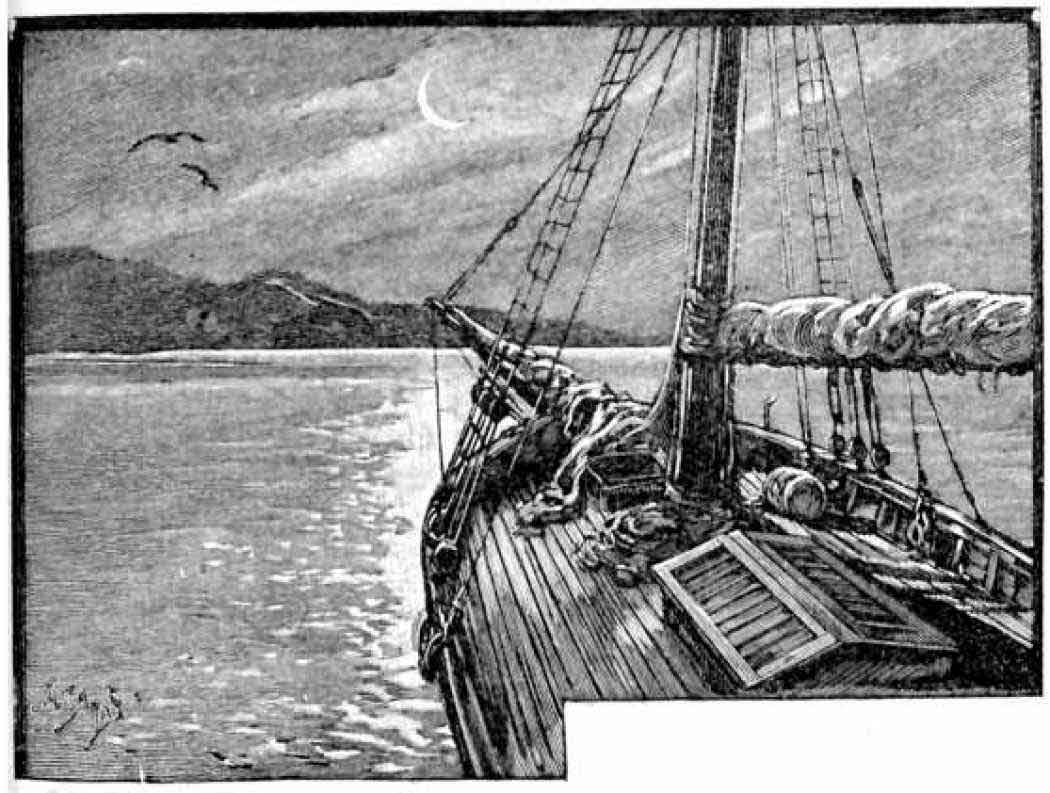
我还想起了阿普列乌斯[阿普列乌斯(约123—170),古罗马作家、哲学家,信奉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哲学。主要作品《变形记》(后改名《金驴》)描写并讽刺罗马帝国的社会生活。]的《金驴》第十一卷卷首的那篇美妙的祝月词。
然而,所有这些诗歌,也写不出这个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的星球在我们心中引起的忧悒感。
我们同情月亮,不由自主,莫名其妙,也不知道什么缘故,的确,我们还爱她呢。
我们对月亮的脉脉温情里,也掺杂着几分怜悯;我们可怜她像一个守身如玉的老处女,因为,不管诗人怎么说,我们还是模模糊糊地猜得到:月亮并不是一具女尸,而是一个童贞女。
星球也像女人一样,需要一个丈夫,而受到太阳冷落的月亮,不也像我们的年过二十五还没有出嫁的闺女圣卡特琳吗?[指圣卡特琳节。法国习俗,在圣卡特琳节这一天,年满二十五岁的未婚姑娘要戴“圣卡特琳帽”,算是进入老处女的行列。]
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月亮羞答答的光线,才会使我们心里充满了不能实现的希望和无法满足的欲望。我们模模糊糊、空空洞洞地在尘世所期待的一切,在惨白的月光照耀下,就像不能妙手回春却又神秘莫测的玉液琼浆一样,激动着我们的心灵。我们抬头一见月亮,就会为了虚无缥缈的梦想而心弦颤动,渴望得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柔情。
这金钩似的一弯新月,现在把一个尖角浸入海水,缓缓地、慢慢地沉了下去,另外一个尖角又细又小,不等你看清楚,它已经消失了。
我抬起头来瞧瞧那个小旅馆。灯光明亮的那个窗子刚刚关上。我忧从中来,实在受不了,就走下甲板,回到我房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