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 | 收藏 |
第六章 鸽子米点的天空
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 作者:蔡崇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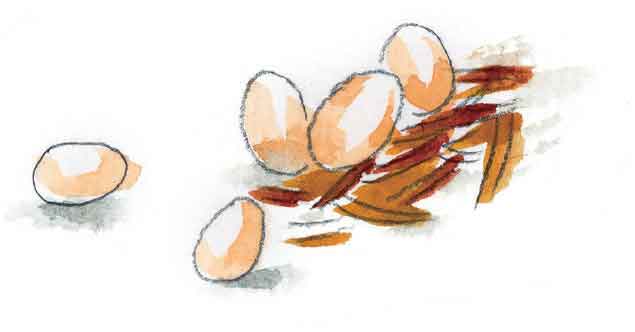
比医生预告的时间早了一些,父亲大概四个多月后,便认为已经寻回自己的左半边身体了。那几天,他总会开心地找到我们,然后缓慢地把左手举到头顶高,激动地说:“你看,我举起来了。”
我们也跟着很激动,似乎父亲举起的是他接下来的所有人生。
犹豫了几天,父亲试探性地问:“要不我重新去开加油站吧?”
母亲说:“好啊。”
我们知道父亲的犹豫,虽然他左半身能调动得了,但毕竟中风过,使不上太多力气,要拎起给小汽车加油的油桶,估计比较困难。父亲最不可能完成的,是大油桶的油抽干了,需要把新的油桶挪出来。
母亲单独去看顾加油站的那段时间,只给摩托车加油。一旦外面的油桶没有油了,母亲只能把外面的大油桶挪一条小缝,依靠自己身体的瘦小,通过缝隙钻进去,从里面的大油桶抽油。
晚饭时,母亲去厨房盛饭,唤我们帮忙拿的时候,和我们商量:“以后黑狗达和姐姐放学后,就一起去加油站,我们一家人把第二天需要的油桶滚到适合的位置,可以吗?”
“要不你阿爸挪不动油桶,肯定要对自己生气的。”母亲说。
我明白母亲的话,我已经发现了,很多时候人的气愤,是因为察觉到了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终于,这一天,父亲要出门去加油站了。他右手拎起热水瓶,转过身来,用力举起左手,向我们挥了挥,然后一拐一拐地和母亲出发了。
沿路有邻居和他打招呼:“去开店啊?”
他说:“是啊。”
又一个邻居说:“看上去好像全好了。”
父亲笑着说:“是啊。”
父亲生病期间,港口那地方开了家全新的加油站。那家加油站配了电动油枪,只要往加油口一挂,油就呼哧哧地喂给了车。而在父亲的加油站加油,顾客有时候还得帮着拿加油漏斗,弄得一手油腻腻的。
但听说父亲回来了,街坊们好像商量好了似的,特意过来加油。不仅摩托车,甚至连原来不怎么愿意来的小汽车、货车都特意开来找父亲加油。
小汽车和大卡车,父亲和母亲要一起抬油桶,父亲出右手,母亲出左手,一个个中油桶来回装。小汽车得装一个来回,而大卡车,得好几趟。
加油站斜对面住着一个老奶奶叫蔡淑女,两个儿子都是开大卡车的,以前都是去大加油站加油。自从父亲开店后,淑女奶奶便要求儿子们只能来我父亲这儿加油。淑女奶奶的儿子不太乐意,他们看着我父亲一拐一拐地和我母亲来来回回忙碌,一辆车半个小时都还没能加完油,自己窝在驾驶座上生闷气。
淑女奶奶站在自家门口看到了,生气地大喊:“你们就不会帮忙吗?愣着干吗?”
他们不想沾手,假装没有听见。淑女奶奶气得直接撸起袖子,冲过来要帮我父亲提油桶,吓得她两个儿子赶紧下车一起抬。
重新开店以来,生意反而更好了,但父亲心里却越来越不是滋味。晚上睡觉的时候,他问母亲:“咱们能不能就不接待卡车了?接待卡车,承别人的好意,还要拖累人家。”
“但不接卡车,收入不高的。”母亲忧虑地说。
“那就不接卡车了,大家已经够帮忙我们的了。”想了一会儿,母亲说。
母亲知道的,对于他人的好意要珍惜,而不是滥用。
第二天,父亲挂上黑板,上面写着:感谢大家的支持,本店不接待大卡车。
父亲生病期间把家里的钱耗得差不多了,现在加油站不再接待大卡车,收入自然捉襟见肘。我本来已经习惯家里的晚餐慢慢没有肉的痕迹,但后来,连唯一的荤菜小肉丸汤,也得两三天才能买一次肉丸。我发现姐姐的鞋底磨破了,她对谁都没有说,自己偷偷用胶纸粘上。放学路上,姐姐走路总是一拐一拐的,那是路上的石头硌得她难受。能不买的东西我尽量不买,练习册也是找高一年级的同学不要的旧册子。
虽然告诉自己这没什么,一家人为了彼此努力、相互陪伴就很好,但我知道自己越来越不对劲。我总怀疑自己身上有油污味,因而总是离同学们远远的。我越来越容易紧张,老师说:“下周学校组织去厦门游学,同学们尽量都报名。”我赶紧低下头。同学问:“你看了新出版的《七龙珠》吗?魔人布欧又进化了。”我赶紧低下头……渐渐地,我发现自己越来越爱低着头,走路低着头,到学校低着头,回家也低着头。
父亲和母亲当然看到了。
“黑狗达你有心事吗?”父亲问我。
我说:“没有啊。”说完,我又低下头。
“那你为什么总低着头?”
我赶紧抬起头说:“没有啊。”
“阿爸会好起来,咱们家会好起来的。”父亲试图安慰我。
“我知道的,你放心吧。”说完,我还是不自觉地低下了头。
那天放学,我低着头回到家,父亲笑眯眯地坐在厅堂等着我。我看到他身后的桌子上放着用布盖起来的一个纸箱子。
“来,这是我和你阿母送你的礼物。”父亲说。
礼物?为什么要送我礼物?我掀开那块布,打开箱子:是一对鸽子。它们豆子般的小眼睛一直盯着我看,然后咕咕咕咕地叫起来。
“鸽子?”我不解地看着父亲。
“我们看你老低着头,想说,如果你养了鸽子,可能就会喜欢抬头看看天吧。”父亲说。
灰色的鸽子,身上有斑点,我给它取名叫米点,白色的鸽子浑身雪白,所以它叫雪花。阿太和姐姐也很喜欢父亲母亲给我选的礼物,那天傍晚,我们一起在屋顶用木头和此前的兔笼,给米点和雪花搭建了一个窝。

父亲很想上来帮忙,但家里的楼梯没有扶手,上下楼梯要分别用到左右脚,他的左脚无法单独支撑他的身体上屋顶,更无法支撑身体下去。父亲只能坐在下面的台阶上,不断问着:“搭得怎么样?记得上面要用油布盖,下雨了才不会淋湿。记得地下垫些砖头,雨大了才不会淹到……”
阿太说她知道怎么养鸽子:“养鸽子的关键,就是让它认这里当家。只要认了这里,不管天涯海角它都一定会飞回来的。”
“天涯海角也找得回来?”我不相信地看着阿太。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郭岑村有户人家的孩子去下南洋了,那时候正在打仗,下南洋了就不知活不活得下来,更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联系上。家里没有什么可以让他带的,就给他带走了一只鸽子。过了好多年,大家都以为那孩子在南洋失踪了,有一天鸽子真的飞回来了,脚上绑着一张纸条,写着:平安。那人家知道了,他们的孩子是平安的。”
“这么远,鸽子是怎么找到家的?”我好奇地问。
“鸽子就是懂得家在哪儿。人也是这样的。”这是阿太的回答。
我还是没明白,吃晚饭的时候问父亲:“鸽子为什么永远知道家在哪儿?”
“鸽子鼻子上有块石头一样的东西,那是块磁铁,而地球本身也是块大磁铁,鸽子可以通过自己的小磁铁感受到磁力,判断自己的家在这块大磁铁的什么位置。”这是当过海员的父亲的答案。
父亲一笑:“反正我也永远找得到家的,和鸽子一样。”
“那怎么让鸽子把这里当家呢?”
“就是真的把它当家人,它们会知道的。”阿太抢着说。
刚来的鸽子,一放开肯定是要飞掉的。按照阿太的建议,我先把鸽子养在笼子里,等待着鸽子把我家当它们自己的家。
要把鸽子当家人——我记得阿太的话。每天早上醒来,我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到屋顶喂鸽子,我不仅喂它们,还和它们咕咕地说话。我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它们肯定也不懂我说了什么,但它们肯定知道的,我想和它们说话。
下午放学回家,我做的第一件事情也是来到屋顶。我不仅和它们咕咕咕乱说,还会和它们说家里的事情、学校的事情,以及我知道的故事。
七八月的闽南多雨,每次看到下雨我就赶紧往屋顶冲,用油布把鸽子笼盖上。担心它们害怕,我还撑着雨伞陪在旁边。看我在雨中陪着,鸽子对我一直咕咕咕咕咕咕,它们在催我回屋去。等到雨停了,我又到屋顶掀开油布,生怕鸽子憋闷得难受。鸽子咕咕咕,我想它们在问我,被雨淋到了吗?

我不断地问父亲:“鸽子和我亲了吗?它们把这儿当家了吗?”
父亲说:“你觉得呢?”
“我觉得应该很亲了,开始它们一看到我就跑,现在一看到我来了就咕咕叫着朝我靠过来。”
“那放开试一试?”
我在心里掂量了很久,说:“要不咱们再等等吧。”我不知道,感情多深才叫深。
有一天我照常拿着玉米要喂鸽子,突然发现笼子里多了几个小小的蛋,是鸽子下的。
“鸽子下蛋了!”我透过天井对家里喊。
阿太和姐姐兴奋地冲上来看,父亲还是不好上屋顶,他隔着天井说:“太好了,鸽子竟然这么快愿意下蛋了。”
“所以鸽子下蛋代表什么呢?”我注意到父亲用了“竟然”。
“鸽子下蛋,说明它们把这里当家了,所以它们才愿意在这里养育自己的孩子啊。”父亲说。
“那我可以把鸽子放开了吗?”
“可以的。”
“真的吗?”我还是担心鸽子会飞掉。
“没有一个父母会愿意离开自己孩子身边的。”父亲说得斩钉截铁。
我想了想,是啊,我父亲就是这样的。
父亲很激动,他觉得自己应该和我一起放飞鸽子,他试着把左脚抬到楼梯上,但是抬右脚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左脚根本没力气单独支撑。
后来,他想到了办法,对我喊:“先别着急放啊!等我走到大门口,鸽子一飞起来,我在下面也看得到的。”
父亲兴奋地一拐一拐地拐到大门口,站好,对我发信号:“我准备好了。”
我又确认了一句:“真的可以放吗?”
父亲说:“相信我。”
我紧张地打开笼子,鸽子先是有些吃惊,看着打开的笼子门发了一会儿呆,还相互看了看,或许在相互询问发生了什么,然后先是米点走出来,雪花也赶紧跟上。
它们走出笼子,一会儿看看我和姐姐,一会儿看看阿太和母亲。
“飞吧鸽子。”我对鸽子说。
米点歪着头,似乎在努力听清我的话。
我又说了一遍:“飞吧,飞起来吧。”
米点似乎听懂了,往前快速地走了几步,抖动羽毛,突然一跳。米点飞起来了,冲向天空,然后转出一道椭圆形的弧线。
雪花看着飞起来的米点,咕咕地叫了一下,好像在说“等等我”,然后也几下助跑,扑棱着翅膀,飞起来了。
我高兴地向父亲喊:“阿爸你看到了吗?鸽子飞起来了!”
“我看到了。”父亲的语气听上去是如此开心。我站在屋顶上,看到庭院里的父亲拄着拐杖仰着头,一直笑着看着天上的鸽子,似乎飞起来的不仅仅是鸽子,还有他的许多希望。
因为一直看着鸽子,我这才发现天空是如此好看。那时候大概是五六点钟,橘子一般的夕阳把天空染得金灿灿的。

真的有金色的天空啊,我想,以后还是要多抬头看看天。
鸽子在天空一圈一圈地盘旋,越飞圈越大。
我问庭院里的父亲:“它们会回来吧?”
“会的,一定会的,因为它们的家在这里。你叫一下它们试试。”
我对着它们咕咕咕,它们好像听到了,低下头看看我。
我抓一把玉米举起来,继续对它们咕咕咕。
米点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朝我飞过来。雪花紧紧跟在米点身后,也飞了过来。
“好了,鸽子知道这里是家了,鸽子把你当家人了。”阿太很开心地宣布。
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光真是又辛苦又幸福。那段时光也让我知道,辛苦和幸福一点都不冲突,人是可以在辛苦中很幸福的。
每天下课,我和姐姐帮助父亲母亲倒腾油桶,回家母亲准备做饭,我和姐姐赶紧清洗身上的油渍。我们清洗完就开始做作业,抢在夕阳落山前,上屋顶去喂鸽子,然后对鸽子说,飞吧。鸽子便在天空中盘旋。
但有时候我回来得实在太晚,还在做作业,鸽子们已经等不及,便在笼子里不停地咕咕叫。后来,我干脆一回来就把鸽子笼打开,只要不是下雨天,我就搬了小桌子和凳子,在天井中做作业。
做作业累了,抬起头,便可以看到正在天空中飞舞的米点和雪花。我是那么喜欢盯着它们看,看着看着,我总觉得自己也在飞翔。
那一天我在天井做着作业,听到鸽子在屋顶上着急地呼唤着我们。我上去查看,发现原本三颗鸽子蛋,只剩一颗,剩下的这颗,也被咬破了。
阿太说:“看样子老鼠已经知道屋顶上有鸽子了,一定会来偷鸽子蛋的。”
“那怎么办呢?”
“以后估计得等到我们陪着的时候再打开笼子,放飞鸽子了。”阿太说。
那天,我们一家商量,阿太和母亲帮我和姐姐把桌子搬到屋顶。就此,只要不下雨,我们便在屋顶做作业。
我很喜欢在屋顶做作业,风把东石镇的各种声音送过来,我像被很多人陪伴着。而鸽子在天上飞,我们在屋顶保护它们的孩子,我们彼此都很安心。我想,家或许就是这样的相互陪伴吧。
或许鸽子也心安,很快又生蛋了。蛋孵化出来,我们又多了几只小鸽子,从此我抬头看到的天空,便是一群鸽子在飞。
闽南的冬天就是这样,象征性地凉个几天,强调一下自己真的是冬天,偶尔或许是担心别人觉得它不够称职,会突然来一次漫长且刺骨的冷。那种冷天,海风似乎也总要大起来,冷飕飕的风,仿佛为了取暖,找石头房子的缝隙拼命想钻进来。
每次那种天气,我们都拼命把自己全身包裹起来,一层又一层,像粽子一样。
我记得那一年的冬天,冷得反常。冷到,好像所有人都懒洋洋的。我懒得起床、懒得走路,一大早我就爬到屋顶打开笼子,鸽子也懒得飞。
我是后来才知道,天气一冷,人和动物的血管都会收缩,所以就会比较懒。而对中风的人来说,冷是很危险的事情——中风就是因为血管被堵住了,而冷会让血管收缩,堵得更厉害。
当时的我不知道,只感觉父亲似乎比我更懒,甚至懒得有些疲倦。他疲倦地挣扎起床,疲倦地努力做着康复操,疲倦地关心着我:“多穿点啊。”说着说着,眼睛快要闭上了,感觉就要睡着了。
“阿爸你没事吧?”
“没事啊。”父亲疲倦地对我笑了笑。
那天,我还在屋顶上看着鸽子飞,突然听到母亲喊:“大家赶紧来,你阿爸晕倒了!”
虽然一送到医院,医生说:“看来你们有经验了,送得很及时。没事,待会儿你父亲就会醒了。”但父亲“待会儿”并没有醒。
我看到医生来了,又走了。然后叫来更多医生,又来了,又走了。来来往往许多次。
终于,医生找到我们。医生说:“我们开了溶解血管中脂肪的药,并没有起作用。”
医生说:“我们怀疑,你父亲的第一次中风,也不是脂肪血栓造成的。待会儿我们会开扩张血管的药,这样他可能会醒来,但是,建议你们商量下,要不要转到省城的医院。”
“转,现在就转。”母亲说。
去往福州的救护车上,父亲醒了。
父亲看到自己在输液,开着玩笑说:“我就睡一觉,你们就又把我送医院了啊,我以后可不敢随便睡觉了。”然后他察觉到不对,“我怎么还是在救护车上?”
母亲张了张嘴,不知道怎么解释。
“泉州的医院说找到病根了,但得去福州的医院看。”阿太找了个安慰父亲的说法。
父亲似乎明白了什么,一脸悲伤地沉默着。
开往福州的救护车上,风呼呼地吹着。
“咱们似乎离家好远了,而且越来越远了。”姐姐看着窗外说。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
“没事,多远咱们都认得回家。”阿太说,“和鸽子一样。”
一到省城的医院,我们又开始奔波在各种检查中。
门诊到处都是人,被各种疾病抓来这里的人。我看到一个个病人的床前,围着一群群家人。这里的每户人家也和我家一样,发生过那么多痛苦、挣扎与希望。
检查做完了,医生看了看所有的检查报告,最终把父亲安排在重症病房。病房很干净,一个房间三个床位。我看到床位边放着可以供家属休息的躺椅,我知道了,住在这里的病人,都要待很长一段时间。
护士来叫家属,说医生有事要和家属商量。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让父亲生病的罪魁祸首。在父亲大脑的X光片上,有一个刺眼的小黑点。
医生对我们说:“你看,就是这个堵住了。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医生又找出一张图片,是像鱼唇一样的东西:“它本来是在人的心脏里,管理着血液的进进出出,它叫作瓣膜。现在它脱落了,一部分堵在你父亲的脑血管里。”
我看到它了,就是它锁死了父亲的左半身,让我们家如此辛苦。
“现在你们得商量下,要不要赶紧做心脏手术?”医生问。
“不做是不是不可以?”母亲问。
“不做,瓣膜随时还可能脱落,再脱落估计人就要……”说到这儿,医生停顿了。
“做,当然做。”母亲说。
“但做这个手术有很大的危险,成功率目前只有百分之六十多。”
母亲一下子愣住了,转过头来惶恐地盯着我。我知道母亲害怕了。我的身体也不自觉地颤抖起来。
医生看出来我们一家的慌张,说:“要做这么大的心脏手术,身体必须得先恢复,要不人扛不过去的。我们等病人身体指标快到手术标准的时候,再来决定。”
按照医生的说法,父亲可能要在医院边治疗边观察十多天,身体才有机会达到手术标准。所以,我们得商量谁留下来陪护。
阿太抢着说:“当然我了。阿珍你回去看着加油站,还要照看孩子,这里交给我。”
医生惊讶地打量苍老的阿太,阿太知道医生的担心,用一种中气很足的声音说:“别小看我,我现在还能挑着担从郭岑村走到东石镇。”
医生还是用一种无法置信的眼神看着阿太。
“当然是我留下来。”母亲说。
医生交代,每个病人可以有个陪护睡在旁边的躺椅上,叫我们在附近找个宾馆。虽然医生这么说,但为了省点钱,那天我们谁都没有提要去找宾馆的事情。护士几次过来提醒:“路对面就有宾馆的,你们赶紧去问问还有没有房间。”母亲说:“好啊,稍等就去。”护士提醒了几次后,突然小声地和我们说:“其实走廊许多长椅,你们累了就可以去睡一会儿。”
那是我们一家第一次聚在城市中心一栋很高的楼上,虽然这是病房。从窗户看出去,有高楼的霓虹和万家灯火。
我想象着,每点灯火照着的该是怎样的生活,他们是否也和我们家一样,经历着那么多不易……
看着城市那空荡荡的天空,我突然想起来:我忘记关鸽子笼了。
关于怎么从福州回到东石镇,对阿太、姐姐和我来说是个挑战。阿太似乎从来没坐过公交车,我和姐姐也从来没有在城市里自己坐过公交车。
“你们可以吗?”母亲担忧地问。
“当然可以啊。”阿太依然回答得很笃定。
一出门她就问姐姐和我:“对哦,那个护士是教我们朝哪个方向走?”看来阿太跳过她不熟悉的所谓“公交车”,直接设定为走路了。
“阿太,走路我们更不知道怎么走,而且估计一天都走不到汽车站吧。”我说。
“没事,咱们边走边问,肯定找得到路的。”说完,阿太拉住一个路人问,“请问汽车南站怎么走啊?”
“走路,去南站?”路人愣住了,看了看阿太,又看了看我和姐姐,“要不要我帮你们找警察来帮忙呢?”
最终,我们还是拉住阿太一起等公交车。搭21路,转5路,到南站,找到泉州的巴士,到了泉州汽车站,再坐到东石镇的小巴……
终于回到东石镇,我担心家里的鸽子,撒腿就跑,姐姐也跟着我跑。跑着跑着,我突然想起来,阿太都那么大年纪了,怎么跑得了?我赶紧停下来,看见阿太正气喘吁吁地拄着拐杖在跑。
“阿太别跑!阿太别跑!”我担心地喊。
阿太恍然大悟一般:“是哦,我可不能跑。都这把年纪了,万一骨头散架了呢……”
跑到家一开门,我便往屋顶冲。鸽子笼开着,里面没有鸽子,也没有了又生下的鸽子蛋。
是我害了鸽子,它们还在孵化的蛋被老鼠偷了,还有可能它们晚上睡觉的时候被老鼠咬了。
我难过地对着天空咕咕咕,咕咕咕。天空,空荡荡的。
“是啊,如果是我,一定也会生气地离开吧。如果这个地方连护自己周全都没办法,我肯定要离开吧。”我坐在屋顶上发呆。
忘记发呆了多久,先是天空突然出现一个小小的身影,我认出来了,是米点。
米点在空中对我咕咕地叫。
我立刻站起来,对它咕咕地叫。
但米点没有停下,绕着我飞了几圈,突然又飞走了。
我想,米点没有原谅我。我想,我应该理解米点的。
我还在胡思乱想,突然听到天空一声又一声的咕咕咕,抬头一看,米点带着雪花和它们的孩子,往我这边飞过来。一只两只三只四只……鸽子们都回来了。我欣慰地想着:父亲说得没错,鸽子是认家的。我心酸地想着:只要认定是家了,即使再不好,它们也会回来的。

傍晚五六点,我窝在屋顶上,陪着鸽子们。
听到有人在叫门。
阿太去开门,是邻居健康伯。他嗓门还是那么大,他说:“邻居看到您和孩子先回来了,我担心你们晚上来不及做饭,拿来一大块红烧肉和一些豆腐。”
过了一会儿,红线奶奶来叫门,她送来了炒米线。
文才叔也拿着铺盖来了,他说:“你们老老小小在家,邻居们可担心了,商量轮流来你家打地铺,第一晚就我来吧。”
第二天早上,开小卖部的阿丽姨迈着小碎步气喘吁吁地跑来敲我家的门:“黑狗达,你阿母从医院打电话过来了。你们赶紧来接。”
我和姐姐跑到阿丽姨家,一接电话,发现电话已经挂了。阿丽姨重新挂好电话,等了好一会儿,电话还是没响。
“这怎么回事?”阿丽姨问。
我说:“我阿母肯定是为了省等待时的电话费,把电话挂掉了,现在应该要重新排队。医院的插卡电话永远有人在排着。”
果然,过了十五六分钟,电话响起,是母亲。为了省钱,母亲讲话很急切:“你们顺利到家就好,我们这边都很好。不用担心。你们要互相照顾。我隔天这个时间打一次阿丽姨电话。”
“好的……”我还想要问父亲的情况,母亲已经把电话挂了。
父亲和母亲都不在家,加油站也不用开了,我和姐姐不需要帮忙滚油桶、抽油,时间突然空出来。一空出来我就往屋顶跑,还好屋顶上有鸽子,还有天空。
大概是父亲去福州住院的第三周,母亲的电话来了,母亲说:“医生说,过几天可以安排手术了。”
母亲说:“能不能你们来一趟?”
母亲还是道歉了:“抱歉啊黑狗达,我不敢签手术同意书。”
“当然我来签啊。毕竟我是一家之主了。”我尽量掩饰着自己的慌张说。
约定的是三天后,期末考试一考完就去福州。阿太和姐姐也说一定要去,我知道她们在想什么——毕竟手术成功率只有百分之六十多。
但如果我们三个人一起去福州,鸽子们怎么办?手术要等父亲身体状态最好的一天,而且这是个大手术,做完后,至少得住院十天才能回家吧。这一来一去将近二十天。
我一个人跑到屋顶上想了很久。看着米点和它的家人在天空盘旋,我知道我只能这么做了。
“我们把鸽子送人吧?”晚饭的时候,我装作不在意地随口一说。
姐姐低下头,但她肯定也琢磨过这个问题了,她只是问:“那送谁呢?”
“我挑去送你大舅好不好?你外婆走后,你大舅总是一个人发呆,这么多年了,他和你们一样,也一直想念着你外婆。”看来阿太早已经想到了解决方案。
期末考试最后一天,阿太、姐姐和我一大早起床,把鸽子一只只抓进用竹篾盖着的箩筐里。前面的箩筐放着鸽子,后面的箩筐放着笼子和玉米。
阿太拄着拐杖,挑起箩筐,说:“那我们走了哦。”我知道的,阿太的“我们”,指的是她和鸽子们。
我假装自己没有不舍,我说:“记得教大舅,要等鸽子认定家了才放出来哦。”
阿太说:“知道了。”
“记得让大舅要小心老鼠哦。”
“知道了。”
很幸运,手术很成功,一早七八点推进去,到下午四五点才推出来。父亲被救回来了,只是医生提早预告,父亲这次中风和上次不一样,因为那个掉落的瓣膜,已经把父亲一部分的脑血管堵死了,按照现在的技术取不回来——那意味着,父亲再也找不回他另一半的身体。
关于这个事情要不要和父亲讲,阿太、母亲、姐姐和我开了几次会。最终,我们决定不说。
父亲果然还是倔强、坚强的父亲,手术第二天,听说得放屁才代表伤口正在愈合,我们便看到他很认真地在寻找屁意,一发现有机会,就赶紧用力。听医生说,一般最快五六天就可以试着起床走走,帮助恢复,父亲在第四天就嚷着要起来……
父亲下床了,我和母亲左右边搀扶着他,父亲信心满满地用力要站起来,身体却没有反应。第二次咬着牙用力,屁股只离开床几厘米却又坐下来了。父亲一慌,想用手帮忙支撑,这才发现,这次和此前不一样,他的左手一直蜷缩在胸前,怎么都不听使唤。
父亲惶恐地看着自己的身体,看着我们,他明白了。他嘴角抽搐着,眼眶红红的,但尽力控制着不让自己哭,然后他拼命地安慰自己,喃喃自语:“没事的,没事的,我会找回来的。”
父亲不自觉地安静了。但为了不让我们察觉到他的痛苦,我们无论说什么,他都微笑着应和。笑完,便又坠入深深的沉默中。
那一天恰好是元旦,这座城市的欢声笑语,乘着风不断隐隐约约地吹到父亲的病房,父亲望着窗外,突然问:“对哦,那些鸽子呢?米点、雪花和它们的孩子呢?”
我支支吾吾地不知道如何说。
“鸽子……黑狗达送他大舅了。他大舅这么多年来一直想念他外婆,很孤单,黑狗达让鸽子去陪大舅。”最终还是阿太来说。
父亲忧伤地看着我,他明白我为什么把鸽子送人。
“哦。”沉默了许久,父亲就回了这么一个字。我知道父亲伤心了,我知道父亲哭了。
许久许久,父亲开口说:“但没有鸽子,你还是要记得抬头看看天啊,不要老低着头好吗?”
“好啊。”我赶紧回答,不敢抬头看父亲的眼睛。
第十天,医生终于答应让父亲出院了。一大早,母亲和阿太忙忙碌碌地收拾。父亲还不太站得起来,护士特意叫来护工轮流搀着,这才终于把父亲扶上车。
这次父亲没有嚷着要坐公交车回去,他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了。
我家的巷子口太窄,救护车开不进去,父亲实在走不了路,我们一家呆呆地坐在救护车上不知道怎么办。正在发愁,海森伯探头探脑地走过来,他一看到是我们,高兴地喊起来:“我听着救护车声就在想,是不是你们回来了。太好了!真的是你们,怎么还不进来?”
海森伯说话的时候,文才叔、健康伯也来了。他们都是听到了救护车的声音。
母亲说:“黑狗达阿爸走不动了,得有人抬。”
“这好办,我们不都来了吗?”健康伯说。
邻居两两替换着抬,父亲终于回到了家。
但是,父亲不肯进房间,说他想在厅堂坐一坐。
“那待会儿你怎么到房间躺着啊?”海森伯问。
父亲说:“这几步路我拄着拐杖应该可以的,就让我在这里坐坐吧。”
父亲坐在厅堂上,一直望着天空。他走动不了,只能看着天空流动的云。父亲从下午一直坐到傍晚,像棵植物一样,我们不知道怎样去安慰他,只能拿着椅子也坐在旁边陪他。
那天,漫天的红霞,像浪一样翻滚。父亲眯着眼睛,静静地看着。突然他激动起来,他喊着:“是米点吗?”
我循着父亲目光的方向望去,看到一个小小的黑点正朝我们飞过来。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是米点。
米点似乎也看到我们了,咕咕咕地叫起来,在天空盘旋了一圈,停留在天井上空,朝我们打量。
米点咕咕咕地叫着。
父亲开心地说:“你是来看我们的对吧,我们很好,你回你的家吧。”
米点依然咕咕咕地叫着。
父亲说:“放心吧,我会好起来的,这个家会好起来的。”
米点是夜色暗到快看不见天空的时候才飞走的。第二天,它又准时来了。自那之后,米点雷打不动地每天来探望我们一次。
多亏了米点,无论日子多辛苦、多艰难,父亲因此每天都会抬头看看天空。
后来我高中去外地读书,为了节省路费,每两周回家一趟。父亲说:“你好好努力,阿爸自己也会努力。放心,米点每天来看我。”
我每次回来都会向米点表示感谢。我会抓一把玉米,在它还在天空飞的时候上屋顶坐着,等着喂它,等着和它说说话。
后来我去读大学了,只能一个学期回来一次。父亲说:“放心吧,米点每天来陪我。你好好努力,阿爸也好好努力。”
我知道的,父亲那几年的确非常努力。我听说,他每天五六点起床,每天坚持到巷子走一个来回,每天要摔个十几次,身体青一块紫一块的,到处是瘀青。母亲很努力,一个人守着加油站,和姐姐一起扛起摔倒的父亲。阿太很努力,一天天发起和父亲的比赛,比赛抬脚、比赛拐杖跑步……
我也很努力,我知道的,堵着我们家的,是父亲脑血管里那块鱼唇一样的心脏瓣膜。我找了各种资料,了解到美国新推出一种纳米针的手术方法,可以取出那块瓣膜。我必须抓紧时间攒够钱。
大学毕业后,我到北京找了份记者的工作。有固定的底薪,再加上稿费,我开始可以攒钱了。为了多攒点钱,我拼命跑新闻写稿子。我甚至春节都不回来了——因为春节假期留京工作,工资可以拿三倍,而且从北京回家的路费我想省下来,给父亲治病。
家里安了电话,我也买了手机。父亲太久见不到我,经常忍不住打电话给我。电话里他一次次和我说,他很想我,他问我可不可以不攒钱了,多回来看看他。他说他真的很努力在锻炼,或许不用去美国做手术就可以好起来。
我和父亲说:“快了,我攒够拿掉脑血管里那块瓣膜的钱,我就回来。”
父亲问:“那还要多久?”
我和父亲说:“就三年,再等我三年。”
我算得没错,在北京工作的第三年年底,我就可以攒够三十万了。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要登录银行账户查看自己存的钱,满心欢喜地想,今年春节我就可以带父亲去美国治疗,我们家又要好起来了。
我记得那年的秋天,北京满街金黄金黄的树叶,特别漂亮。我正通宵写一个稿子,母亲打来了电话。母亲说:“黑狗达别难过,你父亲走了。”
母亲说:“你千万别怪自己的父亲,他真的尽力了。你也千万别怪你自己,你父亲和我都知道,你真的尽力了。”
父亲终于还是没有等到我攒到足够的钱,我终于还是没能抢在父亲扛不住之前回到家。
时隔三年第一次回家,竟然是为父亲办葬礼。族里的亲戚帮忙料理得很好,不熟悉习俗的我一点忙都帮不上。按照繁文缛节我把自己该做的都做了,心里憋得难受,干脆沿着东石镇到处走。走着走着,我走到了等父亲回来的那个码头,走到了父亲开酒楼的地方,走到了海鲜干货店,走到了父亲开的加油站。我看到那个西装革履的父亲,看到那个拼命想挣钱的父亲,看到那个艰难地一拐一拐地走路、试图寻回自己身体另一半的父亲。我知道的,父亲这一生已经用尽全部的力气去护着我、爱着我,父亲真的尽力了。
往回走的时候,已经接近傍晚。我沿着从小走到大的石板路往家里走去,我在记忆里看到了石板路上的小白,看到了阿花,看到了黑咪,我悲伤地想,所以人生就是这样吗?不断地告别和失去吗?我还在想着,突然听到咕咕咕的叫声,抬起头,我看到了,我家的屋顶上站着一只鸽子。是米点。
米点又来看我们了,米点又回家了。阿太说得没错,鸽子一旦认为哪里是家,就永远会回来的。

父亲去世后的第三年,母亲有一天傍晚突然打电话给我,说:“黑狗达啊,告诉你一个事情你不要难过。前几天米点就没来了,今天我等到这个时候,还是没等到它,我想,米点可能走了。”
“我算了算时间,米点确实年纪大了,真是难为米点了,这么多年,每天来看我们。”听着电话里的声音,我知道母亲在伤心。
我走出办公室,爬到办公楼的楼顶。北京的天空湛蓝湛蓝的,北京的天空没有米点。但我知道的,这世界有那么多人,这世界有那么多部分,其实都在试图陪伴着我。
去吧米点,你放心吧,现在的我,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会经常抬头看看天空。因为我记得的,天上有米点,天上有我父亲,天上有永远在陪着我的你们。我知道了,天空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怀抱,一直在拥抱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