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血孩子 | 收藏 |
近亲
Near of Kin
血孩子 作者:奥克塔维娅·E·巴特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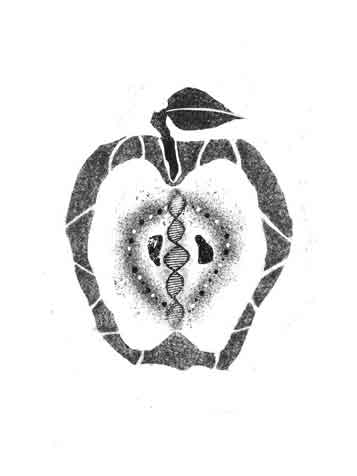
本篇最早刊登于《蛹4》(Chrysalis 4,1979)。
——编者注
“她想生下你,”我的舅舅说道,“她没必要非生个孩子不可,你知道吧,哪怕是二十二年之前。”
“我知道。”在母亲公寓的客厅里,我舒舒服服地坐在木头摇椅上,面对着他。脚边放着一只大纸箱子,它本来是装生菜的,如今塞满了纸——散页的、折角的,铺平的、叠起的,重要的、琐碎的,全都混杂在一起。这里面有她的结婚证,有她在俄勒冈州的房契,有用廉价纸张做的手工卡片,上面用红色和绿色的蜡笔写着“祝妈妈圣诞快乐”。卡片是我六岁时做的,送给了外婆,当时我管她叫“妈妈”。现在想来,外婆或许将它连同善意的谎言一起交给了母亲。
“你还没出生她就守了寡,”舅舅说,“她没办法独自抚养孩子。”
“别人都行。”我说。
“她不是‘别人’,她是她自己。她知道自己能应付什么、不能应付什么。她深思熟虑后才认为你跟着外婆过比较好,也算有个家啊。”
我看着他,不明白为什么事到如今他还要煞费苦心地替她说好话。我对她是什么感觉——或者根本没有感觉——有什么区别吗?“记得我八岁时,”我说,“她来看我。我问她能不能带我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也好。她说不行。她说她得工作,家里没地方,也没钱,反正一大堆理由。于是我就问她到底是不是我亲妈,难不成我是领养来的孩子。”
舅舅面色一紧:“她怎么说?”
“什么也没说。揍了我一顿。”
他叹了口气:“她就是这脾气。太紧张,太敏感。这也是她把你留在外婆身边的原因之一。”
“那其他原因是什么?”
“想必你也听说过。缺钱,缺时间,缺地方……”
“缺耐心,缺母爱……”
舅舅耸耸肩。“你想跟我说的就这些吗?一大堆讨厌你妈妈的原因?”
“不是。”
“那是?”
我看着地上的纸箱。从母亲的衣橱里往外搬时,沉甸甸的纸张把箱底压破了。也许这公寓里的某个角落能找到胶带。我站起来四处翻看,以为舅舅会因为受够了我的沉默而离开。他有时候确实会这样——不声不响地表达他的不耐烦。我小时候还会觉得害怕,现在反而求之不得了。要是他走了,我就不用继续回答刚才的问题了……暂且不用。他是朋友,也是亲人——母亲的哥哥,比母亲年长五岁——是除了外婆,唯一一个不只是泛泛之交而是真正关心我的亲人。以前在外婆家,他有时会跟我聊聊天。他把我当作小大人儿,因为他的兄弟姐妹都成家了,生的那么多孩子,就没有一个不像小大人儿的。他无意中给我施加了不少压力,但和其他舅舅姨妈相比,和外婆的朋友们相比,和那些拍着我的脑袋告诫我要“做个好女孩”的人相比,我还是更喜欢他。比起母亲,我和他相处得更好,所以哪怕是现在,尤其是现在,我不想失去他。
我在厨房的抽屉里找到了胶带,回来时他还在。没到其他地方,只是从纸箱里拿了张纸。我费劲巴拉地粘纸箱时,他就坐在那儿看那张纸。场面尴尬,但我又不希望他主动过来帮忙——也许,其他男性亲戚无所谓,但他不行。
“那是什么?”我看了一眼那张纸问。
“你五年级的成绩单。成绩很烂。”
“天哪,赶紧扔掉。”
“你就不想知道她为什么一直留着?”
“不想。她……我认为我多少了解她一些。孩子是她想生的——怎么说呢,为了证明自己是个女的,能够生育,诸如此类,她也想看看到底能生出个什么来。可一旦生出来了,她又不想浪费时间养了。”
“生下你之前,她流产过四次,你知道吗?”
“她告诉我了。”
“她确实很关心你。”
“偶尔吧。比如每当我拿出那种烂成绩单时,她肯定会骂我。”
“所以你才故意考得很烂?故意惹她生气?”
“我考得很烂是因为我根本不在乎——后来有一次你冲着我大吼一顿,我吓得要死,才稍微上心。”
“等等,我记得那次。我不是故意要吓你。我只是觉得你明明有脑子,却不好好用它,这些我也告诉你了。”
“但你确实吓到我了。你当时坐着,怒气冲冲,一脸的厌恶,我还以为你要彻底放弃我了。”我瞟了他一眼,“你当时那个样子,好像哪怕我不是领养来的,你也不是我亲舅舅。所以我必须牢牢抓住你、缠住你才行。”
我从没见他笑得这么开心,仿佛年轻了好几岁。他已经五十七岁了,单薄、清瘦,不过依旧英俊。母亲这边的亲戚都是如此——瘦小,甚至有些虚弱。拥有这些特质的女性总是惹人怜爱。
我觉得这样的男性也颇有魅力。不过我知道,我那些表兄弟为了证明自己的男性气概,没少花功夫打架、炫耀。这让他们变得敏感、易怒、戒心重。我不知道这种风气是否影响了小时候的舅舅,反正他现在不太爱生气。要是惹毛了他,最多冷冰冰地说你几句。要是还不解气,打起来也能收放自如——他年轻时就是这样——总之,我从来没见过他故意闯祸。我的表兄弟们都不喜欢他,见他不生气就说他冷漠。我不这么想,于是他们也说我冷漠。那又如何呢?我和舅舅待在一起就是自在、舒服。
“你打算怎么处理她的东西?”他问。
“卖掉。捐给救世军[Salvation Army,意为(基督教的)救世军,是一个成立于1865年的基督教教派,组织的目的是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社会服务,同时也进行基督教福音传道。——编者注]。不知道。你有什么想留下的吗?”
他站起来,走进卧室,动作中有着岁月未曾侵蚀的顺畅、敏捷和优雅。他拿来了母亲放在梳妆台上的那张照片。照片是放大版,是他在纳氏草莓园给外婆、母亲和我拍的,当年我十二岁。那次不知为什么,他说要带我们出去享受享受。这是我们三人唯一的一张合照。
“要是把你也拍进去就更好了,”我说,“应该找个陌生人帮忙拍照。”
“不不,你们三个正合适——母女三代人。你真的不想留下这张照片吗?或者再冲一张?”
我摇摇头:“你留着吧。别的呢?你还想要什么?”
“没了。你打算怎么处理俄勒冈州的房产?亚利桑那州应该也有一些。”
“哪儿都有房子,偏偏这儿没有,”我咕哝着,“要是她愿意花钱在这儿买房子,我就能搬过去和她一起住了。说到底,她哪儿来的钱?她不应该是个穷光蛋吗?!”
“她已经不在了,”舅舅淡淡地说,“你还要浪费多少时间和精力来怨恨她?”
“我当然想省点力气,”我说,“可我也没办法像关水龙头似的一下子就截断感情。”
“那我在的时候你就把它关上。她是我的妹妹,你不爱她,我爱她。”他说得平静、温和。
“好吧。”
我们沉默了好一会儿,后来一位姨妈来了。我将她请进门,她却一把抱住我哭个不停。我忍了又忍,毕竟我母亲也是她的妹妹。她是个讨厌的女人,每次去看外婆,总是一边炫耀自己的孩子天赋异禀,一边拍着我的脑袋,好像我是这个家族里的傻瓜。
“斯蒂芬。”她跟舅舅打招呼。他不喜欢自己的名字。“你拿了什么?一张照片。挺好。芭芭拉当年多漂亮啊。她一向是个美人,就算死了尸体也如此鲜活呢……”
她说着就走进卧室,在我母亲的遗物中翻找起来。翻到衣橱时,她叹了口气。我记得过去她们身量相当,但现在她至少比我母亲重二十磅。
“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些精致的东西?”她问我,“应该留下一些当作纪念吧。”
“是吗?”我说。我当然打算清理掉,越快越好——捆起来,送到救世军那儿去。可是这位姨妈多年来一直伪善地反对我母亲“不像母亲”的行为,要是我表现得满不在乎,她肯定会大发雷霆的。
“斯蒂芬,你是来帮忙的?”姨妈问道。
“不是。”舅舅轻声道。
“嗯,只是陪着,是吧?也好。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没有。”舅舅答道——有点奇怪,因为这个问题显然是在问我。姨妈有点儿惊讶地看着他,他则面无表情地回看过去。
“那好吧……如果有需要,尽管给我打电话。”她说着又敛起几件我母亲的首饰,然后又拎起那台小型黑白电视。“我想把这个拿走,你不介意吧?孩子们总是为了抢电视吵来吵去……”她走了。
舅舅看着她,摇了摇头。
“这位也是你的妹妹。”我笑道。
“如果她不……算了。”
“怎么?”
“没事。”淡淡的警告意味又出现了。我没理会。
“我知道。她是个伪君子——别的就不提了。我看她比我更不喜欢我母亲。”
“那你为什么允许她拿走那些东西?”
我望着他:“因为我不在乎这公寓里的一切。无所谓。”
“好吧,”他深吸一口气,“至少你不虚伪。你母亲有份遗嘱,你知道吧?”
“遗嘱?”
“房产很值钱。她留给你了。”
“你怎么知道?”
“我留了一份副本。她觉得没人能翻出来。”他冲着那只大纸箱摆摆手,“这么归档可太不牢靠了。”
我不高兴地点点头:“确实。我根本就不知道她都有些什么。可是,就不能转给你吗?我不想要。”
“她想为你做些事。就随她吧。”
“可是……”
“随她吧。”
我深深吸气,又缓缓呼气:“她给你留下什么了吗?”
“没有。”
“这可不太对。”
“我满足了——或者说,你能接受她留给你的东西,我就满足了。还有些钱。”
我皱起眉头,无法想象母亲竟然存得下钱。要不是整理遗物,我都不知道这些房产的存在。还留了一笔钱,这就更离谱了。不过,这至少给了我开口的机会。“这钱是她的?”我问,“还是你的?”
他迟疑了片刻,答道:“是写在遗嘱里的。”这可不是他惯有的讲话方式——好像我的问题让他措手不及。
我笑了,但看到他因此流露出窘迫,我不愿意惹他不自在,便收起了笑容。我要追问下去——必须问个清楚——但我并不期待,也不打算从中获得什么乐趣。
“你不是那种心机深重的人,”我说,“看起来却是满腹算计。神秘、冷淡又克制。”
“我控制不了自己的长相。”
“人们说我也是这副模样。”
“不,你的样子像你妈妈。”
“不是吧。我觉得我像我爸爸。”
他没接话,只是盯着我看,眉头紧锁。我摸了摸纸箱里那几张折角的纸页。“钱还要留给我吗?”
他不肯回答。他用人们称之为“冷淡”的神情望着我。其实那不是“冷淡”——我知道他“冷淡”时是什么样子。现在,他更像是在痛苦中挣扎,仿佛我伤害了他。想必我确实如此,但我停不下来。来不及了,收不回了。我紧张地把手指插进那些纸页里,低头端详了一会儿,突然怨从心生。我为什么不躲在学校里袖手旁观呢?我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丢给亲戚?她当年不是也总把我丢给亲戚吗?要么就当个负责任的女儿,老老实实地料理好母亲的后事。我怎么就不能只做不问、把嘴闭上呢?他会怎么样?会离开吗?我连他也要失去了吗?
“无所谓,”我不看他,自顾自地说,“算了。我爱你。”相同的意思我含糊地对他表达过好多次,但这三个字,我从来没说过。就像在请求许可。我爱你,这是可以的吗?
“你是不是在箱子里找到了什么?”他柔声问。
我没听懂,皱眉愣了一会儿,后来才反应过来——我的紧张让他想多了。“什么也没有,”我说,“至少据我所知,没有。别担心,我觉得她不会写下来。”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不知道,只是猜的。很久以前就猜到了。”
“为什么?”
我踢了踢纸箱。“线索很多啊,”我说,“最简单的就是长相吧,我和你。外婆有一张照片,把那里面年轻的你和现在的我放在一起,简直就像双胞胎。我的母亲很漂亮,她的丈夫英俊魁梧,而我……我长得像你。”
“长相不能代表什么吧。”
“我明白。但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而且,还有些无形的东西。”
“猜测。”他苦涩地说,向前倾着身子,“我确实藏不住秘密,是吧?”他站起来,往门口走去。我连忙冲上去拦住他。我们一样高,一点儿不差。
“请你不要走,”我说,“别走。”
他轻轻地把我往旁边推,但我站定不动。
“说吧,”我央求道,“我不会再问了,提也不会提。她已经不在了,这伤不到她啊。”我犹豫了一下,又说,“请你不要离开我。”
他叹了口气,垂头望着地板,而后又望向我。“是的。”他轻声道。
我让开了,突然间,我如释重负,差点儿哭了出来。我有父亲了。我从来感觉不到自己有母亲,但我一直是有父亲的。“谢谢你。”我轻声道。
“没有人知道,”他说,“你外婆不知道,所有的亲戚也不知道。”
“我不会告诉他们的。”
“不。我从不怕你会告诉别人。我不在乎别人,但我担心他们会伤害她和你——痛苦会逼迫你……追问到底。”
“我不觉得痛苦。”
“真的?”他似乎有些惊讶地看着我。我意识到,他其实和我一样害怕。
“她是怎么让她丈夫同意在我的出生证上留名的?”我问。
“撒谎。不会戳破的谎言。怀上你的时候,她丈夫还活着,只是早已离开了她。但家里人一直不知道,后来发现了也无从查对时间。”
“他离开是因为你吗?”
“不是,是因为他找了别的女人——不会流产、能为他生下孩子的女人。被抛弃后她来找我——找我倾诉、哭泣、发泄情绪……”他耸耸肩,“她和我一向亲近——非常亲密。”他又耸耸肩,说道,“我们爱着彼此。如果有可能,我真的会娶她。我才不在乎什么流言蜚语,我真的会这么做。后来,她发现自己怀孕了,我们都很害怕,可她想生下你,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不相信最后这句话,哪怕是现在。我相信我之前说的——她只是想证明自己是个女人,能生孩子。一旦证明可以,她就撒手不管,干别的去了。但他爱她,我爱他。所以我什么也没说。
“她一直害怕你发现真相,”他说,“所以才不敢把你留在身边抚养。”
“她觉得我是她的耻辱。”
“她觉得自己是耻辱。”
我看着他,想从他难以捉摸的神情中读出些什么。“那你呢?”
他点点头:“我也是耻辱——你,从来不是。”
“可你没有像她那样抛弃我。”
“她没有抛弃你;她不可能抛弃你。不然你问她你是不是领养的孩子,她何必那么生气?”
我摇头:“她应该信任我啊。要是她也像你这样多好。”
“她已经尽了全力。”
“我本来可以爱她。其实知道了我也不在乎。”
“以我对你的了解,我知道你可能真的不在乎。但她不那么确定,她不敢冒这个险。”
“你爱我吗?”
“爱。她也爱你,尽管你不信。”
“她和我……真该好好地互相了解了解。我们一点儿也不了解对方,真的。”
“是啊。”沉默之中,他又看了看纸箱里的东西。“如果有不知道怎么处理的,就拿来给我。”
“好。”
“遗嘱的事打电话谈吧。你要回学校吗?”
“对。”
他向我微微一笑。“那钱就用得上了。别再让我听见什么你都不肯要的废话了。”他走了,悄无声息地带上了门。
后记
首先,这篇《近亲》与我的另一部小说《血缘》(Kindred)没有任何关系。我曾对负责收录选集的编辑提起过,但他只记得我有两部标题相似的作品,于是想当然地认为它们必然有所关联。其实完全不相干。
《近亲》源自我童年做浸信会教友的经历,以及我的习惯。那时我年纪很小,已经喜欢跟随兴趣探索不同的领域。作为信仰浸信会的好孩子,我最初是把《圣经》当作培养信仰、规训行为的指示来读的,后来则是为了背下那些指定的诗篇,再后来,便沉浸于其中环环相扣的有趣故事。
那些故事吸引着我:冲突、背叛、折磨、谋杀、流放、乱伦。我读得如饥似渴。当然,我妈妈鼓励我多读《圣经》,肯定不是出于这种目的。然而,我还是觉得这些主题非常迷人,所以当我开始写作时,便在自己的作品中做了相应的探索。《近亲》就是这种兴趣的古怪成果。我大学时就做了尝试,但失败了。这个念头一直缠绕着我,催着我把它写出来:一个令人同情的乱伦故事。我借鉴了这几个故事:“罗得与女儿同寝”“亚伯拉罕娶异母妹”“亚当之子与夏娃之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