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血孩子 | 收藏 |
语音
Speech Sounds
血孩子 作者:奥克塔维娅·E·巴特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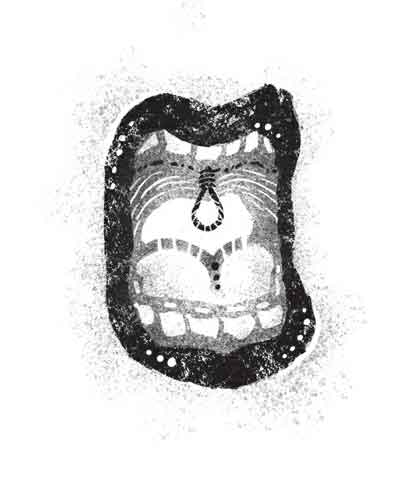
本篇获1984年雨果奖最佳短篇小说奖。
最早刊登于《艾萨克·阿西莫夫科幻杂志》(1983)。
——编者注
华盛顿大道上的公交车出事了。赖伊觉得迟早会在路上遇见麻烦事。她一直在家拖延时间,最后还是被孤独和绝望赶出了门。她估计还有几个亲戚在世——一个哥哥带着他的两个孩子,住在二十英里外的帕萨迪纳市。如果运气好,一天就能到。从弗吉尼亚路上的家里出来时,公交车刚好驶来,这似乎算得上幸运。没想到却出事了。
两个年轻人似乎因为误会起了争执,他们堵在过道上,连说带比画,左右叉着弓步,随着驶过坑洼的汽车东倒西歪。司机好像故意想让他们站不稳似的。不过,他们比画归比画,却一直没碰着对方——拳打脚踢仅限于装装样子,互相嘲弄的手部动作代替了无法说出口的诅咒。
乘客们看看二人,又互相看看,焦虑地哼了几声。两个小孩呜咽起来。
赖伊坐在后门对面,距离他们有几英尺远。她谨慎地盯着那两个人,知道一旦谁忍不住了、手滑了,或是有限的沟通能力到头了,就会真的打起来,随时都会。
担心的情况果然出现了:公交车轧过一个大坑时,那个一直面带讥笑的瘦高个儿没站稳,狠狠地撞向了对面的矮个儿。
矮个儿立刻挥起左拳回敬,虽然对方身材高大,但他只管一拳一拳地猛捶,仿佛除了左手的拳头,再没有别的武器,也不需要别的武器。他出拳又快又狠,不等人高马大的对手稳住身子反击,就已经把他打倒在地了。
乘客们吓得或尖叫,或粗吼,那些离得近的全都争相躲避。还有三个年轻人兴奋地大喊大叫,也发疯似的比画起来。接着也不知怎么回事,其中又有两人打起来了——很可能还是因为不小心碰到了、撞到了。
第二拨打架的人挤散了受惊的乘客,一名女子摇晃着司机的肩膀,一边指着出乱子的方向,一边费力地出声求助。
司机龇着牙,气哼哼地吼了一声,吓得那名女子退回去了。
赖伊知道公交车司机惯用的伎俩,她稳住自己,紧紧抓住前面座位的靠背横杆。当司机猛踩刹车时,她早有准备,而打架的人毫无防备,他们摔向两侧的座位,砸在乘客们身上,这下更乱套了。卷入打斗的人又变多了。
公交车一停下来,赖伊就起身去推后门,推了两下,后门开了,她连忙抱着背包跳下车。有些乘客跟着下了车,但也有些留在车上。如今,公交车又少又不准时,好不容易赶上一辆,无论如何也得坐。说不定今天都等不来别的车了——明天也不见得有。人们得边走边等,看见公交车就招手叫停。像赖伊这样从洛杉矶到帕萨迪纳的城际旅行者,只能做好露营的准备,要么就得冒着遭到抢劫或谋杀的风险,到沿途的陌生人家借宿。
公交车没再往前开,赖伊却躲得更远了。她打算等冲突平息后再回到车上,但万一闹到开枪的地步,她得找棵树挡一挡才行。快走到路边时,街对面一辆破旧的蓝色福特掉头开过来,停在公交车前面。这年头轿车已经很少见了——燃料严重缺乏,连勉强能配上的零部件也很难搞到。还能开上路的汽车可以是交通工具,也可以是武器。所以,当福特轿车的司机向赖伊招手时,她警觉地退开了。司机下车了——是个大块头男人,年纪不大,蓄着整齐的胡子,头发又黑又密。他穿着一件长大衣,像赖伊一样谨慎小心。她与他隔开几英尺远,等着看他到底想干什么。他看看公交车——混战摇晃着车厢——又看看刚才下车的一小撮乘客,最后目光又落在赖伊身上。
赖伊也看着他,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外套里藏有一支老式45毫米口径自动手枪,于是盯住他的双手。
他抬起左手,指了指公交车。深色的车窗遮住了车厢内部,他看不清里面发生了什么。
他用的是左手,这比他的疑问更让赖伊关注。左撇子大多受损较轻,更通情达理,也更不容易受挫折、困惑和愤怒的情绪驱使。
她模仿着他的动作,也用左手指指公交车,然后双手握拳,凭空挥打了几下。
胡子男脱掉大衣,露出洛杉矶警察局的制服,手里还拿着警棍和左轮手枪。
赖伊又退了一步。洛杉矶警察局已经不存在了,所有大型机构都不存在了,不论是官方的还是私人的。只有社区巡逻队和持有武器的普通人。再没有别的了。
胡子男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把大衣扔回轿车里。接着,他示意赖伊折回去,回到公交车的后部。他手里拿着一个用塑料做的玩意儿。赖伊不明白他想干什么,只是看着他走到公交车的后门那里,向她招手,让她站在那儿。出于好奇,赖伊照做了。不管是不是警察,没准儿他真有办法平息这场莫名其妙的斗殴呢。
胡子男向前绕到车道一侧,驾驶室的窗户开着,赖伊隐约看见他往公交车里扔了什么东西。她还想透过深色的玻璃向里张望,但乘客们突然跌跌撞撞地冲出了后门,又是咳嗽又是抹眼泪。原来是催泪瓦斯。
赖伊扶住一位差点儿跌倒的老太太,又拎起两个小孩,免得他们被人撞倒、踩到。她看见胡子男守在前门帮忙。一个刚才打架的家伙推开瘦小的老人往外挤。赖伊连忙抓住老人,但还是被他带了个趔趄,最后一个年轻人冲出来时,她差点儿没躲开。这人口鼻流血,踉踉跄跄,一头撞上了别人。两人又不管不顾地陷入了扭打,一边打一边被催泪瓦斯呛得哼哼唧唧。
公交车司机也从前门出来了,胡子男帮他一把,但他似乎并不领情。有那么一瞬间,赖伊还以为他俩也要打起来了。司机比画着威胁的手势,发出无声的怒吼,而胡子大汉只是后退几步,冷冷地看着。
他既不挪动,也不出声,拒绝回应那些下流的手势。受损最轻的人往往如此——除非受到人身威胁,否则只是退后观望,任凭那些控制力差的人喊叫、跳脚。他们似乎认为,像那些理解力差的人一样一点就着,实在有失身份。这种态度显得有些高人一等,公交车司机那样的人都这么想。这种“优越感”常常会惹来殴打,甚至让人送命。赖伊自己就有过因此死里逃生的经历。所以,她再也不敢手无寸铁地出门。在这个以肢体语言作为通用语言的世界,有武器就够了。不过她很少动枪,也很少亮出来。
胡子男的左轮手枪一直亮在外面。显然这已经足够震慑公交车司机。司机厌恶地啐了一口,瞪了胡子男好几眼,然后才迈着大步走向了满是浓烟的公交车。他愣了一会儿,想进去,可烟雾还很浓。所有的车窗中,只有驾驶室的那扇是开着的。前门也开着,但后门就得有人扶着才行,否则就会自动关闭。当然,车上的空调早就不能用了。想等烟雾散去,还需要好一阵子。公交车是司机的财产,是他的生计。车厢两侧贴着旧杂志里的图片,表示图片上的东西可以充作车费。收来的东西可以用来养家糊口,或是以物易物。车子停着不开,就意味着他没饭吃。但话说回来,要是莫名其妙的斗殴砸烂了车厢,同样会影响他的收入。他显然没想到这一层。他所看到的就是车子暂时不能开走。他冲着胡子男挥舞拳头,大呼小叫,似乎也喊出了几个字眼,但赖伊听不懂。她不知道这是自己的问题还是司机的问题。在过去的三年里,她几乎没有听到过连贯的人类语音,所以无法确定自己听懂了几分,也无法估计自己的损伤程度。
胡子男叹了口气。他瞥了一眼自己的轿车,朝赖伊招了招手。他要走了,但得先跟她提些要求。不,不对,他是想带她一起走。上他的车可有点儿冒险。尽管他穿着警察制服,但如今早已没有什么法律和秩序了——连话语都没了。
她摇摇头——是拒绝的意思,尽人皆知,可他还是连连招手。
她挥手让他走开。在受损较轻的人之间,像他这样故意引起对方潜在负面情绪的是很少见的。其他乘客纷纷张望过来。
一个刚打过架的家伙拍拍另一位的胳膊,指指胡子男,又指指赖伊,然后举起右手,伸出食指和中指,好像行了三分之二个童子军礼[童子军礼是食指、中指和无名指三指并列伸出,故此处称三分之二个童子军礼。]。他动作很快,但即便在远处,那意思也是明摆着的:她和胡子男是一伙儿的。接下来会怎样呢?
那家伙朝着她走过来了。
赖伊不知道他想干什么,但站在原地没动。他比她高半英尺,可能比她小十来岁。她觉得自己跑不过、逃不开,万一需要帮忙,周围的人也指望不上。他们全都是陌生人。
她又一次示意——非常明确地要求他停下。她不打算再比画了,但幸运的是,他没再往前走。他做了个淫秽的手势,惹得几个男人哈哈大笑。有声语言的丧失催生了一整套新的粗俗手势。这家伙的意思简单明确:他污蔑她和胡子男有一腿,要她也陪陪其他男人,由他本人先来。
赖伊看着他,只觉得疲惫厌倦。要是他冲上来强奸她,别人肯定只会干站着看热闹。要是她开枪自卫,他们也会一样无动于衷。他会把事情推向那一步吗?
不会。他手舞足蹈地表达了下流的咒骂,但没再靠近,而是轻蔑地转身走开了。
而胡子男还在等着。他已经把左轮手枪连同枪套都摘掉了,两手空空地继续招呼她。毫无疑问,枪就在车里,随时都能拿到,可是,卸枪的行为打动了她。也许他没什么恶意。也许他只是觉得孤单。她也孤身一人生活了三年。怪病夺走了她的一切,一个接一个地杀死了她的孩子、她的丈夫、她的姐妹、她的父母……
这种怪病——如果它真是某种疾病——甚至把活人之间的联系也切断了。它迅速席卷全球,人们都顾不上甩锅给苏联(不过苏联也和其他地方一样,陷入了沉默),或是归咎于新型病毒、新的污染物、核辐射、天谴……怪病会让人突然病倒,连同某些后遗症,都有点像中风。但它表现得更为具体——语言系统严重受损,乃至彻底丧失,并且无法恢复,也无法重新习得。此外,便是常见的瘫痪、智力障碍、死亡。
有两个年轻人吹着口哨、拍着巴掌,还冲着胡子男竖起拇指,但赖伊并不理会,向他走去。但凡他露出一丁点儿笑意或是同流合污的意味,她都会改变主意。但凡她愿意想想搭陌生人的车可能带来的致命后果,她都会改变主意。然而,她想到的是住在街对面的那个男人。自从得了怪病,他就不怎么洗澡,而且还随地小便。他已经有了两个女人——每人替他照料一个大花园。为了换取他的保护,女人们只能忍着。而他明确表示过,想让赖伊成为他的第三个女人。
她上了车,胡子男关上了车门。她看着他绕到另一边的驾驶室——盯着他,因为他的枪就放在她旁边的驾驶座上。公交车司机和那两个年轻人走近了几步,但没什么举动,直到胡子男也上了车,其中一人才扔过来一块石头。其他人纷纷效仿,轿车开走时崩开了几块,人和车都没什么事。
公交车被远远地甩在后头,赖伊擦擦前额的汗,特别想放松一会儿。公交车其实已经开了大半程,她只要再步行十英里就能到达帕萨迪纳。可现在她拿不准还有多远了——而且,除了徒步跋涉,可能还有别的难题。
菲格罗亚大街和华盛顿大道交叉口是公交车左转的地方,轿车开到这里停下了,胡子男看着她,示意她选个方向。她指了左边,他真的左转了。她开始放心了。既然愿意按她选的方向开车,他应该没有恶意。
轿车掠过焦黑瓦砾、断壁残垣、空荡荡的街巷、损毁废弃的汽车,他绕头取下金链子递给她。坠子是一枚光亮滑润的黑色石头——黑曜石。看来,他的名字可能是洛克、彼得,或是布莱克,不过她决定称他为奥普斯汀[这四个名字分别有不同的寓意:洛克(Rock)意为石头;彼得(Peter)源自希腊语Πετρος,意为岩石;布莱克(Black)意为黑色;奥普斯汀(Obsidian)意为黑曜石。]。虽然她的记忆力有时候不太顶用,但记住这样一个名字还是可以的。
她也递上了自己的“名片”——麦秆形状的金色徽章。这是很久以前买的,在罹患怪病、陷入沉默之前。现在,她把它戴在身上,作为最接近“赖伊”[赖伊(Rye),意为黑麦。]的象征。不认识她的人,比如奥普斯汀,可能会以为她叫惠特[惠特(Wheat),意为小麦。]。无所谓。反正再也不会有人念出她的名字。
奥普斯汀把徽章还给她,趁她来接时拉住了她的手,大拇指摩挲着她手上的老茧。
轿车开到第一街,他又停下来,问她要往哪个方向走。按照她的意思,他向右拐弯,而后在音乐中心停了车。他拿起仪表盘上的那张叠着的纸,把它打开。赖伊认出那是一张地图,只是上面的字她全都不认得了。他把地图摊开铺平,又一次拉起她的手,用她的食指指向一个位置。他碰碰她,又碰碰自己,然后指了指地面。意思是,“咱们在这儿”。她知道,他想问的是,她要去哪儿。她很想告诉他,但还是悲伤地摇了摇头。她已经失去了读和写的能力。这是怪病带给她最严重也是最痛苦的损伤。她曾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历史。她还当过自由作家。可现在她连自己的手稿也看不懂了。她有一屋子的藏书,却再也无法阅读,也不忍心充作燃料。她如今的记忆就是,以前读过的书,全都记不起来了。
她盯着地图,试着计算。她出生在帕萨迪纳,后来在洛杉矶生活了十五年,此刻,她位于洛杉矶市民中心附近。她知道两地的相对位置,知道街道、方向,甚至还知道要避开高速公路,因为撞坏的汽车和坍塌的立交桥会把路堵死。就算她认不出“帕萨迪纳”这几个字,也应该能在地图上指出来吧。
她犹豫着,把手挪到地图右上角,按住了那个淡橙色的小方块。应该没错。帕萨迪纳。
奥普斯汀把她的手抬起来,看了看遮住的地方,然后叠好地图,放回仪表盘上。
他能读,她后知后觉地想。说不定,他也能写。她突然恨起他来了——深深的、苦涩的恨意。于他——一个玩“警察抓小偷”游戏的成年男人——读写能力有何意义?可是他,能读能写,她,却不能读也不能写。永远也不可能了。憎恨、沮丧和嫉妒翻腾得她直恶心。而她手边,只隔着几英寸,就有一支上膛的枪。
她死死地盯着他,几乎可以看见他流血的模样。可怒气忽高忽低、起起伏伏,她什么也没做。
奥普斯汀迟疑而亲昵地向她伸出了手。她看看他。她的脸色已然暴露无遗。任何一个还在人类社会的废墟中苟延残喘的人都不会认错这种嫉妒的神情。
她疲倦地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口气。对昔日的渴望、对此刻的憎恨、与日俱增的无助和茫然,她全都体会过,但她从未体会过如此强烈的、想杀死一个人的冲动。她最终踏出家门其实是因为她差点杀死自己。她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了。或许,正是这个理由让她上了奥普斯汀的车。她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
他用手碰碰她的嘴唇,手指一搭,开合两下,模仿张嘴的样子,意思是问她,能不能说话。
她点点头,看着他脸上淡淡的嫉妒转瞬即逝。这下,两个人都坦承了可能带来危险的秘密,而暴力没有发生。他拍拍自己的嘴,又拍拍脑门儿,然后摇摇头。他不能发音,也不能理解话语。怪病仿佛故意捉弄,夺走了他们各自最为珍视的东西。
她扯扯他的袖子,想知道他为什么还要用自己的孑然残躯留住洛杉矶警察局。除了这一桩,他可算得上心智健全了。他怎么不在家里种玉米、养兔子、带孩子呢?可是她不知道该怎么提问。这时,他把手放在她的大腿上,新的困扰来了。
她摇摇头。怪病、怀孕、绝望、孤独的痛苦……不行。
他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腿,笑了,显然并不相信。
三年来,没有人碰过她。她不愿意,任谁都不行。这是怎样的世界啊?即便父亲愿意留下来尽责,也不能冒险让孩子来到人世。可是,这太难挨了。奥普斯汀可能并不知道自己在她眼里多有魅力。他年轻——可能比她还小——干净,坦诚索取而不苛刻强求。可是这些不重要。与拖累余生的后果相比,片刻欢愉算得上什么?
他把她拉过去,凑得更近,她也放任自己享受这短暂的亲密。他身上很好闻,男性的气息,舒服的气味。她违心地躲开了。
他叹了口气,伸手去开前面的杂物箱。她僵住了,不知道他想干什么。但他只是掏出了一只小盒子。盒子上的字她一个都不认得,直到他撕开封口,打开盒子,拿出一个避孕套,她才明白过来。他看看她,她惊讶地避开目光,可紧接着就咯咯咯地笑了起来。她都不记得上次笑出声是什么时候了。
他咧开嘴,指了指后座,她笑得更厉害了。她不喜欢后座,哪怕十几岁时也不喜欢。可眼下看着四周空无一人的街巷和毁坏殆尽的建筑,她下车,钻进后座。他任由她给他戴上避孕套,似乎惊讶于她的饥渴和热切。
后来,他们坐在一起,身上盖着他的那件大衣,暂且不想当着陌生人的面穿衣理容。他做出摇晃婴儿的动作,用疑问的目光望着她。
她咽下沉默,摇了摇头。她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她的孩子都已不在人世。
他拉过她的手,用自己的食指在上面画了个十字,然后又晃晃无形的襁褓。
她点点头,竖起三根手指,背过身去,努力地按捺住汹涌袭来的记忆。她曾想过,那些活到现在的孩子才可怜。他们在这通都大邑里穿梭,却一点儿也不记得曾经的那些高楼大厦,甚至不记得它们是如何沦为废墟。如今的孩子们收集书本就像捡拾木头一样充作燃料。他们在大街上疯跑,追来赶去,像黑猩猩一样大呼小叫。他们没有未来。他们的未来就是现在。
他将手搭在她的肩膀上,而她却突然转身,摸过那只小盒子,催促他再来一次。他能给她暂时的欢愉和忘却。在此之前,还没有什么能够实现这些。在此之前,日复一日不过是将她推向离开家才可能避免的事:将枪管塞进嘴里,然后扣动扳机。
她问奥普斯汀愿不愿意跟她回家,和她一起生活。
他弄明白之后显得惊讶而开心,但是没有立刻回答。最终,他还是如她所惧怕的那样,摇了摇头。可能还是到处勾搭女人、玩“警察抓小偷”的游戏更有趣吧。
她沉默而失望地穿上衣服,对他没有丝毫的怒意。或许他是有妻子、有家的。这很有可能。怪病对男性的打击更大——男性的死亡比例更高,幸存者的后遗症也更严重。像奥普斯汀这样状况尚好的男人不多见。女人要么降低要求,要么独身一人,要是能碰上个“奥普斯汀”,必然会使出浑身解数缠住他。赖伊猜测,可能有更年轻、更漂亮的女人占有了他。
她挂好枪,系好带子。这时他摸摸她,比画着复杂的手势,问她有没有上膛。
她冷冷地点了点头。
他拍了拍她的胳膊。
她再次问他愿不愿意跟她回家,用了不同的手势。他似乎有些犹豫。或许她还可以争取争取。
他没给答复,下了车,坐回前排的驾驶座。
她也回到之前的位子,注视着他。他扯扯自己身上的制服,看着她。她觉得他是在问她,但问题到底是什么,她就不知道了。
他摘下他姓名的象征物,伸出一根手指敲敲,然后拍拍自己的胸脯。当然。
她接过他的项链,把自己的麦秆徽章别在上面。如果“警察抓小偷”是他仅有的荒唐失常,那就随他吧。她可以带他一起走了,连同他的警察制服。她突然想到最终可能还是会失去他:他会遇到别人,就像今天遇到她这样。但拥有一段时间也是可以的。
他又拿过地图,展开来,大致地指了指帕萨迪纳所在的东北方向,然后看着她。
她耸耸肩,先拍拍他的肩膀,又拍拍自己的肩膀,然后紧紧地并拢食指和中指,再次向他确认。
他攥住她的两根指头,点了点头。他跟她走。
她接过地图,扔到仪表盘上,指向西南方——回家的方向。现在没必要去帕萨迪纳了。就让那三个右撇子男人——哥哥和两个侄子——继续悬在那儿吧。现在她不用去确认他们的死活、不用担心自己会不会孤独无依了。现在她不是孤家寡人了。
奥普斯汀沿着希尔街往南开,然后向西拐上华盛顿大道,赖伊向后倚着,琢磨着再次拥有一个人陪伴会是什么样子。她搜罗来的、存下来的、自己种的那些食物,足够他们两个吃饱。带有四间卧室的房子,空间绰绰有余。把他的家当搬进去都可以。最大的好处是,街对面的那个禽兽会消停些,也就不至于逼她动手杀人了。
奥普斯汀把她拉到身边,她的头依偎着他的肩膀,这时他突然踩下刹车,差点儿把她甩出去。她的余光瞥见前面有人横穿马路。街上只有这一辆车,这人还非得从前面抢过去。
赖伊直起身子,看清那是个女人,她从一间木架旧屋逃出来,正冲向木板封起来的临街店面。她跑得无声无息,但追她的那个男人却边跑边嚷嚷,声音像乱码一样。他手里拿着什么东西,不是枪,可能是刀子。
女人想要开门,但门锁着,她绝望地四下环顾,只好捡起一块破碎的窗玻璃,转身应对追上来的男人。赖伊觉得比起刺伤别人,她那块玻璃可能更容易划伤自己。
奥普斯汀跳下车,叫了起来。这是赖伊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怪病留下了低沉、沙哑的嗓音。他像不能说话的那些人一样,不停地重复着同样的音节:嗒!嗒!嗒!
赖伊下车时,奥普斯汀已经朝着那两个人跑了过去。他拔出了手枪。赖伊害怕起来,也拿出自己的,打开保险。她四处张望,想看看还有没有人注意到这一幕。她看见那个男人瞥了一眼奥普斯汀,接着突然冲向对面的女人。女人挥着碎玻璃刺向他的脸,但他扭住她的胳膊,哗哗两刀捅过去。奥普斯汀开枪了。
男人捂着肚子,弯腰倒在地上。奥普斯汀嚷嚷着,比画着,让赖伊过来帮帮那个女人。
赖伊走到女人身边,这才想起自己的背包里只有些绷带和消毒剂。可女人已经没救了。刺伤她的是一把又长又细的剔骨刀。
她碰碰奥普斯汀,想告诉他,女人已经死了。奥普斯汀正俯身查看——挨枪子儿的男人倒地不动,好像也死了。可就在奥普斯汀回头去看赖伊的手势时,地上的男人突然睁开了眼睛。面目狰狞,一把抽出奥普斯汀刚刚装进枪套里的手枪,扣动了扳机。子弹射穿了奥普斯汀的太阳穴,他应声倒地。
一切发生得那么干脆,那么迅速。转瞬间,赖伊也开了枪,把那个奄奄一息却还想朝她开枪的男人打死了。
又只剩下赖伊一个人了——还有三具尸体。
她在奥普斯汀身旁跪下,两眼干涸,眉头紧锁,实在不明白怎么突然就全都变了。奥普斯汀不在了。他死了,抛下她——就像其他人一样。
这时,刚才冲出男人和女人的那间木架旧屋,走出两个小孩。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年纪很小,大约只有三岁。他们手拉着手,穿过马路,朝着赖伊走来。他们盯着她看了看,然后侧身绕过她,走向那个女人。小女孩摇晃着女人的胳膊,想要唤醒她。
这一幕太沉重了。赖伊站起来,悲伤和愤怒顶得她犯恶心。要是两个小孩哭起来,她肯定会吐出来的。
他们只能相依为命了。这个年纪应该已经会翻垃圾了吧。她没必要自寻伤痛。她没必要去管陌生人的孩子。那些孩子长大后也不过是无毛的黑猩猩罢了。
她转身往轿车那儿走。至少,得开回家。她还记得怎么开车。
还没走到车边,她又想到,应该将奥普斯汀安葬。这念头真的让她吐出来了。
和这个男人的相遇是如此迅速,失去也是如此迅速。就好像有人把她从自己的安乐窝里拽出去,莫名其妙地暴揍了一顿。她的头脑昏昏沉沉,不能思考了。
迷离之间,她折回去,凝视着他。她跪在他身旁,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曾经跪下过。她抚摸着他的脸,他的胡子。小孩发出了点儿声音,她望过去,望着他们和那个或许是他们母亲的女人。两个孩子回望着她,显然吓坏了。或许,最终打动她的就是这恐惧。
她本来都要开车走人了,留下他们自生自灭。她差一点就走了,差一点就撇下两个刚会走路的孩子,让他们等死。等死的人已经够多了。她要把这两个小孩带回家。决心已下,不照做就活不下去。她四下张望,想找个地方埋葬三具尸体。或许,是两具。她猜测那凶手是两个小孩的父亲。在怪病和沉默降临之前,警方就常常表示,最危险的出警就是处理家暴事件。奥普斯汀应该知道这些——但知道这些,他也不能允许自己就这么待在车里。她自己也不会袖手旁观。她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个女人惨遭杀害却无动于衷。
她拖着奥普斯汀往轿车那边走。她没有挖土的工具,也没人能帮忙望风。还是把尸体带回去,埋在她的丈夫和孩子们旁边吧。奥普斯汀,终究跟她回家了。
当她把他拖到轿车后排的底板上,又折回去搬那个女人时,那个小女孩——面黄肌瘦、脏兮兮、板着脸的小女孩——猝不及防地给了她一份礼物。赖伊正要拉起女人的胳膊,她突然尖叫:“不!”
赖伊松了手,怔怔地盯着小女孩。
“不!”她重复,护在女人身边,警告赖伊,“走开!”
“别说话!”小男孩拦着她。这不是混乱、模糊的声音。两个孩子发出的语音,赖伊都能够听懂。男孩看看殒命的凶手,躲开了,接着拉起女孩的手,轻声说:“安静。”
流利的话语!那女人是因为自己能说话,也教孩子们说话,所以才死于非命的吗?杀死她的,是丈夫与日俱增的恼怒,还是陌生人因妒而生的恨意?这两个孩子……肯定是出生于语音消亡之后。是怪病退散了吗?还是说,只有孩子们拥有免疫能力?不然他们早该罹患怪病、失去语音了。赖伊的思绪跳得飞快。是不是三岁以下的孩子不受影响,还有习得语言的能力?他们会不会只是缺少老师?老师,还有守护者。
赖伊瞥了一眼死去的凶手。她心里有些愧疚,因为不论他是什么人,驱使他行凶作恶的冲动,她是可以理解的。愤怒、沮丧、绝望、疯狂的嫉妒……无法拥有就毁掉,像他这样的人,还有多少?
奥普斯汀曾经是个守护者。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选择了这个角色。他宁愿穿上过时的警察制服,在空荡荡的街上巡逻,也不愿把枪管塞进自己嘴里。现在,值得守护的对象出现了,他却不在了。
她当过老师,当得很不错。她也充当过守护者,只不过守护的是自己。当活着变得毫无意义时,她守护着自己,活了下来。如果怪病放过了这些孩子,那么她就该守护他们,让他们活下去。
她把死去的女人抱上轿车后座,两个小孩哭了。但她在残破的人行道上跪了下来,生怕自己那久违的刺耳声音吓着他们。
“没事的,”她对他们说,“你们也一起来,走吧。”她抱起他们,一手一个。真轻啊。是不是一直没吃过饱饭?
男孩捂住了嘴巴。她望向别处。“跟我说话是可以的,”她告诉他们,“只要周围没有别人,就可以。”她把男孩放在前座,不等她提醒,他自己就挪了挪,给女孩让出了地方。赖伊最后上了车,倚着车窗,看着孩子们。他们现在不那么害怕了,至少,他们的眼神里出现了和恐惧一样多的好奇。
“我叫瓦莱丽·赖伊,”她咀嚼着口中的语音,“你们跟我说话,是可以的。”
后记
《语音》是在疲惫、沮丧和悲伤中诞生的。刚开始写的时候,我对人类不抱希望,也没有好感,但写到结尾时,希望又回来了。似乎总是如此。《语音》背后其实有个真实的故事。
20世纪80年代初,我的一个好朋友罹患了多发性骨髓瘤,时日无多。这是一种特别危险、特别痛苦的癌症。在此之前,我失去过高龄长辈和家族世交,但从未失去过个人的朋友。我没有见过相对年轻的人痛苦而缓慢地因为疾病走向死亡。我那位朋友还有一年的时光,所以我每个星期六都带上新写的一章小说去看望她,渐渐成了习惯。当时我正在写的是《克莱的方舟》[Clay’s Ark,《克莱的方舟》为译者译,“clay”有引申义“肉体”,“ark”有另一词义“约柜”。故事背景为一场瘟疫。],它的主题是疾病和死亡,并不适合卧病在床的人。但朋友常读我的小说,这一本也想先睹为快。我猜,或许我们都觉得她等不到这本书正式面世了——当然,这话我们谁也没说出口。
我讨厌这种探望。她是个好人,我很爱她,不愿意看她就这么死去。然而,每个星期六,我还是照旧乘上公交车——我不会开车——到她的病房或公寓去看她。她日渐消瘦,每况愈下,并且因为疼痛的折磨而变得暴躁。我的心情也越来越压抑。
某个星期六,我坐在拥挤难闻的公交车上,一边闪躲腾挪,不让人们踩到我的脚,一边尽量不去胡思乱想,这时,我发现对面正有一桩麻烦事酝酿着。一个男人觉得某人看他的眼神不对,惹他不快。眼神有什么对不对的!在公交车上挤着,谁知道该往哪里看呢!
对方辩解说自己什么也没做错——确实如此。他慢吞吞地往外挤,似乎不想惹祸上身,可随后又绕回去了,继续争辩不休。或许是出于自尊心吧。他又没错,为什么要落荒而逃?
这次,那个男人觉得“不对的眼神”转向了坐在他身边的女朋友,于是大打出手。
这场斗殴短暂而血腥。其他乘客躲躲闪闪,大呼小叫,生怕被误伤。最后,打人的家伙怕司机报警,带着女朋友匆匆下了车。挨打的倒霉蛋自尊心全无,晕头转向,满身是血,环顾四周,好像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我坐在原处,更加沮丧了。整件事是多么愚蠢,多么让人绝望啊,人类这个物种什么时候才能有些长进,学会不用拳头的交流方式呢。
于是,故事的开头跃入脑海:“华盛顿大道的公交车上出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