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为独特 | 收藏 |
附录 泡泡玛特高管口述
在年轻时吃苦
执行董事刘冉
因为独特 作者:李翔
我相信王宁
我是王宁的大学师妹。在入学的第一年就加入了他创立的Days Studio社团,听说之前他还成立过一个街舞社团,后来交给其他人运营了。Days Studio成立之初就是去做一些纪录片,记录大学生活,然后刻盘售卖。我当时觉得“记录生活”这个想法挺不错的,再加上我当时就有相机,就去申请加入这个社团。后来我一直跟他开玩笑说:“你当时是看上我这个人,还是看上我手里的相机了?”
我记得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还在跳街舞,发型非常杀马特,穿的衣服是oversize(大码)的——看不见手的那种,很热情地跟我打了招呼,就是这样了。这个答案或许非常平淡,但真的就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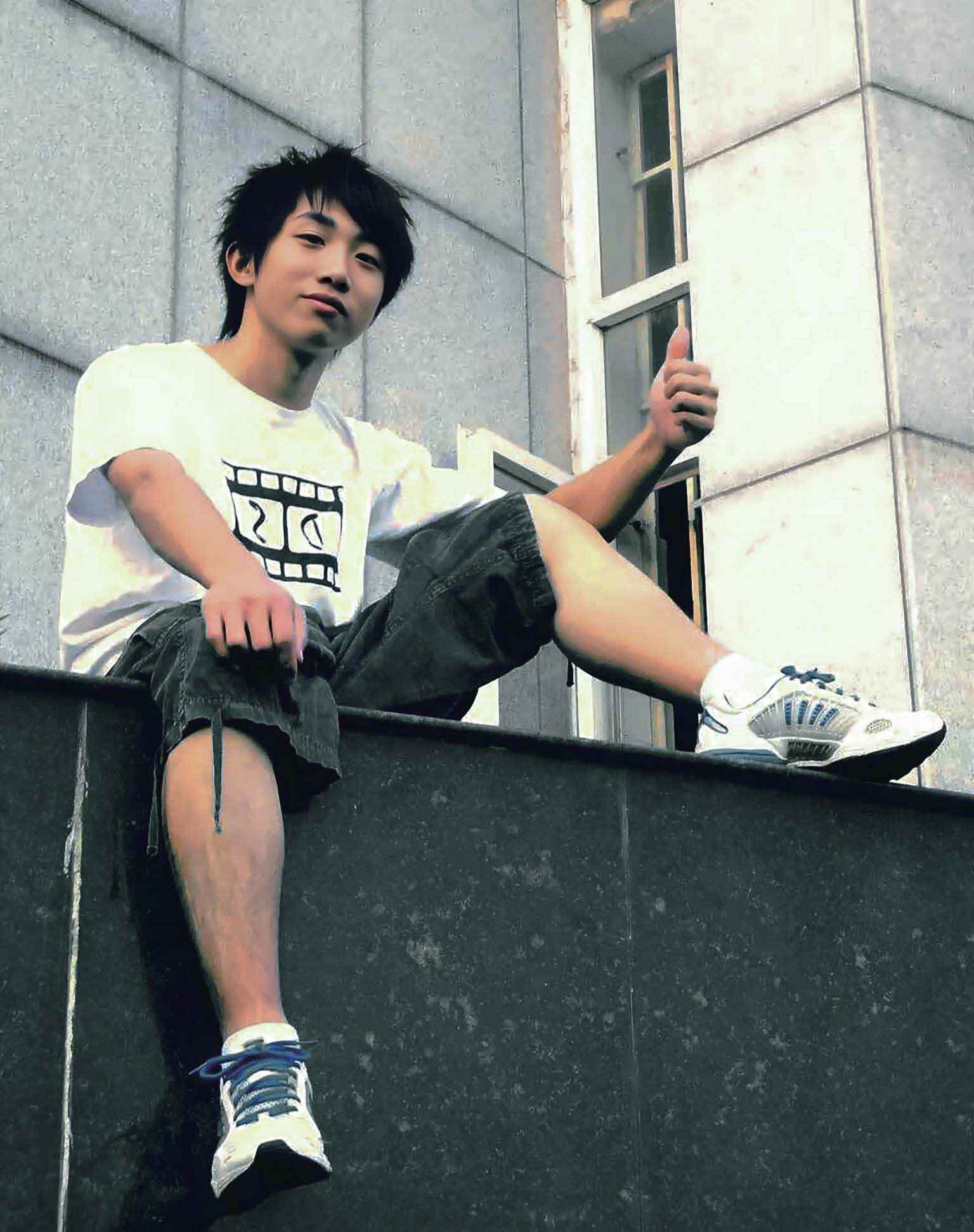
我们自己开玩笑说,我们的第一桶金就是靠卖光盘得来的。当时就是把校园生活记录下来,刻录成光盘售卖。那时候没有短视频,没有朋友圈,流行的是人人网,当时我们做的视频,大部分人是用电脑或者DVD、VCD看。
其实这个社团人挺多的,但是参加每一次核心活动的可能也就一二十个人。当时也没有实际职务和分工,主要工作就是拍视频和制作视频——拍摄、剪辑、制作、售卖、营销、售后这一系列的工作。为什么没有分工呢?因为工作都是阶段性的,这一段时间大家都在拍视频,另一段时间大家都在筛选素材。当时的业务量也非常小,不需要像公司一样有明确的部门和分工才能做下去。就像抬桌子,我需要把桌子从这个房间抬到另外一个房间,有时候我一个人就能把这张桌子搬过去;有时候需要抬重一点的桌子,那就喊三五个人帮我一起抬过去。
我们当时一年会出两季纪录片,9月入学开始拍,12月发布这张光盘,记录的就是这半年的新生生活。如果从2月开始拍,那拍的就是毕业生离校,在主题上会有一些差别。我们会根据当时入校的人数,计算大概能卖出的份数,再加上一定的售后份数,直接生产出来一批光盘。那时候还分VCD和DVD,VCD卖5块钱一张,DVD卖8块一张,完全在学生的接受范围之内,所以购买率、购买意愿都挺高。
王宁是学广告专业的,营销这部分我们做得还是蛮好的。学校也比较支持社团活动,我们会自己制作海报,甚至第二张纪录片出来的时候,还开了发布会,让大家提前看一看片子内容,看完之后如果愿意购买、想留个纪念,他们就会买回家,再跟家人分享。食堂的电视、学生电影厅,各种能播视频的地方都会去播放,我们会尽可能多地做宣传。
其实,最难的部分不是销售,是拍摄和制作。一个片子需要拍大量的素材,哪些素材是学生的共同记忆?哪些素材可以打动人心?有时候拍了30分钟素材,最后只用一两秒钟,这是一个非常耗时和碰运气的事情。还有就是制作,那时候剪辑软件也没这么强大,我们需要把视频剪出来,配上音乐,然后再配上文字。这个过程要有连续性,如果要换音乐,节奏、鼓点全变了,就要重新贴合视频素材,素材的前后顺序也要换,这是一个比较折磨人的过程。王宁自己承担了很多任务,他会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调整很长时间。我们基本上每半年做一次,那几天他非常疲劳,精神比较萎靡。第一年我们赚了钱之后,王宁组织了一次小旅行,去了上海、杭州和义乌,还给社团添置了一台数码摄像机,然后就开始做第二张光盘。
2008年,我大二、他大三的时候,我们开始做格子铺,就转移了重心。最开始一起开店的人,也是从这个社团里拉出来的。当时转做格子铺,是因为我们卖光盘赚了点钱之后,王宁发现零售的效率更高。当时大家对零售的理解很简单,就是买进卖出,低买高卖。光盘的制作涉及拍摄、剪辑、刻录,以及售后,这个过程要半年的时间,而市场就是对它感兴趣的一部分同学,不管从规模还是客户群体来讲,这都是个小生意。我们就想,如果选对一个产品,左手买进,右手卖出,它的效率会非常高。所以那时候王宁就决定:我们要不要试一下零售。
王宁是一个执行力非常强的人,我们团队的人也听他的,他要求怎么做就怎么做。当时因为卖光盘赚了点钱,生活费多的同学也可以再凑一凑,剩下的钱王宁会想办法搞定。我们基本属于“边跑边调整姿势”,不是一定要姿势优美,有一个多么完美的想法才开始做。
做格子铺后我们就没有再成立新的社团,但是同样有新的人员加入,也就是招店员。因为我们是一个全学生社团,每个人的上班最小单位时间是2小时。比如今天早上我8点到10点没课,我就负责开门、打扫卫生,10点有同学下课了,就赶紧跑过来跟我交班,因为我要去上课。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把这家店运营起来了。当时格子铺就是一个小店,如果用全职员工可能四五人就足够了,但我们用了二三十个员工,都是同学,有些是我们认识的,有些是我们贴招聘广告招来的。本来选的是学校里面的位置,我们还挺喜欢的,但是付不起租金,学校旁边有一家新开的商场愿意租给我们,我们就去了。我们一直都没有借钱做很大的事情,就是手里面有点什么、自己懂什么,就紧着条件去折腾。当时发的工资也很少,一个小时就几块钱。
大学生想做事情,基本上都止于想一想,王宁这种敢想敢做的,在大学生中还是挺受信任的。我们每次开始做一件事,都会吸引很多人。后面因为个人原因或者大家相处的原因,肯定会有人走。至于我自己留到现在,有两个原因:一是我觉得他这个人很有能力,二是他做什么事都会带上我,可能脾气相投。我喜欢干事,但是没有什么天马行空的想法。他有这些想法,我就去想一想怎么落地,我觉得这是我擅长的,也是我喜欢的,所以也就一直做下来了。
我们当时还注册过一个网站,叫“我爱DIY”。当时的想法是帮大家定制T恤,但是学生社团没什么钱,而且那时候DIY技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制作单件的成本比现在要高很多,所以做着做着就放弃了。
王宁去上海实习期间,一直跟我们联系,这就像是一个社团的传承,他需要把这个店铺顺利运营下去。那时候我也要考虑实习和找工作,也在想办法把这个店交接出去,基本上我们都会找下一届的师弟师妹去带,等他们相对熟悉之后就交给他们。最后王宁把这个店铺卖掉了,所以有了在北京创业的第一笔启动资金。
我觉得王宁心里一直有一股劲儿。他其实是先到上海,后来又到北京工作,工作不久后还是决定创业。那时候他开完店也没有更多的预算招人,即使挂出来招聘,估计愿意来投简历的人也不多。我们几个同学就从学校过来,帮他把店开起来,然后我们又回去实习了。后来他陆陆续续地从社会上招了一批店员,也有他在北京工作时认识的伙伴加入我们,其实就是这几拨人轮着把这家店给撑起来。当时是挺艰难的。
在他决定创业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让我来北京。当时他说:“我们还是要做一件自己的事情。”我都不太记得他具体跟我说了什么,但是我记得他每天都给我打电话,每天《新闻联播》结束之后,他的电话就来了。我专业是学旅游管理的,到旅行社实习以后发现旅游行业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我原来想的旅游业是人文历史、山川风景,而当时我看到的旅游业,是要导游通过带游客去购物来赚钱。我不愿意做这种事情,再加上王宁一直在邀请,我就来北京了,那是在我毕业大概一年的时候。当时的想法就是大家一起做一些想做的事情,做成就做成,做不成就再回去。
北京的第一家店是2010年11月17日开的,那时候的营业额非常低,基本没什么利润。我们当时还用信用卡借钱,营业结束之后,需要用ATM把现金存到卡里,再去便利店通过固定设备把信用卡还上。一般我们都会在信用卡还款截止日的零点之前把钱还上,比如我们今天营业额有一千块,把这个存上之后才够还信用卡,但是如果有一张钱比较旧,ATM识别不了,就真的会很沮丧。因为那个时候银行都已经关门了,周围也没什么人,不可能再去换一张新的一百块,信用卡就面临逾期。
刚开店的时候王宁自己租的是一个6楼的房间,没有电梯。开业前我们统一进货,他和杨涛要把几十箱货搬到6楼,开业的时候再搬下来。我当时跟另外一个同学来北京,我们租了一个小出租屋的隔断间,只能放得下一张上下床,像学校的高低床,但学校的床是钉在墙上的,这个上下床是房东临时买的,床很晃,一个人要到上铺睡觉的时候,下面那个人得平躺好,不然床就会被整个拽倒。
现在我觉得苦一定要年轻的时候吃。今天成功了,回想起来,当时觉得好玩、挺有意思,但是如果三四十岁的时候再去体验,就会有一些辛酸了。如果为生活所迫,可能还是会去做,但不会这么快乐了。那个时候大家在一起,基本上就是工作、吃饭、玩,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和不开心的,所以也就没有考虑太多——比如五年之后我还挣三千块钱怎么办。
我后来想了想,那时候我们相信王宁,王宁相信自己。我记得王宁说过一句话:“我才20多岁,就算失败了又能怎么样呢?我相信我这辈子挣的钱,肯定不止这点。”
我觉得当时不需要激励,需要激励的人都走了,因为当时王宁还没什么能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的。当时就是年轻,觉得在一起做事有意思。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更认同那句话:“你不在意结果,往往结果会给你更大的惊喜。”中间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有家里催着要结婚的,也有觉得太辛苦的。还有一些人,觉得回老家找份工作也能挣三五千块钱,何必在北京挤在出租屋里,挣着三五千块钱的工资呢?王宁当时也没有办法给大家激励,给大家股份。那时候都没有股份制的概念,也不知道这个盘子会有多大,而且也没有人投资。
我觉得比较稳定一点的时候,可能就真的要到2017年了,直到我们开始做MOLLY,开始觉得潮玩这个方向是对的,我们才觉得这件事“敢”想了。记得2018年,我看一个综艺节目里说:盲盒就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小确幸。我们之前跟别人解释什么是盲盒,都要解释半天,看到这个综艺节目里有人开始拿盲盒去定义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它肯定是大家都熟知的概念了。
爆款会成为品牌符号
我们的品牌名是POP MART,翻译过来是潮流超市,最开始我们什么都卖,后来发现客单价集中在39元。为什么是39元?因为我们那时候卖一款流行的无镜片眼镜框,它的价格就是39元,每个月都能卖好几百个。它的销售数量大,我们也就能拿到更低的成本。我们就想,是不是能多卖一些这种量大的、大家都喜欢的东西?店里有好多柜台,我们都有机会尝试,你觉得笔好卖,他觉得发卡好卖,她觉得眼镜好卖,大家都可以试一试,最后谁进的货好卖,谁就去当采购;谁选的品类对,谁说了算。
对泡泡玛特而言,我觉得一个重要的选择就是融资。最开始我们想做加盟,但是发现加盟商非常不稳定,他们要求变现的时间很紧,因为加盟商基本上也是一个家庭拿出积蓄来做这件事,再加上品牌做大之前,很难建立信任感。后来我们就决定融资,拿了融资之后,相对来说缓了一口气,至少我们不用再考虑怎么还信用卡。
“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是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的选择。我们其实在创业开始的时候成立过一个网站,叫淘货网。当时的想法是,我们自己有一家零售店,那是不是可以去货源地守着,做一个一件代发的平台。其实是从我们自己的需求出发。我那时候就去广州待了半年。我们把店里卖的东西上传到网站上,有客户下单我们就从店里帮他一件代发货。如果店里没有,我就守在批发市场购买。后来发现做线上是需要流量的,线下的人流量你是看得见的,线上的流量你看不见,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投流,不知道大家怎么才会看到你,而且也没有钱投流,所以就慢慢放弃了。
因为泡泡玛特的员工都挺年轻的,我们当时没有潮玩概念,但是我们有手办、动漫的概念,也卖过一些大版权的手办,比如钢铁侠、蜘蛛侠。我们自己是年轻人,我们喜欢这些。我们的消费者也是年轻人,他们也喜欢这些。再加上当时卖Sonny Angel卖火了,成为了爆款。所有这些因素都让我们觉得可以做潮玩,泡泡玛特将来会成为一个大品牌。我们一直相信爆款的逻辑:做一个爆款,它就会变成一个品牌符号,或者品牌的代表。
团队的分工基本上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当然也有客观原因,比如最开始只有一家店,不需要物流,后来我们的货开始多了,甚至还有分销商,就需要物流,那时候王宁之前的同事超哥就加入做物流。在需要的时候,这个工种就产生了,这个合适的人就出现了。有一些岗位是客观需要,有一些岗位就是因为当时没钱,你做也行,我做也行,那就怎么省钱怎么来设计岗位。
这里面也有一些挺有意思的事儿,我们2009年开始做格子铺,2010年开始做泡泡玛特,但是直到2013年,有一个专业做商品的同事加入我们,我们才知道SKU的概念。之前不知道,基本上是以懵懂的状态一路往前跑。
我自己觉得压力最大的时候是2015年。那个时候我们把Sonny Angel卖火了,对方担心我们的发展不受控制,想去培养更多的分销商。这就相当于把我们的脖子卡在了别人手里。因为这个商品占销售额的比例太高,如果我们没有拿到它的授权,一家店就白开了,或者说肯定会赔钱。所以那时候压力非常大的原因就是,你不知道新开一家店,别人能不能给你授权。
2015年,我们的身段非常柔软,姿态也非常低,和Sonny Angel做了很多轮的沟通,还去了深圳公司和日本总公司。尤其是2017年我们办第一届潮流玩具展,当时我们只有MOLLY一个IP,其他IP还在规划中,特别需要外部IP来帮我们撑场子。当时我们找到Sonny Angel说:“你们能不能来我们这儿参展,我们给你们一个最大的展位,我们来出全部费用。”他们依然拒绝了我们。从2015年开始我们感觉难受,一直到2017年都还在妥协。但后来我们自己的IP多了,产品也陆陆续续上市,市场上也开始有我们的一席之地了,自己的腰杆也硬了,就彻底放弃了跟Sonny Angel的纠缠。

当时它拒绝我们有三个原因。一个是它有自己的商品定位,觉得自己不是潮玩,而是家居和生活方式。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发展得太快,他们不想做这么快。这两点是核心原因。最后一个原因是他们也不够开放,当时我们的量已经非常大了,就提出帮我们生产一些特殊产品的需求,只在我们的渠道卖,他们都拒绝了。在我们看来,这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我们想不明白,也不符合我们自己的发展节奏,那就只能分道扬镳了。
再后面我觉得压力就相对小了一些,因为我们自己心里很笃定:相较于其他潮玩公司,我们的零售是有优势的;相较于其他零售公司,我们又有IP优势。现在我们也有其他的零售公司或者IP公司带来的竞争压力,但是我感觉想办法突破自己的压力更大。
后来我们准备上市,提交了报表之后,大家可能看到了这里面的利润空间,开始有更多的人进入这个行业。当时有公司在我们隔壁楼设立了办公室,用两到三倍薪水挖我们的人。那时候我觉得HRBP(人力资源业务合作伙伴)可能是最焦虑的,因为人被挖走之后,他们还要继续招人。别人真金白银来挖人,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会劝、会留,但总会有些人抵不住诱惑,就走了。
在内部的学习和讨论里,乐高跟迪士尼这两家公司最近出现得比较多。同时我们现在在关注用户反馈的产品质量和瑕疵率问题,所以我们对工厂的学习也比较多,服装工厂、饰品工厂,甚至我们也看机械零件配件工厂和汽车工厂。我们还曾经去一些酒厂,看他们怎么做文化。所以我们学的企业类型还挺多的,从中抽出来自己感兴趣的那部分去看。比如看酒厂,酒的毛利率是非常高的,尤其像茅台、五粮液和郎酒,它们怎么能把酒卖到这么高的价格?营销是怎么做的?文化是怎么做的?都是我们感兴趣的点。我们去体验了酒企的庄园,看它们怎么做酒,以及如何设计表演和制作特色餐饮,这就是一个完整的道场,也就是主题沉浸式的设定。我们的乐园和门店,怎么能给别人一种潮流文化道场的感觉,这也是我们一直追求的方向。
受人尊敬的百年企业对我们来说一直都非常有吸引力。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新闻,迪士尼米奇的第一代形象马上就要过版权保护期了,它可以把这个IP运营百年,到现在大家都还愿意买单,它是怎么做的?大家都说学不会迪士尼,它的体系到底是怎么样的?有人说,迪士尼乐园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如果去了迪士尼不快乐,那是个人的问题,不是迪士尼的问题。迪士尼是怎么做到这种文化植入的?我们也希望给大家带来快乐,那快乐到底是怎么产生、怎么感染大家的?还有经营,很多百年老店都是小而美,但迪士尼规模这么大,经历了这么多任首席执行官,它的初心是怎么坚守的?怎么能运营这么长时间?我们也都挺好奇的。
前两天我还跟同事讨论,我们最开始的商业模式是做超市,后来想做爆品,选定了潮玩,它是从一种分散的状态变成合集的状态。现在我们又开始把不同的产品线提级,把衍生品提级,再变成分散的状态。衍生品的优先级提升,如果更早一点,可能会更好。但是没关系,如果你要做一个百年企业,晚一两年怕什么?
上市让我们更从容
我没有感觉到上市给王宁和团队带来明显的变化,但是财务状态改变,肯定会让大家变得更从容一些,这是能感受到的。你可以这样理解,我曾经天真地以为30岁生日零点钟声敲响的那一刻,我会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周围的磁场都会发生改变,但事实上并不会。我们上市时放了一部10分钟的纪录片,里面有一个镜头,我觉得拍得特别好。有一条丝带从天上飘下来,王宁抬头看了那条丝带一眼,就是那种感觉,只是看它一眼,你就知道那是结束,也是开始。
对他而言,如果要说改变,可能是对具体事务的参与程度没有之前高,因为占用他精力的事情越来越多。但是昨天我们开了一天的会,2024年的产品一个一个地过,讨论这件产品到底行不行,到底怎么做。他在关键的事情上还是保持着之前的高参与度。他会关注小红书、关注微博,他非常关注顾客的反馈,要求也非常高。如果有人说我们的产品质量不好,他会非常在意这件事情,会反复拿出来说,所以我们也一直在产品质量上面不停地投入。包括门店射灯的角度、音乐的大小等等,他都会有感知。
我觉得他的脾气不算大。可能因为我们其他人的脾气太好了,所以显得他凶。还有就是职务给他带来的一些天然的威严感,可能会让大家觉得他的压力更大一些,一些小细节很多人也不敢去找他确认。我觉得他挺孤独的,越来越孤独了。有的时候他也希望听到大家的一些反馈,但可能没有人敢去跟他聊。公司越来越大,原来所有人跟他在一米范围之内。一旦组织膨胀,即使你是一个老员工,也会被膨胀到五十米或者是一百米的距离。这时候天然就会产生距离感,并不是说王宁主动地把这个距离给拉开了。
我提醒过他不要皱眉。他说话的时候,总是会习惯性地皱眉。他一旦开始皱眉头,底下人就不敢随意说话了。其实,他皱眉,并不代表他不满意或不耐烦,可能就是个人习惯。
我们之前讨论过一个问题:公司必须赢利吗?其实这是不应该被讨论的,公司就是作为一个赢利机构存在的。但是我觉得它背后反映的问题是:速度重不重要?规模重不重要?情谊重不重要?这些事情会反复地萦绕在我们创业或者经营的过程当中。现在也一样,王宁在内部经常说:“志同道合是兄弟,不志同道合是工具。”我们希望每一位同事都能认同这种文化,并且能够跟公司长久地走下去。当然也不可能公司五千个人就有五千个总监、五千个副总裁,也会有一些人来来往往。
现在和未来新加入的职业经理人,他们是不是真正认同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前进的方向?我觉得这是我们所有人都面临的挑战。我们是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接受现在这个大船上的所有人,还是非常苛刻地去选择跟我们的价值观完全一样的人?之前这会让我挺纠结的,现在也慢慢想通了,公司没有办法保持最开始还很小的那个样子,可能每个人都要经历这道坎儿。现在对于大家的挑战就是公司能不能健康地、长久地走下去。我们一直说:“给大家带去快乐,我们学习的对象是迪士尼。”这不是只在公关稿上才这么说,我们发自内心地想去做这件事情。
我们讨论的结果是:这两者不冲突,一定存在一个方向是让两者可以并立的,只是我们还没有找到这个方向。所以不会是非黑即白的一种选择,不是说我们要选择有情有义,我们的规模就要更小,发展速度就要更慢。
我也看过一些报道,也了解了一些我们同时期的公司,它们其实在创业之初就已经想好要做一件什么样的事,目标非常明确。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目标其实没那么明确,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会让大家觉得不够坚定,目标不够清晰,但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就是多一些体验。你手里有什么牌,就打好什么牌。
我们之前觉得战略没那么重要,原因在于我们觉得战略太远了,我们想随时变化。但是当企业越来越大的时候,就会发现战略开始变得重要,步调一致也变得重要。比如供应链,现在开始做2025年的产品企划了,这在我们开始创业的时候是不敢想的。我怎么能知道明年、后年会流行什么?但是现在作为一个潮流品牌,我们要有自信,也要有能力去引领潮流。另外,我们也要给供应链足够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战略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
其实我们内部一直在说,王宁的特点之一就是他变化很快。今天要这样做,明天不至于大转弯180度,但120度的变化也是有的。这个转变会让人措手不及,也会增加资源浪费,起码浪费很多感情。但是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如果不敢去做这样的调整,没有勇气背负这种指责,我觉得也不对,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企业滑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吗?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迅速调整是很需要勇气的。你去问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大家已经做了三五天的工作,你跟大家说现在要换一个方向,有没有勇气这样说?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勇气去说的,更别说几千人都在看着你的时候。
你要说平静接受,大家都是人,谁也做不到,但是会执行。因为他不会简单说就按他说的来,王宁还是会跟大家讲,他为什么会这么想,他昨天这么想是因为什么,他今天这么想又是因为什么。很多人是被沉没成本限制的,但我觉得他是一个从来都没有这方面顾虑的人。一句话——不行马上调。比如创业初期,有的桌子尺寸不合适,但凡有点钱,王宁就会把这张桌子换掉。他是完全不凑合的一个人。
短期内可能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全球化和集团化。如果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往这两个方向努力,可能这个期间生长出的能力,也足够让我们应对各种各样的市场变化。
我们前两天聊战略的时候说:“我们的愿景是成为一家全球领先的潮流文化娱乐公司。”司德说:“其实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是为了写在招股书上,但是现在想想,这句话太厉害了,不能多一个字,也不能少一个字。”所以有时候是我们主动思考,有时候是形势逼着我们思考。有可能就是在那一刻你会想:现在你是一家公众公司了,公司的账上有钱,怎么样把它花得更聪明?这才开始思考长期战略的问题。
现在回过头来看,运气真的蛮重要。如果从我们几个人的背景、出身,甚至启动资金来看,没有理由是我们站到这儿。可能就是坚持了别人坚持不了的,相信了别人不敢相信的。零售的市场空间很大,但是年轻人从这里起步创业的,当时非常少。我们就是打好手里的牌,从这个地方慢慢起步,然后杀出一条血路。泡泡玛特的成功跟王宁有很大关系,跟创始团队的因缘际会也有很大关系,也许团队里每个人都不是最优秀的,但是在那一刻刚刚好。